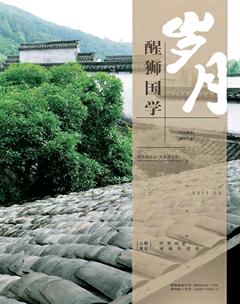留下祠堂,別將它送上最后一段不歸路
呂若涵
“在城市急速擴張及社會的現代轉型中,可能一夜之間一座存在數百年甚至更久的祠堂就消失了,歷史與文化的活文獻以驚人的速度消失,皮之不存,所謂民間文化、地域文化、傳統文化也將無所依附而分崩離析。”
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第一課,多是從陳獨秀的《敬告青年》開始。陳氏文章有股演說氣,句式鏗鏘,探及進步與保守時認定“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誠不知為何項制度文物,可以適用生存于今世”——這是新文化運動的宣言。之后,幾乎整個20世紀,與宗族相關的祠堂、村廟、祭祀等,都成了落后消極封建保守的東西。現當代文學作品中相關場景著實不少,稍加檢點,或能借此一窺祠堂文化的命運及其當下困境。
魯迅筆下的呂緯甫年輕時思想激進到去“城隍”廟拔圣像的胡子;吉光屯里有個狂熱的“瘋子”,一心要滅了“社廟”里那盞守護全村百姓的“長明燈”,全忘了他的祖先還捐過錢。這個被村人罵作數典忘祖的“不肖子孫”,終于引起公憤,連“四爺”大人都“嚴肅悲憫”起來,整個村莊籠罩著一片緊張氣氛。上無片瓦寄居于土谷祠的阿Q突然想要“姓趙”了,似乎有那么點認祖歸宗的小意思,更有可能是趙氏宗族在村里地位最顯赫。當時還有個年輕作家許杰寫了《慘霧》,鄉間一場械斗,便彰顯出不同宗族爭奪土地的強悍——當然,越是強悍越顯其“野蠻”,越是團結也越發“愚昧”。五四小說中的祠堂社廟村規家譜,好比一個個祖先崇拜、尊尊親親的家族倫理的文化隱喻,祠堂隱喻新文學作家眼中的“鄉土中國”,昏暗陰森,卻如鐵罩一般冷酷強大地屹立著,代表現代文明的“瘋子”則勢單力薄,難以撼動,最終還要成為它的祭品。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小說中的大家族紛紛走向衰敗。寫實的作家不再停留于封建宗法社會的文學象征,他們發現在社會經濟大變局中傳統的鄉村組織結構已經搖搖欲墜。文學家偏好一雙社會學家的眼睛,祠堂開始上演種種現實人生可悲可怖可笑的劇目:軍人在祠堂里逼死活人,祠堂的公道連同人一起被送進棺材(如沙汀《在祠堂里》);族長在列祖列宗前為非作歹,作奸犯科,可見祠堂威嚴不再;當然,也有帶著溫情的,犯了族規的蕭蕭竟然有了生路,可以不“被沉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吳祖緗《一千八百擔》,副標題赫然是“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寫”,這一天,荒年里的農民暴動摧枯拉朽,宋氏祠堂一千八百擔糧食遭搶,宗族各支各室表面和氣,利益面前是各懷心事、暗中斗法,地方望族至此氣數已盡。吳祖緗這位“客觀主義”者眼光犀利,非要揭開給人看,由社學、義倉、鄉約、防御等構成的宗族組織,如何在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國內的高賦稅和農民暴動中毫無招架之力。這是宣告“封建宗法社會”的末路吧,字里行間藏了作者多少奚落與嘲諷!后半個世紀不用說了,白毛仙姑由鬼變人,小二黑的婚事由區長作主,裝神弄鬼神神叨叨都得“改造”,文化變革與社會變革雙管齊下,連最小單位的家庭秩序都要改變,何況這“封建制度之遺”。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寫實又讓位于象征。祠堂廟宇書院再一次與傳統文化畫起等號,只是這次意象的情感內涵完全與五四悖反。《白鹿原》廣受好評緣于它把祠堂、書院、鄉約等代表鄉村倫理和儒家文化的符號,來了一番濃墨重彩的生動演繹,說是新歷史主義,實在與魯迅當年的寫作一樣,一種對歷史重新評判的態度。閩籍當代女作家項小米《英雄無語》這樣寫道,當“我”來到連城貧瘠大山里尋找祖父的革命印跡時,收獲的是對客家歷史的全新認識。小說未寫“祠堂”,但當“我”身為知識分子、名副其實的紅色后代,奔赴偏遠故鄉為祖爺爺祖奶奶修墳時,累累白骨前恍然聽到一聲“不孝子孫”的天庭霹雷。作者感嘆:“血緣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奇怪。”這真是饒有意味。讓人聯想到中年呂緯甫為早夭的弟弟遷墳時喃喃細語的情形。當然,很多人既聽不到天庭的霹雷,也聽不見人心的細語,20世紀文化與社會巨變帶來的結果是21世紀“拆哪”的加速度,配合著城鎮化的步子,迅疾,兇猛,無所顧忌。
一個世紀里,文學中的那座祠堂,似乎走了一個圈,但并非回到原點。宗法社會的崩頹是歷史的必然,但它所承載的文化在新世紀里卻未必沒有可資使用的價值。我們不是稔熟地、大張旗鼓地用著“回歸”“血濃于水”“四海一家”“同文同種”“葉落歸根”“敦睦鄉誼”“慎終追遠”等話語么?試問,這其中哪一個詞不是來自傳統宗族文化呢?現實中的宗親大會與尋根之旅,是從一宗一姓的歷史認知與情感需求出發,發現我們身上共同的文化基因,最終獲得對民族文化的認同,乃至于建構起對民族未來的共同想象。如此說來,將大地上所剩不多的“祠堂”“廟宇”送上最后一段不歸路,也就等于拆解了文化認同的“基石”,我們這代人,豈不真的成了“不孝子孫”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