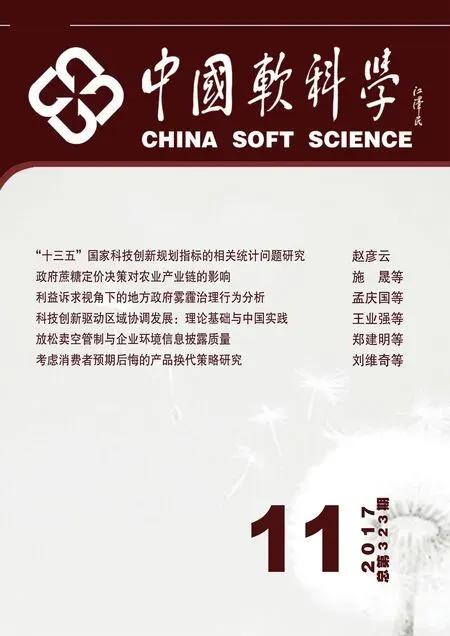知識員工工作流動中的非經濟報酬及其激勵效應
趙 晨,高中華,謝榮艷
(1.北京郵電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876; 2.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北京 100070;3.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MBA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2)
一、引言
作為創新型人才隊伍的主力軍,知識員工在創新創業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由于知識員工的工作流動能為行業或地區帶來較高的知識溢出效應,因此能夠更好地促進通過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加快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落實[1, 2]。從美國硅谷的經驗來看,創新創業文化氛圍的塑造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知識員工自由的工作流動。硅谷的知識員工更像自由的合同工,可以在不同工作間自由地轉換,這使硅谷本身就成為了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的人才儲備庫。例如從貝寶(PayPal)團隊走出的員工創建了領英(LinkedIn)、YouTube、Yelp點評、Yammer等7家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再例如,創立于2007年的Dropbox公司,最近一次融資時估值已達100億美元,其發展迅猛的原因之一是公司大多數員工來自Facebook、Google等創新企業。
由于市場在人才資源配置中日益扮演決定性作用,知識員工流動中經濟報酬的變化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在實踐領域中,用人單位通常會為引進的知識員工提供更加豐厚的報酬,以便激勵他們在本單位的創新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學術領域,大多數研究聚焦于以現金薪酬為代表的經濟報酬,例如通過收益或利潤分享來認可知識員工在價值創造工作中投入的知識資本,或者提高研發或科研項目中的人頭費用來補償知識員工在創新活動中付出的額外勞動[3]。然而,作為一種具有較高自我實現需求的群體,知識員工在工作流動中除了追求經濟報酬的增長外還非常重視非經濟報酬的改善[4]。現有研究尚未以實證研究的方式揭示他們到底追求哪些非經濟報酬要素的改善,以及不同非經濟報酬要素的改善對于提升其創新績效能夠發揮何種激勵效應。
時間比較理論為彌補這個研究不足提供了有益的視角。該理論視角的核心邏輯是人們會不由自主地比較現在的自我與過去的自我,從而實現自我提升的目的。為了進行這種時間性地比較,人們會主動尋求一些在進行時間比較時可以參照的依據[5]。經濟報酬和非經濟報酬是知識員工在工作中獲得的兩種主要報酬方式。根據該理論,我們認為除了經濟報酬增長外,非經濟報酬改善也能夠為知識員工進行時間比較從而實現自我提升提供重要的參照依據。
二、理論與假設
(一)知識員工工作流動中非經濟報酬的要素
非經濟報酬是全面報酬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世界薪酬協會構建的全面報酬中,除了薪酬、福利等可以用貨幣衡量的、有形的經濟報酬外,還包括認可與成就感、學習成長、工作生活平衡、社會地位等無法直接用貨幣衡量的非經濟報酬要素[6]。非經濟報酬是探討知識員工激勵與管理問題的重要切入點。這是因為:一方面,知識員工會依靠頭腦中較為隱性的知識來創造價值,這部分貢獻難以單純地依靠經濟報酬來加以衡量和激勵,當他們所獲得的報酬體現不出自己做出的貢獻之后將導致工作滿意度的下降[7]。另一方面,知識員工具有較高成就動機,他們希望在工作中獲得更高水平的成就感,提升自身價值,而不僅僅取得以貨幣收入為主的經濟報酬[6]。
在工作流動背景下,非經濟報酬改善不僅能夠讓員工對新的工作環境產生更高的滿足感與成就感[8],而且還能夠讓他們產生更為積極的自我評價。時間比較理論指出,為了實現自我提升的目的,人們往往希望通過多方面的證據來形成積極的自我評價,即認識到當前的自我是否顯著優于過去的自我[9]。知識員工工作流動中非經濟報酬的改善往往會成為他們進行時間比較的一種重要依據。然而以往研究在探討知識員工的非經濟報酬時,更多基于單一的雇主模式定性地指出一些構成要素,但很少以實證方法來動態地分析知識員工通過變換工作追求哪些方面非經濟報酬的改善。因此,本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來揭示知識員工工作流動中非經濟報酬所包括的要素。
(二)非經濟報酬改善對知識員工創新績效的直接激勵效應
非經濟報酬主要體現的是員工與雇主之間的社會交換關系,雇主能夠通過為員工提供挑戰性的工作任務、有前景的職業發展、穩定的工作環境和保障等非經濟報酬,幫助他們更好地獲得個人成長和自我實現[10]。研究表明,合理的非經濟報酬有助于激發員工對工作任務的內在動機[11],而內在動機又從根本上決定著人們的行為,具有較高內在動機的個體更容易體會到工作的巔峰感受,也就是說當人們受到內在動機驅動時,更加容易在工作或者其他感興趣的活動中,獲得強烈的適應感和成就感,并因此沉浸其中[12]。對于知識員工而言,由于非經濟報酬有利于滿足他們在尊重認可、自我實現等較高層次的需求,因此可能會很好地激發他們的內在工作動機。
時間比較理論表明,人們根據特定的參照依據進行時間比較之后形成的自我知覺會影響他們之后的態度和行為[5, 9]。工作流動是知識員工進行時間比較的重要契機,他們通過工作變換獲得的非經濟報酬改善,例如獲取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自我價值能夠被更多的人尊重認可等,不僅能夠很好地滿足他們較高層次的需要,激發對創新工作的內在動機[12],而且還能夠為他們與過去的自我進行多方面比較提供更多的依據,形成有利于維持和提升自我概念的積極評價,進而在當前單位的創新工作中付出更多的精力。因此,我們假設:
假設1:知識員工從工作流動中獲得的非經濟報酬改善對他們在新單位的創新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三)非經濟報酬改善對經濟報酬增長與創新績效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
經濟報酬主要體現的是員工與雇主之間的經濟交換關系,即員工在工作中付出努力之后會從雇主那里獲取相應的報酬作為補償[13]。研究發現,在預測績效改進方面,經濟報酬比社會認可、績效反饋等非經濟激勵手段更為有效[6]。對于知識員工而言,創新績效是最能代表他們績效水平的指標[14]。由于是一種具有探索性和創新性的高強度勞動,需要耗費大量的腦力與精力,為此知識員工必須全身心地投入,而充足的經濟報酬能夠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為之提供一份安穩的生活保障,讓他們不必為生計而疲于奔波,安心于當前的創新工作,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創新活動之中[4]。
然而,經濟報酬在知識員工激勵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3]。首先,在創新活動中,知識員工需要掌握前沿的知識與技能,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創新。前沿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則具有較強的未來導向,而經濟報酬的發放依據主要是當前的工作績效,是一種對已經取得的績效給予的補償性回報,僅向知識員工支出經濟報酬不足以促使他們不斷更新工作相關的知識或技能[15]。其次,從知識員工本身來說,他們具有較強的自主性需求,希望自己在創新工作中有較大的話語權,這種需求也難單獨用經濟報酬來滿足,組織可以通過工作設計來賦予他們更多做決策的權利[16]。知識員工從工作流動中獲得的非經濟報酬改善不僅能夠很好地補充經濟報酬增長的不足,而且還可以幫助他們形成更加積極的自我概念,更好地實現自我提升的目的,進而讓他們更加信心滿滿地投入創新工作[17]。因此,我們假設:
假設2:知識員工從工作流動中獲得的非經濟報酬改善對經濟報酬增長與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即能夠強化經濟報酬增長對創新績效的正向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的樣本來自于南京、成都、廣州、哈爾濱和武漢5個省會城市的85家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科研人員。由于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都需要大量地運用自身擁有的知識,因此符合本研究界定的知識員工群體。根據本研究的目的,知識員工需要對當前單位與之前單位非經濟報酬和經濟報酬的變動情況進行比較,并且我們關注的因變量創新績效的實現需要一定的時間周期,因此我們確定了三個標準對樣本進行篩選:本科以上學歷,有一次以上的工作變換經歷,在當前單位從事創新工作滿一年。根據這三個標準獲得的最終研究樣本包括個人有效問卷637份(其中企業361份、高等院校163份、科研機構113份)。
(二)非經濟報酬改善、經濟報酬增長與創新績效的測量
非經濟報酬改善的測量指標基于以往文獻和訪談總結而來,包括“自我成就感”、“與領導的關系”以及“工作與家庭的平衡”等17項內容,詳情如表1所示。在調查問卷中,本量表的引導語為“與上一個單位的工作相比,您當前的工作在以下各方面的變化如何?”采用5點李克特量表要求被調查者評價當前單位和上一個單位在這17個方面是否有所改善,其中1表示比上一工作單位差很多,3表示基本不變,5表示比上一工作單位好很多。

表1 知識員工非經濟報酬改善的三因子結構
注:各維度的因子載荷用加粗字體表示。
由于上述17個測量指標涉及非經濟報酬改善的多個方面,對這些指標進行逐一分析容易分散研究者的注意力,因此為了對知識員工非經濟報酬包括的要素做出更為深入的分析與解釋,本研究應用Stata13.0統計軟件對17個指標進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通過Bartlett球形檢驗(χ2= 6289.96,df= 136,p< 0.001)及KMO檢驗(KMO= 0.93),表明各指標之間相關度較高,存在共享潛在因子,適合進行因子分析。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對測量指標進行Promax斜交旋轉,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最終抽取出3個因子,累計解釋方差比例為65.06%,各指標在相應因子上都具有較大的載荷,處于0.56至0.91之間。
其中,因子1共有10個指標,主要內容包括個人成就、能力開發、研究興趣和發展機會等,我們將該因子命名為“學習成長”。因子2共有4個指標,其主要內容包括與單位同事、領導和同行的關系等,我們將該因子命名為“人際交往”。因子3共有3個指標,其主要內容包括工作穩定、工作壓力釋放以及工作與家庭平衡等,我們將該因子命名為“穩定平衡”。詳見表1所示。在此基礎上,我們根據因子得分函數系數矩陣計算17個測量指標的線性組合,并將各因子得分值保存為新的變量,分別命名為“學習成長”、“人際交往”和“穩定平衡”,用此3個新變量代替原有17個測量指標進行回歸分析。
經濟報酬增長主要反映知識員工報告在當前工作中稅后現金薪酬是否有一定的漲幅,我們在衡量經濟報酬增長時僅考慮了現金薪酬,包括工資、津貼、獎金等,但沒有考慮單位提供的各種福利。一個原因就是本研究的不少樣本來源于科研院所和高校,在大多數情況下,福利更多是由工會統一發放,與績效關聯較小,不同員工之間缺乏差異性,對他們的激勵作用并不大。經濟報酬增長的具體測量方法是當前稅后年收入減去剛到本單位時稅后年收入的差值。在本研究中,經濟報酬變化的均值為2.72萬元,標準差為2.91萬元。
近日,國家重點災后重建項目——甘肅省舟曲縣縣城及周邊地域山洪災害防治監測預警系統通過了甘肅省舟曲水利災后重建項目辦公室組織的驗收,該項目由武漢聯宇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承建。
因為本研究樣本涵蓋科研院所、高校和企業等多種類型的單位,各類型單位對創新績效的評價不盡相同,所以我們提出了盡可能廣泛代表各單位評價特征的5個測量指標,具體包括“近三年主持的科研/研發項目經費”、“近三年負責科研/研發項目轉化的銷售額”等,詳細如表2所示。
為集中反映創新績效的主要方面,本研究同樣對以上5個指標進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通過Bartlett球形檢驗(χ2= 829.52,df= 10,p<0.001)及KMO檢驗(KMO= 0.58),各指標之間相關度較高,適合進行因子分析。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對測量指標進行Promax斜交旋轉,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最終抽取出2個因子,累計解釋方差比例為79.76%,各指標在相應因子上都具有較大的載荷,處于0.62至0.96之間。

表2 創新績效的兩因子結構
注:各維度的因子載荷用加粗字體表示。
因子1共有2個指標,其主要內容包括近三年負責或參與的科研/研發項目轉化的銷售額,我們將該因子命名為“成果效益”。因子2共有3個指標,其主要內容包括近三年專利數量、論文數量、科研/研發項目經費金額等,我們將該因子命名為“成果數量”。從實現周期長短來看,科研成果效益反映的是他們長期的創新績效,而成果數量反映的是科研人員短期的創新績效。在此基礎上,我們根據因子得分函數系數矩陣計算5個測量指標的線性組合,并將各因子得分值保存為新的變量,分別命名為“成果效益”和“成果數量”,用此2個新變量代替原有5個測量指標進行下面的回歸分析。
由于知識員工的創新績效可能會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為了避免這些因素對本研究的結論產生過多干擾,我們在本研究中把這些因素設置為控制變量:性別(女性為參照類)、年齡、教育水平(本科為參照類)、婚姻狀況(未婚為參照類)、子女狀況(無子女為參照類)、調研城市(南京為參照類)、工作流向(企業流向企業為參照類)以及當前單位工作年限。
四、數據分析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3顯示了各主要研究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系數。除現金薪酬改善與穩定平衡改善、成果效益與人際交往改善和穩定平衡改善之間相關性不顯著之外,其余變量之間均顯著正相關,這為建立回歸模型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回歸分析與假設檢驗
工作流動后,經濟報酬改善、非經濟報酬改善以及二者的交互效應對知識員工在新單位的成果數量和成果效益的影響如表4所示。根據模型1和模型2,在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的條件下,現金薪酬增長對成果數量和成果效益均有顯著影響(β= 0.10,p< 0.01; β= 0.05,p< 0.10),而且對成果數量的影響要大于成果效益。
假設1預測知識員工從工作流動中獲得的非經濟報酬變化對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如表4中模型3和模型4所示,學習成長改善和穩定平衡改善對成果數量分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 0.24,p< 0.01;β= 0.18,p< 0.01),而人際交往改善對成果數量的影響不顯著(β= -0.06,p> 0.10)。與對成果數量的影響不同,學習成長改善對成果效益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 0.34,p< 0.01),人際交往改善對成果效益具有顯著負向影響(β= -0.26,p< 0.01),而穩定平衡改善對成果效益的影響不顯著(β= -0.06,p> 0.10)。因此,假設1得到部分驗證。

表3 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注:*p< 0.1,**p< 0.05,***p< 0.01。

表4 回歸分析結果
注:教育水平的參照類別為本科;城市的參照類別為南京;工作流向的參照類別為企業到企業;高科表示高校和科研院所;*p< 0.10,**p< 0.05,***p< 0.01。
假設2預測非經濟報酬變化能夠強化經濟報酬增長對創新績效的正向影響。我們將以現金薪酬為代表的經濟報酬增長,以學習成長、人際交往和穩定平衡為代表的非經濟報酬改善以及二者的乘積項,分別引入對科研成果數量和成果效益的回歸模型。如表4中模型5和模型6所示,現金薪酬增長與學習成長改善的乘積項以及現金薪酬增長與穩定平衡改善的乘積項對成果數量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 0.05,p< 0.05;β= 0.07,p< 0.01),現金薪酬增長與人際交往改善的乘積項對成果數量的影響不顯著(β= 0.03,p> 0.10)。與對成果數量的影響不同,現金薪酬增長與學習成長改善的乘積項對成果效益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 0.10,p< 0.01),而現金薪酬增長與人際交往改善的乘積項對成果效益具有顯著負向影響(β=-0.08,p< 0.01),現金薪酬增長與穩定平衡改善的乘積項對成果效益的影響不顯著(β=-0.02,p> 0.10)。因此,假設2得到部分驗證。
為更直觀地反映非經濟報酬改善對經濟報酬增長與成果數量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我們繪制了如圖1所示的調節效應圖。對于獲得較多學習成長的知識員工(高于均值1個標準差),現金薪酬的增長能較大幅度提升成果數量;而對于獲得較少學習成長的知識員工(低于均值1個標準差),現金薪酬的增長對成果數量的提升作用并不明顯(見圖1a)。與之類似,對于獲得更多穩定平衡感的知識員工(高于均值1個標準差),現金薪酬的增加能較大幅度提升成果數量;而對于穩定平衡感降低的知識員工(低于均值1個標準差),現金薪酬的增加對成果數量的提升作用并不明顯,甚至略有降低(見圖1b)。
圖2表示非經濟報酬改善對經濟報酬增長與成果效益之間關系的調節作用。對于獲得較多學習成長機會的知識員工(高于均值1個標準差),現金薪酬的增加能較大幅度提升成果轉化效益;而對于獲得較少學習成長機會的知識員工(低于均值1個標準差),現金薪酬的增加反而會降低成果的轉化效益(見圖2a)。與之相反,對于較上一工作單位感受到人際交往關系改善的知識員工(高于均值1個標準差),現金薪酬的激勵作用降低,并且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果轉化效益;而對于感受到人際交往變差的知識員工(低于均值1個標準差),現金薪酬的激勵作用增強,并且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成果轉化效益(見圖2b)。

圖1a 學習成長改善的調節作用 圖1b 穩定平衡改善的調節作用圖1 非經濟報酬改善對經濟報酬增長與成果數量之間關系調節作用

圖2a 學習成長改善的調節作用 圖2b 人際交往改善的調節作用圖2 非經濟報酬改善對經濟報酬增長與成果效益之間關系調節作用
五、分析與討論
(一)主要結論
第一,知識員工在工作流動中希望獲得的非經濟報酬改善包括學習成長、人際關系與穩定平衡三個要素。其中,學習成長是指這份工作是否為知識員工提供專業特長發揮、自我價值實現、職業提升與發展等的機會。除了學習成長之外,知識員工還在乎人際關系和穩定平衡,他們與領導、同事、同行等較為融洽的關系能夠讓他們更好地融入單位內外的各種圈子[18]。此外,在特定社會秩序下獲得穩定平衡,例如較高水平的職業穩定性和工作家庭平衡、較低水平的工作壓力等,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人們所廣泛追求的一種生存狀態[19],企事業單位把穩定平衡作為一種非經濟報酬能夠讓知識員工更加安心于創新工作。
第二,學習成長改善不僅對成果數量和成果效益均有顯著的直接正向影響,而且對經濟報酬增長與成果數量、成果效益之間的正向關系有強化作用。該結論說明,知識員工一方面可以利用諸多學習成長機會來獲取前沿的知識和技能,提升個人專長和研究勝任能力,創造出更多的創新成果,另一方面還可以擁有更大的平臺來實現創新成果的轉化[19]。此外,學習成長還能強化經濟報酬增長對知識員工的正向影響,即在學習成長得以較大幅度改善的條件下,當前單位提供的經濟報酬增長能夠更好地促進他們投入到創新工作之中,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提升創新績效水平。
第三,人際交往改善對成果效益有顯著的直接負向影響并且能夠減弱經濟報酬增長與成果效益之間的正向關系,但對成果數量本身以及經濟報酬增長與成果數量之間的關系沒有顯著影響。以往研究廣泛地從社會關系網絡視角探討了人際交往對員工績效和行為的積極影響[20]。然而,本研究發現人際交往改善并沒有起到預期中的積極作用,不僅對成果效益有直接的負向影響,而且還能改變經濟報酬與成果效益之間的正向關系,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工作流動后相對集中的人際交往會分散并消耗知識員工本該投入到創新工作中的認知資源,導致他們無暇顧及創新成果向市場效益的轉化。
第四,穩定平衡改善對成果數量有顯著的直接正向影響并且能夠強化經濟報酬增長與成果數量之間的正向關系,但對成果效益本身以及經濟報酬增長與成果效益之間的關系沒有顯著影響。穩定平衡改善之所以對成果數量和成果效益這兩種創新績效產生不同的作用,是因為這兩方面的創新背后需要的支撐動力有所差異。專利、論文、項目經費等成果數量能直接受到知識員工努力程度的影響,而成果轉化除了知識員工自身的努力外,還受到政策、經濟、市場等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知識員工的成果能否轉化為銷售額,還需要所在單位做好協調配合工作,例如后續開發、成果轉移、市場推廣等。
(二)管理啟示與對策建議
第一,基于全面薪酬的視角吸引和激勵人才,為創新驅動發展提供人才支撐。當前人才市場主要以現金薪酬和股權激勵為代表的經濟報酬來優化人力資本配置,企事業單位也主要依靠經濟報酬來促進人才資源集聚。本研究發現知識員工在工作流動中不僅追求經濟報酬的改善,而且還希望在個人學習成長、人際關系改善與工作生活穩定平衡為代表的非經濟報酬要素上獲得提升。這就要求企事業單位采取適應創新驅動發展要求的人才引進思路,整合經濟報酬和非經濟報酬各自的優勢,使非經濟報酬同樣成為吸引和激勵人才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經濟報酬短期內無法顯著提升的條件下,企事業單位可以通過內部激勵制度的完善和人力資源管理水平的提升來激發知識員工隊伍的創新活力。
第二,本研究發現,學習成長的改善不僅可以直接促進成果數量和成果效益的提升,而且還可以強化經濟報酬增長的激勵作用。據此企事業單位應通過如下措施為知識員工搭建有利于學習成長的平臺。一是提供多種形式的學習成長機會,注重有其他單位工作經歷的新員工在本單位研究能力的再度提升,而不是單純消耗這些新員工在原單位的知識經驗儲備。二是構建有效的行政和學術服務支撐體系,簡化繁文縟節式的管理,支持知識員工把有限的時間和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任務本身以及自身的學習成長之上;三是放開職稱職務、技術級別的數量限制,建立以第三方獨立組織的科研績效評價、同行評價和專業評價相結合的晉升制度,完善職業發展通道建設。
第三,企事業單位應從人際交往與穩定平衡兩方面著力塑造能讓知識員工獲得人文關懷的制度環境。本研究發現,人際交往并非如預期一樣會對成果數量和成果效益這兩種創新績效均形成積極的影響,相反會對成果效益產生消極影響,并且減弱經濟報酬增長對成果效益的積極影響。這就意味著在工作流動中,知識員工的人際關系改善并非越多越好,過多的人際交往不僅會消耗知識員工自身的時間與精力,而且還會在項目評審、成果鑒定等活動中損害公平競爭的原則,挫傷廣大知識員工的積極性,降低現金薪酬的基礎性激勵作用,因此企事業單位應對知識員工的人際交往進行合理引導。此外,本研究還發現,穩定平衡雖然對成果效益影響不顯著,但對創新績效中的成果數量有顯著影響,這是因為在創新活動中充斥著大量不確定因素,企事業單位需建立創新創業的容錯機制,營造寬容失敗、鼓勵創新的良好文化氛圍,為知識員工提供穩定平衡的工作環境,能讓他們更加心無旁鶩地去做創新。
第四,企事業單位應實施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保障知識員工經濟報酬的合理增長。本研究發現在經濟報酬增長比較合理的前提下,非經濟報酬的改善才能對知識員工的創新績效起到杠桿作用。然而,不少單位的薪酬增長制度與知識員工在創新工作中創造出的價值缺乏必然的聯系,導致“留不住人”的現象非常普遍。這就需要企事業單位創新性地通過股權期權分配、成果收益共享等激勵措施來認可知識員工在創新活動中的貢獻,這有助于充分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據此,企事業單位也應確立合理的薪酬增長制度,吸引并留住能為創新發揮重要價值的知識員工。
[1]馮南平, 魏芬芬. 創新要素區域流動的影響因素及其時間差異分析[J]. 中國科技論壇, 2017(2): 114-120.
[2]謝榮艷, 葛 鵬. 基于組織層面的科研機構人員流動影響因素研究[J]. 中國科技論壇, 2017(1):129-135.
[3]郭英遠, 張 勝. 科技人員參與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的激勵機制研究[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15, 36(7): 146-154.
[4]Yan M, Peng K Z, Francesco A M.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job design on knowledge workers and manual workers: A quasi-experimental field study in China [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1, 50(3): 407-424.
[5]Ross M, Wilson A E. It feels like yesterday: Self-esteem, valence of personal past experiences, and judgments of subjective distanc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5): 792-803.
[6]Aguinis H, Joo H, Gottfredson R K. What monetary rewards can and cannot do: How to show employees the money [J]. Business Horizons, 2013, 56(2): 241-249.
[7]Porfeli E J, Mortimer J T. Intrinsic work value-reward dissonance and work satisfaction during young adulthood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0, 76(3): 507-519.
[8]Krausert A. HRM systems for knowledge workers: Differences among top managers, middle managers, and professional employees [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4, 53(1): 67-87.
[9]Wilson A E, Ross M. From chump to champ: People’s appraisals of their earlier and present selv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0(4): 572-584.
[10]Kwon J, Hein P. Employee benefits in a total rewards framework [J]. Benefits Quarterly, 2013, 29(1): 32-38.
[11]Kruglanski A W, Riter A, Arazi D, et al. Effect of task-intrinsic rewards upon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75, 31(4): 699-705.
[12]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68-78.
[13]全裕吉. 高新技術企業虛擬型學習團隊的雙重激勵約束機制——經濟契約與心理契約的互動[J]. 管理世界, 2010(6): 179-181.
[14]張宏如. 心理資本對創新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J]. 管理世界, 2013(10): 170-171.
[15]徐 鵬, 白貴玉, 陳志軍. 知識型員工參與激勵與創新績效關系研究——組織公民行為的非線性中介作用[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16, 37(5): 129-137.
[16]Yanadori Y, Cui V. Creating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 dispersion in R&D groups and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12): 1502-1511.
[17]張 婕, 樊 耘, 張 旭. 組織激勵與組織約束對員工創新的二元影響研究——基于應激交互作用理論[J]. 預測, 2015, 34(6): 1-7.
[18]高中華, 趙 晨, 李超平, 等. 高科技企業知識員工心理資本對其離職意向的影響研究——基于資源保存理論的調節中介模型[J]. 中國軟科學, 2012(3): 138-148.
[19]阮國祥, 毛薦其, 馬立強. 員工即興行為對個體創新績效作用機制的跨層次研究——基于新能源創業企業的實證[J]. 中國軟科學, 2015(1): 108-117.
[20]M?kel? K, Brewster C. Interunit interaction contexts, interperson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differing levels of knowledge sharing [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9, 48(4): 59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