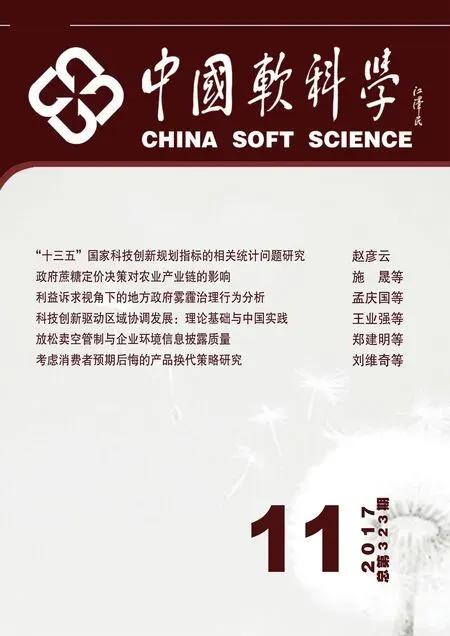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產生了“補償”還是“侵蝕”效應?
龔 紅,羅 巖,彭 姍
(1.武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2.武漢大學 中國產學研合作問題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一直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近年來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已對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截至2016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2.3億,占總人口的16.7%。據預測,2020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將占總人口的19.3%,2050年將達到38.6%。隨著人均預期壽命和人力資本周期的“雙延長”[1],促進老年再就業、實現“老有所為”已成為我國老年群體的迫切希望。
長期以來,技術進步被認為是影響就業的關鍵因素之一。而相對于中青年員工,老年員工由于受年齡、健康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可能更容易受到技術變革的沖擊。進入21世紀以來,技術變革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推進,這將會對我國老年再就業產生巨大沖擊。而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將是我國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制定老年再就業相關政策和措施時需要考慮的關鍵依據。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關于技術進步與老年再就業關系的探討為后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但從目前來看,仍存在著較大的爭議,其研究結論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 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產生了“補償效應”
技術進步能開發出新產品,開辟新的生產服務領域和新的產業,從而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這種影響被認為是技術進步對就業的“補償效應”[2]。此外,技術進步還能夠降低工作強度、縮短工作時間,從而有利于老年員工實現再就業[3]。與中青年員工相比,老年員工盡管在體力上沒有優勢,但卻擁有豐富的經驗以及熟練的技能,因此技術進步為老年員工帶來了更多適宜的崗位[4]。對此,Paul 等人[5]的研究也證實,那些長期工作于高技能行業的老年員工,由于學習能力較強并且已經適應了不斷變化的工作環境,技術變革并不會迫使他們提前退休,而延遲退休反而能夠激勵他們去學習掌握新的技術,不斷優化自身的人力資本。因此,應該為老年勞動者提供更為靈活的工作方式、時間以及更為舒適和安全的工作環境,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資本[6]。
我國學者的研究發現,技術進步能夠催生出一些新的產業,促進就業的增長。只要技術選擇能夠使資本勞動比保持穩定或穩中有升,不過分地向資本替代勞動的路徑偏移,技術進步就能夠有效地發揮其就業促進作用[7]。而政府通過鼓勵科技創新、促進教育培訓事業的發展,可以有效地促進就業的增長[8]。在我國,老年人的技能和經驗等人力資本,不僅可以擴大人力資源的供給,延長“人口紅利”,而且可以緩解我國人才資源的結構性短缺[9]。因此在21世紀,年老的人將是老齡社會的創造者,老年勞動者的生產率和績效將對提高未來的社會競爭力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0]。
(二)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產生了“侵蝕效應”
“侵蝕效應”強調技術革新對老年人力資本的侵蝕,老年員工學習新技能的速度相對較慢,未來從新技能中獲得的預期收益小,因此在技術變革來臨時他們往往選擇提前退休[11];同時新設備的引進也使得部分傳統崗位減少甚至消失,長期就職于傳統崗位及行業的老年員工更容易受到沖擊[12]。此外,由于技術與勞動之間的替代效應,企業也會因為技術進步而減少勞動力使用。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的身體素質逐漸下降,雇主會因此降低對他們價值評估。而技術變革帶來的年齡歧視問題也會對老年員工的薪酬以及就業前景產生不利影響[13]。對此,Koning等[14]在研究中指出,應對雇用老年員工的企業給予補貼,為老年人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避免因年齡歧視問題導致老年員工失業。而Fulmer[15]則認為,當技術變革的程度較小時,技術變革對老年員工就業的“侵蝕效應”會占主導地位,而當技術變革程度較大時,技術變革對老年員工就業的“補償效應”會占主導地位,對老年員工的再培訓成本與技術進步則呈顯著的倒U型關系。
姚先國等的研究發現,技術的不斷更新使企業對勞動力的技能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使得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形勢更為嚴峻[16]。姚戰琪等利用中國31個省市的截面數據研究發現,如果勞動者的質量和人力資本的分配不能及時適應技術進步以及產業升級的需要,企業就有可能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17]。朱軼等通過引入交互效應模型,探討了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變動對我國整體就業的影響,認為第三產業的技術進步會制約其對就業的貢獻,產業結構的劇烈變動會引發結構性失業[18]。王君斌也認為,由于價格粘性以及工資剛性的存在,技術進步引起的工資水平提高帶來的替代效應較大,收入效應相對較小,從而導致就業在短期內下降[19]。
國內外關于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影響的研究存在著較大爭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國別、行業、時間等環境的差異,導致了研究結論存在差異;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的影響存在著差異。因此,本文在總體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技術進步細分為勞動節約型和資本節約型,更加深入地分析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的影響。
三、實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我國目前的退休政策規定,男性退休年齡為60歲,女性退休年齡為女工人50歲、女干部55歲。由于我國的統計年鑒并未對女工人和女干部進行明確區分,因此本文統一選取55歲以上的女性再就業人員為研究對象。為了分析技術進步對不同年齡段老年再就業的影響,本文最終選取的退休再就業人員年齡段為:女性55-59歲、60-64歲、65歲及以上,男性60-64歲、65歲及以上。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2004-2016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樣本涵蓋制造業、信息傳輸及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等19個行業門類。
(二)變量定義
老年再就業率(EMPL)。計算方法為城鎮老年再就業人數除以城鎮老年總人數(分年度)。變量包括老年再就業率、老年男性再就業率和老年女性再就業率三類。
勞動生產率(LP)。本文采用勞動生產率度量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計算方法為分行業的增加值*本文使用的分行業增加值、行業平均工資及固定資產投資等指標均以2005的不變價格平減后得到。除以分行業的從業人數,單位是萬元/人/年。
資本生產率(CP)。本文采用資本生產率度量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計算方法為分行業的增加值除以分行業的資本存量。由于缺乏資本存量的官方統計數據,本文運用永續盤存法,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進行推算。計算公式為:Ki,t=Ki,t-1(1-&i,t)+Ii,t,Ki,t表示i行業t年的資本存量,Ii,t表示當年新增投資,&i,t表示資本折舊率。
全要素增長率(TFP)。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計算的全要素增長率度量總體的技術進步水平。計算公式如下:GA=GY-αGL-βGK,其中α為平均資本產出份額,β為平均勞動力產出份額,GY表示產出增長率,GL表示勞動力增長率,GK表示資本增長率。
本文選取行業平均工資水平(萬元)、固定資產投資額(萬億)、平均受教育水平(年)作為控制變量。為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平均工資水平、固定資產投資以2005年為基期對以后各年都進行了平減處理。對于行業平均受教育水平,本文結合年鑒中“按行業、性別劃分的城鎮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根據各學歷水平的受教育年限(未上過學=0;小學=6;初中=9;高中及中專=12;大專=15;本科=16;研究生以上=19)對平均受教育水平進行了計算。表1 描述了所選樣本的相關特征。
(三)模型設計
本文使用面板數據回歸分析法進行實證檢驗,Hausman檢驗結果表明模型(1)、(2)、(3)支持固定效應模型,模型(4)、(5)支持隨機效應模型。使用廣義最小二乘法(EGLS)對模型的異方差進行了修正,模型擬合結果為修正異方差之后的結果。統計模型如下: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① VIF 值小于10,表明本文所選取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EMPLit=α0+α1TFPit+α2EDUCit+α3WAGEit+α4CAPLit+εit
(1)
其中,i表示行業,t表示年份。EMPLit分別表示Lowit、Midit、Highit,即i行業t年55-59歲、60-64歲、65歲及以上年齡段的老年再就業率。TFPit表示i行業t年的全要素增長率,其余為控制變量,包括i行業t年的平均受教育水平(EDUCit)、行業平均工資水平(WAGEit)以及行業固定資產投資(CAPLit)。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的影響
表2分析了總的技術進步對我國老年再就業的影響。結果顯示,總的技術進步對低齡及中齡老年再就業具有顯著的“補償效應”。全要素生產率每提高1%,55-59、60-64歲的老年再就業率就會分別提高0.043%和0.016%。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技術進步開辟了新的生產服務領域以及新的產業,創造出了新的就業崗位。另一方面,技術進步帶來的一些新的自動化設備使得原本復雜的工作簡單化、易操作,為老年人再就業提供了更多適宜的崗位。
此外,表2 的結果還顯示,行業實際工資水平以及固定資產投資與老年再就業顯著正相關。這可能是因為投資的增長會為企業帶來更高的產能,而產能的提高又會帶來相應配套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從而對老年再就業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表2 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的影響:總的分析
注:***、**、*分別代表在1%、 5%、 10%的水平下顯著。
(二)勞動節約型與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行為的影響
盡管總的分析發現,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行為產生了“補償效應”,但是為什么國內外較多的研究對此結論不一?我們認為,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對就業行為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進一步將技術進步細分為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和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更加細致地分析不同類型的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的影響。建立模型如下:
EMPLit=α0+α1LPit+α2EDUCit+α3WAGEit+α4CAPLit+εit
(2)
EMPLit=α0+α1CPit+α2EDUCit+α3WAGEit+α4CAPLit+εit
(3)
其中,LPit表示i行業t年的勞動生產率,CPit表示i行業t年的資本生產率,其余變量同模型(1)。

表3 不同類型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的影響
注:***、**、*分別代表在1%、 5%、 10%的水平下顯著。
表3的分析結果顯示,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具有顯著的補償效應,能夠有效促進老年再就業。勞動生產率每提高1%,55-59、60-64、65+三個年齡段的老年再就業率就會分別提高0.038%、0.025%、0.024%,這可能是因為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擴大企業的生產規模,進而增加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對此Avner等人認為,如果一種要素相對充足,那么偏向該要素的技術將更有價值,因此企業更愿意研發偏向該要素的技術[20]。我國作為人口大國,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開發勞動節約型技術符合我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對于實現“保增長、促就業”的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具有顯著的“侵蝕效應”,降低了老年的再就業率。資本生產率每提高1%, 55-59、60-64、65+三個年齡段的老年再就業率就會分別降低0.32%、0.179%、0.092%,這可能是因為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提高了企業的自動化水平,淘汰了一些低端崗位,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人力,從而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
20世紀80年代,由于勞動力資源豐富,物質資本匱乏,我國將食品、紡織等輕工業作為主導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此時,技術進步對我國的就業總量具有正向影響,經濟產值與就業總量呈現“雙增”勢頭。而進入90年代之后,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重工業被置于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此時我國走的是一條資本偏向型的技術路徑,資本替代勞動的特征顯著。技術進步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了對就業的吸納,因此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并沒有相應地帶來較高的產業勞動力需求。
(三)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影響:基于服務業和制造業的比較分析
前面的研究發現,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具有顯著的補償效應,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具有顯著的侵蝕效應,為了進一步分析兩類技術進步的具體影響,本文結合了相關的行業來進行分析。
在我國,零售、餐飲以及生活服務等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具有相當大的就業吸納能力。服務業吸納勞動力的數量迅速增長,并于2011年超過第一、第二產業成為我國吸納勞動力最多的行業,已逐漸成為我國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要渠道。因此,本文進一步基于服務業和制造業進行比較分析,并以制造業、建筑業等其他行業作為參考(見表4)。

表4 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的影響:基于服務業和制造業的比較分析
注:***、**、*分別代表在1%、 5%、 10%的水平下顯著。
表4的結果表明,對服務業來說,技術進步對55-59、60-64歲老年再就業具有顯著的“補償效應”,全要素增長率每提高1%,低齡及中齡的老年再就業率就會分別提高0.063%、0.022%;而對于制造、建筑等其他行業來說,技術進步與老年再就業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產生了顯著的“侵蝕效應”。
這支持了表3的分析結果,即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產生了顯著的補償效應,而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則產生了顯著的“侵蝕效應”。服務業是勞動相對密集的行業,企業成本的構成主要是人工成本。為節約生產成本,企業會努力提高勞動效率,因此其技術進步的類型更偏向于勞動節約型。制造業是資本相對密集的行業,企業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購買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其生產成本的構成中,資本所占比重較高。為節約生產成本,企業會追求自動化、規模化,努力提高資本生產率,其技術進步的類型偏向資本節約型。
當前,隨著制造業在全球范圍內產能過剩,服務業已成為吸納就業增長的主要渠道。因此,在我國,要實現“保增長,促就業”的目標,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充分挖掘服務業吸納就業的潛力。
(四)技術進步對不同受教育水平老年再就業的影響
對于不同受教育水平、性別的老年勞動者,技術進步對其就業的影響可能存在著差異,因此本文進一步根據性別、受教育水平對老年再就業群體進行分組,分析技術進步對不同特征的老年群體再就業的影響。
隨著行業技術水平的提高,企業對于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的需求也會發生變化。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決定了其獲取再就業機會的概率和能力。此外,個體的受教育水平會影響其自身的職業選擇。因此,本文以受教育年限是否大于12年(高中學歷)為標準,將19個行業分成兩組,對比分析技術進步對不同受教育水平的老年再就業的影響(見表5)。

表5 技術進步對不同受教育水平的老年再就業的影響
注:***、**、*分別代表在1%、 5%、 10%的水平下顯著。
表5 的結果顯示,技術進步對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老年人的再就業具有顯著的“補償效應”,但對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老年人的影響并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我國企業更多地是采取外延式的擴張模式(資本和勞動的投入)謀求發展,企業的技術進步并沒有帶來高技能工人比例的顯著提高,反而大幅增加了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8]。此外,結果還顯示,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帶來的侵蝕效應對平均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老年人影響更大。我們推測這可能是因為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老年人更容易適應技術進步帶來的變革,從而更容易實現再就業。而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老年人更難適應技術進步帶來的變化,難以獲得再就業機會。
(五)技術進步對不同性別老年再就業的影響
在按照受教育水平對老年再就業群體進行分組分析之后,本文又分性別分析技術進步對老年群體再就業的影響。建立模型如下:
mEMPLit=α0+α1TFPit+α2LPit+α3CPit+α4EDUCit+α5WAGEit+α6CAPLit+εit
(4)
wEMPLit=α0+α1TFPit+α2LPit+α3CPit+α4EDUCit+α5WAGEit+α6CAPLit+εit
(5)
mEMPLit分別表示mMidit、mHighit,即i行業t年60-64、65+兩個年齡段男性老年再就業率,wEMPLit分別表示wLowit、wMidit、wHighit,即i行業t年55-59、60-64、65+三個年齡段女性老年再就業率,mEDUCit表示i行業t年男性職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wEDUCit表示i行業t年女性職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其余變量同上。
表6分析了技術進步對不同性別的老年再就業的影響。結果顯示,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對老年男性及女性再就業都產生了顯著的“補償效應”,但對老年女性的影響程度更大。這可能是因為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多發生于勞動相對密集的輕工業以及服務業等行業,這些行業對女性勞動者的需求相對較大,因此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會更多的促進老年女性再就業。

表6 技術進步對不同性別老年再就業的影響
注:***、**、*分別代表在1%、 5%、 10%的水平下顯著。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利用中國近十年來19個行業的面板數據,在將技術進步細分為勞動節約型與資本節約型兩種類型的基礎之上,從技術進步類型的角度探討技術進步與老年再就業的關系。結果顯示,我國總的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具有顯著的“補償效應”,而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具有顯著的“侵蝕效應”;就產業層面來看,對服務業來說,技術進步對老年再就業具有顯著的“補償效應”,但對于制造、建筑等行業來說,技術進步與老年再就業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此外,就個體層面來看,技術進步對受教育水平較低的老年人的再就業具有顯著的“補償效應”,但對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老年人的影響并不顯著;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對老年男性及女性再就業都產生了顯著的“補償效應”,但對老年女性的影響程度更大。
(二)對策建議
在人口快速老齡化與技術變革日益加劇的環境下,為使我國老年人能夠更積極地實踐自我養老,實現“老有所為”,應結合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要素稟賦結構,積極推進勞動節約型技術的發展,適度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我國老年再就業提供更多的機會和空間。老年人實現了再就業,創造了收入,不再是政府和家人的負擔,甚至還能為我國GDP的增長貢獻一份力量。
而對于個體來說,技術進步對不同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性別的老年工作者的影響程度都不同。盡管在短期內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不會大量淘汰低技能的勞動者,但長期來看,隨著產業升級的不斷推進以及企業生產的集約化,高技能勞動力將會有更為廣闊的就業和發展空間。因此,國家應積極鼓勵企業對老年人口的在職培訓,這對于延緩老年人口的人力資本貶值、增強老年人口的就業意愿及就業能力、增加老年人口未來再就業的自主性和靈活性都具有重要意義。
[1] 桂世勛, 李建民, 杜 鵬,等.新時期的老齡問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J]. 人口研究,2011(4):29-43.
[2] MOSCARINI G, POSTELVINAY F. The relative power of employment-to-employment reallocation and unemployment exits in predicting wage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5): 364-368
[3] DE LA CROIX D,OLIVIER P,HENRI R.Aging and pensions in general equilibrium:labor market imperfection matter[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13, 37(1):104-124.
[4] GORDO LR, SKIRBEKK V.Skill demand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age:Jobs tasks and earnings from the 1980s to the 2000s in Germany[J].Labour Economics,2013,22:61-69.
[5] PAUL B, DAVID A.Spatial equilibrium with unemployment and wage bargaining:Theory and estimatio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5,79:2-19.
[6]郭凱明,顏 色.延遲退休年齡、代際收入轉移與勞動力供給增長[J]. 經濟研究,2016(6):128-142.
[7]葉仁蓀,王光棟,王 雷.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與技術進步路線的選擇——基于1990~2005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分析[J]. 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2008(3):137-147.
[8]翟振武.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J]. 求是,2013(23):57-59.
[9]蔡 昉.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J]. 經濟研究,2010(4):4-12.
[10]彭希哲,胡 湛.公共政策視角下的中國人口老齡化[J]. 中國社會科學,2011(3):121-138.
[11]JUNG S, LEE JD, HWANG WS.Growth versus equity:A CGE analysis for effects of factor-biased technical progres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J].Economic Modelling,2017,60:424-438.
[12]LELAND NE, ELLIOTT SJ.Special Issue on productive aging: Evidence and opportunities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practitioners[J].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2012, 66(3):263-265.
[13]MESSE PJ, ROULAND B.Stricter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firms’ incentives to sponsor training:The case of French older workers[J].Labour Economics, 2014, 31(12):14-26.
[14]KONING P, RATERINK M.Re-employment rates of older unemployed workers:Decomposing the effect of birth cohorts and policy changes[J].Economist,2013, 161(3):331-348.
[15]FULMER IS, PLOYHART RE.Our most important asset:A multidisciplinary review of human capital valuation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4,40(1):161-192.
[16]姚先國,周 禮,來 君.技術進步、技能需求與就業結構——基于制造業微觀數據的技能偏態假說檢驗[J]. 中國人口科學,2005(5):47-53.
[17]姚戰琪,夏杰長.資本深化、技術進步對中國就業效應的經驗分析[J]. 世界經濟,2005(1):58-80.
[18]朱 軼,熊思敏.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變動對我國就業效應的經驗研究[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5):107-119.
[19]王君斌,王文甫.非完全競爭市場,技術沖擊和中國勞動就業——動態新凱恩斯主義視角[J]. 管理世界,2010(1):23-35
[20] AHITUV A, ZEIRA J.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arly retirement[J].The Economic Journal,2011, 121(3):171-193.
[21]辜勝阻,吳華君,曹冬梅.構建科學合理養老服務體系的戰略思考與建議[J]. 人口研究,2017(1):4-14.
[22]楊立雄.北京市老齡產業發展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17(3):7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