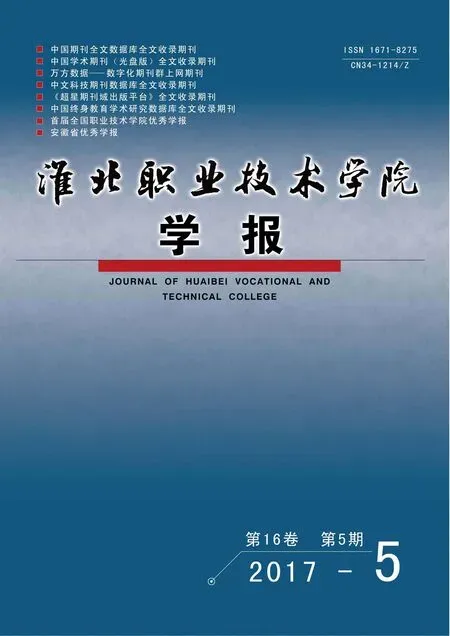論柳永以俚語入詞
楊戴君
(廣州大學 人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論柳永以俚語入詞
楊戴君
(廣州大學 人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為了傳唱的歌妓舞姬和市井中“不知書”的聽眾,柳永把北宋時期民間非正式、較口語的俚語俗言引入詞中,用俚語表達新鮮事物,或對舊事物賦以新的說法,重新把詞帶回到市井坊曲。這既吸引了一大批市民聽眾,又打破了詞雅俗分流的界限,因此受到市民聽眾的歡迎。柳永采用長調慢詞形式,廣泛引用民間俚語俗言,不僅豐富了詞的語言,擴大了詞的表現能力,而且也因此恢復了詞的生命,對后來宋元戲曲、通俗小說等俗文學登上文壇做出了貢獻。
柳永;《樂章集》;俚語
柳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因排行第七,故又稱柳七,因最后官職為屯田員外郎,所以世稱“柳屯田”,他撰有詞集《樂章集》,存詞212首。柳永幼年隨父轉徙各地,少年時代則與父親定居于汴京。他精通音律,有著深厚廣博的文藝修養,不僅為教坊樂工寫詞,也為秦樓楚館中的歌舞妓作詞。在仁宗初年,柳永雖然通過考試,臨到發榜時卻被仁宗黜落,他在未及第之前,就已經先以喜愛譜寫樂工歌舞妓的俗曲,并與他們往來而名噪一時。深惡虛華之文的仁宗,不可能容忍他。嚴有翼在《藝苑雌黃》中云:
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自稱云:“奉圣旨填詞柳三變。”[1]
“奉圣旨填詞”是柳永與市民審美趣味的投合,柳永長期混跡在勾欄瓦舍,這使他能夠和底層老百姓有較多交流,為了迎合底層市民的需求,他把北宋時期的民間非正式、較口語的俚語俗言引入詞中。作為一種非正式、通俗易懂順口且具有地域特色的語言——俚語,一般會被使用在非正式的場合,但是柳永變俗為雅,把俚語雅化;以雅從俗,把詞寫得更通俗,用俚語表達新鮮事物,或對舊事物賦以新的說法。久困科場而混跡底層的柳永,越發致力于民間俗詞的寫作,從而領導了宋詞的一次變革。
一、柳詞新變,褒貶不一
“詞”是在隋唐時期興起的,起初是為民間盛行之樂曲供歌唱的歌辭,后經白居易、劉禹錫等文人的改造而不斷提升。唐五代以后,“詞”開始慢慢打破詩以言志的傳統與文以載道的傳統,當時士大夫們在聚會歌宴間填寫歌詞時,其內容所寫大多以女性與戀愛為主,可以說是擺脫了倫理道德之約束的一種體裁。因此,通常很容易引起讀者的遐想,而且在其發展中,更使一部分作品形成了一種既可以顯示作者心中隱藏之本質,又能夠激發讀者潛意識中豐富想象的微妙作用。詞發展到北宋初期,詞作雖然日多,卻依然無法取得和詩文相等的地位。這和“詞”起于檀板宴會之間有關,另外,和它那狹小的內容形式、嚴整的音律要求亦不無關系。而文人未盡全力、隨興鋪寫的態度,也使得“詞”無法脫離樂歌的身份而獨立。在這種情況下,“詞”不但不足以與詩文抗衡,甚至可能在二晏、歐陽修等令詞名家出現后,逐漸衰微。奠定詞體獨立、發展的基礎,須賴長調慢詞之興起,說到長調慢詞,繞不開的便是柳永。
柳永大量使用長調慢詞,他師承漢魏六朝賦的“鋪敘”手法,盡情描繪,恣意敷設,將寫景、敘事、抒情融為一體,在結構上又有一定的層次,有首有尾地寫出分明的層次和場面。因為柳永全力填慢詞,長調慢詞因而興盛,他是在詞史上影響一代的大家,歷來論詞者論柳詞往往褒貶不一,同時代或后世詞論家給予柳詞之藝術技巧相當高的評價,都認為其詞擅于鋪敘,用字細密妥溜,敘事則明白家常、形容曲盡。但由于柳詞形容上太真實,好用俚語白話,白描過多,不免淺近卑俗,最為士大夫所不滿。自宋以來,柳詞屢次遭受詞論者之譏,招致“詞格不高”,詬病柳詞之“俗”。“俗”,似乎成為柳永詞風格特征的標志。徐度的《卻掃編》(卷下)記載:
其詞雖極工致,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為歌詞,體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劉季高待郎宣和間嘗飯于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氏,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于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為不佳者,盍自為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后知稠人廣眾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2]
徐度指出,歐陽修、蘇軾“高雅”之詞出,士大夫漸漸厭棄柳詞,而市民對柳詞的喜愛卻絲毫未變。底層老百姓依然極度喜愛柳永詞,并且義無返顧地維護柳詞的地位,面斥士子的惡意毀謗。柳詞之所以在民間被廣為傳唱,原因之一就是語言的俚俗,可知柳詞深得流俗人的喜愛。文人士子則不同,陳師道說柳詞“骫骳從俗,天下詠之”[3],嚴有翼評柳詞“言多近俗,俗子易悅”[1]等。總觀這些評論,大抵針對柳詞之格調鄙俗和語言俚俗兩方面。
二、俚語俗言,明白如話
從唐末五代起,詞就開始以雅俗作為標準分流,一方面文人士大夫在歌舞宴會上以詞作為娛樂節目為嘉賓助興,慢慢地把俚俗的歌妓舞曲詞變成“文人曲子詞”。由于是在宴會上即興揮毫,并命歌妓演唱,因此,這種詞就不可避免地體現出文人士大夫的審美情趣,后來西蜀的韋莊,南唐的李璟、馮延巳等人開始把自己的感慨寄寓在詞中,抒寫自己的境遇;再后來南唐國破,李煜淋漓盡致地把自己的亡國之恨與對故國的思念寫入詞中。經過不斷的發展,詞漸漸成為一種可以表現自我情性的“新詩體”,又經過與風騷傳統的結合,可以用詞寄托對國家的忠愛,而在藝術上也就開始追求詩的精粹和典雅。詞既可唱,又可讀;既娛賓遣興,又抒情言志。柳永深受到民間俗文學的影響,大量引用俗言俚語入詞。因此,北宋乃至北宋以后的學者評論柳詞褒貶不一,褒柳詞者贊其詞雅,貶柳詞者貶其詞俗。的確,從內容到語言,柳詞大量引用俚語俗言,并因此博得天下世俗之人的偏愛。但是,我們并不能單純地以俚俗概括柳永的詞,柳詞也有高雅脫俗的一面。柳永的許多名作,不但“市井之人悅之”,而且是雅俗共賞的。鄧延楨《雙硯齋詞話》是這樣評價柳詞的“雅”和“俗”:
《樂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輕浮猥媟,取譽箏琶……惟《雨霖鈴》之“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雪梅香》之“漁市孤煙裊寒碧”,差近風雅。《八聲甘州》之“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乃不減唐人語。“遠岸收殘雨”一闋,亦通體清曠,滌盡鉛華。[4]2528
《雙硯齋詞話》所舉的冶游之作都是俗詞,而從《雨霖鈴》開始,都是柳永雅詞的代表。就柳詞的內容與主題而言,俗詞主要是其艷情詞,而雅詞大部分是其抒寫羈旅愁思、詠史詠物之詞。宋翔鳳《樂府余論》云:“雖多俚語,而高處足冠群流,倚聲家當戶而祝之。”[4]2499柳詞多為勾欄瓦舍之歌女舞妓所傳唱,聽眾大多是“不知書”的市井百姓,為了照顧這些聽眾,柳永大量借鑒民間俗文學,因此,柳詞的語言往往采用民間俚語俗言,明白如話,他是北宋初期詞壇上第一位大量引用民間俚語俗言入詞的詞人。劉熙載稱其詞“明白而家常”[5],這也許是因其字句多出之以俚語俗言之故。柳永引用的都是當時底層人們所能聽懂、看懂的俚語白話,都是一些很口語化的語言。這些口語化的語言豐富了柳詞的詞匯,不僅親切易懂,而且能夠“散播四方”。柳詞口語化的程度很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柳永為詞中之白居易,當是白與柳二人之最大相同之處,即是語言的通俗明白。試看《玉女搖仙佩》(佳人):
飛瓊伴侶,偶別珠宮,未返神仙行綴。取次梳妝,尋常言語,有得幾多姝麗。擬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細思算、奇葩艷卉,惟是深紅淺白而已。爭如這多情,占得人間,千嬌百媚。須信畫堂繡閣,皓月清風,忍把光陰輕棄。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當年雙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憐我多才多藝。愿奶奶、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為盟誓,今生斷不孤鴛被。[6]2
作為自制曲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詞牌,柳永在詞中把仙女比作美女,所詠的女子,貌美而又淡妝,其中“擬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這幾句,通過“擬把”這個俚語俗詞,十分口語化地表達了丈夫與妻子的至深感情,即使把名花和妻子相比,又怎及其妻之美于萬一。此外,詞中還使用了“奇葩”“忍把”“且恁”“未消得”等俚俗詞語,使得全詞明白如話,自然生動,聽眾一聽便能懂得。柳永大量使用俚語俗詞寫作,不僅是對唐五代敦煌曲子詞的繼承與發展,而且擴大了詞的表現能力,進一步推動了宋詞的發展。
此外,柳永還擅長使用白描手法。文學中的白描,是以樸素、簡單的語句,細密簡練的描摹各類形象,不加以烘托,沒有隱喻,較少使用典故,更乏深遠的寄托。《樂章集》中,大部分詞都使用了白描與俚語。試看《鶴沖天》(大石調):
閑窗漏永,月冷霜花墮。悄悄下簾幕,殘燈火。再三追往事,離魂亂、愁腸鎖。無語沈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則個。從前早是多成破。何況經歲月,相拋嚲。假使重相見,還得似、舊時么。悔恨無計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6]29
這首詞一開始便采用白描手法寫景,用“閑窗”“霜花”“簾幕”“燈火”等一連串意象描繪出一幅蕭條的圖畫,表現出詞人的愁思。后面幾句也全部采用白描的手法進行抒情,不僅抒寫出詞人內心深處對妻子的思念,而且害怕此去一別的分離會破壞夫妻間的深情,和盤托出詞人愁腸百結的悔恨情態。全詞除了使用白描的手法寫景抒情,把詞人愁悶復雜的心境表現得通俗曉暢,而且使用了“再三”“好天好景”“未省”“則個”“自家”等俚語俗言入詞,使整首詞自然生動。
三、俚語入詞,別具一格
柳永串連了“雅”“俗”兩種不同的詞,即士大夫宴會上的文人詞和勾欄瓦舍間的民間詞,這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唐五代詞的語言經過兩百多年的重復使用,已逐漸變成陳腔濫調,若不革新,則會成為死文字,詞的生命也將結束。由于文人詞的過度詩化、雅化,詞逐漸偏離了它作為音樂文學的本質。柳永擺脫了唐五代以來小令語言的典雅,大規模地采用民間盛行的長調慢詞形式,引用宋代底層社會流行通俗的俚語白話,在宋詞中獨具一格,不僅豐富了柳詞的語匯,而且擴大了宋詞的表現力,獲得更多的現實感和生活感,也因此恢復了詞的生命。他把達官貴人的宴會詞曲再次引向青樓市井,極大地擴大了它的社會基礎,加強了詞作為俗文學的色彩。雖然柳永出生在官宦家族,卻跨出其出身背景的枷鎖,早年便留戀于秦樓楚館,與歌妓樂工打成一片,為他們作曲填詞,并將經過文人“變俗為雅”的歌詞,又“以雅為俗”,重新把詞帶回到市井坊曲,既吸引了一大批市民大眾,又打破了“詞”雅俗分流的界限。
其實引用民間俚語俗言并不是柳永的專利,但絕大多數人都不如柳永。柳永的語言一般少雕琢、少用典故,天然似不甚經意,而有“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之效,顯示出他駕馭俚語俗言的高超藝術,因而受到市民群眾的歡迎。而且他常常通過簡單的俚語白話,就能夠展現出主人公的內心豐富的世界,例如:“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清瘦”(《傾杯樂》)[6]22,傳達出了一種無希望的愛情給主人公帶來的相思之苦。“假使重相見,還得似、舊時么”(《鶴沖天》)[6]29,這是因許久未見面,愛情空虛,耽心情感變化的可能性,暗示女子的不幸。柳永的“詞”,語言雖然通俗,但是并沒有停留于它的表面層次,而是對底層老百姓的生活、感情和命運表現出深切的關注。柳詞大量引用俚語俗言的成功,別具一格,對后世宋元戲曲、通俗小說等俗文學的發展,應有直接的先導意義。
四、結語
為了傳唱的歌妓舞姬和市井中“不知書”的聽眾,柳永不避俚語俗言,少用典故,亦罕見隱喻,多用市井群眾耳熟能詳的俚語白話,因而受到市民群眾的歡迎。與一般文人詞相比,顯得較為生動活潑,具有更多的現實感。柳永引用民間俚語入詞,從“詞”的整個發展歷程來說,他不僅豐富了“詞”的語匯,擴大了“詞”的表現能力,而且在中國文學史上,對后來宋元戲曲、通俗小說等俗文學登入文壇有所貢獻。
[1] 脫脫,等.宋史·藝文志[M].北京:商務印書局,1957.
[2] 徐度.卻掃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5.
[3] 何文煥.歷代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1.
[4] 唐圭璋.詞話叢編(第3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5] 劉熙載.藝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 姚學賢,龍建國.柳永詞詳注及集評[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責任編輯:張彩云
DiscussiononLiuYong'sUseofSlanginSongCi
YANG Daijun
For the sake of kabuki and the audience who don't know books, Liu Yong brought the folk informal and oral slang words into Song Ci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ime to express new things with slang, or endow old things with new expressions. He took the Ci back to the town square, which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audience, and broke the boundaries of the elegance and vulgarity of the Ci words. So it was welcomed by the public audience. Liu Yong adopted a large scale of the forms of Changdiao and Manci and a wide quotation of folk slang or vulgar language, which not only enriched the language of the Ci word, expanded the Ci expression ability, but also restored the life of Ci, and contributed for the later Song Yuan opera, popular novels and other folk literature to step onto the literary world.
Liu Yong;LyricChapter(YueZhangJi);slang
2017-05-30
楊戴君(1993—),男,廣東韶關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2016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詩學。
I206.2
:A
:1671-8275(2017)05-008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