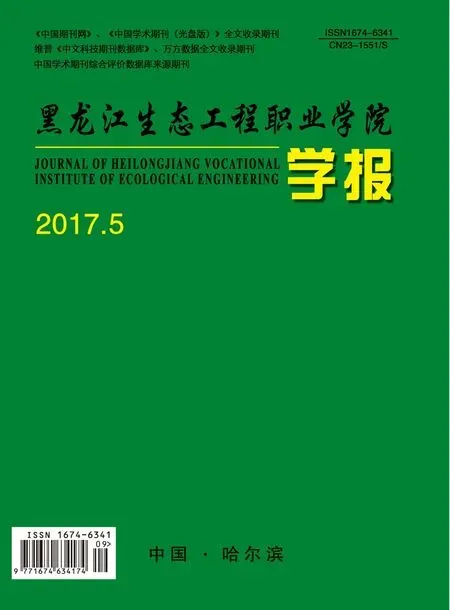從創傷角度解讀后9·11文學中的人文主義關懷
任冰
從創傷角度解讀后9·11文學中的人文主義關懷
任冰
(東北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黑龍江哈爾濱150040)
9·11后產生新的社會形態與個人及文化想象的互動,為9·11小說的創傷敘事文本注入了新的文化意義和現實意義。擬從創傷角度分析后9·11文學作品中的多種創傷,并進一步從人性的角度探究作品所展現的人文主義關懷。
創傷;9·11小說;人文主義
0 引言
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紐約的恐怖襲擊事件,造成了大量民眾的傷亡,給美國人帶來了難以估量的精神創傷。十多年來,新聞媒體、文學藝術等9·11事件的話題從未間斷,尤其是世界文壇的作家們正以各自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對人們心靈的慰藉。“美國9·11事件之后,全球性的反恐和后冷戰思維逐漸催生了一種具有反思生命意義、深度觀照歷史并使歷史與現實交融的文學,被稱之為后9·11文學。當代作家將9·11事件從一場悲劇轉化為景觀,在創作中巧妙地處理文學創作與民族文化心理建構、文學創作與歷史敘事、文學創作與意識形態等諸多關系。美國后9·11文學集想象與反思于一體,具有寬廣的全球化意識,揭示了遭受恐怖襲擊后普通美國人的創傷記憶、心理承受和救贖軌跡。”[1]當代英美作家如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唐·德里羅(Don DeLillo)、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等用自己的經歷和想象對9·11事件進行了敘寫。根據伯吉特·戴維斯(Birgit Dawes)的統計,截至2011年6月,美國文學中至少有162部作品可以被歸類為“9·11小說”[2]。這些文學作品具有鮮明的后現代主義特征,從某種語境上反映了美國集體創傷,拓展了對人類心理創傷母題的倫理探詢,并進一步從人性的角度探索創傷與救贖等涉及人文主義關懷的主題。
1 創傷理論
作為心理學的一個分支,精神創傷學是一個相對較新的學科。創傷泛指各類天災人禍給人造成的意外傷害;精神創傷指創傷所引起的心理、情緒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狀態[3]。人的一生中都會遇到生老病死,創傷每天都可能伴隨著人類并帶來巨大的心理陰影。最后,即便生命終結,但人的精神仍會以創傷的形式長時間留在親友心中。盡管心理創傷在人類生活中非常普遍,但創傷理論的發展卻是始于20世紀90年代。這個術語首先由美國學者凱西·卡魯斯提出。她認為,災難會在人們的內心留下創傷,但心理創傷不是出現在災難發生時,而是在災難發生后的某段時間,留在人們對災難的回憶中。災難在受害者的心里可留下陰影和傷害,會影響他們未來的生活。隨著創傷理論的發展,又出現了心理創傷和精神創傷的概念。心理創傷主要有兩種形式:個人心理創傷(Individual trauma)和集體心理創傷(collective trauma)。集體由個體組成,因個人心理創傷與集體心理創傷相互依存,密不可分,集體的凝聚力通過傾聽個體講述創傷故事來獲得。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民族創傷(national trauma)和歷史創傷(historical trauma)都是集體創傷的重要組成部分[3]。既然有了創傷,人們就會研究創傷的治療方法。創傷治療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人們提出了許多治療創傷的辦法,其中語言是一種改善和治療創傷的有效手段之一,無論口頭還是書寫,這兩種方式都有顯著效果。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與創傷有著密切的聯系,創傷亦是文學的一個常見母題。在英美文學史上,從印第安人的戰爭創傷到黑人和亞裔的精神創傷,直至9·11事件的文化創傷,無不是統罩在創傷主題下的個性創作。美國后“9·11”文學創作以神奇的想象獨特的視野來審視恐怖襲擊事件。并注入了作家對于歷史的反思和對倫理的考問。他們在后現代語境下思考創傷、詮釋創傷、書寫創傷,更是進一步跨越創傷綜合創傷。
2 克萊爾·梅蘇德《皇帝的孩子》中的美國社會心理創傷
《皇帝的孩子》這部小說始于2001年3月,完成于11月,期間經歷了“9·11”事件。時代大事件賦予了小說更多的內涵,使小說人物產生進一步的變化,也為讀者提供了更廣闊的思考空間。《皇帝的孩子》圍繞著三個中心人物——丹尼爾·明克夫、馬麗娜·思韋特、朱利葉斯·克拉克展開故事。他們十年前是布朗大學的同學,九十年代相會于紐約。故事開始時,他們已屆而立之年,但在生活、愛情以及工作上都沒有步入正軌。丹尼爾是電視紀錄片制片人,她在工作上并沒有獲得理想的成就;在戀愛上,她也沒有明確的追逐對象。在澳大利亞采訪期間與盧多維克·思韋特產生戀情,但是9·11事件中斷了她們的關系。馬麗娜則年輕漂亮,條件優越。因借著父親的名聲,想當一名作家,與人簽約寫一本關于兒童服裝的書,而幾年過去,書也沒能寫出來,直到三十多歲仍然住在父母家里。她不想做平庸之輩,但在婚姻上卻十分不順,男朋友艾爾拋棄了她,后來,她嫁給西利。但因為9·11事件,西利想要創辦雜志的夢想成為了泡影,西利獨自去英國另謀出路,馬麗娜的生活陷入一片黑暗。朱利葉斯出生在密歇根州的一個小鎮,從布朗大學畢業后不久來到紐約,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經常為雜志寫書評,也曾因經濟拮據做過臨時工。朱利葉斯從小就是同性戀,打工期間與老板戴維墜入愛河,后因朝秦暮楚而被戴維毆打。戀愛不成,又耽誤了寫作。作者在小說中的幾個人物間轉換敘事視角,通過心理描寫和內心獨白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塑造了非傳統意義上的正面或反面形象。這些人物失去了天真和自我,失去了方向和目的,生活中充滿了焦慮和苦惱,而9·11事件又加重了他們的心理創傷。9·11事件使他們每個人物的生活軌跡都發生了變化,他們無法用語言傳遞經歷過創傷的內心感受,創傷使他們處于麻木的狀態,無法感知生命的意義。他們雖然沒有親歷9·11事件,但是這一事件帶給他們的震驚和沖擊卻是巨大無比的,他們每個人的內心都間接地受到創傷。
3 科倫·麥凱恩《轉吧,這偉大的世界》中的越戰創傷
《轉吧,這偉大的世界》20世紀70年代初的越戰為小說的背景。越戰撕裂了眾多的家庭,制造了深重的創傷。在作品中作者講述了越戰后人們如何嘗試相互溝通,那些破碎的心靈以不同方式走向愈合的過程。創傷可能是由一連串生活經歷、一種持續的狀態造成的,也可能是由某一個突發的個別事件所引起的[4]。對于參加戰爭的士兵的母親而言,她們所遭受的創傷始于孩子上戰場的那一刻。文中的母親克萊爾在聽聞兒子陣亡的消息時,她微微笑了,她對報信的人笑了,因為“臉上也擺不出來什么別的表情來”[5],之后臉因為笑太久而發燙了。這完全是不知所措的震驚和麻木。克萊爾在兒子去世兩年多的時間后,在與其他的越戰士兵的母親講述自己當時的經歷時,才漸漸將創傷講述出來。她一直在腦中思索,自己當初在送別兒子時為什么沒有對他說出自己想說的話,那就是“對戰爭,認識一點就夠了——不要去參加”[5]。這場戰爭對于克萊爾而言是永久的創傷,想要治愈很難。朱迪斯·赫曼認為創傷康復的主要階段應包括營造安全感、重構創傷敘事,恢復幸存者與所在社區的聯系[6]。克萊爾用電為自己營造了一個充滿安全感的與兒子溝通的環境,在這里她可以通過電冰箱感受兒子的存在。她看到任何的電子產品都會想起這是與兒子進行溝通的媒介,而如果停電,她則會非常恐慌,感覺和兒子失去了聯絡。創傷患者在自己熟悉的事物中宣泄心中的恐懼、焦慮和抑郁等復雜的消極情緒,從而試圖調整自我,雖然克萊爾自己營造了安全的氛圍,但她的創傷難以愈合。兒子戰死沙場和丈夫的緘默讓克萊爾無所依歸、孤獨無助,創傷治療受阻。直到生命的終結,她也沒有緩解自己心中的傷痛。雖然小說未直接提及9·11事件,卻講到了越戰和越戰后的另外兩場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戰爭帶來的創傷依然在蔓延,使克萊爾至死都沒能擺脫戰爭帶來的死亡陰影,并使越戰創傷在代際間漫延和傳承了下去。
4 伊恩·麥克尤恩《星期六》中的泛創傷社會圖景
《星期六》以2003年2月英國爆發的伊拉克反戰示威游行為背景,通過神經外科醫生亨利一天的經歷描寫了9·11事件發生后的倫敦的生活。在泛創傷社會圖景的建構中,反諷敘事成為主要的類比手法,它在創傷罹受者的潛意識中將歷史記憶與現時情景進行比照。在小說中,9·11事件的陰影就如同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在主人公亨利的意識中不停出現,成為敘事的一個焦點,展現了創傷的起源。
麥克尤恩對創傷的描寫并不局限于對危難時刻的精準臨摹,而是更多地關注受傷害者的后創傷認知和記憶。正如亨利有了對9·11恐怖襲擊的遺留創傷,因此當他目睹一架飛機失事時,誤認為這又是一起恐怖襲擊事件,并不斷將其與之前的情景相比較。這一點深切地描繪出他對于9·11這一歷史遺留創傷的恐懼。心理學家克里斯塔爾(Henry Kristal)指出,人們在面對措手不及的危機時往往表現出怯懦,身為醫生的亨利有救死扶傷的使命,覺得“自己應該做一點事情”以將傷亡減到最低,然而他又遲疑著是否要打電話求助——“發動機的噪音已逐漸退去。貨艙被卸下來了嗎?他思索著,他也希望它能夠這樣。算是一種祈禱嗎?他找不到任何人施以援手。即便是降落燈的光芒一點點散去,他依舊看著西方的天空,因為害怕出現爆炸的場景而無法將目光移至別處。”[7]此處正反映出后9·11之后創傷泛化對于個體的影響。在過去的災難面前,亨利是創傷的目擊者,同時也是無能為力的幸存者。當下的情景中,這種雙重角色再度合體,受害者的矛盾心境也在反諷敘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一方面亨利擔心自己夸大其詞引起社會恐慌;另一方面又擔心這就是一場真實的災難,唯恐自己會因為救助不力而再度感到愧悔。
除了歷史創傷事件對創傷受難者心理空間的介入,泛創傷化的社會圖景還表現在小說對于人物關系的反諷上。亨利與家人的關系疏遠,與陌生人的沖突交鋒都投射出后9·11社會的政治影響,個體與他者的心理距離也成為麥氏倫理批判的一個核心所在。麥克尤恩用悲觀的筆調描繪了宏大的創傷性社會圖景,同時也對現代社會中的人物進行了剖析。當亨利在大街上遇到巴克斯特時,他對后者的外表描述充滿了鄙夷,覺得他的寶馬汽車都充斥著“犯罪和毒品交易的氣息”[7]。在一段段的客觀描述中,作者傳神地刻畫了主人公的心理歷程。作者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與內視角的結合中描繪了9·11后的社會群像,彰顯了泛創傷性焦慮主導下的個體困惑,再現了麥克尤恩對于后創傷集體癥的全面把握。
5 結語
雖然創傷在人類生活中非常普遍,但作家們還是從自身的角度給予創傷足夠的關注;雖然創傷很難愈合,但人們還是會努力地為受傷的主體營造相對安全的環境。后9·11文學正是展現了文學對人性的透視,對社會熱點的關注。
[1]楊金才.9·11之后美國文學發生了什么[N].文藝報,2013-12-11.
[2]曾艷鈺.后9·11美國小說創傷敘事的功能及政治指向[J].當代外國文學,2014(2).
[3]薛玉鳳.美國文學的精神創傷學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4]Caruth,Cathy.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5.
[5]科倫·麥凱恩.轉吧,這偉大的世界[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3.
[6]Herman,Lewis.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Basic Books,1992.
[7]伊恩·麥克尤恩.星期六[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責任編輯:李增華
On the Humanism of Post 9/11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uma Theory
REN Bing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landscapes after 9/11 interact with individual and cultural imaginary to produce new cultural meanings and realities.Aims to analyze the various trauma and to explore the humanism in these novels.
Trauma;9/11 novels;Humanism
I02
A
1674-6341(2017)05-0147-03
10.3969/j.issn.1674-6341.2017.05.050
2017-07-04
黑龍江省經濟社會發展重點研究課題(外語學科專項)“美國后9·11文學的倫理闡釋”(WY2015029-B)的研究成果;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16WWD04)的階段性成果;同時獲得“外教社全國高校外語教學科研項目”(2015HL0007B)的資助。
任冰(1981—),女,黑龍江哈爾濱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和教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