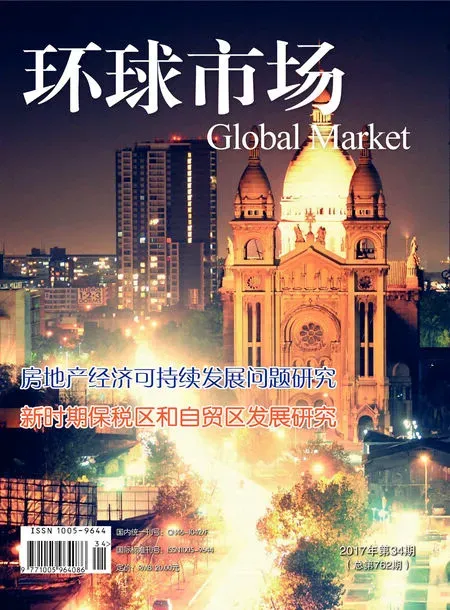從《第二性》看波伏娃的主要女性主義理論
席 宇
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在傳統的男性社會中,他們所推崇的女性是溫柔、純潔、深居簡出、持家有術的賢妻良母型,直到女權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她們將新興的女性推上歷史的舞臺,“新女性有較強的自我意識,和相對獨立的個性,受過一定的教育,不為傳統的家庭觀念所累,活躍在慣常屬于男性領地的公共領域。”波伏娃作為西方當代女性主義的先驅,她在書中宣揚了自己的平等理想,她認為要想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就必須要先正視男女之間的差異,同時她深刻的揭示出了父權制是造成女性受歧視的文化根源。
波伏娃的女性主義理論,主要集中系統地體現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本文試圖通過女人是什么、女性的處境和女性的出路三方面來探討波伏娃的女性主義理論。
一、女人是什么
波伏娃用“擁有一個女性氣質的人”來回答“女人是什么”這個問題,這樣的回答是為了延續那個最關鍵的否認,以便其參與到那個最漫長的壓迫中,即持續了幾代的女性壓迫。
波伏娃在書中批評了關于女性氣質的僵化教條,認為女性氣質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社會和社會制度還有社會的習俗讓女性形成的,同時讓人們清楚的明白當今社會仍然是一個男權的社會,認清那行所謂的“女性氣質”產生的根源。
波伏娃波伏娃一開始就為我們介紹了她對所謂女性氣質的一種反諷,即“它似乎處處瀕于崩潰的邊緣,像紙一樣薄卻又堅硬如鐵。”這個諷刺性的概念在波伏娃看來其實是被它自身的脆弱性給禁錮了,這種所謂的女性氣質影響了整個歷史,幾代人甚至是幾個世界的人們,都幾乎認為這個概念是真實的、是固定的,同時也是人類同自然界之間的聯系。她提出了女性氣質實際上是一種錯誤的本質。
二、女性的處境
在波伏娃看來,女性的那些種種特征既不是由于荷爾蒙所決定的,也不是因為女性的頭腦所決定的,而是被她們的處境所塑造出來的。
波伏娃認為現下女性的處境就是對于女性的壓迫,而這種壓迫多數來源于自欺,這種自欺既屬于女人也屬于男人,但是波伏娃并沒有指責這種自欺,她認為男人和女人都有權利保持這種自欺,如果他們傾向于選擇自欺,傾向于選擇一種對于總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經歷的否認,那么我們就必須試著去理解他們的世界是怎樣鼓勵或強迫他們對自己這么不誠實的。波伏娃在《第二性》的正文部分多用了這種方式來分析自欺的根源,那就是對于女性互惠權利的半清醒的否認,這種否認實際上扭曲了整個人類的歷史。
波伏娃指出,由于自欺,使得一些女性可以得到她是世界中心或至少是她那個小圈子中的核心的感覺,因為這時的她們把自己想象成為大家的焦點,所有人的目光都會聚集到她們的身上。但值得同情的是,在這樣的自我欺騙中,她們是分裂的,她們把自己分成了男性主體和女性客體,她們用男人的目光來打量自己,同時也被這種目光所打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便是她們在男權社會中的處境,她們為了能夠更好的生存下去,不得不進行這種訓練。
關于自欺的觀點中,我們看到了波伏娃所采用方式的核心就是“壓迫不是天然的,它是一些情況的結果,這些情況是可以改變的,”“真相引出了自由—否認真相是進行壓迫的前提,”“自欺是壓迫的關鍵—因為自欺是種忽視解放真相這一模糊概念的能力,但真誠卻總是可能的。”
三、女性的出路
在波伏娃看來,自由就意味著給予自己塑造未來的機會,波伏娃的理論范圍以自由為基礎,她所關心的是作為整體的女性自由度,個體的人首先應該要有責任為其自身的存在提供意義,由此人們才可以真正的得到“人”的意義上的自由。不過,波伏娃清醒的認識到,對于女性來說,選擇自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里有很多的限制讓她們不得不視而不見。女性和男性不同的是,社會并沒有賦予她們與男性相同的自由度,她們所謂的那些自由是受限制的。波伏娃在《第二性》最后中,發表了她自己對自由的看法,她認為那是情感壓迫的漫長歷史的另一方面,也是賦予愛新的含義的一種解放。
波伏娃認為自由和自我實現是不可分離的,“獨立的女人”會變得“多產”而且“積極”,她抓住了她自己的超越性,這超越曾長期被男性制度和神話否定。她認為自由的女性定義自己的目的,并且同時獲得經濟獨立的政治權力。還有就是她的重要性就在于她在分析壓迫時提出了女性自由的本質問題。
在現代社會中,女性已經擁有了與男性一樣的受教育的權利,并且因此在經濟和政治活動中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了家門,她們像男性一樣,爭取在社會活動中博得一席之位。然而,當今社會的女性還不能完全的實現這種角色的轉換,她們很容易為了尋找歸宿和孩子而放棄她們自己對事業的追求。這也導致了她們無法成為真正自由的人。現在的女性其實面臨了重要的選擇,那就是自愿的將自身處于“第二性”,還是追求真正的自由實現兩性的平等。然而,現在的女性往往會選擇后者,所以,真正的兩性平等也是不能夠瞬間完成的。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西蒙·波娃回憶錄.譚健、溫子建、陳欣章等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名士風流[M].許鈞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3][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美麗的形象[M].范榮譯.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人都是要死的[M].馬振騁譯.譯林出版社,1997.
[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女賓[M].周以光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
[6][法]西蒙娜·德·波伏娃.他人的血[M].葛雷、齊彥芬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