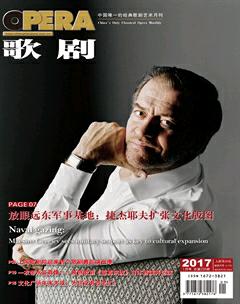把巴洛克音樂帶到中國生根發芽
2016年11月27日晚,由假聲男高音兼豎笛與短雙頸琉特琴演奏家高孟麟(Menglin Gao)、維奧爾琴與巴洛克大提琴演奏家埃里克·廷克赫斯(Eric Tinkerhess)、巴洛克小提琴演奏家雷納多·帕提諾(Reynaldo Patino)、管風琴與羽管鍵琴演奏家珍妮弗·鮑爾(Jennifer Bower)和現代與巴洛克小提琴演奏家姜珊(shan Jiang)組成的上海古樂團(shanghaiCamerata),滿懷著“把巴洛克音樂帶到中國生根發芽”的雄心與愿望,從美國漂洋過海而來,假座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演奏廳,舉辦了一場滬上難得一遇的“1690巴洛克室內樂演奏會”。音樂會后,筆者與參加演出的目前正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攻讀早期聲樂博士學位的高孟麟先生進行了一次關于巴洛克聲樂作品的對話。
匡國清(以下簡稱匡):在國內,對古典和浪漫時期的音樂始終擁有不少熱衷的樂迷和聽眾,而對巴洛克音樂的熟知和理解卻一直大大落后于歐美西方世界。大多數早期音樂的古樂愛好者只能局限在家中聆聽唱片,很少有機會親近表演的現場。請談一談上海古樂團策劃此次“1690巴洛克室內樂演奏會”的初衷與設想。
高孟麟(以下簡稱高):新成立的上海古樂團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的首演曲目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們把重點放在巴洛克中早期的音樂,在時間上跨越了100年左右,在地理上覆蓋了意、英、法、德、西、奧六國。大多數作品和作曲家未必為上海的聽眾熟知,但是無一不非常有代表性。器樂作品中從巴洛克時代小提琴技術發展的先驅海因里希·比貝爾(HeinrichI.Evon Biber)到法國宮廷音樂的馬蘭·馬萊(Marin Marais)都有觸及,聲樂作品則挑選了亨利·珀塞爾(Henry Purcell)與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Dieterich Buxtehude)的三首杰作。
匡:由于西方教會禁止婦女在教堂和舞臺上歌唱,假聲歌手(Falsettist)與閹人歌手(Castrato)在西方音樂史上曾經出現過一段很長的輝煌時期。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由于格魯克歌劇改革和男聲“關閉”唱法的突飛猛進,加上不人道的閹割行為遭到人們的反對,閹人歌手和假聲歌手開始衰落并退出了歷史舞臺。隨著發端于上世紀50年代的古樂復興運動,英國具有“假聲男高音教父”之稱的阿爾弗雷德·戴勒(Alfred Deller)復興了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的琉特琴歌曲(Lute Song)以及幾百年間被人遺忘的作品。從此,淡出人們視野已久的假聲男高音(Countertenor),又稱為高男高音,取代閹人歌手并逐步發展到了一個造詣極高的水平。不久,上海巴洛克樂迷將有幸現場聆聽兩位當代假聲男高音——英國青年才俊蒂姆·梅德(TimMead)和德國大師級的安德烈亞斯·肖爾(Andreas Scholl),演唱亨利·珀塞爾根據莎士比亞戲劇《仲夏夜之夢》改編而譜曲的半歌劇《仙后》。
高:這次演唱的曲目中有兩首來自英國作曲家亨利·珀塞爾。珀塞爾和莫扎特一樣是少年天才,只是當時音樂并沒有像莫扎特時代那樣成為消費品,所以珀塞爾在現代音樂界名氣不那么大。可以說珀塞爾是整個英國巴洛克聲樂作品當之無愧的翹楚。他在詞和曲的搭配上無懈可擊,而且充分運用了繪詞法(Word Painting)來凸顯重要的語句和情感。對于假聲男高音來說,珀塞爾也是一個特別的作曲家。有史料表明珀塞爾本人就是一名假聲男高音——英國聲樂傳統中那種音域偏低的假聲男高音,而不是意大利引進的那種閹人歌手。對于現代的假聲男高音來說,珀塞爾為這個聲部譜寫的音樂非常舒適,也充分運用了這種聲音的表達力。許多現代假聲男高音追逐為閹伶譜寫的歌劇角色,在我看來,這對于讓女中音反串男角是進了一步,但是假聲男高音畢竟不是閹伶,并沒有那種男童般毫不費力的高音。反觀珀塞爾的假聲男高音是為男人的假聲量身定做,并且在許多地方過渡到真聲中。
匡:201 0年安德烈亞斯·肖爾與拜占庭學院合奏團合作過一張以珀塞爾作品《噢,孤獨》(O Solitude)命名的專輯,并獲得了2012年“BBC音樂雜志獎”。珀塞爾在歌曲《噢,孤獨》中贊嘆“噢,孤獨,我最令人滿意的選擇!我多么喜愛孤獨!”:對于國內鐘情于古典和浪漫時期音樂的大多數樂迷和聽眾來說,巴洛克時期的音樂畢竟年代久遠,不免有些陌生以至于不甚了解。特別想傾聽您講述在音樂會上演唱的幾首巴洛克聲樂作品的內容涵意與心得體會。
高:首先,《它就是自然之聲》('Tis Nature's Voice)來自珀塞爾的一部對音樂女神的禮贊《歡迎你,光明的澤濟莉亞!》(Hail,Bright Cecilia!)。這部作品中每個章節都贊美了音樂的各個元素,從具體的管風琴、小提琴到抽象的聲音、靈魂等。《它就是自然之聲》描述了音樂——自然的聲音如何跨越語言和種族讓天下眾生都能被觸動。這首曲子的風格明顯是17世紀早期意大利的單聲歌曲(Monody)風格——這種風格當時在意大利本土已經不再流行,但是珀塞爾卻在英國把它抬上一個新的高度。曲子的和聲復雜程度大大超過了17世紀初意大利的水平,加上珀塞爾對于通奏低音譜寫比較隨意的態度,對于伴奏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歌曲極大地利用了早期意大利風格較自由的節奏,描繪出各種音樂的方方面面,并頻繁地轉換情感。
《孤獨之歌》(O Solitude)的歌詞來自法文,由一位英國女文學家凱瑟琳·菲利普斯(Katherine Philips)譯成英文。這首歌曲建立在四小節的固定低音基礎上,并且沒有變奏。這首歌曲表達了對于離世隱居的向往,通篇泛著一種苦澀的滿足。珀塞爾在這首歌曲中把英語語言的表達力發揮到極致,在四小節不停重復的簡單和弦中構建了他最有代表性的杰作之一。
迪特里希·布克斯特胡德是北德巴洛克風格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的作品對巴赫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巴赫早年曾經步行數百公里只身去呂貝克向布克斯特胡德學習,并且到達之后決定曠工數月,留在呂貝克學習。這導致后來巴赫返回之后立即被暴怒的上司投入監獄,但看來這很值得——巴赫后來的作品中常會有前輩的影子。他的《康塔塔》(JubilateDomino,BuxWV 64)為低音維奧爾琴、假聲男高音及通奏低音而作。在這首大意為歌唱和器樂齊奏歌頌上帝的宗教康塔塔中,人聲和維奧爾琴都模仿著小號的自然泛音階。這首曲子的音域也是為假聲男高音量身定做的,高音低音都不出假聲的范圍。維奧爾琴在這個康塔塔中的作用不是伴奏而是獨奏,有一些對技巧要求非常高的段落,而且幾乎用到了低音維奧爾琴能演奏的最高音。
匡:我們知道,巴洛克音樂時期通常被認為是數字低音時代。數字低音(Figured Bass)是用一系列數字和記號來表示不是處于根音位置的和弦的一種音樂速記法,又稱通奏低音(BassoContinuo)。作為通奏低音的伴奏聲部為一系列構建在低音線條音符上的和弦,為歌唱的旋律提供和聲支持。演奏時,最令人期盼的是其中占據首席地位的羽管鍵琴演奏者作類似于爵士樂那樣的各種即興演奏。請您談談此次音樂會中各位演奏家是如何在巴洛克樂器的伴奏中演奏通奏低音的。
高:本次演出的通奏低音演奏由三位低音樂器演奏者共同完成。通奏低音作為一種伴奏的創作和演奏方式貫穿了整個巴洛克時期。巴洛克音樂經過150年的發展,晚期時的風格已經和17世紀初期大相徑庭,但是通奏低音的運用卻一直延續到莫扎特的時代。通奏低音也稱作數字低音,因為它的譜寫方法是一條低音線上面加上了表達和弦的數字。經過訓練的伴奏樂器演奏者可以從數字中得知所有的和弦變化,并按照曲子的速度、樂器編制、表達的情感等因素即興演奏出多聲部的伴奏。由此可知,當時的音樂家達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因為數字低音的彈奏離不開對和聲的理解,尤其對鍵盤樂器演奏者來說,必須有遵循對位法規則即興創作多聲部和聲的能力。通奏低音樂器有很多種,可以是羽管鍵琴、管風琴、維奧爾琴、大提琴、各種形制的琉特琴和吉他、豎琴等,而且可以有多種組合。本次音樂會我們決定附上部分樂譜,讓觀眾更加直觀地認識通奏低音。
匡:古樂復興運動提倡經過嚴謹考證研究、使用古樂器或其復制品進行演奏的本真演奏(Authentic Performance)。請問,在演奏巴洛克音樂時,應該如何把握本真演奏與符合當代人審美情趣和欣賞口味兩者之間的關系?
高:從上世紀60年代到現在,古樂運動逐漸從刻板的形象中走出來。在我最初接觸并投身于古樂事業時,曾經也是個非黑即白的教條主義者,認為本真主義大于一切,一定要用原版的樂器、原版的樂譜、原版的調律,不接受任何程度上的妥協。然而音樂的最終目的畢竟是感染人類的心靈而非考古。就本次演出來說,因為條件限制,我們使用的樂器不但和有些曲目的創作日期相差百年,甚至還用了一臺電子小管風琴,這對于一些極端的本真主義者來說可能難以接受。然而我們在演奏技法和音樂處理上最大程度地做到了原汁原味,參考了與曲目年代和國家風格最為相關的多部演奏法書籍,力求還原作曲家心中的聲音。
匡:室內樂是巴洛克音樂時期最為流行的一種形式。為了帶給中國聽眾一些不一樣的聲音,使得音樂會變得意義非凡,我們注意到,此次“1690巴洛克室內樂演奏會”除了在早期樂器上演奏巴洛克中早期音樂外,還保持了巴洛克音樂時期特有的一些演奏方法。如小提琴,除了使用古琴、古弓和羊腸弦外,演奏時,兩位巴洛克小提琴演奏家的右手采用了不同于現代的、力度偏小而能較好地發揮歌唱性的意大利式握弓法,左手只是有限地使用小幅度的揉弦,以賦予巴洛克音樂一種極為樸素的性質。
高:巴洛克音樂起始于一個擺脫了中世紀的宗教壓迫不久、人文主義開始萌芽的時代。佛羅倫薩樂派(FlorentineCamerata)在16世紀末宣告新音樂的到來,在今天的音樂學家看來這正式拉開了巴洛克的序幕;而巴洛克風格出現的初衷則是為了更好地表達人類的各種情感——某種程度上來說,巴洛克音樂是徹徹底底的世俗音樂、人文音樂。在我看來,巴洛克音樂雖然在中國仍是小眾,但淳樸的表現方式和相對古典和浪漫時期不那么復雜的和聲實在是一種雅俗共賞的藝術形式,或許在主流的古典樂迷之外都能有一批聽眾。上海古樂團的創建就是為了能把貌似高不可攀的音樂帶給大眾,讓歐洲啟蒙時代的音樂可以在中國生根發芽。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會為大家帶來來自17世紀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