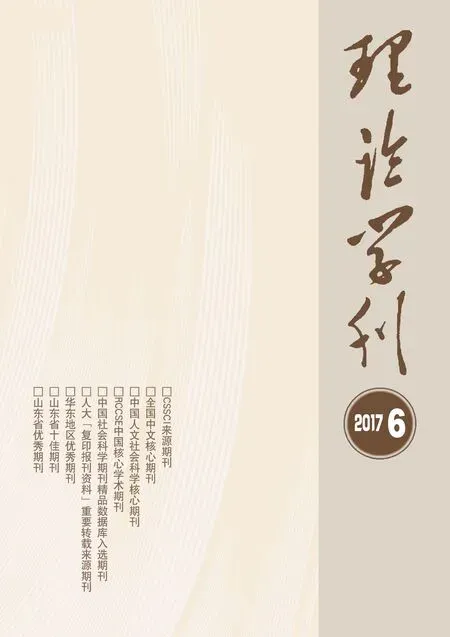習近平德法并舉思想探析
呂本修
(山東省倫理學與精神文明建設研究基地, 山東 濟南 250013)
習近平德法并舉思想探析
呂本修
(山東省倫理學與精神文明建設研究基地, 山東 濟南 250013)
習近平總書記對于德治與法治的關系進行了多次論述,其基本思路是強調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德法并舉。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主張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習近平總書記德法并舉思想是對傳統社會這一思想的繼承與超越;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德法并舉思想也是道德與法律關系原理的靈活運用。
習近平;德治;法治
2017 年5 月3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養 勵志勤學刻苦磨煉促進青年成長進步》,《人民日報》2017年5月4日。2016 年12 月9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法律是準繩,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循 ;道德是基石,任何時候都不可忽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依法執政基本方式落實好,把法治中國建設好,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1日。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不但強調法治,而且強調德治,認為法治與德治相統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方略。
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深入挖掘中華優秀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19日。2014年10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習近平總書記德法并舉思想正是對中國傳統“禮法合治、德主刑輔”思想的繼承與超越。
中國傳統文化中,“德”字的出現及德的觀念的產生具有重要意義,它意味著宗教社會向世俗社會、神靈世界向倫理世界的轉化。“德”字在商代已經存在,但是德的觀念在當時并不是重要的價值觀念,“至少從周初開始,德在古代的思想世界中就開始占據核心的地位。從《詩》《書》可見,周人把德視為最重要的和人相關的品質,同時也是贏得天之眷顧的依據”*王博:《中國儒學史·先秦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比如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商朝因天命而治,西周則因天命而滅之,如果是一個天命的話,為什么要西周取而代商呢?其實天命只有一個,但“命”即命令的內容是可以變化的,正所謂“惟命不常”、“天命靡常”,問題的關鍵在于天命變化的依據是什么?周公對此作出了新的解釋:天命變化的依據在于道德。商紂王自己無德,這本身就是逆天而行,就是有違天命,所以天帝就命令周文王取而代之,西周代商就自然是順應天命而為之。這不僅為西周的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是對西周統治者自身的告誡、教育與敬告:以德配天,天命惟常。可見,道德是天命變化的依據,是無德的統治者失去權力的依據,也是有德的統治者獲取權力的依據。此時,雖然人們仍然強調天命,但是人類在天命面前不再是完全被動的、消極的存在,而是積極的、主動的,人們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通過成己之德在世俗社會中實現幸福的生活,因為人們相信天帝神對于人類的努力與德性會給予認可、垂青和恩賜。因此,幸福生活的根源不再完全是天命,而在于自己的德性。這體現著西周時期道德已經被抬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的德治思想得到了發展與完善。《論語·八佾》記載:“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據《論語·述而》,孔子還曾感嘆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前者之周,通常解釋為周禮,體現著孔子畢生追求的社會理想;后者之周公,正是制禮之人,體現著孔子對周公的尊敬與仰慕,體現著孔子追求的人格理想。因此,孔子繼承了周公崇德的思想,強調德治。他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政者,正也”*《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倡導“以德服人”。他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可見,孟子并不主張利用嚴刑峻法治理社會,而是倡導“省刑罰”,教育百姓向善擇善從善,并提出“制民之產”、“取于民有制”等仁政思想。先秦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荀子,同樣主張以德治民、以德治國,他提出了“三威”之說:“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義則修,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荀子·強國》。
秦朝二世而亡,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德治思想最終確立。據班固在《漢書》中的記載,董仲舒在給漢武帝的對策中曾說:“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癢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人。’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在這一策論中,明確主張德治教化。漢初承襲秦朝法治,結果卻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社會問題不但不能解決,而且如抱薪救火,愈加嚴重,因此,董仲舒主張必須由法治轉向德治,因為“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他明確提出用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教化百姓,德治天下。
正是由于儒家重視道德的價值,因而在處理德治與法治的關系時,重德治而輕法治,或者說,德治與法治相比較,德治具有價值選擇的優先性。孔子曾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前文董促舒也說“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孟子》里也記載了“桃應之問”的故事。孟子的學生桃應問孟子說:“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然則舜如之何”?孟子說:“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徙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然,樂而忘天下”*《孟子·盡心上》。。可見,在孟子看來,如果舜的父親殺了人,那么舜應當放棄天下,而偷偷地背著他父親跑到海邊藏起來。類似的故事《呂氏春秋》中也有記載:“荊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為政,道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返,立于廷曰:‘殺人者,仆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于是乎伏斧锧,請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锧,刎頭乎王廷。王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為人也,可謂忠且孝矣。”*《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如果從法治的角度來看,這一故事中,君主荊昭王、大臣石渚都是徇私枉法者。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對于法律事實的認識與理解,不論是石渚之父殺人,還是石渚私放其父,都是違法行為,但是石渚以及時人認為,不放其父,是不孝;私放其父,是不忠。因此,石渚私放其父是謂孝,舍命是謂忠,時人稱之為人臣者忠且孝矣。這里,從形式上看,是忠孝之間的沖突,之所以如此,而在于時人是從道德的角度進行了考量,或者說,時人根本沒有把這件事情當成法律事件,而是當成道德事件來考量,這充分說明,在當時人們心目中,道德對法律有壓倒性優勢。從實質上看,這件事情體現著道德與法律的沖突。私放其父,這是道德要求;不放其父,這是法律要求。兩者同時對同一個人提出要求,行為人不可能兩全,所以形成道德要求與法律要求的沖突,當事人只有選擇其一,最終的結果說明:道德要求占了上風,它被優先選擇。總之,不論怎么說,在傳統儒家看來,道德比法律更可靠,德治也比法治更有價值。
在儒家文化的視域下,德治比法治更重要,更具有價值選擇的優先性,但是儒家并沒有否定法治的作用,因為離開了法治的強制力量,德治難以實施,即使實施也難以取得實效,德治必須依靠法治的力量來實現自身。中國歷史上,漢代以“以孝治天下”而著稱,當時“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白虎通·論〈孝經〉〈論語〉》。,“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后漢書·荀韓鐘陳列傳》。。為維護孝道,漢宣帝親自下詔從法律上肯定了父子相隱、親親相隱:“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漢書·宣帝紀》。。利用法律制度維護孝德行為,對于孝德思想的落實起了重要推動作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在傳統社會,德治與法治總體上體現為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的關系。
二
2001年1月,江澤民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講話中提出:“要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積極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深入持久地開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頁。2014 年 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強調“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道德,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也如前文所述,后來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重申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的法德并舉的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法德并舉思想不僅有著傳統文化資源的支撐,而且具有法律與道德關系原理的理論基礎。
法律和道德是社會規范的兩種基本形式,也是社會治理的兩種基本方式。通常我們認為,法律是由社會認可、國家確認、立法機關制定的行為規則,并由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保證實施的,以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的一種特殊行為規范或社會規范。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具有權威性、程序性、強制性、可訴性和統一性特點。而道德是由一定的經濟關系決定的特殊意識形態,是以善惡為評價標準,依靠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風俗習慣來維持的,調節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社會規范的總和。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相比,具有應然性、自律性、弱約束性以及相對性特征。因此,法律與道德不論作為社會規范,還是社會治理的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點與功能,相互之間存在著諸多的不同,因而不能相互取代。兩者之間的區別至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表現形式不同
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強制性規范,它具有明確、具體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其制定、公布、修改和廢除等,都要由國家權力機關按照特定的程序來進行。而道德這一社會規范,其表現形式具有多樣性。從歷史角度來看,在人類漫長的道德生活中,曾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僅僅從純形式上來概括,我們可以把這些數不清的道德規范的形式概括為圖騰、禁忌、風俗、禮儀、準則、箴言、義務及責任種種*羅國杰:《倫理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頁。;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道德規范的鮮活具體的方式,比如,準則守則、村規鄉約、家風家訓、校訓校風、標語口號、座右銘等等,可以說,道德規范在我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相對于法律規范,道德規范表現形式更具有多樣性與靈活性。
2.內容結構不同
第一,法律規范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范圍內,其內容具有確定性、普遍性、統一性與一元性。在一個政治共同體內部,不論宗教信仰、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等如何不同,法律規范是唯一的,其要求也是一樣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具有對等性與一致性,任何人都沒有特權,這也是法律公正性與平等性的體現。而道德規范是社會意志的體現,它是具有層次性、多樣性的社會規范體系。道德規范的層次性,首先體現在規范自身所具有的層次性——比如我國社會主義道德規范體系就是由道德核心、道德原則、基本道德要求與規范以及三個特殊領域中的道德規范等組成的規范體系;其次體現在道德境界的層次性——如大公無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顧、先私后公的不同境界;最后還體現在道德要求的層次性——對于不同職業、不同地位的人道德要求應當有所區別,比如官民之間,對于領導干部應當有更高的道德要求。道德規范的多樣性體現著道德的相對性,在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內部,宗教、文化的差異,甚至是同一宗教文化背景下,社會地位的差異也會導致道德規范的不同。因此,道德規范相對于法律規范的一元性而言,具有多樣性與多元性。第二,法律規范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并且一般要求權利義務的對等性,意即只要享有權利,則必須盡義務;只要盡了義務,也自然享受相應的權利;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規范則不同,道德通常只強調道德主體的義務,并不要求對等的權利。當然,目前倫理學理論中,也開始講道德權利,但是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不同,通常認為道德權利與道德義務不具有對等性,甚至更多的時候,道德義務本身被當成是道德權利來理解。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人們有救人的義務,同時這也是每一個人的道德權利,但是救人者并沒有向被救者索要報酬的權利,反之,如果有人向被救者索要報酬,則往往被視為不道德行為。第三,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在結構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法律規范一般具有比較嚴格的邏輯結構,通常由條件假設、行為模式、法律后果三部分構成,因而法律規范的內容是具體、清晰、確定的,具有非常強的可操作性;而道德規范缺乏這種比較嚴格的邏輯結構,不論是道德原則還是道德規范,內容上相對比較抽象、模糊、概括,通常表述為“應該如何”,既沒有具體的行動方案,也沒有“如果不這樣會有什么后果”,因此,許多道德規范缺乏可操作性,即使是人們熟知某一道德規范,當人們處于具體的道德情境時,這一道德規范未必能夠指導人們作出具體的行為選擇。
3.調整范圍不同
第一,從深度上看,道德規范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動機與效果的統一是道德評價的根據,甚至當動機與效果都比較確定的情況下,道德評價會更加重視動機,因此,道德不僅關注行為及行為的后果,而且關注人的內心世界以及心靈的秩序,道德規范也更加追求通過改造人的內心世界從而實現美好生活的愿望,它要求人們從高尚的意圖出發,內心向善而擇善從善。法律規范調整的主要是人的行為。人的內心活動,包括動機、企圖、認識、思想等,在對行為進行法律判斷時,通常起一種輔助作用,比如定罪量刑時要考慮故意和過失的區別,侵權行為要以主觀故意為要件等。但是,即使是惡毒的卑劣的企圖或念頭,它如果不表露為外部行為,法律規范就不會干預,也不會制裁。馬克思曾說:“對于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我的行為就是法律在處置我時所應依據的唯一的東西,因為我的行為就是我為之要求生存權利、要求現實權利的唯一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頁。第二,從廣度上看,道德規范對社會生活的滲透性比法律規范要廣泛得多。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道德就是人的本質屬性的體現,是人作為人成為人的基本特征。從個體的人來說,不論人的外在行為,還是人的內在動機、目的、意識、思想等,都要受道德規范的調節;從社會領域來說,不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領域等,都無法擺脫道德規范的約束;從社會關系來說,不論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是人與自身之間的關系,也都受到道德的調節。因此,道德規范就像空氣一樣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角落。而法律規范調整的社會領域是相對確定的,它只是對社會生活中的基本關系和重大關系進行調整,從而維護社會的根本利益、總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因此,法律規范并沒有必要滲透于全部的社會生活空間。同時,法律規范還存在著一個有效性問題,也就是說并不是所有的領域法律調節都是有效的。有的學者認為,特定領域法律調節的有效性取決于兩個重要前提:其一,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能夠被合理配置和清晰界定;其二,確實存在著能被執行的后果模式。只有符合這兩個前提,被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才能夠被實質性地規則化,才有可能得到有效實施*應飛虎:《論法律與道德的功能協調》,《山西師大學報》2001年第3期。。
4.作用機制不同
第一,法律規范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只要人們違反法律,就會受到法律的懲罰,就要承擔違法的后果,因此,法律規范具有他律性;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的力量來維護,道德規范作用的發揮需要道德主體的認可與接受,因此,道德規范具有自律性。第二,法律由于以國家司法機關為依托,通常以強制性剝奪違法者的人身、自由、財產、生命等利益來實現其功能,其效果立竿見影,但是法律實施成本較高。而道德規范依靠社會輿論、內心信念發揮作用,當違反道德規范的人良心受到蒙蔽并且面對社會輿論無動于衷時,道德規范則會失去其應有作用,可見,其約束力是軟性的。道德規范雖然不能強制性剝奪人的外在利益,但是道德可以直擊人的精神世界,使人通過內心的情感體驗感悟到道德規范的作用,比如當人們完成一件善事時的自豪感與榮譽感以及當人們做一件惡事后的內疚與慚愧,將會是一股強烈的力量推動人們向善擇善從善,從而塑造人的美好的精神世界,進而推動現實的物質世界的完善。
三
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都屬于上層建筑,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作為兩種基本的社會治理與調控方式,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必然會同時發揮作用,不可偏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1.道德規范為法律規范提供道義基礎
第一,從法律規范的起源上來看,道德不僅為法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而且風俗習慣成為法律的重要的直接源頭。關于法律的起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曾作出系統闡述:國家和法不是從來就有的,依據史前史的研究所提供的具體實際材料,在人類歷史上確實有過不知國家和法為何物的社會。法是伴隨著階級的出現而產生, 它是氏族習俗的延續和變革,是私有制和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和法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即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因階級的完全消亡,國家和法也就失去存在的條件,將自行消亡。在此,恩格斯揭示了法律是一個歷史的產物,它不是從來就有的,人類歷史初期的漫長時期并不存在法律規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伴隨著階級的出現,才有了法律規范;同時,恩格斯預言,法律也不是永恒的,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伴隨著階級與國家的消亡,法律也必將消亡。恩格斯在此揭示了法律最初來源于“氏族習俗”。習俗是道德規范的重要形式,它已經不是個別的習慣或一時的禮儀,而是在很多代人的相互承襲中,天長日久而形成的一種具有社會意義的風氣及習慣。這種習俗在人類歷史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就像法律規范一樣,對原始部落內部人們的行為具有強烈的約束與規范作用, 后來這些習俗就逐漸演變為法律,就是習慣法。習慣法的出現標志著法律規范的產生,在習慣法的基礎上才會有今天的成文法。可見,法律規范最初就是來自于道德規范,沒有道德,法律無法產生,道德不僅是法律的基礎,而且是法律的源頭。
第二,從立法環節上來看,任何立法者的頭腦中都不是道德的空場,其中的道德觀念在立法過程中必然起著這樣那樣的作用,其結果也必然是把社會上人們認可的道德規范的要求上升為法律規范。美國著名法哲學家博登海默在《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方法》中說:“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當原則,在所有的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的約束力的增強,當然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原則而實現的。禁止殺人、強奸、搶劫和傷害人體,調整兩性關系,制止在合意契約的締結和履行過程中欺詐與失信等,都是將道德觀念轉化為法律規定的事例。”*[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方法》,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376頁。同時,他還說:“法律的制定者經常會受到社會道德中傳統的觀念或新觀念的影響。如前所述,這種道德中的最為基本的原則,大多已不可避免地被納入了法律體系之中。此外,我們還應當注意,在那些已成為法律一部分的道德原則與那些仍處于法律范圍之外的道德原則之間有一條不易確定的分界線。例如,時至今日,普通法還沒有承認人們具有幫助一個生命垂危的人的法律責任。因此,一個醫生沒有任何義務去理睬一個生命垂危但仍有可能有救的病人。任何人都不能要求某人扮演樂善好施者的角色去為一個流血不止的陌生人包扎傷口,或是在見到有人走向危險的機器時向他發出警告。也許在將來的某個時候,隨著其他國家的發展,幫助處于嚴重危難中的人的義務,會在某些適當的限制范圍內從普通的道德領域轉入強制性法律的領域。”*[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方法》,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376頁。這里,博登海默向我們闡明:任何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都不是任意地,都不能根據自己的喜好,而是根據“社會道德中傳統的觀念或新觀念”,把那些“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當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法律規范通常可以分為禁止性法律規范、授權性法律規范與命令性法律規范。殺人、放火、搶劫、偷盜、詐騙等行為之所以能夠成為禁止性法律規范,其根本原因不在法律本身,而在于這些行為是損害他人或社會利益的惡行,在道德上具有非正義性;命令性法律規范的根據在于那是人們必須履行的道德義務;授權性法律規范的根據在于那是道德上體現人性光輝、人道精神的鼓勵性行為或容許性行為。當然,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規范并不能覆蓋所有的道德規范,否則,道德規范則真的沒有存在的必要,我們的法律體系也是如此,比如體現孝德的“回家看看”已經入法,但是諸如“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等行為還沒有入法,只有依靠道德來調節,博登海默先生對此好象很樂觀,認為將來也會入法。
2.法律規范為道德實施提供支持保障
道德規范具有歷史性、民族性與應然性等特點,歷史性代表一種縱向的時間概念,意味著不同時期(時代)的人,道德規范就會有差異;民族性代表一種橫向的空間概念,意味著同一時代的不同(民族)的人道德規范也會有差異;應然性代表一種總體性概念,意味著道德規范具有理想性,它來自于現實同時又高于現實。從這三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道德沖突的復雜性:從歷史性角度來看,道德規范的樣式從時代性上可以分為傳統道德規范、現代道德規范、后現代道德規范,從階級性上可以分為封建主義道德規范、資本主義道德規范和社會主義道德規范,這些不同時期、不同階級屬性的道德規范之間必然存在諸多差異,其間便會形成道德沖突;從應然性角度來看,道德規范本身的要求與人們現實的道德價值觀念及行為狀況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沖突;上述道德規范的樣式及沖突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社會中同時存在,再加上社會個體成長過程及環境不同導致的差異與沖突,使現實的道德規范及沖突更加復雜。前文已述,道德規范主要通過社會輿論與內心信念發揮作用。社會輿論的實質是道德評價,尤其體現為社會道德評價,即別人對我、我對別人的評價,由于社會實現了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變,同時人們關注的焦點從他人轉向自我、從遙遠未來轉向現實,再加上“網絡社會”的快速發展,總之,社會道德評價主觀上存在人為操作、惡意為之的現象,客觀上存在著失真、片面的現象,現實社會中存在著社會輿論的失控現象,進而導致社會輿論失信于民,最終的結果就是社會輿論失效;內心信念是人們內心堅守的不可動搖的原則與準則,它能夠在人們處于具體的道德沖突情景中給人們指明選擇的方向。當人們的內心信念動搖時,或者是人們原有的正確的內心信念已經被錯誤的信念所代替,甚至是有的人根本沒有確立過正確的內心信念,不論什么情況 ,都會導致內心信念失靈的現象,即它不能給人們指明正確的道德選擇的方向。當外在的道德輿論失控與內在的道德信念失靈的情況下,道德規范的效果就會大大折扣,甚至導致失效的現象。現實生活中,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以及個人品德方面存在的大量問題,從實踐上反證了我們的道德建設確實存在著問題。
正確處理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的關系,充分發揮法律規范的作用,對于促進道德建設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第一,從積極方面來看,法律規范把社會主義道德原則、基本道德規范甚至是普遍獲得認可的具體規范都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以國家的強制力量為堅強后盾保證其核心地位以及順利實施。《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總綱》中重申了“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社會主義道德核心,也重申了“實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總綱》中不僅把“集體主義”這一社會主義道德原則寫入憲法,而且把公民基本道德規范“五愛”寫入了憲法:“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并且把公民應當遵守的具體的道德規范也寫入了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與法律,保守國家秘密,愛護公共財物,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這樣,社會主義道德就以法律條文的形式,以國家的強制力保障了其主體地位,這不是社會主義道德在消弱,恰恰相反,是道德借助于法律的強制力得到了強化。同時,一些實體法也把諸多道德規范的要求具體化,道德規范給人抽象、模糊的感覺,而法條法規則極其具體,這樣比較抽象模糊的道德要求通過法條法規轉變成具體的可操作的法律義務與責任。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第二條就寫了“男女平等”,作為一種道德規范,現實生活的具體境遇下可能我們感覺到無所適從,但是《婚姻法》中通過若干法條把“男女平等”的道德要求落到了實處。比如姓名權、子女姓名權、工作權、學習權、財產權等等把“男女平等”的要求轉化成了具體的法律責任。其二,從消極方面看,法律規范通過強制性懲罰手段保障了道德規范的實施與落實。道德規范是軟約束性規范,如果人們缺乏道德的覺醒,那么道德規范就會流于形式。法律規范則不然,對于惡劣的敗德形式,如殺人、放火、搶劫、詐騙等,法律規范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通過各種形式剝奪敗德者的人身、自由、財富甚至生命。像“誠實守信”的道德規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等都有關于不誠實守信行為的具體法律規定。這樣,法律規范一方面對違法敗德行為保持高壓態勢,另一方面也保障了道德規范的價值與威嚴。
習近平總書記德法并舉的思想,一方面是對中國社會發展過程的歷史經驗的繼承與超越,另一方面也是道德與法律關系原理的靈活運用。正確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德法并舉的思想,要注意克服兩種片面性錯誤觀點:其一是肯定道德否定法律的德治主義觀點;其二是肯定法律否定道德的法治主義觀點。兩種觀點都是片面的、錯誤的。尤其是今天,我們在強調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更要警惕法治主義觀點的滋生。德治與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離之則傷,齊之則美。
AnalysisofThoughtsof"GoverningtheCountryBothbyLawandMorality"byXiJinping
Lv Benxiu
(Shandong Research Base of Ethics and Building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Jinan Shandong, 250013)
General secretary Xi Jiping has discuss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ule of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several times. He basically stressed governing the country both by law and morality. On the one hand,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dvocates the governance both by the ritual and by the law and also support the idea of morality given priority over penalty, and Xi Jinping's thought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oth by law and morality is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is traditional idea. On the other hand, Xi Jinping's thougth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oth by law and morality is the flexible employ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law.
Xi Jinping; rule of morality; rule of law
本文系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創新工程項目“習近平道德建設思想研究”(項目編號:2017CXZ015)的階段性成果。
呂本修,男,山東省倫理學與精神文明建設研究基地學術骨干,中共山東省委黨校校刊部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倫理學與思想政治教育。
B822
A
1002-3909(2017)06-0027-08
[責任編輯:裴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