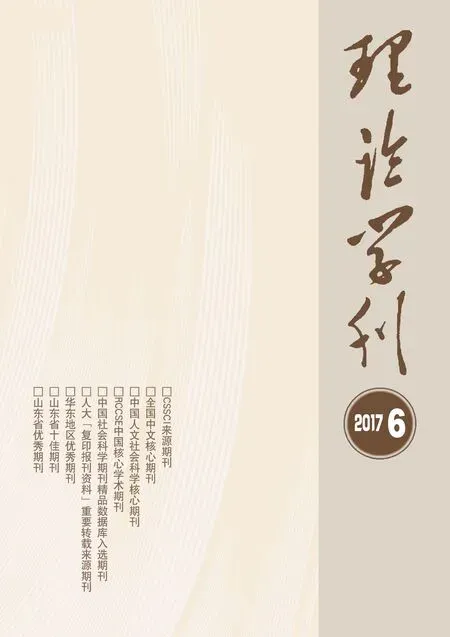移植與再造:論《赤光》與中國革命話語的建構
賈 凱
(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5)
移植與再造:論《赤光》與中國革命話語的建構
賈 凱
(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5)
《赤光》是中共旅歐黨、團組織創辦的刊物,該刊物在建構中國革命話語的過程中,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為武器,圍繞反軍閥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兩大中心內容,向旅歐華人揭示了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革命、國民革命與共產主義革命的關系,批判和揭露了軍閥禍國與內訌的真相、世界資本主義的反動風、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的本質。《赤光》的話語建構是將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移植”到中國,再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是對近代中國革命話語“再造”的嘗試。
赤光;少共;革命話語;帝國主義;國際聯合
留法勤工儉學生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影響很大的一個群體。留法時期是這一群體形成并成長為職業革命家的關鍵階段,了解這一時期他們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作為中共旅歐黨、團組織機關報的《少年》、《赤光》恰好是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少年》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不可忽視的文獻資料,《赤光》則是中共旅歐黨、團組織宣傳國民革命的重要報刊。目前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周恩來的相關思想和實踐,也有個別學者以《少年》為切入點探討該群體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影響,而對于《赤光》的研究尚未有專題成果。因此,以《赤光》為切入點探討該群體建構中國革命話語的探索,有助于深化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的研究。
一、“實際的”《赤光》創刊及其概況
1922年6月18日,中國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法國巴黎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以下簡稱“少共”),這是一個共青團性質的組織。當時中共旅歐支部處于秘密工作狀態,黨的活動主要以團的名義開展,因此“少共”在當時的旅歐華人中影響很大。兩個月后,“少共”機關刊物《少年》創刊,在中、法均有代售處。該刊物最初由趙世炎負責,張申府、周恩來經常為其撰稿。《少年》原為半月刊,出至第6號停刊;1923年2月“少共”改組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該刊物復刊并改為月刊;7月1日后改為不定期刊物。到1924年2月為止,《少年》共出13號,其中第12號僅28頁至47頁可見*崔春雪:《<少年>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5期。。盡管存在時間較短、僅出刊13號,但是《少年》對于“少共”的思想訓練、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以及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具有重要作用。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國民黨的改組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達成。為適應當時的革命形勢,“少共”于1924年2月1日出版了《赤光》雜志以代替《少年》,原為半月刊,后改為不定期出版。《赤光》繼承了《少年》宣傳蘇俄革命的特色,意蘊“革命的赤光,從北俄騰起”,“夜已闌,天將曉,赤色之光,早在東方閃動了”*《赤光的宣言》,《赤光》1924年第1期。;圍繞著反軍閥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赤光》更加突出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介紹,為國民革命宣傳和中國革命話語的建構提供了載體。《赤光》現存19期,其中1924至1925年有16期(第21、21期為合刊),部分有缺頁,字數總計愈19萬。另外,1929年出版的第45、48、54期不完整。由于組織經費緊張,只能采用手刻印刷。
分析1924至1925年共計16期的雜志,不難看出,《赤光》具有三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章體裁多樣,語言犀利深刻。每期文章篇數、頁數不一,文章包括政論139篇。其中2篇譯文,讀者來信8篇,中國共產黨或“少共”的文件、通告、啟事共計17篇,卷首語9篇,含多篇詩歌。第二,編輯者、作者眾多,可考證的作者有16人,其中周恩來、任卓宣、蕭樸生、李富春、鄧小平、熊銳發表文章較多,分別為37、30、11、6、3、3篇,且周恩來、任卓宣均擔任過主編。第三,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論述國民革命問題,圍繞“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的中心主題展開。與偏重理論的《少年》相比,《赤光》更為關注現實問題,因而問題意識強、現實指向明確。統計詞頻可以發現,“革命”“階級”“帝國主義”“軍閥”“國民”“資本”“壓迫”“無產階級”“共產黨”為主要的高頻詞匯,說明該雜志主要圍繞中國革命展開論述。正如《赤光的宣言》所聲明:“改理論的《少年》為實際的《赤光》”*《赤光的宣言》,《赤光》1924年第1期。。《赤光》基于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法,在旅歐華人中揭露了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的反動本質、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北洋軍閥的禍國行徑,為中國革命話語的建構作出了有益探索。
二、《赤光》與反軍閥反帝革命話語的建構
《赤光的宣言》提出了刊物宣傳的“唯一目標”: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按照辦刊設想,《赤光》主要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介紹、評論中國時事,指出中國政治經濟的亂源及解決辦法;二是揭示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國際背景,即介紹“國際情勢”;三是指出中國的唯一出路,揭示其他救國道路不能實行的原因。綜觀《赤光》16期的內容,該刊物圍繞著這“唯一目標”,從以上三個方面建構革命話語和開展宣傳工作。當時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對于“國民革命”“軍閥”“帝國主義”等革命話語的認識存在差異,而“少共”身處國際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又面對著《先聲》等反動輿論攻擊,其建構中國革命話語的側重點也會有所不同。
(一)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為基礎,劃分中國革命的各派勢力
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是《赤光》運用的主要方法,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將與中國革命有關的人劃分為軍閥、國際帝國主義、被壓迫民眾三類;二是認為中國尚處在“有產階級尚未勝利,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又萌芽底時候”,社會階級包括封建階級(滿清余孽——軍閥)、有產階級(各種資本家和依附于他們的智識者)、無產階級(產業工人,商業雇員,農村的工人、佃農、貧農等)三個部分*任卓宣:《國民革命與階級爭斗》,《赤光》第9期。;三是認為革命勢力包括四類人——學生(智識分子)、商人(既被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掠奪,又求卵翼于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工人(能夠擔當統治階級,但尚處于幼稚階段)、農人(數目很多,散居在農村,智識落后,有待于組織和訓練),這四類人若能聯合,革命力量就能發展壯大,并能打倒軍閥和推倒國際帝國主義*任卓宣:《國民革命必然和可能》,《赤光》第3期。。《赤光》又根據各階級與生產力的關系,將他們分為最復古的、較進步的、最進步的三種勢力,并把國民革命總結為各階級的革命勢力聯合向封建階級進攻,同時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爭斗。“軍閥”被定義為封建余孽、落后生產力的代表和非正義的一方,變成了國民革命的對象;原本“集中全力于軍事行動,忽視了對于民眾的政治宣傳”的國民黨,在《赤光》等刊物的宣傳下改變了以往“南北軍閥如一丘之貉”的形象,朝著“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國民革命之領袖”的方向進步。以上幾個方面均為“少共”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為基礎建構的中國革命話語。
(二)闡述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革命的關系,論證打倒軍閥必須先推翻帝國主義的主張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與國民革命的關系,也是《赤光》論述的基本內容。一方面,《赤光》指出:軍閥與帝國主義是狼狽為奸、二合一的“妖魔”、人民公敵,國際帝國主義是軍閥的“太上政府”,軍閥是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紀人”。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滲透是為了獲得原材料、傾銷商品、刮取人民“脂膏”。國民革命及其革命成功后的實業發展與帝國主義的利益存在根本沖突,他們會揭開親善的面具,露出猙獰的鬼臉來束縛中國工人、學生的革命行動,壓迫中國的革命勢力*任卓宣:《國民革命必然和可能》,《赤光》第3期。。因此,國民革命的成功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為條件。另一方面,《赤光》主張:中國的國民革命并非完全意義上的民主革命,不能忽視中國的國際殖民地屬性,以及中國革命是殖民地有產階級革命的特殊形式*卓宣:《中國革命運動之進化》,《赤光》第17期。;國民革命與封建制度下的工商資本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被封建制度壓迫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性質不同,是一種被半封建制度、帝國主義強權壓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蕭樸生:《中山逝世與國民革命》,《赤光》第28期。。這說明中國社會存在各類矛盾,國民革命的敵人并不是唯一的。從軍閥與帝國主義的關聯、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兩方面來看,開展國民革命與推翻帝國主義是“合二為一”的一場革命,這是《赤光》所建構的革命話語的基本觀點。
(三)辯證分析國民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系
無產階級革命(即社會革命)與國民革命的關系如何,共產黨人為何要與國民黨合作,這是將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移植”到中國、“再造”中國革命話語無法回避的問題。當時中國青年黨是“少共”的勁敵,他們以《先聲》為陣地歪曲國民革命、國共合作。對此,《赤光》一方面指出中國目前應實行國民革命,因為立即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既有昧于本階級底革命勢力,亦且不懂得中國底有產階級還未掌握政權底形勢。這樣的爭斗只是延長了封建階級底政治”*任卓宣:《國民革命與階級爭斗》,《赤光》第9期。。針對“共產主義者干國民革命是列寧所反對的”的謬論,任卓宣反駁指出:“國民革命符合列寧《怎么辦?》、《兩個策略》及共產國際二大、四大的精神”*任卓宣:《國民革命與階級爭斗》,《赤光》第9期。。針對青年黨“共產黨人為何不直接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詰難,《赤光》積極回應并認為,共產主義者認定國民革命后還有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的革命,如果國民革命不成功,那么“共產主義革命不能發生”,正所謂“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恩來:《再論中國共產主義者之加入國民黨問題——答胡瑞圖、吳樵甫、威重三君》,《赤光》第9期。。另一方面,針對曾琦等人發表的“共產主義者就不應該加入國民黨”的觀點,《赤光》進行了反駁。林蔚指出,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做國民革命的工作,是符合《共產黨宣言》的精神、遵從第三國際的決定、經中國共產黨全黨贊成、國民黨決議通過的革命實踐;國民黨是集合各派革命分子的政治團體,“熱心革命”的共產黨人自然要加入,青年黨如果要革命就應當與國民黨合作*林蔚:《批評曾琦君底<神圣聯合與統一前敵>》,《赤光》第7期。。《赤光》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國民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系進行了闡釋和宣傳,貫穿著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的基本原則,即革命要促進社會進步,共產主義革命要從推翻一切現存制度著手。
(四)論證建立反帝國主義國際聯合戰線的必要性
論證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與國民革命的關系,是“少共”建構革命話語的一項重要內容。《赤光》主要從列舉蘇俄和各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對華友好的事實,從分析蘇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民族平等和自決的政策這兩個角度宣傳建立反帝國主義國際聯合戰線的必要性。第一,宣傳蘇俄對華友好、平等、和平的事實。針對蘇俄與北京政府談判陷入僵持的局面,《赤光》向旅法華人解釋:“蘇俄不計較中國從前之倒俄政策,數年以至今日仍堅持忍耐,力謀兩國正式邦交致恢復,難道他(蘇俄)還變更么?”*署名、標題因缺頁無法得知,參見《赤光》第8期。,并警告《先聲》不要站在攻擊蘇俄的反革命陣線上;中俄協定簽訂后,周恩來指出“蘇俄永遠是弱小民族的朋友”*恩來:《中俄協定的簽字后》,《赤光》第10期。,以后將站在帝國主義的對立面為中國說話。第二,報道各國共產黨、工人階級聲援中國人民反帝運動的事例。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托洛茨基致電中國人民,聲稱蘇聯“十分完全地站在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底地位上……為中國人民之解放爭斗,是每個革命者底義務,尤其是共產黨人底義務。”*石電:《“北京反帝國主義大同盟”》,《赤光》第17期。莫斯科于1924年9月成立“勿犯中國會”,“全俄工會聯合會”通告表示反對帝國主義、援助中國人民,莫斯科的大學生組織示威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在第一國際成立60周年紀念大會上,法共將“反對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列入會議議程,開會時各國工人高呼“中國萬歲”以聲援中國人民*富春:《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之新發展》,《赤光》第17期。。第三,從理論上論證蘇俄不僅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先鋒,也是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使者。《赤光》認為,蘇俄是由工農兵掌握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唯一地以解放被壓迫階級為目的之社會主義國家,所以蘇俄要本其解放自國無產階級之志愿,來解放他國被壓迫民族”;蘇俄是無產階級國家,反對侵略、有產階級,因此要組織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對于被壓迫民族主張民族平等、民族自決;蘇俄鼓勵中國、波斯、土耳其等國的獨立運動,因為“在帝國主義國家稱霸底世界中,蘇俄只有于集中各國無產階級于其旗幟之下,再集中一切被壓迫民族于其旗幟之下,才能生存于世”*任卓宣:《蘇俄與被壓迫民族》,《赤光》第21、22期。。總之,《赤光》圍繞著以上三點從實踐、理論兩個層面論證了蘇俄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和建立反帝國主義國際聯合戰線的必要性。
三、《赤光》建構中國革命話語的特色
作為機關報的《赤光》,是“少共”宣傳革命理論與政策的“喉舌”,該刊語言犀利活潑、分析論證嚴密,在旅歐華人中起到了重要的宣傳和啟蒙作用,對于國內的革命宣傳也有幫助,特別是介紹國際帝國主義的反動風方面。時任《中國青年》編輯的蕭楚女評價《赤光》:“對于歐洲方面的時局觀察,頗能予人以一種明了確當的觀念……有[尤]可貴者,則為揭發海外各帝國主義者對華組織之侵略的黑幕……吾人深居國內,一切不明究竟,得此則眼光如炬。”*楚女:《新刊批評》,《中國青年》第40期。同時,《赤光》以大量篇幅報道、分析國內政治局勢,轉載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最新精神,其話語風格免不了受中共中央的影響。《赤光》建構的中國革命話語反映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局勢的新特點,對中共中央的宣傳具有積極影響;另外,《赤光》注意結合旅法華人的生活實際,自覺地宣傳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這體現出旅歐“少共”建構革命話語過程中國內外因素的互動,也使《赤光》呈現出與其它刊物不一樣的特色。
(一)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唯物史觀為武器,力求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的統一
中共二大提出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號召建立包括工人、貧農、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民主主義聯合戰線。但陳獨秀認為“民主革命”這個口號“偏于純資產階級的”,中共開始以“國民革命”口號代替“民主革命”來進行宣傳。“少共”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為基礎宣傳國民革命作為中心內容,即反軍閥的國民聯合和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革命”是當時《赤光》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高達1294次。與青年黨的“全民革命”主張不同,“少共”的革命話語建構貫穿著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階級”“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國民” “壓迫”“無產階級”“共產黨”“中山”是另外9個高頻詞匯,“國民”“帝國主義”與青年黨的“全民”“強權”含義均有大的差別,這也是雙方分別以馬克思主義和國家主義建構革命話語的不同結果。“少共”的話語已避免直接談及“共產革命”“專政”等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但是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又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以闡述“軍閥”“國際帝國主義”概念的科學性以及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的關系。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貫穿于《赤光》的論證分析中,而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軍閥禍國史”“資本主義反動風”的梳理論證,體現出該刊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的統一。這也是將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移植”到中國,“再造”中國革命話語的具體表現。
首先,指出軍閥不可靠,唯有民眾才是中國革命的可靠力量。周恩來指出:“新舊軍閥既都不足恃,所恃者以救中國的只有全中國的工人、農民、商人、學生”,并預言“許多的革命潮頭已漸涌起于冷靜無波的中國民眾海中,我們相信不久全中國的工人、農民、商人、學生均將會沖上前鋒來做弄潮人。”*伍豪:《軍閥統治下的中國》,《赤光》第1期。這體現出對歷史發展動力的科學認識。其次,通過對經濟現狀的分析,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應被推翻、新中國能夠被創造。《赤光》通過多篇文章分析歐戰后資本主義的危機,指出:各帝國主義國家由于國內經濟的危機,不得不與蘇俄“重修舊好”,承認蘇俄;蘇俄經濟基礎已經穩固,已能與世界帝國主義相抗衡;中國留學生也應該從德國貨幣改換之中得到教訓,對社會制度發展有所覺悟*強:《旅德的中國人快興起了》,《赤光》第3期。。再次,以唯物史觀為武器批判國家主義的“唯心論”。針對青年黨人搬出“孔子的國家主義”,以“內諸夏而外夷狄”之見來抵抗侵略的妄想,《赤光》批判其不注意物質生活、經濟利益等“實際問題”,以“我國光榮之歷史”來培養國民自尊心、敵愾心的做法是“非科學的夢想”,并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出于資本階級輸出商品、掠奪原料的需要,而非出于“夷狄之見”,最后指出資本主義已不符合時代發展需要,社會主義是大趨向*任卓宣:《答曾琦君書》,《赤光》第9期。。《赤光》依據唯物史觀對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分析,使旅歐華人明確了國民革命的依靠力量和內在邏輯,大大消除了唯心史觀的負面影響。
(二)以建構中國革命話語為主,兼與反革命勢力爭奪話語詮釋權
“國民革命”一詞是《赤光》建構的核心話語,該詞最早出現于1906年孫中山、黃興等人起草的《軍政府宣言》,但此后革命黨人較少使用該詞。1922年之后,中國共產黨賦予“國民革命”新內涵并進行“再造”后,該詞才逐漸風靡,也被孫中山和國民黨人認同。“少共”對于“國民革命”話語的建構,得到了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及大部分旅歐華人的支持和響應。根據各階級是進步還是反動,《赤光》分析了幾對矛盾關系:封建軍閥、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革命派(共產黨、國民黨左派)與反革命派(北京政府內的各派別、青年黨人、基督教青年派、無政府主義者、國民黨右派)。是否進步和革命是1920年代政治價值評判的主要標準,基于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少共”將是否代表民眾利益、工人階級立場作為劃分進步與反動的標準,這樣便把新舊各派軍閥列為反動力量的代表。是否代表民眾利益很難量化,“少共”又基于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將與蘇俄是否友好作為衡量革命與否的標準,將反對與蘇俄合作的青年黨人、國民黨右派列為反革命的代表,并將國民黨劃分為左、中、右三派。
同時,“少共”與國民黨駐法總支部的右派分子、青年黨人積極爭奪話語詮釋權,批判他們對“革命”“愛國”的闡釋,并將右派分子稱為“叛黨之徒”“反革命派”,還揭露了他們相互勾結“出反共產主義底惡氣”的行為*紅焰:《國民黨駐法總支部果真在森嚴紀律、肅清內部么?》,《赤光》第25期。。在《赤光》所建構的中國革命話語中,要救亡圖存必須革命,要革命必須實行反軍閥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若反對這二者,哪怕存在任何妥協行為,便不是真的革命和愛國,甚至是反革命和賣國。與之相對應,青年黨人“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主張便顯得落后了。“愛國和革命——國民革命——反軍閥、反國際帝國主義”的內在邏輯貫穿于“少共”的批判和分析中,并以其批判青年黨“振興中國——培養國民的自尊心和敵愾心——引用傳統光榮的歷史”的話語及其論證邏輯,指出青年黨人完全看不到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乃出于資本發展的內在邏輯;所謂的“內懲國賊”也沒有揭示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軍閥,認識不到“軍閥是一個階級”,及其與政客、官僚、鄉紳、流氓等“毛賊”的“皮”“毛”的關系。《赤光》從唯物史觀、本質與現象、重點與全面等角度對反革命勢力的話語進行了揭露與批判,既爭奪革命話語的闡釋權,又批判對方話語邏輯的內在矛盾。
(三)以建構中國革命話語為中心,堅持世界革命和國際主義原則
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中國民眾所受的壓迫來自國際帝國主義而不是某一個帝國主義“強權”,蘇俄及第三國際對全世界無產階級給予幫助。對于這些方面,“少共”成員均有直觀感受,因此其話語自覺遵循著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和國際主義原則,這很容易得到旅歐華人的接受和認可。就16期《赤光》文章的比重來看,關于世界資本主義反動風、蘇俄等的文章遠多于與中國革命相關的文章,這主要基于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宣傳的考慮。就論證思路來看,《赤光》涉及世界資本主義反動的文章,往往從帝國主義對世界無產階級、落后民族的壓迫以及工人運動、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運動興起或高漲的角度論證;涉及中國革命的文章,一般從揭示軍閥背后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爭斗切入,再與蘇俄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態度進行對比,最后得出國民革命必須與各國工人階級、各被壓迫民族聯合的結論。雖然蘇俄對于留法勤工儉學生提供了物質幫助,但是《赤光》往往不會直接提及這一方面,以免被誣蔑為“賣國團體”,而是從各國工人階級對于中國人民反帝斗爭的聲援、對于本國資產階級抗議的角度來體現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些都是《赤光》以世界革命、國際主義為原則建構中國革命話語的體現及其切入點。
世界革命、國際主義是《赤光》所“移植”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和建構中國革命話語的基本原則,但是不可否認國民革命是當時旅歐華人思考的核心問題,因此《赤光》的宣傳也基本圍繞著中共二大提出的最低綱領展開。《赤光》對于中國革命話語的建構,一方面體現在反軍閥的國民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的論述,另一方面體現在重新詮釋“愛國”與“賣國”的內涵。《愛國與賣國》一文指出,掌握政權的有產階級才是有國的人,在面臨外國侵略或外國尋求獨立時,他們會要求工人階級上戰場,即所謂“工人救祖國”;當外國侵略的危險消失或無產階級要求革命時,他們便要“賣國”,如魯爾地區的德國資本家與法國資本家勾結鎮壓工人暴動。有產階級所聲稱的“愛國”,不過是為了維護他們的階級利益。對于無產階級而言,不但要反對本國的有產階級,還要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只有世界革命成功后財富才屬于無產者,在此之前無產階級都是無祖國、無民族的;就中國而言,中國的各派軍閥維護的不是中華民族的利益,而是本派軍閥及其“太上政府”的利益,各派軍閥之間雖有爭斗,但是他們在壓迫、榨取中國人民方面又是一致的,真正同情中國人民的是蘇俄、各國共產黨、各被壓迫民族,因此國民革命必須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合策略。正是基于對國家本質的分析,《赤光》揭露了各派反動勢力“愛國”的虛假性,指出了國際聯合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宣傳了國際主義,批判了國家主義。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留法勤工儉學群體對中國共產黨國民革命話語體系建構的探索及其當代價值研究”(項目編號:17YJC710030)和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60批面上資助(項目編號:2016M602077)的階段性成果。
賈 凱,男,法學博士,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
D26
A
1002-3909(2017)06-0049-06
吳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