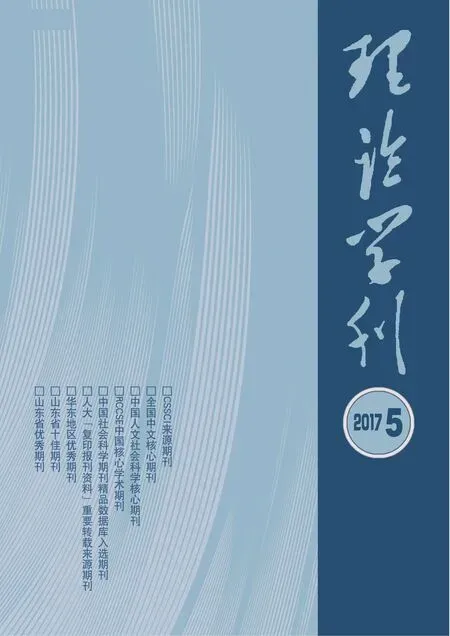論梁武帝的歷史貢獻
楊恩玉
(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02)
論梁武帝的歷史貢獻
楊恩玉
(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02)
梁武帝積極興辦學校,倡導講學活動,實行經學生策試入仕制度,編纂五禮,這一系列措施促使魏晉以來式微的儒學得以復興。梁武帝開創的“三教同源”說為儒釋道的融合奠定了理論基礎,他樹立的三教兼修的范式則在實踐上為儒釋道融合開辟了道路。梁武帝經常召集文士吟詩作賦,晉升詩賦優秀者的官職或賞賜金帛,同時重視整理和編纂典籍,從而推動了文學和文化的昌盛。五館、經學策試、官班制等制度和“唯才是舉”的政策,打擊了門閥士族的勢力,促成了寒庶階層的崛起,推動了貴族制向官僚制的演變。梁武帝的一系列舉措對推動中國歷史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梁武帝;儒學;貴族制
因為佞佛和侯景之亂的緣故,使得梁武帝在后世的名聲很不好,而這也的確是梁武帝的兩大缺點。然而梁武帝對歷史的發展作出過較大貢獻,也是客觀事實。本文擬就梁武帝的歷史貢獻略作探討。
一、推動經學復興
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用儒經來選拔官員,致使儒學在兩漢盛極一時。東漢末年以降,直到蕭齊,由于政局的動蕩、玄學的興起、道教和佛教的沖擊等原因,儒學大大衰落,以至宋、齊兩代的國子學存在不到十年。梁武帝即位后,重視學校教育,推崇儒學,促使經學再度復興。陳朝吏部尚書姚察對此有生動描述:“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于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遂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后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十數年間,懷經負笈者云會京師。”*《梁書·儒林傳序》。王夫之更是明確指出:“(梁)武帝之始,崇學校,定雅樂,斥封禪,修五禮,六經之教,蔚然興焉,雖疵而未醇,華而未實,固東漢以下未有之盛也。”*[清]王夫之:《讀通鑒論》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89頁。沈玉成先生也說:“南朝的儒學在梁代最為興盛。《隋書·經籍志》經部著錄魏晉南朝的學術著作,除《周易》而外,絕大部分出于南朝人之手,南朝人中又以梁代為多”*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6頁。。這具體反映了蕭梁時期經學的復興及其巨大成就。
蕭梁時期經學的復興,直接得力于梁武帝一系列興辦學校、敦崇儒經的政策和措施。建武元年(317),東晉建立,68年后的太元十年(385)才建立國子學。永初元年(420),劉宋建立,22年后的元嘉十九年(442)才建立國子學。但8年過后,即元嘉二十七年,就因為與北魏的戰爭導致財政拮據而裁撤了國子學。建元元年(479),蕭齊建立,6年后的永明三年(485)才建立國子學,永明十一年又因太子蕭長懋病逝致令國子學停辦。所以史家說宋、齊兩代的國子學存在的時間都不足十年。梁武帝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認為“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④ 《梁書·儒林傳序》。。因此,他登基的當年即天監元年(502)就建立了國子學和太學。之后,他感到國子學成就不夠顯著,于是在天監七年下詔擴大規模、增加生員;九年又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齡適宜者皆入國子學受業*參見楊恩玉:《蕭梁國子學與太學考論》,《理論學刊》2014年第5期。。為了激勵國子學官員的教學,天監九年三月,梁武帝到國子學視察,親臨講堂,依照官階的高低賜帛給國子祭酒以下人員。該年十二月,梁武帝再次駕臨國子學,親自策試國子生,并再次賜帛給國子學官員。由于國子學是高門士族子弟受業的貴族學校,太學是下層士族子弟學習的場所,天監四年,梁武帝決定建立五館,專門招收寒庶子弟,并選拔精通儒學的著名學者明山賓、嚴植之、賀玚、陸璉、卞華擔任五經博士,分別主持五個學館的教學。每個學館都有數百名學生。天監五年五月,梁武帝又設集雅館,以招收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學生。大同七年(541)十二月,在宮城西邊設立士林館,作為官員講學、整理和編纂典籍的機構。除了大力興辦京師兩學(國子學、太學)三館(五館、集雅館和士林館)外,梁武帝還在地方普遍建立學校,“選遣學生如會稽云門山,受業于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④。地方官員積極響應梁武帝的政策和舉措,建立學校,獎勵教學。荊州刺史、安成王蕭秀,“立學校,招隱逸”*《梁書·安成王蕭秀傳》。;益州刺史、始興王蕭憺,“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由是多向方者”*《梁書·始興王蕭憺傳》。;后來的荊州刺史、湘東王蕭繹,“于府置學,以(賀)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荊楚衣冠聽者甚眾”*《梁書·賀玚傳附子革傳》。,他還“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南史·梁元帝紀》。。隨著各地學校的建立,地方的教學活動也呈現出活躍的局面。
梁武帝在積極興辦學校的同時,還增加國子學的講授內容。劉宋時的國子學,《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各為一經,《論語》和《孝經》為一經,共計十經。蕭梁時,《周易》的鄭玄注與王弼注、《尚書》的孔安國傳和鄭玄注、《孝經》的孔安國傳和鄭玄注、《論語》的鄭玄注和何晏集解并立國子學;除《孝經》的孔安國傳在梁末亡佚外,其余都被陳朝繼承*《隋書·經籍志一》。。天監四年二月,梁武帝在國子學設置律學,由博士講授。中大通四年(532)三月,在領國子博士蕭子顯的建議下,國子學設置《制旨孝經》助教1人,專門講授梁武帝所撰的《孝經義》,學生有10人。大同七年,在國子祭酒到溉的建議下,梁武帝所撰的《孔子正言》被立于國子學,設置《正言》助教2人、學生20人;后又接受尚書左丞賀琛的建議,增設《正言》博士1人*參見楊恩玉:《蕭梁政治制度考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94~295頁。。
蕭梁之前,“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為了改變這種風氣,梁武帝親自示范,登堂講授《孝經》。太子蕭統效法父皇,于天監八年在壽安殿講授了《孝經》。第二任太子蕭綱則在玄圃講授梁武帝所撰《五經講疏》,聽眾濟濟一堂。梁武帝還將兼任國子助教的皇侃召入壽光殿講授《禮記義》。梁武帝撰成《五經講疏》后,選拔精通儒學的官員到全國各地去宣講。在梁武帝父子的影響下,京師和地方官員都競相傳授學問。梁武帝統治后期最受寵信的大臣朱異,在儀賢堂傳授梁武帝所撰《老子講疏》,聽眾多達千余人。朱異與尚書左丞賀琛在士林館內,每天輪流傳授梁武帝所撰的《中庸講疏》。太子蕭綱將朱異召入玄圃,傳授《周易》。“皇太子、宣城王亦于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于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云集于京師矣。”*《梁書·武帝紀下》。在梁武帝父子和朝廷大臣競相講學的刺激下,私人講學也蔚然成風,生徒的數量之多不亞于兩漢。會稽山陰人孔僉,“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并數十遍,生徒亦數百人”*《梁書·孔僉傳》。。隱士“(諸葛)璩性勤于誨誘,后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梁書·諸葛璩傳》。。“(賀)玚于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余人”*《南史·賀玚傳附弟子琛傳》。。這與此前“鄉里莫或開館”的境況相比,可謂是天壤之別。
梁武帝在直接敦崇經術的同時,還實行了士族子弟通過經學策試入仕的制度。天監四年正月,梁武帝頒詔:“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梁書·武帝紀中》。曹魏以來實施九品官人法,門閥士族子弟依照這一制度,僅憑借家族門第就可直接入仕,這是導致經學式微的一個重要原因。按照梁武帝的詔令,士族子弟要想在30歲之前入仕,就必須經學策試合格;如果像往常那樣直接入仕,必須年滿30歲才行。為了在有生之年晉升到高官,士族子弟必須盡可能早地入仕,而官員要想在年輕時就登上高位,更需要較早入仕。蕭梁時期官員的平均入仕年齡不足21歲(虛歲)*參見楊恩玉:《蕭梁政治制度考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64頁。。如果考慮到寒庶子弟入仕時年齡普遍較大,則士族子弟的平均入仕年齡還要更小一些。士族子弟顯然不愿等到30歲以后入仕,而為了早日入仕,只好去勤奮學習儒經。沒有入仕特權的寒庶子弟,更需要憑借經學策試入仕。這種深具利害關系的限年入仕制度,無疑極大地促進了經學的發展。
梁武帝發展經學的另一項重要措施,是組織精通禮學的官員編纂五禮。早在齊武帝永明二年(484),五禮的編纂就已開始,但到蕭齊滅亡時,五禮尚未編纂完成,并且由于變故頻發,已編成的文稿多次散失,特別是在齊末戰亂中,更是大部分文稿蕩然無存。天監元年,梁武帝登基伊始,就詔令立即著手編纂五禮。于是以明山賓掌吉禮,嚴植之掌兇禮,賀玚掌賓禮,陸璉掌軍禮,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其事。何佟之亡故后,伏暅接替他的工作。由于禮儀深廣、記載殘缺,需要集思廣益,梁武帝又令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和徐勉共同參與其事,不久又欽點徐勉總其事。后來,中書侍郎周舍和庾于陵也奉旨參與其事。眾學者不能決斷的疑難問題,提交梁武帝裁決。五禮歷時22年,于普通五年(524)二月編纂完畢。吉、兇、軍、賓、嘉五禮的《儀注》保存在尚書省,副本存放在秘閣,還撰寫了五禮典書。五禮的系統整理,既統一了錯綜分歧的見解,也有利于五禮及相關文獻的保存,同時更有利于禮制的順利實施。毫無疑問,這項巨大的工程極大地推動了經學的復興和發展。
皮錫瑞指出:“北朝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能一變舊風,尊崇儒術。考其實效,亦未必優于蕭梁。”*[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82頁。正是由于梁武帝不遺余力地采取了一系列重教崇儒的政策和措施,經學開始復興,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繁榮局面。這在經學發展史上是一項重要貢獻,梁武帝的功績不可磨滅。
二、促進儒釋道融合
孔子創立的儒學,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學說,不僅符合最高統治者的需要,而且是個人修養的不二法門。它不僅是封建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也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內容。道教以黃帝、老子的思想為理論根基,由戰國時期的神仙方術演變而來,其核心則是內丹養生之道。佛教宣揚善惡報應、生死輪回的教義,彌補了儒學對終極關懷的缺失。作為舶來品的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二者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沖突,不斷有人公開反對佛教。顯著的事例是:蕭齊時,竟陵王“(蕭)子良精信釋教,而(范)縝盛稱無佛,……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梁書·范縝傳》。。佛教與儒學以及中國固有道教的融合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在蕭梁時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梁代之前,就有人儒佛雙修、道佛雙修,或由儒入佛,或由道轉佛。但在中國歷史上,儒釋道三者兼修的學者,梁武帝堪稱是第一位。他在《述三教詩》中寫道:“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卷,猶月映眾星。”*[唐]道宣:《廣弘明集》卷30。從表面上看,梁武帝信仰儒學、道教和佛教是人生三個階段的事,并且將佛教抬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但由于他從小就學習儒經,儒家的思想觀念在他的頭腦中其實是根深蒂固的。儒家學說作為入世、濟世理論,對于治理國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佛教作為出世學說,在治國理政方面無法和儒學相提并論。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梁武帝對此是心知肚明的。他抬高佛教,是由于很多人抵制和反對佛教,而在他的思想深處,儒學始終居于主導地位。誠如潘桂明先生所說:“梁武帝提倡佛教,每每結合儒教;他闡述佛學,常援引儒家經典”;他提出“三教同源”說,“以‘心’為三教共同本源,以‘善’為三教共同歸趣”;他提倡三教合一,“是在消化基礎上的吸收融合,它為后世學者以儒家為主體、合三教思想為一的繼續具體實踐開辟了道路”*潘桂明:《試論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歷史影響》,《孔子研究》1986年第4期。。
梁武帝雖然極力推崇佛教,但實際上是儒釋道兼修。他的著述既有《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尚書大義》《孔子正言》《毛詩答問》《春秋答問》等儒學類,也有《老子講疏》等道教類,還有《涅槃》《大品》《凈名》《三慧》諸經義記的佛教類。梁武帝開啟的儒釋道兼修的范式被人們紛紛效法。王褒在為教育諸子而撰寫的《幼訓》中說:“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汝能修之,吾之志也。”*《梁書·王規傳附子褒傳》。庾承先“弱歲受學于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于群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曾“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鄱陽王蕭恢令其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梁武帝在征召他的詔書中說:“潁川庾承先學通黃老,該涉釋教”*《梁書》之《庾承先傳》《庾詵傳》。。馬樞“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陳書·馬樞傳》。。這都是儒釋道三教兼修的典型事例。陳代的徐孝克不僅儒釋兼修,而且能同時講授佛學和禮學。他“少為《周易》生,……及長,遍通《五經》”;后“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陳書·徐陵傳附其弟孝克傳》。。
梁武帝三教兼修而格外推崇佛教,他將佛教視同月亮,將儒教和道教等視作“眾星”。不僅如此,梁武帝甚至更明確提出:“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跡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唐]道宣:《廣弘明集》卷4。。這就將佛教抬高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梁武帝身居九五之尊,他的言行對世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張孝秀,“博涉群書,專精釋典”*《梁書·張孝秀傳》。;庾詵,“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晚年以后,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梁書·庾詵傳》。;劉歊,“六歲誦《論語》《毛詩》,……既長,精心學佛”,道人釋寶志稱贊他“隱居學道,清凈登佛”,劉歊自己在所撰《革終論》一文中說:“余以孔、釋為師”*《梁書·劉歊傳》。;“吳郡陸慶,少好學,遍知《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陳書·王元規傳附吳慶傳》。。當時一些學者儒釋道兼修,客觀上有利于佛教的推廣和普及。
梁武帝開創的“三教同源”說為儒釋道的融合奠定了理論基礎,他樹立的三教兼修的范式則在實踐上為儒釋道的融合開辟了道路,也極大地促進了儒釋道的融合。
三、促成文學文化繁榮
蕭梁時期,不僅經學開始復興,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且文學空前繁榮,在中國文學史上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這一成就同樣與梁武帝密不可分。時人劉勰曾稱贊說:梁武帝登基以來,“文思廣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于天衢,駕騏驥于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梁]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對于蕭梁文學的鼎盛及其原因,李延壽評論說:“自中原沸騰,五馬南度,綴文之士,無乏于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南史·文學傳序》。沈玉成先生具體指出:“梁代是南朝辭賦的全盛時期,作家、作品的數量都超過前代。”*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頁。曹道衡先生統計,有詩傳世者,東晉113人、劉宋59人、南齊43人、梁代167人*曹道衡:《南朝文學的衰落》,《文史知識》1998年第12期。。逯欽立先生輯錄的《先秦漢魏南北朝詩》,有魏詩12卷、晉詩20卷、宋詩12卷、齊詩7卷、梁詩30卷、陳詩10卷、北魏和北齊詩都是4卷、北周詩6卷*詳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目錄第3~15頁。。文學界習慣稱齊梁文學,實際上成就主要在梁代,梁代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全盛時期。蕭梁文學的繁榮與梁武帝的喜好、獎掖密不可分。
梁武帝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詩人和文學家。史家稱贊他“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詔銘贊誄,箴頌箋奏,爰初在田,洎登寶歷,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梁書·武帝紀下》。,這雖不無溢美,但也基本符合實情。梁武帝的確文學才華超群,是位詩賦行家里手。他有《詩集》32卷,逯欽立輯錄其詩多達101首*逯欽立輯校:《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513~1539頁。。梁武帝酷愛詩賦,平時的一大樂趣就是與擅長文學的官員一起吟詩作賦,篇什優秀或才思敏捷的作者有時獲得晉升官職的褒獎,有時獲得金帛的賞賜。比如征虜主簿到沆“善屬文”,“高祖初臨天下,選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為太子洗馬”*《梁書·到沆傳》。;“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于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天監)六年,(王府參軍袁)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梁書·袁峻傳》。。梁武帝選拔的“賢俊”,主要是富有文學才華者。“自高祖即位,引后進文學之士,(劉)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并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雖仕進有先后,其賞賜不殊”*《梁書·劉苞傳》。。不僅文才出眾者得到晉升官職、賞賜金帛的獎勵,而且文章優秀的士人還被直接授予官職。比如“有才思,居喪過禮”的何之元,因司空袁昂的推薦而被梁武帝召見,梁武帝直接任命其為太尉臨川王蕭宏的揚州議曹從事史*《陳書·何之元傳》。。與何之元類似,憑借文才直接入仕的還有周興嗣。史載:“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儛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為賦,高祖以興嗣為工。擢員外散騎侍郎”。其后,周興嗣與陸倕分別創作光宅寺的碑文,梁武帝又選用了周興嗣的作品。“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并使興嗣為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梁書·周興嗣傳》。。周興嗣文學才華超群,深受梁武帝賞識,起初依靠優美的《休平賦》起家,繼而因為《儛馬賦》的工巧優美,由一班的安成王國侍郎超遷三班的員外散騎侍郎,后來又獲得金帛的賞賜。劉孝綽因為文才超群,深受梁武帝的寵愛。他擔任廷尉卿因故被免官后,還經常被召去參加朝廷舉行的宴會;奉詔創作《籍田詩》的有數十人,梁武帝認為劉孝綽作的最好,于是下詔起用他為西中郎將湘東王的咨議參軍。故史稱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梁書·劉峻傳》。。唐朝進士科以詩賦取士,其淵源可以追溯到梁武帝依據詩賦選拔官員或晉升官職。
梁武帝還親自編訂了歷代賦,并敕令左衛率周舍作注。在梁武帝編纂文集的啟發下,太子蕭統“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⑤ 《梁書·昭明太子蕭統傳》。,其中《文選》又名《昭明文選》,流傳至今。在此影響下,蕭梁時期涌現出一大批文集,包括《詩纘》13卷、《眾詩英華》1卷、《詩類》6卷、《玉臺新詠》10卷、《詩英》10卷、《西府新文》11卷、《弘明集》14卷等,其中《玉臺新詠》和《弘明集》流傳至今。唐代的道宣仿照梁代僧祐編的《弘明集》而編纂了《廣弘明集》,也流傳到今天。
在梁武帝篤好文學的熏染和帶動下,前后兩個太子蕭統與蕭綱也都愛好并擅長文學,經常招集文學之士討論文學問題或創作詩賦。蕭統“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閑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并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⑤。蕭綱“篇章辭賦,操筆立成,……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恒討論篇籍,繼以文章,……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于輕艷,當時號曰‘宮體’”*《梁書·簡文帝紀》。。當時詩歌創作非常盛行,鐘嶸在《詩評·序》中對此評論道:“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于是庸音雜體,各為家法。至于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余,何嘗不以詩為口實”*《梁書·鐘嶸傳》。。對此,史家評論說:“梁武帝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隋書·經籍志一》。這生動反映了蕭梁文學的繁榮。正是在當時文學繁榮的社會背景下,劉勰創作了中國古代最系統的文學評論經典之作《文心雕龍》,鐘嶸則創作了中國最早的詩歌批評專著《詩品》。
蕭梁時期不僅經學得到振興、文學一派繁榮,而且整個文化事業都達到了魏晉南朝的頂峰。李延壽稱贊說:梁武帝“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愈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南史·梁武帝紀下》。。魏征對蕭梁文化成就的評價更高,其云:梁武帝“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沖樽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梁書·敬帝本紀》。。蕭梁文化達到魏晉南朝的鼎盛,直接原因在于梁武帝勵精圖治發展文化事業。
梁武帝為保存、整理和編纂典籍做了大量工作。齊末的兵火燒毀了秘書省,保存在里面的典籍蕩然無存。梁武帝登基后,在百廢待興、政務極其繁忙的情況下,詔令秘書監任昉著手搜集典籍。很快就收集到數萬卷圖書,僅保存在文德殿的就有23106卷,而華林園的佛教典籍還不包括在內。進而,梁武帝在文德殿設置學士省,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校定墳史。太子洗馬到沆、劉峻與學士賀蹤等人都被派去從事這項工作。為了更好地保存典籍,梁武帝派人專事抄寫副本——到洽抄寫甲部即經部書,張率抄寫乙部即史部書,后又抄寫丙、丁二部即子部和集部書。梁武帝還敕令劉勰與慧震沙門在定林寺撰寫經論*《梁書·劉勰傳》記載:“勰為文長于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為文。有敕與慧震沙門于定林寺撰經證”。“經證”應為“經論”,形近而誤。《南史·劉勰傳》也作“經證”,同樣有誤。佛教的經典分為經藏、律藏、論藏,即所謂三藏。“經論”指經藏與論藏,這在史書中多有記載。《梁書·謝舉傳》:“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又如《魏書·劉芳傳》:“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而“經證”為中醫學名詞,“指邪在三陽經脈所引起的病變”(《辭海》第3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6頁)。。史學著作的整理和編纂更是梁武帝非常重視的一項工作。員外散騎侍郎袁峻受命改編《史記》《漢書》,各為20卷;吳均等奉旨撰寫《通史》,始于三皇,止于蕭齊,共計600卷,梁武帝親自撰寫了序和贊。周興嗣和任孝恭也都被召入修撰史書,王僧儒奉旨撰寫《中表簿》和《起居注》。
天監十五年,梁武帝敕令太子詹事徐勉選拔才學之士到華林園編纂大型類書《華林遍略》。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云、鐘嶼等5人歷時8年修成,共計700卷。《華林遍略》編成不久就流傳到北朝,備受重視。北齊的《修文殿御覽》和隋朝的《長洲玉鏡》兩部類書的編纂都是以《華林遍略》為藍本,唐代編纂的《藝文類聚》也充分利用過《華林遍略》,因而該書對中國古代類書的編纂具有深遠影響。梁武帝還先后令人編纂了佛教類書《佛記》和《經律異相》,其中后者保存至今。流傳至今的還有釋慧皎撰寫的《高僧傳》、釋僧祐撰寫的《出三藏記集》、釋寶唱撰寫的《比丘尼傳》等佛教典籍。
蕭梁時期文化的昌盛,突出表現在私人藏書數量眾多。太子蕭統在東宮聚書近3萬卷,第七子蕭繹在荊州聚書更是多達8萬卷*[梁]蕭繹:《金樓子·聚書篇》。,梁武帝從父弟蕭景之子武平侯蕭勱聚書也達3萬卷*《南史·武平侯蕭景傳附子勱傳》。。沈約“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梁書·沈約傳》。。沈約藏書之宏富,在皇族之外位居首位。任昉、張緬和王僧儒的藏書也都達到萬卷*詳見《梁書》之《任昉傳》《王僧儒傳》《張緬傳》。。私人藏書的盛行及其數量的巨大可謂空前,是當時文化繁榮的一個生動寫照。
在梁武帝的敦崇和推動下,蕭梁時期的文學和文化事業都達到魏晉南朝的鼎盛,其杰出成就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而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卓著的貢獻。
四、通過制度創新實現政治革新
眾所周知,東晉是典型的門閥政治時代,門閥士族壟斷了軍政大權,皇權式微。劉宋和蕭齊時,門閥士族雖然逐漸走向衰落,但仍還具有強大的勢力,庶民入仕仍然相當困難。極少數庶民僥幸躋身仕途,則被稱為“恩幸”或“幸臣”,意謂他們是憑借皇帝的寵愛而飛黃騰達者,遭到士族蔑視是可以想見的。蕭梁時期,梁武帝推行的一系列制度導致士族勢力受到抑制,庶民勢力迅速崛起,從而促成了社會從貴族制向官僚制的轉變。
曹魏時起,士族依據九品官人法、憑借門第就可直接入仕,基本不問才學的有無,甚至白癡也可以做官。例如,出身江左第一高門陳郡謝氏的謝靈運,其“父瑍,生而不慧,為秘書郎”*《宋書·謝靈運傳》。。有些根本沒有政治才干的高門士族同樣可以身居高官要職。例如,元嘉三年(426),王敬弘“為尚書仆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常豫聽訟,上(文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六年,遷尚書令”*《宋書·王敬弘傳》。。尚書仆射王敬弘不批閱文件,是高門士族崇尚玄虛、不問政務的表現。王敬弘說自己看不懂案件審訊的筆錄,也許是實情。他在其位而不謀其政,宋文帝對他盡管大為不滿,但仍然晉升其為“任總機衡”的尚書令,這主要是由于王敬弘出身江左第一高門的瑯邪王氏。這種士族政治當然不利于政府職能的實現。有鑒于此,梁武帝讓門閥士族“身居高位,不親事務”,“把他們當作擺飾,而另外任用一些真能關心‘簿領文案’的人來進行統治”,這些人基本上都來自士族的中下層*周一良:《論梁武帝及其時代》,《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門閥士族壟斷軍政大權的局面。
西晉以來,由于門閥制度的確立,士族壟斷了受教育的權利。為了讓寒庶子弟也有機會接受教育,天監四年,梁武帝設置五館,專門收攬“寒門俊才”。這些學生由政府供給飲食,他們只要考試合格就可以到政府部門任職。為打破士族對寒庶的歧視和壓制,天監八年五月,梁武帝下詔:“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后,選可量加敘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后門,并隨才試吏,勿有遺隔。”*《梁書·武帝紀中》。這就是說,無論出身士族還是寒庶,只要精通一門儒家經典,并且的確愛好學習,就可以入仕。這無異于公開宣布了“唯才是舉”的政策。天監九年病故的賀玚,其弟子明經對策就達到數十人,可見梁武帝這一舉措成效之顯著。如前所述,天監四年梁武帝曾頒布詔令,要求士族子弟的直接入仕必須年滿30歲,否則就要通過經學策試起家。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士族的入仕特權,打擊了士族勢力,迫使他們屈服于皇權,從而促進了貴族制向官僚制的進一步轉變。天監七年,吏部尚書徐勉主持制定了官班制。士族子弟從流內十八班起家,寒庶階層具備了士人文化修養的人,依靠才學從流外七班起家,一般庶民從士兵或胥吏做起,依靠吏績、軍功或年資從三品勛位或蘊位起家。官班制不但是維護士族利益的有力工具,也為寒庶階層的入仕和升遷打開了通道,因為寒庶階層的人可以從流外七班晉升入流內十八班,也可以從三品勛位和蘊位依次晉升入流內十八班。例如,“家世農夫”的沈峻由于精通《五經》,從流外六班的王國中尉起家,晉升至流內四班的中書舍人;其子沈文阿也精通經術,則從流內一班的臨川王國侍郎起家,升遷至十一班的通直散騎常侍*參見楊恩玉:《蕭梁政治制度考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95、151~153頁。。這一制度創新無疑極大地削弱了門閥士族的勢力,促進了寒庶階層的崛起,以致被杜佑稱為從此“無復膏粱寒素之隔”*[唐]杜佑:《通典·選舉二》。。
蕭梁時,一些官職的選用基本體現了“唯才是舉”的原則。史載:“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⑦ 《隋書·百官志上》。。梁代,中書通事舍人的選拔條件主要是才能,取消了門第的限制,這是歷史的一大進步。實際上,不僅中書通事舍人,尚書侍郎的選拔也要求以才能為標準。“自晉以后,(尚書)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秕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三年,置侍郎,視通直郎。其郎中在職勤能,滿二歲者,轉之”⑦。依靠才能擔任尚書侍郎者,以到沆及其從兄到溉、到洽為代表。 “(天監)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到)沆為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并有才名,時皆相代為殿中,當世榮之”*《梁書·到沆傳》。。尚書侍郎的選拔條件不僅是“勤能”或“人才高妙”,還要任職滿兩年。歷來為高門士族壟斷的太子洗馬,其用人標準也發生了變化。“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為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庾)于陵與周舍并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梁書·庾于陵傳》。太子洗馬原來是由高門士族壟斷,梁武帝則任命一般士族庾于陵和周舍擔任此職,因為庾于陵“清警博學有才思”,周舍“博學多通,尤精義理”*《梁書》之《庾于陵傳》《周舍傳》。,就是說,梁武帝所看重的是二人的才學。梁武帝旗幟鮮明地提出“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的觀點,即侍從之類清貴的官班需要選拔有才華的人擔任,而不以門第高低為限,只要有才華,門第低的人也可以出任,出身高門士族而才華不佳者同樣不能入選。這些制度創新,體現了梁武帝抑制門閥士族、“唯才是舉”的用人理念。陳朝吏部尚書姚察評論說:“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于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于上,職事隳于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梁書·何敬容傳》。這深刻揭示了魏晉以來長期形成的政治腐朽的具體成因和嚴重危害。梁武帝注重才能、績效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打擊了士族根深蒂固的傲氣和惰性,重振了皇帝的威權,促使貴族制進一步衰落,賢才主義和官僚制乘勢復興。
另一方面,本來由寒庶階層或下層士族擔任的一些官職,其用人標準也開始改變。尚書省的“五都令史,與左、右丞共知所司。舊用人常輕,九年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眾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每盡時彥,庶同持領,秉此群目。’于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年,以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戶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五人并以才地兼美,首膺茲選矣”*《隋書·百官志上》。。五都令史雖然職責很重要,但以前選用的人屬于寒庶,所以才學普遍較低。為了提高五都令史人選的文化素質,梁武帝詔令此后不僅要改用士流,而且要選拔優秀的士族,即所謂“時彥”。當時選拔的五都令史全部“才地兼美”,即不但門第高貴,而且富有才學。其次是尚書郎的人選之變化。太子舍人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瑯邪)王氏過江,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乃欣然就職”*《梁書·王筠傳》。。出身江左第一名門望族的王筠是王導的嫡孫,被任命為江左以來王氏從未擔任過的尚書郎,王筠欣然接受。這主要是因為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門第這塊金字招牌的作用已經今非昔比了。這些制度的創新和實施改變了以前基本依據門第選拔官員或晉升官職的傳統,淡化了士族和庶族的界限,發揮了移風易俗的作用。
梁武帝的學識才華,在古代帝王中是罕有其匹的。在其統治前期的梁武帝是一位勵精圖治的君主。他洞悉時政的弊端,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通過實行一系列的政策引導和制度創新,使經學得以復興,儒釋道的融合取得重大突破,文學和文化繁榮昌盛,打擊了門閥士族,促成了寒庶的崛起,推動了貴族制向官僚制的轉變。這些歷史性貢獻值得充分肯定。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魏晉南北朝社會階層研究”(項目編號:17BZS009)、山東省社科規劃研究項目“中古社會階層變遷研究”(項目編號:15BLSJ01)的階段性成果。
楊恩玉,男,歷史學博士,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
K239.13
A
1002-3909(2017)05-0147-09
[責任編輯裴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