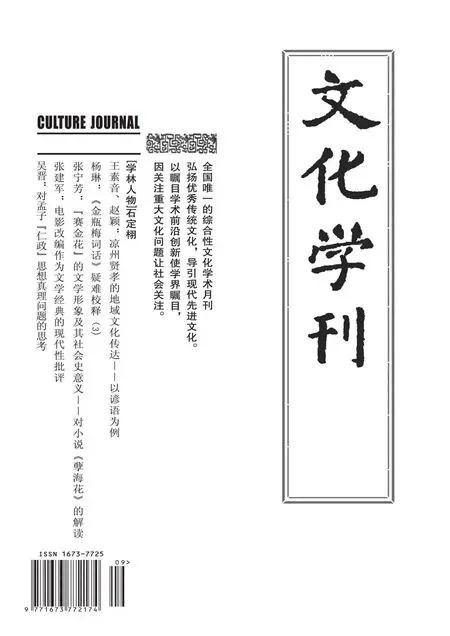談嚴歌苓小說中的異質文化身份建構
張海燕
(山西大同大學文學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文學評論】
談嚴歌苓小說中的異質文化身份建構
張海燕
(山西大同大學文學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作家嚴歌苓是當代北美移民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其在很多文學作品中都極度表現出了對自身文化的追求和對傳統文華的探尋意識。由于長期的國外生活,使嚴歌苓受到異族文化的沖擊和熏陶,其在作品中表現出了自身的焦慮,甚至是自我懷疑。本文從嚴歌苓的經歷和作品出發,詳細分析嚴歌苓在作品中表現出的焦慮感,并對嚴歌苓作品中的主體意識進行闡述,探究嚴歌苓擺脫身份焦慮,并最終完成自我身份構建的過程。
嚴歌苓;異質文化;身份建構
一、嚴歌苓作品風格簡介
嚴歌苓出生在中國上海,是著名的旅美作家之一,其作品有獨特的魅力,對于東西方的文化都有獨特的見解,作品中對于社會基層人物及邊緣人物都表示出關懷,講訴出不同時代人性復雜的一面。作為海外華文文學家,她經歷了從故鄉到海外文化身份的轉變,與本土不同的生活習慣,迫使她對生活的觀察及人生的觀點都發生了變化,慢慢地形成了一種新的審視世界與自我的角度。和其他海外華文文學家一樣,嚴歌苓在創作過程中,認定與追尋文化身份顯得尤為重要。在嚴歌苓的作品中,曾經非常形象地對異域生活的生存情況做出了描述,并將其比喻成生命的移植。所以,在嚴歌苓創作的作品中,身份認同危機感幾乎一直存在。例如,《紅羅裙》中的卡羅、《小姨多鶴》中的多鶴、《風箏歌》中的英英等,這幾部小說中的人物都存在一定的身份危機感,其可能與嚴歌苓的生存狀態比較相似,所以她能夠深刻體會到作為寄居者的生存困境。[1]
二、在異質文化中徘徊的邊緣人
離婚后,嚴歌苓前往美國留學,其使嚴歌苓離開了生活多年的故鄉。在異域生活的嚴歌苓,是異域文化主流中的非中心化的個體,由于生存環境驟然發生改變,其失去了內在依托,與多數海外移民的文學家一樣,在異域環境中陷入了孤零與漂泊的狀態。在他世界的環境中,嚴歌苓想要對自我進行確認,我是從哪里來,終究要到哪里去?嚴歌苓因為這種不斷涌現出來的自我審視與追問,最終陷入了焦慮的狀態中。處于這一時段的嚴歌苓,其小說作品主要闡述了移民生活與邊緣體驗的披露。在留學的初期,嚴歌苓創作了多部短篇移民小說,如《女房東》《少女小漁》及《海那邊》等。[2]
其中的一篇短篇小說叫《栗色頭發》,在這部作品中,作家非常巧妙地為主人公設置了異常盡顯錯位的對話,在這段對話中,充分顯露出剛到異國他鄉的“我”和首次見面的“他”之間的尷尬,那種靈魂的游離被描述得淋漓盡致,“他問:你來美國多久了,學什么?我答:我的朋友會來接我的,謝謝你,不用你開車送我。他說:你長得非常……特別,非常好看,我從未見過像你這樣理想的古典類型的東方女子。我說:對呀,天是特別熱。洛杉磯就是熱。不過我的朋友一定會來的,你不必操心……”。作者安排這樣一段對話,小說中的人物對話都處于答非所問的非交流狀態,兩個人都處于急于掩飾自己內心的尷尬,并想證明自己的存在感,這段對話雖然顯得比較滑稽,但是總比沉默要好得多。在這段對話中,嚴歌苓并不是想要諷刺什么,只是單純地在描述這種語言不通的交流狀態,其實質上主要是強調語言作為文化之間的重要交流手段有著非常大的裂隙。在異質文化中游走的人們,大多數都存在著這種失語之痛,這也是異域生存的困境之一。[3]
三、嚴歌苓的主體意識重拾
1981年,嚴歌苓開始創作,最初期的作品有《雌性的草地》《綠血》等。在最開始的小說創作中,主要的敘述視角以女性知青為主。以《雌性的草地》這本小說來講,作品中的敘述者常把寫作動機描述出來,有時甚至將作品中的人物直接對話,將敘述主體的張揚與自由直接體現出來。一般情況下,文學作家從移民生活開始,其寫作視角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即都以移民的視角展開寫作,都使用第三人稱進行敘事,作品中的人物與敘述者自身都以異國文化的闖入者展開,并逐漸失去原有身份認同。在敘述風格上,嚴歌苓已將初期敘述主體張揚的風格丟失,慢慢地以邊緣人的角度對自我及他人進行審視。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女房東》《栗色頭發》《少女小漁》及《紅羅裙》等。[4]
嚴歌苓再婚以后,其創作的作品開始在美國獲得多個獎項,并得到了一定的認可。嚴歌苓在美國留學初期經歷了失我的狀態后,她意識到了這種情況后,開始找尋自我,這時,嚴歌苓的小說才開始再次回到對自我的反思,回到對女性體驗進行描寫的狀態中,這一階段的小說主體大多集中在反思移民的身份與追認自我身份上。如小說《扶桑》,這篇小說中的敘述人“我”,對兩個故事進行了描述,其一是扶桑,其二便是敘述者自己經歷的故事。在小說中,敘述人“我”時常出現,對于事件發表自己的意見,同時進行反思,在不斷地追問與反思之中,小說充分表現出“我”在精神層面上出現的質疑與困惑。以上這些都是作家在經歷了移民的影響以后,對自我身份重新建構的過程。[5]
一般情況下,作家處于什么時期,其心理問題及文化身份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作品中,都能充分地展現出來,且作品中敘事手法的變化,在某種角度上也代表了作家的心理動態。在作家嚴歌苓的小說中,敘事手法的轉變,都源自嚴歌苓在不同階段經歷不同文化身份的變化,小說中敘述著“我”,經常往來于出場和缺席中,小說中最后關于敘述者“我”的重拾過程,就是嚴歌苓回歸主體意識的過程。[6]
四、嚴歌苓文化身份的建構
所謂的文化身份,其實就是對某一個群體文化的認同。為了文化主體的解放,需要對自己的身份進行追尋,獲得一定的主體地位。自我文化有兩個方面,一是自我需求,二是歸屬感,二者關系較為緊密,其中的歸屬感則更多體現了人們的文化心理。著名學者斯圖亞特在多年的文化研究中表示,在自我之中藏有文化身份,其屬于一種共有文化,體現了民族性和無意識性,從作家角度來說是不能夠斬斷或者掙脫的,同時直觀地反應了一個民族的歷史發展腳步和文化共性。以上表述介紹了嚴歌苓的創作特色,在歷經了焦慮和困惑之后,作者對自身文化和身份進行了深刻地理解和構建,促使嚴歌苓的藝術特色回歸了中國文化中,追尋文化的根本。[7]長期的海外生活,使嚴歌苓深刻理解了中西方的差異,尤其是文化風格的差異,與此同時,在這種差異中,又發現了本民族的文字風格帶有不可言說的魅力。
在作品中,嚴歌苓曾表示,“在自己的少年到青年時代,軍隊給予了最深刻的烙印,那時也是人們逐漸形成自己世界觀的階段”。從此段回憶中可以看出,嚴歌苓的早年生活中,傳統的中國文化對其價值觀和人生觀都有深刻的影響,隨后到達美國的初期階段,使得嚴歌苓的創作思路產生焦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留在美國的嚴歌苓已然是而立之年,是一個擁有成熟思維的生命個體,多年的中華文化傳統教育已經在她成長的路途中留下了太多的烙印,同時成就了嚴歌苓成熟的創作風格。在美國的時間里,嚴歌苓從來沒有拋棄自己生命中的中國特性,其坦白地訴說著自己的中國傳統,讓中國的文化底蘊作為自我身份的代表。[8]
五、結語
綜上所述,文學作家的作品風格會受到創作環境的影響。嚴歌苓在自傳中將自己比作是文學中的游牧民族,其中的游牧民族就是說在創作中被迫背離了本土文化,無論是心理還是地理因素,終將自己的作品擱置在了兩種文化的邊緣地帶,成為寄居者,即兩種文化都得不到認同,甚至最終被異族文化所同化。在移民作家中,嚴歌苓最終戰勝了文化沖擊,逐漸地追尋自我,回歸了本土文化,在重新審視自我后,確立了自己的創作身份和創作風格。中西方文化差異改變了嚴歌苓,也正是這種差異和轉變的過程,讓嚴歌苓的創作經歷得到了歷練,從而形成了嚴歌苓獨特的創作風格。
[1]吳淑波.在他者的時代構建自我——嚴歌苓作品中的文化身份書寫[D].成都:四川師范大學,2012.
[2]吳敏.跨文化書寫:嚴歌苓新移民小說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3.
[3]吳玉苗.論嚴歌苓小說中的身份建構意識[J].云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3,(3):407-408.
[4]王博園.論嚴歌苓移民小說中的身份書寫[D].海口:海南師范大學,2012.
[5]謝雯.永遠的“寄居者”--談談嚴歌苓筆下移民形象的身份認同[J].北方文學(中旬刊),2013,(7):17.
[6]張素娣.“離散”和“融聚”:嚴歌苓與譚恩美小說比較[J].華文文學,2012,(5):36-39.
[7]陳俏湄.異質文化語境中的周旋與迷失——小議嚴歌苓的《扶桑》[J].芒種,2016,(22):71-79.
[8]王謙.身份的認同與重構的焦慮——論嚴歌苓小說中的身份建構意識[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14.
【責任編輯:王崇】
I207.42
A
1673-7725(2017)09-0056-03
2017-07-03
本文系山西大同大學“大同邊塞詩歌研究”(項目編號:2015q16);山西大同大學“移動媒介對地方文化傳播的影響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15Q21)的研究成果。
張海燕(1980-),女,山西靈丘人,講師,主要從事比較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