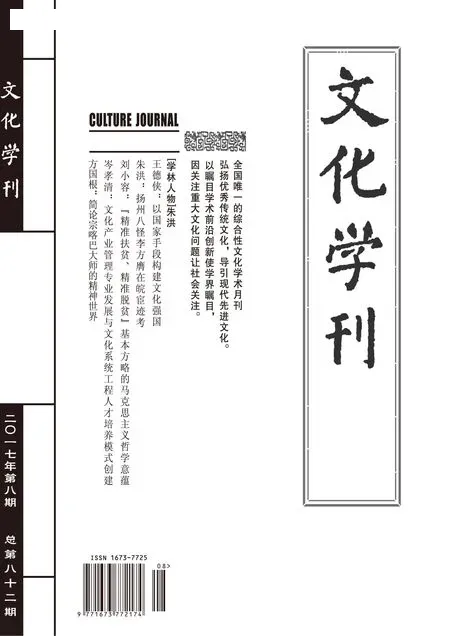唐五代敦煌寺院倉司研究
謝慧嫻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文史論苑】
唐五代敦煌寺院倉司研究
謝慧嫻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 100875)
唐五代時期,寺院經濟高度繁榮,財力雄厚的寺院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淵源于佛教教義以“供養三寶”的“倉”的職能逐漸拓展,成為寺院的財產出納機構和面向社會的借貸機構。“倉司”作為“倉”的執掌機構,設置了分工明確的僧職,逐年輪換,并受到全寺僧眾的監管。倉司進行的放貸活動,展現出宗教與世俗交織的復雜性。
唐五代;敦煌;倉司;寺院經濟
佛教傳入中國之后,寺院逐漸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結合,這不僅體現在脫胎于封建官僚體系的僧官制度上,也表現在寺院通過占有土地和控制農民,發展起了獨特的寺院經濟模式。佛教寺院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寄生于政治權利和民眾信仰之間的供養體系。而“倉”作為這一體系重要的一環,其職能亦隨著寺院經濟的觸角逐步擴張。從最初存放什貨雜物的倉房變為管理寺院收納和民間借貸的中樞機構,“倉”的職能擴展反映了佛教寺院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謀求世俗利益的過程。唐五代時期,“倉”的經營管理逐漸制度化,“倉司”作為倉的執掌機構,不僅管理倉的出納,也作為寺院的財產管理機構,直接從事經濟活動。
一、倉司的設置和職能
唐五代時期,敦煌寺院財力雄厚,建立起倉庫對寺院財產和糧食進行統一管理。都司在靈圖寺設置“都司倉”[1],并通過都司倉進行放貸活動。本文探討的“倉司”是各寺院下屬的對倉庫進行管理以及進行相關經濟活動的機構。分析現存的敦煌文獻得知,至少永安寺、凈土寺、報恩寺、靈圖寺、金光明寺等寺院設置了倉司。而且,一個寺院如果有多個倉庫,那它就有可能存在多個倉司。如P.4694《年代不明某寺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殘卷》,以及S.1519《某寺入破歷》中記載某寺有“南倉司”;P.2032號背《后晉時代凈土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稿》中記載凈土寺有“西倉司”。
P.3223《永安寺法律愿慶與老宿紹建相諍根由責勘狀》[2]記載了永安寺倉司執倉紹建與法律愿慶借貸寺倉谷麥發生的沖突,是幫助我們了解倉司職責及管理人員的重要史料。郝春文先生根據文書的第22行“提招余者,皆例無分”,認為倉司執掌寺院的提招僧物,并進一步判斷倉司又被稱為常住倉司或招提司,而且沙州寺院應該都有倉司或招提司。[3]實際上,雖然倉司也是常住倉司,但倉司與提招司并不能完全等同。佛典中對常住僧物與招提僧物有著嚴格的區分,《大寶積經》中稱:“常住僧物不應與招提僧物共雜,招提僧物不應與常住僧物共雜。”[4]而且據S.1600(1)《庚申年十二月十一日至癸亥年靈修寺招提司典座愿真等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稿殘卷》第5行載:“施及官倉佛食、阇梨手上領入、常住倉頓設料”[5],表明常住倉是靈修寺提招司的收入來源之一,說明招提司與常住倉司并非同一機構。
倉司主要管理寺院倉庫的糧食并經營相關的出納、借貸活動。谷麥、豆、黃麻等都是倉司的主要管理對象。P.3223第15行“倉內谷麥”可知,永安寺倉司管理的主要是寺院倉內的谷麥等糧食。S.4701《庚子年(公元940年)十二月十四日報恩寺前后執倉法進惠文愿盈等算會分付回殘斛斗憑》中也著重記載了倉司中麥、豆、粟、黃麻等糧食的情況。據此可知,寺院倉庫的糧食管理是倉司的工作重心。然而P.3223中還說道:“年年被徒眾便將,還時折入干貨”,即寺院僧徒從倉司中借谷麥,歸還時則常常以“干貨”按一定比率進行折算歸還入倉,“干貨”即布、絹等織物[6],所以除了管理糧食外,倉司還管理著一定數量的布、絹等織物。值得注意的是,倉司并不僅僅是負責寺院倉庫糧食的存儲,P.3223《永安寺法律愿慶與老宿紹建相諍根由責勘狀》中記載的“昨有法律智光依倉便麥子”和“官中稅麥之時,過在倉司”,說明倉司還進行糧食借貸活動,并負責向都司或者官府納糧。
倉司的管理者一般是被稱為“執倉”“把僧人”或“執物僧”的職事僧。P.3223中的老宿紹建稱自己為倉司“執倉”,是永安寺倉司的負責人。S.4701號文書第2行“先執倉常住倉司法律法進、法律惠文等八人所主持斛斗”,文書后有“執物僧”愿盈等八人押[7],與前文常住倉司的八位執倉相對應。這樣看來,“執物僧”為“執倉”的異稱或俗稱,是倉司中擔任相同職務的管理者。由于倉司管理的物品種類較多,對于倉內較重要或數量較多的物品可能會設置專門的管理人員,如“執黃麻人”就是專門管理倉內黃麻的人員,“把麥人”就是專門管理倉內麥子的人員。
倉司管理者為一年一輪換,上屆職事僧和下屆職事僧之間可進行交接工作。P.3290《己亥年(939年)十二月二日某寺算會分付黃麻憑》載:“先執黃麻人法律惠興、寺主定昌、都師戒寧三人手下主持人換油黃麻,除破外,合回殘黃麻肆拾伍碩貳斗伍升壹合,并分付與后執倉黃麻人徐僧正、寺主李定昌、都師善清三人身上訖。一一詣實,后算為憑。”[8]文書中記載的是倉司中新舊“執黃麻人”之間的輪換。其過程大致為:統計舊執黃麻人任期滿后的黃麻數量—進行交接—新任職事僧畫押確認交接工作完成。S.4701號文書在確認先執倉任期滿后所剩的麥、粟、豆和黃麻數量后,還記到,“惠興等三人身上欠黃麻三碩二斗二升”“善清等三人身上欠黃麻兩碩三斗五升”,此記錄即為P.3290中新舊兩任“執黃麻人”的債務,那么此時應該是“舊執黃麻人”已經任滿之時。從時間上來看,P.3290號文書的算會時間為公元939年12月,S.4701號文書的算會時間為公元940年12月,時間相差整一年。另外,S.4701號文書第3行“從去庚子年正月一日入算后”說明當屆執倉是從去年(庚子年)開始擔任倉司的工作,到年底與下一任執倉交接工作。種種材料證明,倉司的輪換制度是每年通過算會進行新舊任職事僧的交接,實行一年一輪換的制度。
二、寺院倉司的放貸活動
寺院或僧尼的出貸行為在魏晉南北朝時就已出現[9],到了唐五代時期,敦煌社會的借貸更加活躍,在這樣一種社會大環境下,寺院倉司的放貸行為已屢見不鮮。都司倉以寺戶和寺院為放貸對象[10],而寺院倉司放貸對象的構成則顯得相當復雜,不僅有寺院僧尼、寺戶、普通百姓,甚至還有官員,以普通百姓為主要群體。對P.3234背、S.5873背+8567綴合、S.6452(4)、S.6452(6)幾件倉司便物歷所載的借貸人信息進行統計,發現其中百姓有112人之多,占總人數的84%。但是,通過分析現存的文書發現,這些在倉司進行借貸的百姓具有明顯的特點。
P.3234背《甲辰年(公元944年)二月后沙州凈土寺東庫惠安惠戒手下便物歷》第46-50行:“張儒通便黃麻貳斗,至秋叁斗。(押)王都頭外甥;米里久便黃麻叁斗,至秋肆斗伍勝。(押)米胡男;行者張建子便黃麻陸斗,至秋玖斗。(押)住在慶子禪師院;安擖便黃麻貳斗,至秋叁斗。(舍在寺前);鄧定子便豆肆斗,至秋陸斗。(押)駱駝官男。”借貸者“押”之后的備注常常是借貸者的住址、有名望的親屬或擔保人。這是倉司為了確認借貸者償還能力的常見方式,或者說是倉司對借貸者的一種實際約束手段。不能給予倉司信任感的人一般不能得到寺院的借貸支持。相比起因土地牽絆而較易受約束的農民,工作地飄忽不定的工匠一般不是寺院倉司的借貸對象。在出便人名單中,借貸者為工匠的僅有屈指可數的幾例。據P.3234背載,71名借貸者僅有“史都料”[11]一名工匠得到了寺院的借貸;S.6452(4)《壬午年(公元982年)正月四日諸人于凈土寺常住庫借貸油面物歷》共四十名左右的借貸者,其中也僅有一名“皮匠”和一名“金銀匠”借貸成功。
總覽敦煌文獻中的寺院倉司便物歷,以及入破歷算會,粟和麥無疑是出現得最為頻繁的物品,其次為豆、黃麻*敦煌文書中的黃麻多指黃麻籽,用途為榨油,經常以“斗”和“升”作為其計量單位。和油,都是百姓維持生活必不可少的。從借貸時間來看,百姓向倉司借貸的時間并不固定,主要集中在二月。二月正是糧食相對短缺的時候[12],而且百姓還有可能面臨官府的臨時抽征[13],生活異常困難。倉司對百姓實行的借貸活動能夠及時地幫助其渡過生活難關。
從放貸利息上看,倉司放貸最高收取50%(二月借八月還)的利息,最低為10%。由凈土寺倉司的借貸活動來看,公元944年以50%的利息放貸,參照其他寺院倉司的放貸情況,50%的利息應該是當時各寺院倉司通行的利息標準。到了公元982年,凈土寺的放貸利息降低為30%,說明倉司借貸的利息呈逐漸降低的趨勢。換算為月息,寺院倉司放貸的最高月息為8%,最低不足2%。
唐五代敦煌的借貸利息存在官民兩套系統[14],相比起民間私人借貸,寺院倉司的借貸利息在大多數情況下相對較低且穩定;而相比官方糧倉放貸,寺院倉司的借貸又顯得更有效率且儲備充足。民間借貸利息與官方規定的借貸利息有著較大出入。民間私人借貸往往可以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如糧食供需狀況等因素來決定利息。在這種情況下,利息通常由貸方決定,借方缺乏主動權,于是高利貸大行其道。北圖收字43號背《唐天復九年(909)十二月二日杜通信便粟麥契》中有“粟兩碩,至于秋四碩”的記載,由此可知利息為100%。當然,100%的利息借貸并不是所有的民間私人借貸利息,因為利息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貸方自由決定。有時民間私人借貸利息甚至可達“數倍之息”,“利貸一斗而償四斗”[15]“每鄉人舉債,必須收利數倍”[16]等情況屢見不鮮。
9至10世紀的敦煌地區,自然災害頻繁發生[17],對社會生產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再加上戰事頻繁,人民生活更加困難。政府專門設置用來賑濟百姓的義倉似乎并沒有發揮其功能。開皇五年(公元585年)工部尚書孫平上書建議“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18],用于救荒賑貸的義倉由此正式建立。唐代義倉在太宗、玄宗、文宗三朝的災荒時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但義倉粟在后來逐漸賦稅化,演變成了地子,不但沒有為百姓解決困難,反而成了一種沉重的賦稅負擔。敦煌文獻中未見義倉對民眾賑濟的相關內容,更多記載的是正倉的借貸活動[20]。S.247V《辛巳年(981年)十月三日勘算州司倉公糜解斗前后主持者交過分付狀(稿)》是研究官方正倉借貸活動的重要文書。這件文書是歸義軍時期州司倉前后兩任負責人的交接手續,文書中第7-8行“利麥貳拾玖碩肆斗壹升叁合陸勺捌硅粟壹伯叁拾叁碩貳斗肆升伍合”,其中的“利”字就說明了州司倉進行有息放貸的活動,但文書中并沒有說明正倉的放貸利息。按照唐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雜令》中“每月取利不得過六分”的規定[21],暫且認為此處放貸的月息不超過6%。
官方糧倉放貸更大的問題在于儲備不足及效率低下。S.5945《丁亥年(公元987年?)長史米定興于顯德寺倉借回造麥歷》中長史米定興連續兩次向寺倉借貸100碩和19碩,應是官府向寺院借貸用以周轉,由此可知官倉的儲備還不如某些寺院倉庫的豐富。另一方面,“官吏漠視民情,賑貸緩不濟急,所給減于所需,甚或惜而不肯與。”[22]種種原因,使得百姓有時不得不選擇向民間私人借高利貸或向寺院借貸。
利用寺院三寶物進行放貸,并將其獲利物用于供養三寶符合佛教內律的規定,因此寺院倉司的放貸行為是佛教內律允許的。倉司的放貸行為是寺院高利貸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寺院牟利不少,相較于官方放貸和民間私人放貸,寺院倉司放貸活動憑借其穩定性、高效性和豐富的糧食儲備,在一定程度上救濟了普通百姓。
三、結語
根據敦煌文書中的記載不難看出,佛教寺院在中古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一方面被賦予一定經濟能力的寺院分擔了政府在慈善救濟方面的部分職能;另一方面寺院作為相對獨立的經濟主體,不僅有自己的收支體系,而且還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正如謝和耐先生所說,“我們可以承認,如果中國經濟的一般形式在5-10世紀發生了深刻變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應該歸于佛教。”[23]作為寺院財貨收支的中樞機構,“倉”,以及它的主管機構“倉司”,無疑是佛教寺院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通過梳理倉司的經濟行為特別是放貸情況可知,一方面佛教寺院通過放貸活動獲取利潤;另一方面,寺院也通過借貸活動行使著一定的社會義務,展現出了宗教與世俗的復雜性。
[1]田德新.敦煌寺院中的都頭[J].敦煌學輯刊,1996,(2):123-127.
[2]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二輯)[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310.
[3][6]郝春文.P.3223《永安寺法律愿慶與老宿紹建相諍根由責勘狀》及相關問題考[A].郝春文敦煌學論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9-90.93.
[4]菩提流志,編譯.大寶積經(第113卷)[M].上海:上海佛學書局,2004.382.
[5][7][8]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三輯)[M].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527.400.346.
[9]魏收.魏書(第11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97.3041.
[10]童丕.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M].北京:中華書局,2005.59.
[11][14][22]羅彤華.唐代民間借貸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93.237.155.
[12]董誥.全唐文(第27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344.
[13]宋敏求.唐大詔令集(第72卷)[M].北京:中華書局,2008.404.
[15]董誥.全唐文(第86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10904.
[16]李昉.太平廣記(第43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2.3523.
[17]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沙漠化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133.
[18]魏征.隋書(第2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97.684.
[19][20]張弓.唐代倉廩制度初探[M].北京:中華書局,1986.129.47.
[21]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6.430.
[23]謝和耐.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M].耿升,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7.
【責任編輯:周丹】
K242;K24
A
1673-7725(2017)08-0231-04
2017-06-05
謝慧嫻(1993-),女,重慶人,主要從事隋唐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