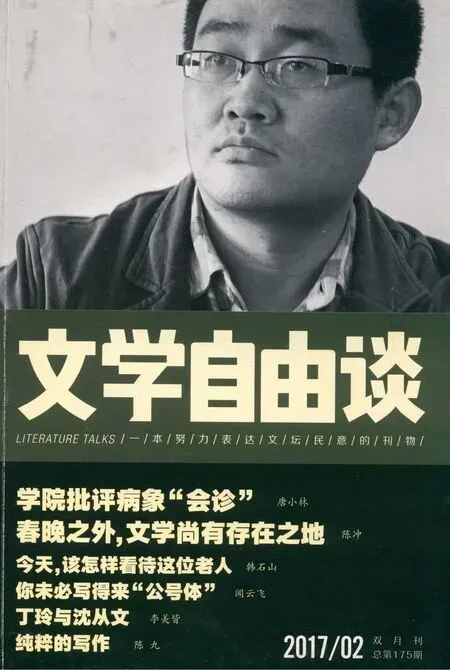經(jīng)典作家的經(jīng)驗(yàn)給我們的啟示
邢小利
經(jīng)典作家的經(jīng)驗(yàn)給我們的啟示
邢小利
李建軍的《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以下簡(jiǎn)稱《并世雙星》),內(nèi)容厚重、廣博,是對(duì)400年前中西方兩位經(jīng)典作家、偉大作家比較研究的力作,也是一部交響樂(lè),關(guān)于歷史,關(guān)于現(xiàn)實(shí),關(guān)于文學(xué)、文化、文明的交響樂(lè)。書(shū)中對(duì)很多問(wèn)題的闡述穩(wěn)健而犀利,文采斐然,讀起來(lái)讓人有一種含英咀華的感覺(jué)。
對(duì)湯、莎進(jìn)行比較研究,涉及東西方戲曲、戲劇、文學(xué)、思想、文化、時(shí)代背景、政治文明等很多方面,需要有“開(kāi)闊的文化視野和成熟的人文精神”(梁實(shí)秋語(yǔ))。《并世雙星》視野宏闊,同時(shí)又能站在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前沿,對(duì)相關(guān)問(wèn)題既有宏觀的總體把握,更能從細(xì)微處入手,進(jìn)入藝術(shù)欣賞的境地。比如關(guān)于“活文學(xué)”與“死文學(xué)”之辯,關(guān)于“文學(xué)”與“純文學(xué)”之辯,關(guān)于湯、莎的作品及其藝術(shù)性,李建軍都能深入藝術(shù)的肌理分析,特別是像漢語(yǔ)之韻致這樣一些有時(shí)只能體味其妙,而難以分析的問(wèn)題進(jìn)行深入地分析。所以,無(wú)論是談思想還是分析藝術(shù),這部著作都能深入其里并將其展開(kāi),沒(méi)有那種凌空蹈虛的空話,沒(méi)有不著邊際的昏話。
李建軍借漢詩(shī)《秋風(fēng)辭》中的詩(shī)句“蘭有秀兮菊有芳”來(lái)概括和評(píng)價(jià)東西方這兩位巨擘,認(rèn)為對(duì)他們強(qiáng)分軒輊沒(méi)有意義。比較研究的意義,在于對(duì)他們所處時(shí)代的政治和文化環(huán)境進(jìn)行分析,進(jìn)而聯(lián)系戲劇家個(gè)人的生存境遇和創(chuàng)作道路,比較他們?cè)趯徝篮蛡惱矸矫娴漠愅偨Y(jié)出他們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偉大經(jīng)驗(yàn)和這種經(jīng)驗(yàn)資源對(duì)后世的啟示意義。書(shū)中有對(duì)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兩部愛(ài)情經(jīng)典作品《牡丹亭》和《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牡丹與玫瑰”的分析,也有對(duì)兩位戲劇家藝術(shù)世界總體性的研究,有對(duì)比較研究中引出的相關(guān)問(wèn)題的梳理,有對(duì)兩位戲劇大師的接受史和研究史的再研究,進(jìn)而理出一些有價(jià)值、有美學(xué)意義的命題,探討兩位戲劇大師所呈現(xiàn)出的美學(xué)與藝術(shù)倫理共同性的問(wèn)題和意義,概括、總結(jié)出三個(gè)“偉大的共同性”:人格、人生哲學(xué)、再度創(chuàng)作。
經(jīng)典作家的偉大經(jīng)驗(yàn)給我們有很多的啟示。《并世雙星》比較研究的是400年前東西方的兩位經(jīng)典作家,該書(shū)在一個(gè)非常廣闊的時(shí)空中所發(fā)掘和討論的一些命題,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來(lái)說(shuō),涉及一些根本性的問(wèn)題,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有些問(wèn)題既具有歷史性,也能讓人感覺(jué)到深深的當(dāng)下性、現(xiàn)實(shí)性以及未來(lái)性。比如時(shí)代對(duì)作家、對(duì)藝術(shù)的深刻影響,比如作家的人格、精神境界對(duì)文學(xué)藝術(shù)的作用,比如創(chuàng)新和如何創(chuàng)新等問(wèn)題,我覺(jué)得都有非常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對(duì)未來(lái)的創(chuàng)作也有一定的規(guī)箴意義。
從時(shí)間上來(lái)說(shuō),湯、莎是同時(shí)代人,考察作家與時(shí)代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就是一個(gè)非常有意義的問(wèn)題,也是一個(gè)大問(wèn)題、老問(wèn)題。“文變?nèi)竞跏狼椋d廢系乎時(shí)序”,劉勰很早就論及時(shí)代、世情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從時(shí)代角度比較湯顯祖和莎士比亞,是《并世雙星》的一個(gè)重點(diǎn)。李建軍認(rèn)為,他們的志趣有很多相似性,但生活的空間不同,亦即他們所處的時(shí)代背景、文化環(huán)境、政治文明等條件不同,他們的命運(yùn)、文運(yùn)、心境以及美學(xué)選擇、敘事策略,當(dāng)然也包括其藝術(shù)世界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風(fēng)格也就不同;時(shí)代在他們的身上打下了非常鮮明的烙印,他們藝術(shù)上的很多選擇既是個(gè)人的,也是時(shí)代的。
李建軍認(rèn)為,文運(yùn)取決于時(shí)代,而莎士比亞之為莎士比亞,是他幸逢其時(shí)。李建軍分析說(shuō):“無(wú)論從哪個(gè)方面看,人都是自己時(shí)代的產(chǎn)物;而他的寫(xiě)作,則是其時(shí)代的精神鏡像。”寫(xiě)作需要最低限度的自由——安全地思考、想象和表達(dá)的自由。在一個(gè)極端野蠻的時(shí)代,只有少數(shù)勇敢的人,才敢于在積極的意義上寫(xiě)作,而大多數(shù)人,或選擇沉默,或滿足于虛假的或不關(guān)痛癢的寫(xiě)作;即使是那些勇敢的寫(xiě)作者,也不得不選擇一種隱蔽的寫(xiě)作方式,例如隱喻和象征。湯顯祖象征化的“夢(mèng)境敘事”,就是一種不自由環(huán)境下的美學(xué)選擇;而莎士比亞的全部創(chuàng)作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極大的自由感和明朗感,則彰顯著寫(xiě)作者與寫(xiě)作環(huán)境之間積極而健康的關(guān)系。
李建軍說(shuō),從物理時(shí)間上看,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確乎是同時(shí)代人;但是,從文明程度看,他們則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時(shí)代——湯顯祖的時(shí)代落后莎士比亞的時(shí)代,何止四百年!”在李建軍看來(lái),就想象力和才華而論,湯、莎兩人“在伯仲間”,但境遇和命運(yùn),卻全然兩樣。莎士比亞生活在伊麗莎白女王時(shí)代,“沒(méi)有伊麗莎白時(shí)代的偉大精神,就沒(méi)有莎士比亞的輝煌成就”。故此,莎士比亞的寫(xiě)作,“在題材取舍、主題開(kāi)掘、風(fēng)格選擇、修辭態(tài)度等幾乎所有方面,都表現(xiàn)出一種自由而積極的狀態(tài)”;即使涉及政治和權(quán)力的主題,也不用左顧右盼,不怕“觸犯時(shí)忌”。而湯顯祖生活在一個(gè)落后而野蠻的前現(xiàn)代社會(huì),恐怖氛圍里的靜止與和諧,是這個(gè)社會(huì)的突出特點(diǎn)。他懷抱利器,無(wú)由伸展,處處碰壁,一生偃蹇。就是在這種“無(wú)可奈何”的寫(xiě)作環(huán)境里,他努力不懈,這才創(chuàng)造出“臨川四夢(mèng)”的不朽成就。
李建軍關(guān)于時(shí)代對(duì)作家及其文學(xué)影響的闡述,不僅在于作家的個(gè)人命運(yùn)以及人格精神這些大的方面,讓人印象深刻,感受真切的,還在于他關(guān)于這種影響達(dá)于文學(xué)修辭方面的闡述。
關(guān)于湯顯祖的創(chuàng)作,李建軍認(rèn)為,“從文學(xué)精神來(lái)看,湯顯祖無(wú)疑屬于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但是,從寫(xiě)作方法來(lái)看,湯顯祖的‘臨川四夢(mèng)’,除了《紫釵記》大體上是用寫(xiě)實(shí)的方法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其他三部全都是象征主義性質(zhì)的作品,就此而言,可以說(shuō),他是用象征主義方法來(lái)寫(xiě)作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家”。他認(rèn)為,湯顯祖的“臨川四夢(mèng)”之“夢(mèng)境”,是作家在“被動(dòng)的境遇”中所選擇的一種“積極的策略”:“湯顯祖的象征主義寫(xiě)作既是被動(dòng)的,也是自覺(jué)的。”“在技巧的背后,人們可以看見(jiàn)強(qiáng)大的皇權(quán)專制,可以看見(jiàn)意識(shí)形態(tài)詭異的面影”。
李建軍指出:“在任何專制主義的寫(xiě)作環(huán)境里,現(xiàn)實(shí)主義都是一種被敵視和壓制的寫(xiě)作方法。”元代的專制統(tǒng)治也很黑暗和嚴(yán)重,知識(shí)分子的地位也很低,但因?yàn)樯儆小拔淖知z”,作家和藝人的自由空間也就相對(duì)大了一些。而與元代相比,明代社會(huì)的思想天空就要黑暗得多,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也要惡劣得多。因此,作為一種安全而積極的敘事策略,湯顯祖喜歡寫(xiě)夢(mèng)境,寫(xiě)夢(mèng)境中有奇人異事,“夢(mèng)境中事,子虛烏有,容易打馬虎眼”。“臨川四夢(mèng)”,《紫釵記》《牡丹亭》以夢(mèng)寫(xiě)人之至性至情,特別是《牡丹亭》,人可以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這是對(duì)人性至真、至純、至美的肯定和贊頌;《邯鄲記》《南柯記》則借夢(mèng)境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和虛妄的人生追求進(jìn)行諷刺和批判。無(wú)論是肯定和贊頌,還是諷刺與批判,以夢(mèng)境來(lái)表現(xiàn),都是一種“安全而積極的敘事策略”,這讓我們對(duì)時(shí)代與文學(xué)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似乎更為內(nèi)在。展開(kāi)來(lái)看,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以詩(shī)詞和文章為主流,這顯然與古代作家的身份構(gòu)成有關(guān)。古代作家基本上是文人士大夫,他們文化高,修養(yǎng)深,且大多居于社會(huì)的上層,而詩(shī)詞文章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和修養(yǎng),才能創(chuàng)作和欣賞,所以,一般而言,詩(shī)詞文章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學(xué),某種意義上說(shuō)是“貴族的文學(xué)”,而不是平民的文學(xué)。現(xiàn)代以來(lái),時(shí)代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社會(huì)改造功能,白話文就大行其道,后來(lái)提倡“為工農(nóng)兵寫(xiě)”甚至“工農(nóng)兵寫(xiě)”,更強(qiáng)調(diào)人民群眾的語(yǔ)言特別是口語(yǔ)化,文學(xué)中“文”的色彩就有些淡化,而“野”的味道就濃了一些。受這種時(shí)代思潮和文化風(fēng)氣的影響,現(xiàn)在的文學(xué),對(duì)詩(shī)詞和文章明顯地不太重視,甚至完全忽視,人們一提文學(xué),似乎只是指小說(shuō)。作家身份的構(gòu)成,從古至今,由文人士大夫而平民而工農(nóng)兵(此時(shí)作家的主體,就是工農(nóng)兵或工農(nóng)兵出身者),這種時(shí)代對(duì)文學(xué)的要求和對(duì)作家的選擇,歷史脈絡(luò)非常鮮明。而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所謂“朦朧詩(shī)”的興起,顯然也與那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氛圍特別是政治狀況有關(guān),是時(shí)代造就了詩(shī)歌“朦朧”的修辭方式和敘事策略。
李建軍在論及湯、莎兩位作家創(chuàng)作的偉大經(jīng)驗(yàn)時(shí),其中有兩點(diǎn)概括:“創(chuàng)作的時(shí)代性”和“集體性共創(chuàng)”,我覺(jué)得對(duì)當(dāng)前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特別富有啟示性。
創(chuàng)作的時(shí)代性就是當(dāng)代性。作品的思想、精神和問(wèn)題首先立足于當(dāng)代,針對(duì)的是當(dāng)代,即使是歷史題材的寫(xiě)作,所指涉的也首先是當(dāng)代。有了當(dāng)代性即時(shí)代性,然后才有可能上升到超時(shí)代的普遍性。李建軍認(rèn)為,湯顯祖和莎士比亞首先是屬于自己時(shí)代的作家,他們的“再度創(chuàng)作”,給后世的作家提供的有價(jià)值的經(jīng)驗(yàn)資源,其中首要一個(gè)就是時(shí)代性。“任何自覺(jué)的寫(xiě)作,都是首先針對(duì)自己時(shí)代的寫(xiě)作。它必須首先立足于當(dāng)代性,然后再由此上升到超時(shí)代的普遍性。”而“一部毫無(wú)時(shí)代性指涉的作品,不可能成為超越時(shí)代的偉大作品;一部不能感動(dòng)自己時(shí)代讀者的作品,也很難感動(dòng)后來(lái)時(shí)代的讀者。”這就要求,“無(wú)論多么古遠(yuǎn)的題材”,“都要將它轉(zhuǎn)化為關(guān)乎時(shí)代生活的敘事內(nèi)容,都要將自己時(shí)代的情緒、問(wèn)題和經(jīng)驗(yàn)灌注進(jìn)去”。這些論述和分析中的點(diǎn)睛之筆,讀之豁人耳目。這種經(jīng)典作家的偉大經(jīng)驗(yàn),對(duì)那種有意無(wú)意回避時(shí)代重大問(wèn)題和普通情緒、忽視時(shí)代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要求,特別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題材的創(chuàng)作,具有警醒和啟示作用。也可以說(shuō),李建軍在這里的研究和論述,也有他的“時(shí)代性”。
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給人以啟示的經(jīng)驗(yàn)資源,還有一個(gè)是“集體性共創(chuàng)”。李建軍說(shuō):“集體性共創(chuàng)是我整合出來(lái)的一個(gè)概念,其基本內(nèi)涵是:一切成熟意義上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為基礎(chǔ),是對(duì)多種經(jīng)驗(yàn)吸納和整合的結(jié)果,因而,本質(zhì)上集體性的,而非個(gè)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參與和創(chuàng)作的,而不是由一個(gè)人師心自用獨(dú)自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它涉及了對(duì)獨(dú)創(chuàng)、生活和內(nèi)心封閉性等問(wèn)題的理解和闡釋。”這個(gè)“集體性共創(chuàng)”觀點(diǎn),說(shuō)清了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gè)根本性問(wèn)題。“創(chuàng)作”固然是一種個(gè)人的“創(chuàng)造”或是某種程度、某種意義上的“獨(dú)創(chuàng)”,但也確實(shí)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為基礎(chǔ),是對(duì)多種經(jīng)驗(yàn)吸納和整合的結(jié)果”。認(rèn)識(shí)到這一點(diǎn),對(duì)創(chuàng)作非常重要的一點(diǎn)啟示,我認(rèn)為就是我們要充分尊重和學(xué)習(xí)前人或同代人的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要 “會(huì)通”古今中外的文學(xué)經(jīng)驗(yàn)。這樣,也許可以少一些那種“無(wú)源之水”和“無(wú)根之木”的所謂“獨(dú)創(chuàng)”,少一些那種不能與時(shí)代、與他人“對(duì)視”和“對(duì)話”的“自言自語(yǔ)”。
李建軍在這里的理論分析也有其“時(shí)代性”。針對(duì)當(dāng)下一些關(guān)于“獨(dú)創(chuàng)性”的言論,他說(shuō):“對(duì)文學(xué)來(lái)講,很多時(shí)候,‘獨(dú)創(chuàng)性’是一個(gè)充滿陷阱的概念。文學(xué)上的完全的‘獨(dú)創(chuàng)’或‘創(chuàng)新’,是不可能的。因?yàn)椋碌慕?jīng)驗(yàn)產(chǎn)生于舊的經(jīng)驗(yàn);只有在舊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才最終形成了一種有意味的‘亦新亦舊’的經(jīng)驗(yàn)。在文學(xué)上,完全與舊經(jīng)驗(yàn)沒(méi)有關(guān)系的‘新經(jīng)驗(yàn)’是不存在的。”這些論述,對(duì)當(dāng)前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長(zhǎng)期流行的關(guān)于“獨(dú)創(chuàng)”和“創(chuàng)新”的一些錯(cuò)謬觀點(diǎn),如所謂的文學(xué)和美學(xué)、后人與前人“斷裂”一類甚囂塵上的說(shuō)法,確實(shí)有補(bǔ)偏救弊之用。
《并世雙星》是一部扎實(shí)的學(xué)術(shù)著作。書(shū)中所有立論,許多很有見(jiàn)地的觀點(diǎn),都有極扎實(shí)的論據(jù)做支撐,論證嚴(yán)密,以理服人。同時(shí),又以飽滿的感情以及華彩篇章打動(dòng)人,很有感染力。這是一部思與詩(shī)并美的學(xué)術(shù)著作。李建軍對(duì)東西方兩位偉大作家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的發(fā)掘和提煉,無(wú)疑是當(dāng)今創(chuàng)作以及未來(lái)創(chuàng)作不可忽視的一個(gè)經(jīng)驗(yàn)資源。這是《并世雙星》紀(jì)念兩位戲劇大師應(yīng)有的現(xiàn)實(shí)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