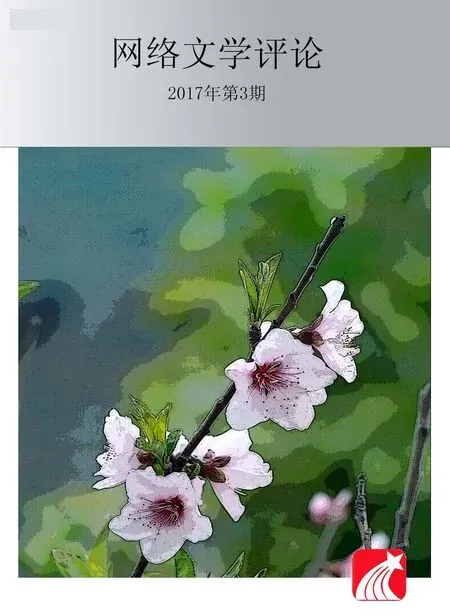新媒體與科幻電影的發展
文/黃鳴奮
通常所說的“媒體”至少有三種不同的含義:一是指包括聲音、氣味、圖像、文字等在內的交往手段,它們對應于人類不同的感覺通道,在藝術領域中轉化成為不同的表現手段、不同的樣態劃分;二是指人類通過信息革命所創造的各種傳播平臺,它們對應于人類不同的信息網絡,在藝術領域中轉化成為不同的衍生產品、不同的運營空間;三是以加工和傳播信息為已任的社會角色,他們對應于人類不同的崗位劃分,在藝術領域中轉化成為不同的思維定勢、不同的創意取向。“新媒體”之“新”既可能體現為從無到有的發明,也可能體現為反常合道的應用,還可能體現為革故鼎新的努力。科幻電影為我們把握新媒體的演變規律和發展趨向提供了有價值的個案,因為它既是一種已經獲得公認的藝術樣態,又是一種富有價值的信息資源,同時還代表了一種激濁揚清的創新精神,值得深入研究。
一、科幻電影與作為表現手段的新媒體
在發生學的意義上,人在社會交往中首先將自己的身體及其衍生物(如發音)作為表現手段,然后將應用工具所制造的產品(如飾物、圖符等)作為表現手段。與上述過程的演進相適應的新媒體在不同歷史時期具備不同的含義。就與科幻電影的關系而言,活動影像、多媒體影像和數碼影像是我們認識新媒體特征的三個切入點。波蘭羅茲大學克呂辛斯基(Ryszard W.Kluszczynski)就此指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電影是唯一賦予活動圖像性的藝術,如今卻必須在非同尋常的條件下尋求其身份。它已經變成只是眾多活動影像藝術中的一種,因此必須做出有關如何在復雜多變的多媒體音像藝術中定位自身的抉擇:或者仍然培育傳統的原則和形式,僅僅將數碼技術當成工具;或者朝交互性電影轉變,拋棄當前的慣例,為觀眾提供迥然有別的體驗,即重視數碼媒體。①這段話有助于我們理解科幻電影的發展和作為表現手段的新媒體的關系。
(一)活動影像與科幻電影的發展
活動影像是訴諸人類視覺器官的有效信號。它是從活動圖像中分化出來的,以投映于屏幕之影區別于西洋鏡之類器具所直接呈現的畫面。對于19世紀末的觀眾來說,它是貨真價實的新媒體。由于活動視鏡(1877)、電影攝影機兼放映機(1886)等發明的問世,活動影像逐漸具備了流行的條件。美國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所發明的電影視鏡(1893)將活動影像展現于一個小匣子,讓人窺視。法國盧米埃爾兄弟(Lumière Brothers)制成的電影機采用直接放映方式,面向公眾,這標志著電影的誕生(1895)。通常將法國梅里愛(Georges Méliès)拍攝的短片《月球旅行記》(Le voyage dans la lune,1902)當成科幻電影史的起點。實際上,梅里愛在此之前還拍攝了科幻題材的《小丑與自動化》(Gugusse et l'automaton,1897)、《 倫 琴 射線》(Les rayons R?ntgen,1898)等。盧米埃爾兄弟拍過科幻題材的《熟食機械公司》(La Charcuterie mécanique,1895),英國的史密斯(George Albert Smith)也制作了《X射線》(The X-Rays,1897)。也許是由于它們的情節相對簡單,因此未受到足夠的關注。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將科幻電影史上溯到19世紀末。
活動影像不僅是我們認識科幻電影誕生契機的切入點,而且是我們認識科幻電影演變的重要參照系。早期的影片幾乎都是二維的。至遲在20世紀50年代初,出現了美國《宇宙訪客》(It Came from Outer Space,1953)那樣的黑白三維片。這類電影以高度逼真的畫面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受,在當時顯示了高技術的震撼力。后來的各種彩色3D大片正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二)多媒體影像與科幻電影的發展
多媒體影像是同時訴諸人類多種感覺通道的活動影像。它誕生的標志之一是1900年在巴黎進行的配音電影公開演示。從1910年開始,電影進入了從無聲片向有聲片過渡的歷史時期。作為新媒體的有聲片以多媒體影像(而非單純視覺性活動影像)作為表現手段。它得益于愛迪生所發明的可以同時攝影、留聲的機器(1910),藝術化于華納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1927)、《紐約之光》(Lights of New York,1928),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逐漸普及,并導致作為舊媒體的無聲片壽終正寢(1936)。就科幻電影而言,美國電影《化身博士》(Dr. Jekyll& Mr.Hyde,1931)是早期有聲片之一。它由馬莫利安(Rouben Mamoulian)執導,派拉蒙電影公司制片并發行,負責音樂的是漢德(Herman Hand)。到1936年之后,有聲片已經是科幻電影的基本形態。
為了增強多媒體影像所產生的心理效果,電影工作者進行了不少嘗試。例如,騎乘電影讓觀眾坐在液壓控制的可移動平臺或座位上,體驗與巨大的活動影像及環境音響同步的傾斜、旋轉、搖晃。美國環球電影公司推出的《大地震》(Earthquake,1974)啟發了主題公園的相應景點設計,環球影城和好萊塢都有這類訴諸多種感覺通道(除聽覺和視覺之外還訴諸觸覺、動覺等)的景點。
(三)數碼影像與科幻電影的發展
數碼影像依托算法在計算機上生成,區別于先前的各種影像。20世紀中葉,以計算機為龍頭的信息革命爆發。受其影響,電影(包括科幻電影)逐漸實現了數字化轉型。數碼電影術(digital cinematography)開始作為新媒體的獨立范疇起作用。
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是電影從模擬技術向數碼技術轉型的歷史時期,其標志性事件幾乎都和科幻電影相關:美國《西部世界》(Westworld,1973)率先運用了數碼圖像處理技術,標志著電影從特技入手推進數字化。1979年,英、美合拍片《異形》(Alien)率先利用電腦技術描繪了外星怪物對人類的襲擊。這是第一部采用三維計算機圖像的長片。《電子世界爭霸戰》(Tron,1982)率先描繪賽伯空間的奇景;《星球迷航》第二集《可汗之怒》(Star Trek II: The Wrath of Khan,1982)率先用顆粒著色算法描繪生命在一個星球上的誕生……科幻電影編導敞開胸懷歡迎數碼影像,因為他們比別人更需要它的卓越表現力。1999年6月18日,美國《星球大戰I:幽靈的威脅》(Star Wars,Episode I:The Phantom Menace)開始進行全球數字電影的首次商業放映(為期一個月),這標志著世界數字電影發展史元年的到來。如今,數字電影主要不是指僅僅將數字技術運用于制作特效的電影,而是指全面將數字技術應用于拍攝、后期加工和發行放映等環節的電影。
以計算機為龍頭的信息革命不但促進了電影的數字化轉型,而且更新了人們對于先前就已經存在的活動影像、多媒體影像的認識。如今我們所理解的活動影像不僅來源于用照相器材所進行的拍攝,而且來源于計算機通過各種算法所進行的生成,所謂“引擎電影”(Machinima)就是這樣誕生的。如今我們所理解的多媒體影像也不僅是指既有圖像、又有聲音,而且是指可以在不同平臺上自由流動、訴諸用戶不同感覺通道(不限于視覺)、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人機交互、充分滿足人類馳騁想象之需要的媒體,所謂“虛擬現實電影”(VR Movie)就是這樣構想的。因此,從表現手段對科幻電影所進行的考察既必須關注各種科幻游戲所包含的過場動畫(屬于引擎電影),又必須關注各種數碼娛樂所呈現的動態奇觀(涉及虛擬現實電影)。這些科幻游戲或數碼娛樂有些和科幻電影本來就出自一源(如大名鼎鼎的《星球大戰》系列、《蜘蛛俠》系列等),有些已經實現了向科幻電影的轉化(如《星際爭霸》等)。
二、科幻電影與作為傳播平臺的新媒體
人類歷史上先后爆發了以口語、文字、印刷術、電磁波和計算機為標志的五次信息革命。每次信息革命的成果都通過打造新的傳播平臺等形態表現出來。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才有相輔相成的“口碑”、“文苑”、書刊報紙發行網、廣播電視網和移動互聯網絡。從歷史上看,科幻電影作為信息固然可以通過所有這五種平臺獲得傳播,作為本體(即活動影像)卻只有依托后兩種平臺才能充分展示其風采,至少在基于增強現實技術的交互式印刷流行開來之前是如此。不過,由于上述五種平臺如今都在數字化大潮中朝新媒體轉變,因此,科幻電影與它們的聯系正多側面、多方位地顯現出來。在這樣的背景下,加拿大肯考迪婭大學沃森(Haidee Wasson)指出:電影不論作為活動影像或者作為物品,早就是時空專門化的物質網絡的一部分。這種網絡包括諸如膠卷罐、郵件之類運送方法,也包括輪船、火車、飛機以至于電視頻道等傳送節點。這些方法和節點都是電影史的一部分。如今網絡化電影發展出兩種迥然有別的形式:一種是小巧的“迅時”,另一種是巨大的IMAX系統。不過,它們都宜于好萊塢電影,都有其對應網絡的標志。②
(一)電力網絡與科幻電影的發展
早期電影以影院為主要傳播平臺。原先的劇院只要能放電影,就成為影院(Movie Theatre)。專門為放映電影而建造的場所(Cinema)固然有之,但非專門性的場所也不是不能放電影。唯一的必要條件是那兒得有電力供應。沒有電力,就沒有電光源,也就沒有電影。這是不言而喻的。電力網絡鋪設到哪里,那兒的演藝場所就可能告別燭光照明或油燈照明,就可能使用電影放映機,原先的劇院就可能朝影院轉化。輸電線路將分布在不同區域、不同街道、不同場所的影院聯接在一起,使之成為電影的傳播平臺。當然,在電影實現數字化之前,影院之間的跑片還需要電力網絡之外的交通設施的支持。但是,任何電影拷貝都只有在電光源的照耀之下才能顯示出活動影像。就此而言,電力網絡的決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雖然電力網絡至今為止仍然主要是能源網絡、讓它同時兼有信息網絡功能的努力僅僅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但是,它對于科幻電影和新媒體聯姻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作為中介,電力網絡促使科幻作品將傳播平臺由書刊報紙發行網轉移到廣播電視網,有力地促進了觀眾由讀書向“讀屏”的轉變。早先主要通過印刷品傳播的科幻小說因此得以大量朝科幻電影轉化。這種現象早在1898年就已露端倪。當時法國出品的《太空人的夢》(La lune à un mètre)就基于著名科幻作家凡爾納(Jules Verne)的小說《月界旅行》(De la Terre à la Lune,1865)與《環繞月球》(Autour de la Lune,1870)。20世紀以來,這類改編在科幻電影領域比比皆是。例如,英國作家雪萊夫人(Mary Shelley)的小說《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受到科幻電影編導的鐘愛,先后十余次被搬上銀幕。值得重視的另一個歷史現象是:從20世紀30年代中葉起,一些帶有科幻色彩的連環漫畫被改編成系列電影。美國13集系列片《飛俠哥頓》(Flash Gordon,1936)就是一部標志性的作品。圖畫和影像之間的相互轉換,至今仍通過美國漫威漫畫公司(Marvel Comics)所塑造的超級英雄等產品顯示出巨大魅力。
(二)電視網絡與科幻電影的發展
廣播電視網絡是第四次信息革命所打造的傳播平臺。電影就其本性而言是活動影像,因此和電視網絡的關系更為密切,雖然也有某些影片取材于廣播劇,如英國科幻片《航天之路》(Spaceways,1953)等。
電視網絡是以電信技術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和以電光源技術為基礎的電影本來運行于不同軌道,但它們也存在交會之處,所謂“電視電影”(TV movie)可以為例。早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雷電華影業公司(RKO Pictures Inc.)就制作了這類專供電視放映的影片,在紐約市電視臺WABD播出。科幻電影將電視網絡當成新的傳播平臺的現象,始于20世紀50年代。當時,美國導演亞歷克斯(Alex Segal)推出了《謀殺與機器人》(Murder and the Android,1959)。此后,科幻電視片的數量日益增多,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日本石井輝男(Teruo Ishii)執導的《空間入侵者》(Invaders from Space,1964)、美國布坎南(Larry Buchanan)執導的《金星怪人》(Zontar,the Thing from Venus,1966)、美國薩拉菲安(Richard C. Sarafian)執導的《地上之影》(Shadow on the Land,1968)等。
電視電影在視聽效果方面比不上劇場版,但在傳播上卻具有便于融入家庭生活等優勢,和電視電影具有親緣關系的科幻電視劇在容量上更是無與倫比。例如,英國BBC出品的科幻電視劇《神秘博士》(Doctor Who)1963年11月23日首播,至今已經播出800多集。就供給端而言,某些科幻作品在影視界發展成為陣容強大的系列,如美國《星際迷航》(Star Trek,1966-)目前已有6部電視劇、1部動畫片、13部電影,堪稱“人丁興旺”。它不僅在社會上催生了諸多科幻迷,而且引發了學術界的重視。以之為研究對象的論著已有多種,如杰洛德(David Gerrold)與薩耶斯(Robert J. Sawyer)合著的《登上企業號:吉恩·羅登貝瑞〈星際迷航〉中的傳輸、毛球族與瓦肯人的死亡支配》(2016)③等。
(三)移動互聯網絡與科幻電影的發展
基于數字技術的移動互聯網絡是第五次信息革命所打造的傳播平臺,也是網絡電影生長的溫床。1993年,美國導演布萊爾(David Blair)推出當時最大的超媒體敘事數據庫——《蠟網》(Wax)。它基于布萊爾本人1991年拍的長度為85分鐘的科幻片《蠟:蜂群中電視的發現》(Wax or the Discovery of Television Among the Bees),被認為是第一部在線長片。換言之,網絡電影是以科幻片為先鋒而載入史冊的。
若將網絡電影理解為在互聯網上首發而專門拍攝的電影的話,那么,Sightsound.com公司所策劃的短片《量子計劃》(The Quantum Project,2000)可以為例。它由阿根廷的扎尼提(Eugenio Zanetti)執導,講述物理學家、奇才保羅對量子宇宙的探索與其生活、尊嚴與愛情沖突的故事。近年來,網絡大電影在我國風頭正健。由于科幻片通常包含大量特效、制作成本較高,因此在以低預算為特點的網絡大電影中并非主流,不過,也出現了《墓志銘》(EPI,2016)、《妙齡爺爺》(2016)這樣的作品。前者講述某手術系統形成自我意識篡改重生者大腦、屠殺人類的故事;后者則描述被外星人抓走的爺爺托體妙齡女椰椰向孫子示警,兩青年在抵抗外星人入侵過程中漸生情愫。與之相關的新品種是網絡劇。在我國,2016年被業界稱為“中國科幻網絡劇元年”。此前,土豆網《烏托邦辦公室》(2011)、北京幻思《金剛葫蘆俠》(2014)、上海聚力等《執念師》(2015)、杭州新媒世傳《大面曹天》(2015)等作品絡繹問世,而且反響都不小,已經為我國科幻網絡劇的興盛做了鋪墊。PPTV聚力等《執念師2》、銀潤傳媒《迷航昆侖墟》、合心天譽(東陽)等《天才聯盟》、杭州已立《命運規則》、騰訊視頻《微能力者》與《守護者》等科幻網絡劇同在2016年播出,彼此響應,使這一領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氣象,這是“元年”之說的根據。不僅如此,我國科幻網絡劇還顯示出強大的后勁。因此,在產業的意義上,“元年”并非止步之年,而是振興之年。
盡管移動通信網絡早已深入千家萬戶、移動視頻的應用也日益廣泛,但是,手機電影的定義、起源及其和科幻的關系仍是有待進一步考察的問題。在世界范圍內,英國“未來一切”(FutureEverything,1995-)藝術節將“移動與位置媒體”(Mobile & Locative Media)當成議題(2003-2006),美國“洛杉磯自由波”(The LA Freewaves,1989-)、“新媒 體電影節”(New Media Film Festival,2010-)等節展都對移動媒體予以關注。2004年12月1日,美國Zoie電影公司舉辦首屆全球性手機電影節(Zoie Cellular Cinema Festival)。2006年10月15日,我國西安舉行了首屆手機電影大賽,由崔雪峰導演的科幻片《第三界》獲得創意大獎。本片所表達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必須和諧相處的理念。雖然手機電影已有十余年的歷史了,若將它理解為完全以手機為工具進行拍攝、加工、傳播與欣賞的電影,那么,它在科幻領域迄今為止仍然乏善可陳(像《第三界》那樣的作品相當罕見);若將它理解為由專業工作者對電影進行適應移動通信特性的再制作,或者是由手機用戶通過網絡付費方式進行觀賞,那么,它對科幻電影的流通倒是已經發揮了一定作用,因為不少手機電影網站都設有科幻頻道,像國內的80s電影網、在線6手機電影、8億手機電影、A6780手機電影等都是如此。吉布森(Ross Gibson)認為電影是使時間碎片化、細薄化的藝術形式之一,未來電影將朝這方面繼續發展(2003)。④
手機電影看來是順應了這一潮流。
從總體上說,電影在上述電力網絡、電視網絡和移動互聯網絡支持下的發展呈現出去地域化趨勢,所追求的是在全球信息基礎設施中的自由流動。不過,由于增強現實、衛星定位等技術的滲透,加上逆全球化潮流的激蕩,電影發展又呈現出再地域化趨勢,表現為對城市空間的深入融合。例如,法國藝術家拉米斯(Catherine Ramus)與德利特雷茲(Caroline Delieutraz)《M 理論》(Théorie M,2006)借鑒了當前仍在發展的以承認物理世界之多維、探索宇宙之多重為特色的M理論,將互聯網、移動電話、電影、繪圖法和城市空間結合起來。它給巴黎城貼上了二維代碼(一種由黑白方塊組成的矩陣條形碼),每個代碼都與一段可在手機上觀看的電影相聯系。在相應的網站(www.theoriem.net)上,個性化的Google地圖為上述標簽做了定位。這一作品因此將現實宇宙和虛擬空間重疊起來。像這樣的作品亦真亦幻,表現了地域化與去地域化、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矛盾。
三、科幻電影與作為構思內容的新媒體
科幻電影不僅將新媒體當成表現手段和傳播平臺,而且將新媒體當成構思對象,對它的歷史、現狀及其與人的關系予以審視,對它的前景加以展望。在這一意義上,新媒體是科幻電影的內容,來自科幻電影編導的想象。盡管具體的科幻影片在內容上都有所側重,但是,由兩千多部(這是筆者所統計的數字)科幻電影所組成的藝術長廊卻作為集合體為觀眾展示了迥異于現實環境的大千世界。在科幻世界中,就物的意義而言,新媒體可能是多樣化智能生物用以交往的手段,由新穎科技所支持的信息工具和產品,或者多重宇宙之間彼此往來的途徑;就人的意義而言,新媒體是具有新定位、新能力和新使命的社會角色,或者說是活躍于跨物種交往、跨物態交往和跨時域交往領域的新人物。下文所關注的主要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新媒體。
(一)跨物種交往與科幻電影的發展
科幻世界以多種智能生物并存為特征。媒體必須不斷推陳出新,才能適應原版人與克隆人、純種人與變種人、電子人與機器人、實體人與虛擬人、地球人與外星人等彼此溝通的需要。很難預測這些智能生物之間的交互需要多少種類型的媒體來支持,也很難預測這些媒體將通過什么樣的通道發揮作用,因為不同種類的智能生物完全可能擁有不同的感受器、處理器與效應器,殊別迥異的生存環境完全可能有大相徑庭的要求。這既是未來實踐的難題,也是現在構思的機遇。就此而言,科幻電影大有可為。
就其字面意義而言,“媒體”是媒人之體,是作為中介的人的身體。當人們將弘揚主體性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時,媒體似乎成為工具性、手段性、附屬性的東西,新媒體似乎只是人類的新工具、新手段、新附屬。然而,在跨物種交往的視野中,人本身(首先是人的身體)是具有本體性、目的性、主導性的媒體,因為是人引領同時并存的多種智能生物的發展,主動調整他們之間的關系,擔負著不同生物之間相互溝通的使命。就此而言,美國動畫片《最終幻想:靈魂深處》(Final Fantasy:The Spirits Within,2001)表達了這樣的觀念:萬物皆有靈魂,星球也不例外。支配各自星球的靈魂的地球蓋亞(原始神或星球靈魂)和外星蓋亞必須和平相處,宇宙才能安寧。為了實現不同蓋亞之間的溝通,格雷上尉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體充當傳導靈魂波的媒體。他雖然因此而死亡,但也因此魂歸蓋亞而永生。能夠溝通不同星球靈魂的媒體是現階段任何媒體都無法比肩的,在發揮了這種前所未有的功能方面無疑是新媒體。充任這種新媒體的是人,當然不是凡夫俗子,而是具有高度使命感和獻身精神的人。
(二)跨物態交往與科幻電影的發展
現階段人們對于新媒體的認識主要是依托電子計算機這一參考系建立的。這體現了20世紀中葉爆發的第五次信息革命的深刻影響。盡管如此,新的信息革命正在醞釀之中,量子計算機可能就是它的旗幟。我們無從知道未來量子計算機的細節,但盡可以依托量子計算機的原理展開想象。如果量子比特序列不但可以處于各種正交態的疊加態上,而且還可以處于糾纏態上,那么,以之為依托的量子通信、量子媒體勢必具備有別于當下電子媒體的特征。早在1987年,一群旨在追求跨學科的西方藝術家就在《多變媒體宣言》(1987)中宣告:“量子機制已經證明最小的基本粒子(如電子)存在于不斷變化的形式中。它們沒有穩定的形式,卻以動態可變性為特征。電子的這種不穩定的、靈活的形式是多變媒體的基礎。”⑤
就科幻電影有關新媒體的創意而言,量子學說所給予的啟示之一是多樣化物態及其相關性。如果我們自己可以因為處身不同維度的空間而具備不同的存在狀態,那么,如何進行自我交流,又如何與人交流?這是英美合拍片《星際穿越》(Interstellar,2014)所觸及的問題之一。在影片中,想用重力波向書房中的父女傳遞編碼信息的未知智能生物居然是穿越蟲洞到了五維空間的父親,他想幫助女兒破解人類撤離地球的關鍵問題,與之交流量子數據。不同維度空間的交流無疑是難題,本片只想到應用莫爾斯電碼,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其實,這無疑蘊含著媒體創新的契機。同年出品的美國影片《超驗駭客》(Transcendence,2014)想到利用量子計算機實現幽明世界之間的通信,讓生者與死者(其意識上載于虛擬空間)對話。這種新型計算機是否有助于實現不同維度空間的交流呢?或者說,如果有了量子計算機,人們是否可能發現自己果真(同時)存在于不同維度空間?生生死死也許不過是不同維度空間的來來去去。特定維度空間的我們也許只是生命在眾多平行宇宙之間一種存在形態。多重自我為什么非得像美國動作驚悚片《宇宙追緝令》(The One,2001)那樣拼得你死我活呢?也許,樂于充當媒體、善于溝通,將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
如果我們發現他人除通常身體狀態之外還有其他存在狀態,那么,如何恰當地與之互動?這是美國《幽靈》(Spectral,2016)觸及的問題。它講述了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一位科學家接受一項致命任務,帶領一群精挑細選出來的的三角洲部隊士兵進駐一個被戰爭摧毀的城市。這里游蕩著被稱為“幽冥”的神秘生物,它們由亦生亦死的人轉變而來,無形無色,出沒不定,能在不經意間造成大規模的傷亡,其特點是幾乎全部原子都聚集到能量最低的量子態,形成宏觀的量子狀態。這就是物質第五態——玻色-愛因斯坦凝聚態。生產、組織和控制這類幽靈的方法是東南歐小國家摩爾多瓦的官方科學家發現的。他們曾經可以給它們下達命令,指揮它們遠程行動,可惜最后失控了。盡管在本片中這些人是沒有多少戲分的否定性角色,但他們的科研成果已經通過四處出沒的幽靈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些幽靈連同其基地最終都被美國特種部隊所消滅,但有關物態的想象無疑仍將通過類似影片的構思和欣賞得以延續。除了我們所熟知的狀態之外,生命的存在狀態究竟還有哪些?與我們交往的其他人究竟是其生命或自我的唯一本體,或者只是引導我們去認識其本體的某種多變媒體?多變而無常,是否必定代表宇宙中的惡?我們能夠欣賞其他人在多種存在狀態中所呈現的美嗎?對于諸如此類的問題,烏托邦電影和惡托邦電影可能給出不同創意。
對習慣于單一狀態生存的人來說,同時性多態存在無疑很怪異,不論亦生亦死、亦此亦彼,還是亦人亦己、亦趨亦返,都是如此。在加拿大《異次元殺陣2:超級立方體》(Cube 2:Hypercube,2002)、美國《創世紀》(Terminator Genisys,2015)等影片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類創意的痕跡。神奇的量子設備被用于直接從佩戴者的大腦皮質中記錄事件,如美國《末世紀暴潮》(Strange Days,1995)中的超導量子干涉儀;又被當成非人類的自我意識的物質承擔者,如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合拍的《絕密飛行》(Stealth,2005)中加載有人工智能“艾迪”的球形量子計算機;也被用為前往未知奇異世界的端口,如美國《神奇四俠》(Fantastic Four,2015)所描繪的量子門。澳大利亞《無極》(Infini,2015)則告訴觀眾:人可以量子化傳送到別的地方再還原,由他們脖子上的裝置完成。也許,量子通信技術所取得的突破真的能夠掀起新一波信息革命,造就不同于當今數碼媒體的量子媒體。這場新的信息革命的弄潮兒,將是標領風騷的新媒體(人)。
(三)跨物域交往與科幻電影的發展
我們所說的“跨物域交往”特指源于古代靈媒某種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活動。這些靈媒據說能夠和鬼神交流,溝通陰陽兩界。不論在古代傳說或當代奇幻中,都有他們的身影。這類人也出現在科幻電影中,但往往經過科技之光的折射。例如,美國《魔域煞星》(Dreamscape,1984)描寫政府機構招募靈媒,利用共享夢境技術將觀念植入美國總統心靈。本片中,靈媒行事的奧秘變成了科研課題。又如,美國《超能敢死隊》(Ghostbuster,1984)設想紐約三個前超心理學教授開商店提供驅鬼服務,將科學家變成了靈媒。
靈媒既能回到過去,與先人對話;又能前往未來,與后人對話;還能周行異域,與鬼神對話。盡管如此,裝神弄鬼畢竟不符合科幻的本性。因此,源于古代靈媒的跨物域交往在科幻電影中接受了相對徹底的改造,以時間旅行的形態表現出來。現實生活中的人們所習慣的是以時間不可逆為前提創立的各種模式。在空間維度上,它們可以允許信息多向擴散;在時間維度上,它們卻只允許信息單向傳播,亦即由過去流向現在,由現在流向未來。在科幻世界中,信息在媒體中流動的向度要復雜得多。如果信息由未來流向現在,這就成了前景預測;如果信息由現在流向過去,那就成了后顧啟示;如果信息在不同時間線之間流動,那就成了橫向交錯。如果進行復雜方向流動的不僅是信息,而且是攜帶上述信息的人,那么,這就構成了時間旅行(常言之“穿越”);如果實現上述流動的是某種專門化的工具,那就構成了時間機器。在某種意義上,時間旅行者就是科幻電影所特有的媒體(人)。他們像傳統靈媒那樣可以穿越于不同時空之中,發揮溝通不同時間段、時間線(因而也可能溝通不同空間域)的作用,又沒有傳統靈媒那種神秘氣息。
與魔幻、玄幻相比,科幻的特點是試圖根據科學原理來解釋科技起作用的機制,或者根據人倫規范來反思科技所可能帶來的后果。在所有的媒體科技中,難度最大的恐怕要數試圖讓時間定位可以任意變化的媒體工程。這當然不是說撥弄一下鐘表指針或重設電子定時器讀數那樣在名義上改變時間定位,而是指實際改變當事人所處的時間坐標,甚至改變整個周邊環境的時間參數。正因為如此,相關想象獲得了科幻電影編導的格外喜愛。例如,有關時間機器的描寫至遲在20世紀40年代的科幻電影中就已經出現,美國系列片《布里克·布拉德福德》(Brick Bradford,1947)可以為證。迄今為止,多少和時間機器相關的科幻電影估計多達數百部,直接以之為名的至少就有匈裔美籍波爾(George Pal)執導的美國長片(1960)、英國威爾斯(Simon Wells)執導的美國長片(2002),還有美國(Alexander Singer)執導的電視片(1978)、印度阿萊提(Arati Kadav)執導的短片(2016)等。
跨物種交往、跨物態交往和跨物域交往構成了科幻世界多種智能生物互動的基本場景,也構成了新媒體發展的科幻背景。在這一背景中,新媒體固然可能是某種表現手段或傳播平臺,但最主要的還是人,或者說是致力于溝通不同物種、不同物態、不同物域的社會角色。他們之所以成其為“新媒體”,既是因為所具備的新能力,也是因為所承擔的新使命。
上文分別從表現手段、傳播平臺和創意內容三個層面考察了新媒體與科幻電影發展的關系。大致而言,作為表現手段的新媒體豐富了科幻電影的形式,作為傳播平臺的新媒體開拓了科幻電影的渠道,作為創意內容的新媒體激發了科幻電影的想象。反過來,科幻電影也以自己層出不窮的作品推動表現手段、傳播平臺和創意內容的推陳出新。人機互動的夢幻界面、作為虛擬世界的賽伯空間、多元宇宙中的時間旅行等議題之所以膾炙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科幻電影的推波助瀾。不僅如此,科幻電影對新媒體應用所可能導致的消極影響頗為警覺,從不同角度加以批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拙著《科幻影視對新媒體的展望與批判》(《福建論壇》2017年第4期)。
注釋:
①Kluszczynski,Ryszard W. From Film to Interactive Art: Transformations in Media Arts.In MediaArtHistories.Edited by Grau,Oliver.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2007,pp.207-214.
②Wasson,Haidee.The Networked Screen:Moving Images, Materiality, and the Aesthetics of Size.In Fluid Screens, Expanded Cinema.Edited by Janine Marchessault and Susan Lord. Toronto;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pp.74-95.
③Gerrold, David, Robert J. Sawyer.Boarding the Enterprise: Transporters, Tribbles, And the Vulcan Death Grip in Gene Roddenberry's Star Trek.New York, NY, US: BenBella Books, Inc.,2016,
④Gibson,Ross.The Time Will Come When....In Future Cinema: The Cinematic Imaginary after Film.Edited by Jeffrey Shaw and Peter Weibel.Cambridge, MA: London: MIT, 2003,pp.570-571.
⑤V2_Organisation.Manifesto for the Unstable Media. 1987. http://framework.v2.nl/archive/archive/node/text/.xslt/nodenr-124560.[2009-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