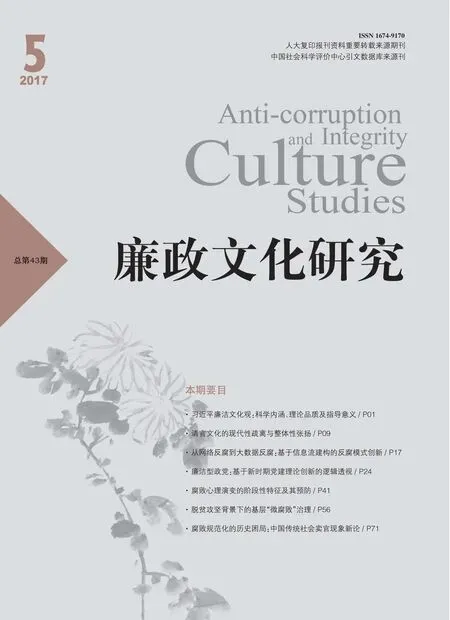腐敗規范化的歷史困局:中國傳統社會賣官現象新論
謝紅星
(江西財經大學 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腐敗規范化的歷史困局:中國傳統社會賣官現象新論
謝紅星
(江西財經大學 法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中國傳統社會的賣官包括制度性賣官和非制度性賣官。制度性賣官公開進行,錢入國庫,非制度性賣官私下進行,錢入私門。我國古代封建王朝的國家汲取能力存在欠缺,財政收入不能隨經濟的增長而穩定增加,但開支卻無限制膨脹,導致財政危機一再發生,政府不得不動用賣官這一政策工具來籌措經費。制度性賣官的制度化水準不斷得到提高的同時,非制度性賣官如影隨形,滲入制度性賣官的體系中,沖擊制度性賣官的實施,并最終“淹沒”了制度性賣官。制度性賣官的失范及非制度性賣官的泛濫,意味著封建王朝政府將賣官規范化努力的失敗。腐敗本質上是反制度、反秩序、反規范和不可控的,封建王朝政府將賣官規范化的嘗試和努力,必定陷入非制度性賣官“淹沒”制度性賣官、反規范化趨勢壓倒規范化努力的歷史困局。
制度性賣官;非制度性賣官;隱性腐敗;潛規則
傳統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官職及隨之而來的權力既是士人一展抱負成就自我的前提,也是個人錦衣玉食光宗耀祖的基礎。與務農做工經商相比,做官是最劃算的投資,是最佳的人生選擇。“人生得意時,金榜題名日”,對廣大寒門士子來說,金榜題名,穿上官服,是人生命運改變的開始,是家族社會地位上升的起點。
然而,“官員有數”,“而入流無限”,(《唐會要》卷 74《選部上·論選事》)在傳統社會,“官缺有定數”和“參選之人無限膨脹”之間,存在著永遠無法避免、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這一矛盾使得仕途壅塞成為盛世官場之常態,同時也催發了官員銓選中經常性的大面積腐敗。其中,最常見、最具有代表性的銓選腐敗,就是平常說的賣官。傳統社會的賣官現象包括哪些類型?有什么可資借鑒之處?本文擬對此展開探討。
一、制度性賣官的背后:走不出的循環
在傳統社會,賣官指公開或私下地“出售”官職、品級、爵位、任官資格、晉級資格等,將官位作為商品處分的現象早在先秦就出現了,《韓非子·八奸》:“(今)父兄大臣請爵祿于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五蠹》:“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
官爵是國家公器,代表著不同于金錢財貨的權力、地位、榮譽與尊嚴,尤其在等級社會,將官爵作為商品出售處分,勢必破壞上下有別、貴賤有等的等級秩序,顛覆尊賢使能、量功授官的行政倫理,最終損害國家的政治統治與公共管理。正因為如此,韓非認為“賣官爵”是“亡國之風”,《管子·八觀》也稱“上賣官爵,十年而亡”。但同屬法家的商鞅對出售官爵卻做出了不同的判斷,《商君書·去強》:“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商君書·勒令》又曰:“民有余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戰國之世,弱肉強食,商鞅變法,農戰為先,商鞅從秦國富國強兵兼并一統的眼前功利出發,將“納粟授官”合法化、正式化,這種基于急迫的眼前功利而階段性出售官爵的做法,為后世王朝所采用。秦王政四年(前243年)十月,“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是為救災而賣爵。兩漢時期,文帝、景帝、武帝、成帝、安帝、桓帝、靈帝都賣過官,或為募集糧食充實邊防,或為籌集軍費,或為賑濟貧民,賣的范圍從爵位逐漸擴展到低等的吏、郎職位。魏晉南北朝適逢亂世,戰亂頻繁,官府經常有籌集軍費而賣官爵之舉。之后隋代享國不長,賣官尚未制度化。唐前期基本上未實施過賣官的政策,安史之亂后,戰亂迭起,國用不足,肅宗、德宗、憲宗、僖宗都頒布過賣官的詔令。五代各朝賣官制度化獲得進展,制度性賣官的種類頗為繁多,有進納官告綾紙標軸錢、光省禮錢、光臺錢、尚書省禮錢、節度使代平章事納禮錢、束修錢、光學錢等。宋代制度性賣官通常被稱為“進納”、“納粟”、“入貲”、“納貲”、“獻納”、“獻助”,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神宗直至南宋滅亡為止,朝廷都因財政危機多次公開實施賣官,有時甚至減價賣官。元代立國后,政府為賑災相繼在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泰定二年(1325年)、文宗天歷二年(1329年)、三年(1330年)實行“入粟拜官”,但此時向“入粟”者“實授”的只是屬于“茶鹽流官”和“錢谷官”的低級職位,到了元順帝年間,由于國運危殆,政府向吏民開放出售“路府州縣官”,然而因元王朝大勢已去,應者寥寥。
明清兩代是制度性賣官臻于完善的時期,其時賣官被稱為捐納。明代捐納產生于正統、景泰之間,此后捐納不斷放開,持續實施,總的趨勢是由地方化轉向全國化,由臨時的權宜之法轉為常制,由捐納散官冠帶擴展為捐納監生、科考資格、參選優先權、開復處分乃至實職,在制度化方面取得重要進展。成化二年(1466年),出現了目前所能看到的為時最早的捐納則例:“在京各衙門辦事官吏納豆出身則例”和“申明辦事官吏納豆則例”。[1]清順治六年(1649年)清廷首開“捐監”,此后康熙、雍正年間,又多次開捐,乾隆即位后,將一部分捐納項目固定下來,作為經常性捐納項目,從此清代捐納有“現行事例”和“暫行事例”之分,“現行事例”又稱“常捐例”,指常年開辦的捐納,旨在籌措經常性經費,主要是職銜、封典、加級記錄、取消行政處分之類,與“實授官職”無關,“暫行事例”又稱“大捐”,指為籌措急需特定經費,在一定時期內開辦的捐納事項,其與“現行事例”最大的區別是,符合條件的可以捐納郎中以下京官及道員以下外官的任職資格(含銓選、晉升時的優先資格)。清代捐納賣官在制度化水準方面堪稱歷代之最,提供多種供報捐者選擇的報捐流程,在印結的出具、捐升、捐復、捐納出身者的候補與銓選等方面,也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備的制度,反映出清代捐納的常態化與規模化。
縱覽封建王朝制度性賣官的歷史,可以發現:(1)制度性賣官的起因基本上都是因為財政壓力,制度性賣官被視為在正規財政外增加政府收入、尤其是解決緊急財政需要的最有效手段。(2)制度化水準不斷提高。明清之前各朝公開賣官雖然也不少,但大多是臨時性的,一旦度過財政危機,政府即結束該次賣官,自明代中期開始,賣官開始轉向常態化,出現了目前可見最早的捐納則例,清代更是將部分捐納項目固定下來,以之為“常捐例”,各種捐納事例種類之多,規定之詳,區分之細,令人嘆為觀止,可以說基本實現了賣官的常態化、正規化、體系化。(3)以賣虛銜和各種資格為主,賣實官的較少。正常情況下,制度性賣官賣的大多是沒有太多實際職權的爵位、官階、官銜、出身,很少賣實官,清代雖然允許捐納實官,但屬“暫行事例”,并非常年開辦。(4)出售的項目呈增加之勢。自戰國至兩漢,國家向納粟者提供的主要是爵位階銜,偶爾賣低級吏職,從魏晉南北朝開始,政府開始出售任官資格和出身資格,隨著科舉制的確立,科舉出身和參加上一級科舉的資格成為出售的項目,最終發展為明清兩代的“捐監”,而明清兩代除了上述項目外,又增加參選資格及優先權、升職晉級資格及優先權、行政處分的減輕或解除為捐納項目。由此,科舉出身可捐而得,參選資格可捐而得,升職晉級的資格可捐而得,各種行政處分可以通過捐納而免除。
賣官當然是有害的,統治者對此心知肚明,“捐班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2],以科舉正途仕進的士子更是視賣官為寇仇,痛聲疾呼賣官之害。然而,所謂政事之先理財為急,財政問題不僅關乎個人的生活與命運,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公平正義,更直接關系到政權的安危存亡:政府如果手里沒有錢,如何維持軍隊司法等暴力機構,如何恩威并用、威懾懷柔不軌之徒,以及鎮壓叛亂,抵御外敵?歷史上許多王朝的顛覆正是以財政危機為導火索,因此對統治者來說,國家財政困境是緊急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否則就會立刻對國家施政造成重大妨礙,甚至危及統治秩序和政權生存,與此相比,賣官及其引發的腐敗盡管有害于民風、士風、官風、國家治理,但這種危害是長期的、長遠的,不會立刻發作。人們常批評公開賣官是飲鴆止渴,但客觀來說,賣官未必毒如鳩毒,而財政危機之害甚于饑渴。
由此,制度性賣官的開辦似乎是可以諒解的,而且大部分情況下,王朝政府反復申明賣官只是萬不得已的權宜之舉,反復強調只要財政危機度過就立即停止賣官,但問題在于,財政危機來而既去,去而復來,始終困擾著王朝政權的統治,成為歷代王朝揮之不去、無法徹底治愈而間歇性發作的致命痼疾,此其一;而一旦財政危機發生,政府又總是選擇公開賣官以籌措資金,此其二。易言之,財政危機發生———公開賣官——財政危機解決——停止公開賣官——財政危機發生——公開賣官……,成了一個走不出的循環,王朝政權越來越腐敗,最終土崩瓦解。
“財政危機——制度性賣官”循環反復發生,反映出封建王朝國家治理能力的欠缺:(1)財政危機的一再發生,說明封建王朝國家規制能力和分配能力的欠缺。封建王朝“國家度支有常”,在“不加賦”的情況下,以田賦為主的國家財政收入每年大致不變,為了保持收支平衡,就必須“出入有經,用度有制”,然而在實踐中,一則“帝王自己的奢靡無度,耗費了大量國家財政收入”,二則“皇室人口不斷擴大,成為國家財政的重大負擔”,三則“官吏集團及其附生人群的不斷擴大”,由此,“財政供養人員的不斷擴大,以及他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必然導致固有財政收入的壓力逐漸加大,加上還有可能受到外敵入侵威脅需要更多的財政支持等原因”,[3]這一切使得封建王朝在事實上“用度無制”,最終必然引發財政危機。(2)制度性賣官成為應對財政危機最基本、最常用的政策手段,說明封建王朝國家汲取能力的欠缺。一般來說,汲取能力是國家能力的根本,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它國家能力,能持續、有效從社會經濟生活中汲取財富的政權一般延續性也更強,[4]而“國家度支有常”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封建王朝汲取能力的不足,在生產力發展、人口及財富增加的同時,國家財政收入竟不能保持同步增長,原因并不是統治者真正輕徭薄賦,愛民如子,而是政府在稅收方面的無能及不作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明代中葉以降,商品經濟尤其是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同時,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的白銀通過貿易大量輸入中國,[5]社會上出現了一個擁有相當財富、渴望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商人及市民階層。對此,政府卻只求助于捐納這一有害的政策工具,以之汲取一小部分剩余社會財富為己所用,充分說明了明清兩代政府的無能。
“無能”不是明清政府的專利,“無能”某種意義上是帝制中國歷代王朝的共性:首先,在一個疆域如此遼闊、受治人口如此眾多、經濟規模相對龐大、構造復雜的帝國,政府在有限的技術條件下要想從民間持續、有效地提取財富與資源,本非易事;其次,高度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下,帝國的可持續的良性運轉以“雙重控制”為前提,一是對君權及其行使者(治理主體)的控制,二是作為治理主體的君主對作為代理人的官僚機構及群體的控制,前者在制度上是缺位的,后者在實踐中是失控的,“雙重控制”由此變成了“雙重失控”,后果是帝國可持續良性運轉事實上的不可能。因此,封建王朝除少數“盛世”外,大多數時候都是以“亞健康”乃至“病態”的狀態在運轉,而這種“亞健康”、“病態”的直觀表現就是“財政危機——制度性賣官”的循環一再發生。
二、錢入私門:非制度性賣官中的博弈
封建王朝政府運用制度性賣官的政策手段,從社會各階層汲取財富與資源,商品交換的經濟原則由此加速滲入公共領域,反過來又使賣官從國家擴大到個人,從公開延伸到私下,非制度性賣官如影隨形,始終存在于封建王朝的政治、社會生活中。漢代察、辟之下,官職的銓選經常成為一種私下交易。自漢初至武帝,以及東漢安帝、順帝、桓帝時都存在很嚴重的權貴私下賣官現象,靈帝甚至開西園自行賣官,“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后漢書·孝靈帝紀》)。魏晉南北朝以九品中正制選官,雖然制度上中正評品要依據家世和才德,實際上卻主要看家世門第、個人愛憎、財貨交情,于是,“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托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晉書·劉毅傳》)。隋朝廢除九品中正制,削弱門閥政治,但私下賣官在某些時期仍較普遍,如煬帝后期內史侍郎虞世基掌選,“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6]。唐初,天下方定,賣官較為少見,之后太平日久,人求仕進,私下賣官現象開始涌現,“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贓污狼藉。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腳、營田、當屯,無尺寸工夫,并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惟求財賄”[7],中宗時的斜封賣官、安史之亂后的債帥,可謂有唐一代私下賣官之極致。宋代的非制度性賣官首先表現為中書門下、吏部等人事部門官吏私下賣官,關于宰執大臣私下賣官,北宋中前期較為少見,但從宋徽宗開始,大臣私下賣官之風就猖獗起來,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人當政,無不是政以賄成,官以賂得。元代私下賣官的內容不限于流內官,更擴大到一般為人所賤的吏職,甚至連監察官職也可買賣而得。
明清時期制度性賣官達到很高的水準,但這并未堵住手握實權的權貴私下賣官的門路。明武宗正德年間,劉瑾用事,賄賂公行,“百官非貲入不得遷”,“禮曹亦必二千,兵曹亦必千金”,[8]自督撫至道府州縣并佐貳,皆各有定價,隨行就市,“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升遷也亦然。某缺銀若干,某缺銀若干,群眾相競,則價值轉增”[9]。康乾雖稱盛世,然早在康熙年間京城就流傳這樣一則民謠:“要做官,問索三;要講情,問老明;其任之暫與長,問張鳳陽。”[10]嘉道以降,仕途日形壅滯,官場更如市場,上下交征利,迄至晚清,上至皇帝后妃太監,下至掌握一省實缺差事分派大權的督撫布政,無不私下賣官取財,宮中以賣各色肥缺為常事,“粵、閩、海、淮、崇文門、張家口、殺虎口、山海關各監督,寧、蘇、杭各織造,此皆專為應賣之品,可以名掛招牌者也;各省三品以上大員,此為帝心簡在,公私不易分晰者也;學政主考,此乃清貴之官,似不至有此卑鄙,實因考差例不發榜,帝簡在心;道府內放之缺,遇有素稱肥缺者,部中書吏將應開列請簡之名,贈與太監而招搖之,多為撞木鐘,非真太后出賣也”[11],《官場現形記》描寫了江西的一個鹽法道署理藩臺,因藩臺不久就要回任,“他便利令智昏,叫他的幕友、官親,四下里替他招攬買賣:其中以一千元起碼,只能委個中等差使,頂好的缺,總得頭二萬銀子”[12],《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也描寫吳繼之被藩臺委了關差后,總督衙門的幕友立馬送了一個折子過來,“上面開著江蘇全省的縣名,每一個縣名底下,分注了些數目字,有注一萬的,有注二三萬的,也有注七八千的”,“若是想要哪一個缺,只要照開著的數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掛牌”。[13]23
制度性賣官,賣官的是國家,錢入的是國庫;非制度性賣官,賣官的是私人,錢入的是個人的腰包。賣官對政權和國家有害,統治者對此心知肚明,只是因為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政策手段來化解與王朝存亡攸關的財政危機,才不得不屢屢以國家的名義“暫時”賣官鬻爵,而非制度性賣官完全無補于國家財政,完全無益于王朝政權,而且因為它賣的是實官,危害性比制度性賣官更大,因此,歷代王朝于此無不立法嚴禁。雖然,遍覽歷代律典,基本找不到“賣官”之罪名,但實際上對非制度性賣官是按照其他一般性罪名來處理的,如在唐律,賣官可能構成受財枉法、受財為請求、監臨勢要受財為請求、受財不枉法、事后受財等罪,要言之,凡是罪狀為“受財枉法”、“受財請求枉法”之類的罪名,都可以成為懲治非制度性賣官的法律依據,因為國家選官(包括賣官)自有制度,不按制度來就是“枉法”,因此賣官就是一種“枉法”,自然在律典禁止范圍內。唐代史書記載的與賣官有關的案件,如李義府案、張錫案、鄭愔崔緹案、元載案等,其中賣官基本上都是按受財枉法、受財為請求來處置的。《大明律》更是把非制度性賣官上升到了“奸黨”的政治高度,除《刑律·受贓》“官吏受財”條的規定可以適用,《吏律·職制》“大臣專擅選官”條還規定:“凡除授官員,須從朝廷選用。若大臣專擅選者,斬。”[14]這一條顯然可以適用于權貴勢要的私下賣官,因為私下賣官違背制度,堪稱“專擅”。
律令的禁與懲,顯然沒有真正遏制住非制度性賣官泛濫之勢;制度性賣官制度化水準的提高,也沒能阻止非制度性賣官的擴張與滲入。在制度性賣官制度體系前所未有完備和法律對非制度性賣官懲治力度空前的明清兩代,非制度性賣官發生的廣度和深度均不遜色于前代。對于傳統社會非制度性賣官的泛濫,必須從買官者、賣官者及兩者間互動的角度來探討:
其一,社會上存在著購買實官的強烈需求。雖然,捐買功名和官銜的人未必都是沖著實官去的,但在傳統社會,做官、做實缺官的確是相當一部分人的人生追求,同時也是民間輿論所最認可的人生成就,想做官才是有志氣,做了官、管了事、掌了權才算有出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的卜子修原來是個學徒,后突發奇想想做官,而且想做知縣大老爺,請教他叔祖,他叔祖立刻就很高興,夸他“志氣不小,將來一定有出息”,“我”家境寬裕,無意功名,不小心捐了個監生和通判,家人就勸他去辦引見。[13]558一般的制度性賣官并不能直接滿足這部分人的需求,因為制度性賣官賣的是官銜和做官的資格,很少是實缺,捐官者仍須走較為正規的銓選程序,經漫長的審查、篩選、等待才能獲得一缺。
其二,分利集團及其成員對賣官之利存有分潤之心。美國學者奧爾森認為,“在邊界不變的穩定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出現大量的集體行動組織或集團”,這些集體行動組織或集團“極力傾向于收入或財富的分配而不是生產更多的產品”,它們是“分配聯盟”(分利集團)[15]36-47,奧爾森關注的是經濟生活和經濟學意義上的分利集團,實際上政治及社會生活中也存在類似的分利集團。傳統社會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國家對社會實行強控制,但所謂分利集團仍然存在,如宗室、外戚、后宮、朋黨、豪強之類的小集團。賣官一本萬利,人盡皆知,政府希冀壟斷其利,同時盡可能縮小其危害,可分利集團及其成員豈能讓政府獨占其利,他們借國家賣官之東風,在制度性賣官的限度之外賣官,實際上分潤了國家制度性賣官應得之利,這樣做對王朝政權當然極為有害。但正如奧爾森所言,分利集團、尤其是缺乏共容性的分利集團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極端的自利性,他們沒有動力使他們所在的社會更加繁榮,而是汲汲于對既有社會財富的分割與掠取[15]47-63,傳統中國社會的分利集團,就是這樣一些缺乏共容性的小集團,遍覽史書,人們每每驚訝于這些人的貪婪、自私與短視,但這正是一切缺乏共容性的小集團的本性。
這里尤其要提一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君主實施的非制度性賣官。從理論上講,在封建王朝,君主不屬于任何分利集團,但事實上,君主卻經常是私下賣官的主體,或者至少縱容身邊親信之人私下賣官。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君主的個人利益并非總是與王朝政權的利益百分百重合,賣官一般不會直接、立刻導致王朝覆滅,卻可以在短時間內搜刮到充足的錢財供己揮霍;二是君主并非總是理性的,他有情感、偏好、屬于個人的人生經歷,這一切會影響到他的性格、人生觀,包括對金錢的態度,如漢靈帝少年家貧的人生經歷及其生母董太后的貪欲,是其即位后瘋狂賣官攬財的內在原因,《后漢書·宦者列傳》:“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后漢書·皇后紀下》:“及竇太后崩,(董太后)始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自納金錢,盈滿堂室。”在帝制中國,君主是王朝政權的人格載體,但是,指望君主任何時候都能“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韓非子·有度》),顯然是不現實的。
總之,非制度性賣官對有能力私下賣官的賣官者有利,對希望買官的買官者也有利,唯獨對王朝政權及國家有害。對賣官者和買官者雙方來說,這似乎是一場正和的博弈、雙贏的交易,但如果加入王朝政權和國家為博弈方,這顯然是一場零和博弈,只是零和的結局并不會立即顯現,也未必由賣官者和買官者本人承擔,而王朝政權和國家作為直接受害方,卻沒有充足的能力來制止這場博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正反映出傳統社會君主政體及國家治理機制難以克服的內在缺陷。
三、規范腐敗: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從商鞅開始,人們就認識到出賣官爵是能“富國”的有效政策工具,西漢晁錯全面總結了出賣官爵的功利:“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漢書·食貨志上》)晁錯認為出賣官爵一則不增賦而財用足,二則使天下多余的財富有一個好的去處,三則開辟由富而貴的通道,從而鼓勵百姓致富。清代雍正皇帝甚至認為,科舉出身未必有用,捐納中亦有人才,他說:
朕近見科目之人茍且因循,而貪贓枉法者亦復不少。至于師友同年,夤緣請托,比比皆是。若仕途盡系科目,則彼此網結,背公營私,于國計民生為害甚巨。古圣人立賢無方,不可執一而論。且使富厚之家叨授官職,使不希冀功名,亦是肅清科場之道。[16]
可見統治者不僅把出賣官爵視為解決財政問題的良策,某種程度上也把它當成了疏通仕進之途、選拔人才的一種另類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和科舉一樣,買賣官爵也是傳統社會人才向上流動的一種重要途徑。
然而,賣官終究是一種吏治腐敗,無論統治者怎么為之尋找正當理由,他們終究不能否認這一點,在無法徹底舍棄這一政策工具的前提下,他們所做的,是努力使賣官這一腐敗規范化,希冀能收其利而遏其害,由此,人們看到了明清時期數目眾多、體例嚴密、內容完備的捐納事例,但賣官真的就此規范化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無論清代中前期還是后期,賣官這一統治者認可的“必要的腐敗”從來就沒如他們設想那樣真正規范過,非制度性賣官的頑強存在,固然是賣官規范化努力失敗的重要表現,實際上,就算是國家認可的制度性賣官如捐納,其運行也很少嚴格按諸項事例文本規定的那么做,而是以另一套規則或說慣例在運作:
其一,報捐必須通過金融機構代辦。依清政府的捐納事例,捐納允許代辦,但僅限于親戚和友人,銀號、錢莊等金融機構代辦報捐屬于“包攬”,為例所禁,但實際上,京城的金融機構為報捐者代辦報捐是清代極為普遍的現象,一則報捐者一般很難讀懂各種專門化的捐納事例和章程,二則報捐者不可能隨身攜帶報捐所需的大量金銀,所以,委托金融機構匯轉、保管資金,由此發展為請其幫忙代辦報捐,自然順理成章。對金融機構來說,則不僅可以收攏資金,還可以收取手續費,自然無不樂意之理。但是,金融機構介入報捐事務之后,通過非法的利益輸送,打通各種關節,與捐納房等辦理報捐事務的衙門及官吏建立起關系緊密的分肥同盟,反過來把持了北京的報捐:如果是自己報捐,即使熟知各種章程和程序,也必然遭到辦事胥吏的層層刁難和需索,相反如果委托與捐納房關系緊密的銀號、錢莊辦理,則一路暢通無阻。由此,委托金融機構、尤其是與中央有關衙門關系密切的金融機構代辦報捐而非自己報捐,成為清代捐納的一條潛規則,這一潛規則的背后,是京城金融機構與中央各辦理捐納事務衙門的勾結與錢權交易。
其二,印結論印計價,錢到即得。在清代,“印結”是一種保證文書,“印”指官印,“結”乃保結,清代捐納制度規定,包括普通庶民和在職、候選候補官吏在內的報捐者在報捐時必須同時提交同鄉五六品京官出具的印結,這是確認報捐者身份的必要文件。從制度上講,出具印結的京官必須在充分了解報捐者個人情況的前提下,自愿并親自出具印結,但實際上,由于報捐者人數越來越多以及代辦報捐的普遍存在,報捐者多是將印結等報捐手續一并委托給金融機構,而由后者去找由本省籍京官組成的印結局,在交納印結局單方規定的印結銀后,再由印結局出具報捐者需要的印結。在此過程中,出結的京官與報捐者不碰面、不認識,當然更談不上熟知情況,他們之間真正發生的關系,是以印結局為中介一手交錢、一手出結,這當然是一種權錢交易。
其三,署差、補缺任由長官意志。捐納一般最多只能獲得參選的資格,報捐者領取捐官執照,向吏部注冊之后,即可參加吏部的銓選。當然,吏部的銓選則例對銓選有詳細規定,有班次、花樣、單雙月、掣簽之類,這些信息是完全公開的,捐納出身的候選官員可以依次推算大致何時輪到自己,可由于官多缺少,即使捐納花樣,他們也很難按部就班在吏部等到官缺。基于此,大部分人選擇分發指省,在京外候補,希冀獲得署事、差委和補缺的機會。理論上講,地方上的署事、差委和補缺也有一定的制度,但總體而言其決定權完全在督撫之手,加之候補官的人數遠遠超出了官制的規定和臨時性行政事務所能容納的人數,因此實踐中,賄賂、人情等“潛規則”替代了關于署事補缺的種種公開規定,督撫藩臺視賄賂的多少、人情的輕重來決定去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將一省之內的候補官分為四大宗,只有前三宗人有署事補缺的機會:
第一宗,是給督撫同鄉,或是世交,那不必說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臺的同鄉世好,自然也是有照應的。第三宗,是頂了大帽子,挾了八行書來的。有了這三宗人,你想要多少差事才夠安插?除了這三宗以外,騰下那一宗,自然是絕不相干的了,不要說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盡長著,候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沒有人想著他呢。[13]265
此外,捐升的引見驗看可以花錢找人頂替;捐復須由督撫先期向皇帝申請捐復,從而為督撫與希望捐復者之間的錢權交易提供了空間;金融機構在代辦報捐的同時,又從事向資財不足的報捐者放貸的業務,由此,許多家境本不寬裕、科舉又無望之人動起了舉債捐官的心思,他們或向親友熟人舉債,或向金融機構借貸,打著補缺后撈錢還債的念頭,成為“帶肚子的官”,完全失卻了捐納“使富厚之家叨授官職”、“富家子弟由捐納一途而進”的本意,對吏治構成直接的危害;隨著捐例越開越多,越開越久,仕途越發壅滯,許多捐官長年難以得缺成為普遍現實,各種報捐項目逐漸失去往日的魅力,難以聚斂到足夠的錢財。對此,清政府一方面對捐項打折減價,另一方面發動地方官員向士民“勸捐”,其中自然又免不了加派、中飽與強制。
總之,清政府希望將賣官規范化,希望能盡攬賣官之利而遏其害,甚至希望捐納能成為科舉之外又一條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有效路徑,成為富家子弟、特殊人才的進身之途,然而,看似完備的捐納制度,根本阻擋不住捐納實施中的私下交易、中飽私囊、弄虛作假,國家意圖掌控的制度性賣官事實上被其無法掌控的非制度性賣官所滲透,對希望做官的報捐者來說,公開的捐官只是第一步,私下買缺是第二步,而且是真正關鍵的一步。捐官花的相對是小錢,買缺花的錢才是大頭,易言之,體系化、看似規范的制度性賣官只是清代賣官的表面,非制度性賣官才是清代賣官的實質或者說主導,清政府規范賣官的努力最終被證明是失敗的。
美國學者魏德安在《雙重悖論》一書中提出,腐敗可以分為發展性腐敗和掠奪性腐敗,發展性腐敗是“一種有組織的犯罪形式”,在這個過程中,“政治上的黑手黨從商界合法或非法所得中扣留一部分據為己有,然后出臺有利于商業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掠奪性腐敗是“掠奪式”的,類似于“明火執仗的搶劫”,在這種腐敗模式下,“腐敗大多是國家組織的自體腐敗,利益只是單向流動,政界打劫商界之后并沒有基于長遠利益的考量而出臺促進商業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魏德安承認,從來就沒有什么“良性腐敗”,但確實存在更為惡性的腐敗,發展性腐敗和掠奪性腐敗都會造成嚴重的危害,但掠奪性腐敗更有可能引發致命的后果,會更加迅速地暴露出惡劣影響,發展性腐敗本身不會促進經濟增長,但因為其有組織性、可控性,相對能遏制掠奪性腐敗造成的消極影響。[17]72
制度性賣官使得傳統社會工商階層的游動資金“投入錢權交易的領域”,而并沒有“按照商品經濟的自然規律,投入商品的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增加商業資本的總量,或在商品流通領域流動”[18],結果是分散了商業資金,分化了工商階層,某種程度上構成傳統社會商品經濟無法充分發展、難以走向成熟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性賣官不能說是發展性腐敗,但是,按魏德安的標準和邏輯,它卻似乎可以說是一種有組織的、可控的、可持續的腐敗,至少從統治者的初衷來看是這樣。魏德安認為,如果腐敗實在難以避免,那就讓腐敗受到某種控制甚至利用它,如樸正熙在韓國、自民黨在日本、國民黨在中國臺灣地區做的那樣,控制腐敗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實現的。[17]29-67然而,傳統社會制度性賣官終歸失敗的歷史實踐卻證明,希冀規范、控制、利用腐敗,只會是政府的一廂情愿,因為從本質上講,腐敗是對規范化治理的違逆,是對法律秩序的破壞、對人之善良品質的腐蝕,對一次違法的放縱必然招來更多的違法,對某種腐敗的容忍必然鼓勵、創造更多的腐敗。當然,在腐敗積重難返、反腐敗斗爭長期、復雜、艱巨的情況下,將規范、控制腐敗作為反腐敗斗爭的階段性工作及目標,未嘗不可,但是,封建王朝將賣官制度化的努力并非基于長期反腐敗斗爭的需要,并非反腐敗建設的權宜之舉,而是為了獨占賣官的收益,以之為滿足財政需要的穩定的政策工具,其結果由此必然是:制度性賣官的法律越來越嚴密,非制度性賣官卻越來越泛濫,制度性賣官在非制度性賣官的沖擊下難以為繼,最終被非制度性賣官所淹沒。
在一個產權得不到充分保護、交易與投資沒有足夠法律保障的國家,社會資本必然流向公共領域,以公開或私下錢權交易的方式,購買足以為身份標識的官職、爵位、榮典、資格。而對缺乏更多有效稅收手段的傳統政府來說,賣官是一種相當見成效的提取社會財富的政策工具。由此,在傳統社會,制度性賣官成為一種法律及社會觀念認可的腐敗,是一種看似“合法”、“合理”、性質隱晦的隱性腐敗。
腐敗本身具有不確定性,無論它是顯性腐敗還是潛規則化的隱性腐敗。我國有學者認為,隱性腐敗的特征之一是“數量的定額化和相對穩定性”[19],但是,潛規則的約束力是“依據當事各方的造福或損害能力,在社會行為主體的互動中自發生成”[20],隱性腐敗下的權錢交易,其數額、程序最終由交易雙方的需求、實力及相互的博弈而定,其中就算有一定的慣例或規則,對雙方的約束也只是軟約束而非硬約束。由此,封建王朝將賣官規范化的嘗試和努力,必定陷入非制度性賣官淹沒制度性賣官、反規范化趨勢壓倒規范化努力的歷史困局。
[1]劉海年,楊一凡.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4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434-435.
[2]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1:22.
[3]洪振快.亞財政:制度性腐敗與中國歷史弈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
[4]張長東.稅收與國家建構: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一個研究視角[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3):195-201.
[5]樊樹志.晚明史:上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4.
[6]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2007:2172.
[7]張鷟.朝野僉載[M].趙守儼,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9:6.
[8]李清.三桓筆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188.
[9]陳子龍.明經世文編[M].北京:中華書局,1962:3523.
[10]昭梿.嘯亭雜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0:287.
[11]王照.方家園雜詠記事[M].北京:中華書局,2007:91.
[12]李伯元.官場現形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5、20-25.
[13]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4]懷效鋒,點校.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0.
[15](美)曼瑟·奧爾森.國家的興衰:經濟增長、滯脹和社會僵化[M].李增剛,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6]蕭奭.永憲錄續編[M].朱南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59:417.
[17]魏德安.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M].蔣宗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8]寧欣.唐史識見錄[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9-10.
[19]晏愛紅.清代官場透視——以乾隆朝陋規案為中心[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5.
[20]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193.
Historical Dilemma in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New Discussions About Position-Selling in Ancient China
XIE Hongxing(School of Legal Studie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Jiangxi,China)
Selling official positions in feudal China had within its inclusion institutional and non-institutional forms.The former was open,income from which went to national treasury,and the latter was private,money going to private purses.Ineffective absorbing abilities of feudal rulers could not have fiscal income meet the unrestricted expenses,resulting in fiscal crises one after another,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collect funds by selling official positions.non-institutionalized selling accompanied the continuously upgrading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ed selling,infiltrating into it,interfering with its implementation,and it finally ended in the latter being immersed by the former.Institutionalized selling that was out of control and the prevalence of non-institutionalized selling indicated the failure of feudal governments to institutionalize selling official positions.At its root,corruption goes against institutions,disorderly,non-regulatable,and uncontrollable.Efforts of feudal governments to put official-post selling under control is doomed to be caught in historical predicament of being immersed in non-institutionalized selling,and of institutionalized efforts being suppressed by non-institutionalized efforts.
institutionalized selling of official posts;non-institutionalized selling of official posts;dormant corrupt;hidden rules
D691.49
A
1674-9170(2017)05-0071-09
2017-07-20
謝紅星(1978-),男,江西贛州人,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5BFX017)
責任編校 王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