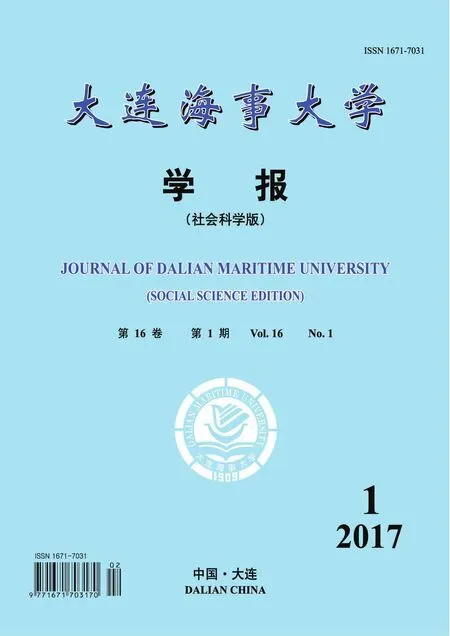中華史觀下的中國當代史學構建
鐘永圣
中華史觀下的中國當代史學構建
鐘永圣
(東北財經大學中國經典經濟學研究中心,遼寧大連 116025)
中華史觀是在徹悟“天人合一”自然真相的基礎上,把歷史發展過程看作“合道而興,悖道而亡”的過程,從而讓歷代炎黃子孫知曉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趨利避害,歷經長久的歷史風雨而不衰亡。對歷史的解讀,反映著一個民族的心靈、境界和智慧,顯示了該民族的自信程度、反省能力和覺悟狀態。從敘述一個被稱為中國史學界在概念上的“笑話”開始,引出“中華史觀”的議題,闡明恢復中華史觀對于當下時代建立文化自信、正確認識華夏的歷史、評估上古文明的價值、借鑒古代文明成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并從“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角度,提出構建中國當代歷史學的基本標準。
中華史觀;天人合一觀;中國史學;文化自信
一、引論:中國當代史學的“笑話”及其糾正
2006年6月和2008年5月,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榮休教授林毓生先生兩次應邀到東北財經大學講學。由于林先生母語是漢語,又在美國主流學術界耕耘半個世紀,所以他的講座對于國內學者準確了解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高等教育的狀況和學術傳統的要旨十分重要。林先生講學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自由”和“自由主義”;二是實質上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和形式主義跨學科研究的謬誤;三是對“五四”思想傳統的認識。作為殷海光和哈耶克的入室弟子,加上一貫嚴禁到苛刻的治學精神,林先生對相關歷史和學術思想的敘述清晰而且詳細,令人十分信服。
作為講座的邀請人和主持人,特別是作為林先生在大連期間的招待人,我有機會朝夕聆聽林先生的敘述和講解。其中有兩個學術判斷,讓人聽后十分意外,至今言猶在耳!第一個是:“國內研究哈耶克的書幾乎都不能看!”第二個是:“在國際史學界看來,中國當代史學鬧了一個笑話!就是‘封建’是指‘分封建國’,所以夏、商、周三代才是名副其實的封建社會,可是被中國史學界按照西方史觀稱為‘奴隸社會’;而秦以后國家治理是郡縣制或者行省制,一直到清代,奴隸制度也都普遍存在,卻被稱作‘封建社會’。連分封建國的事實都不存在,怎么能叫封建社會呢?機械的進化論史觀解釋不了中國的古代史。”為了有關學者不會因此記恨林先生,對于第一個觀點,十年來我一直諱莫如深;第二個判斷自然和如何認識“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內容相關,作為“史學”和“政治學”的雙重門外漢,我知道還遠遠未到解決問題的歷史時機。如今十年過去了,在2016年5月17日北京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之后,中國未來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即將進入“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歷史階段,我想林先生的這兩個重要判斷都到了應該讓國內學者特別是大學生們知曉的時候了。知道前者可以避開研究上的彎路,直接面對哈耶克的英文原著;知道后者可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中華史觀重建中國史學,更加準確、全面、清晰和自信地認識中華歷史、評估中華歷史、借鑒中華歷史,服務于再次創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業。
林毓生先生是國際思想史學界的著名學者,這“著名”的鑄成,不僅僅是鍛造于20世紀60年代如日中天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更主要的還是來源于他堅持不懈地做學問的嚴謹態度。林先生說中國史學界鬧了“笑話”,當然讓人既感驚訝又好奇。我就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去了解有關史實,結果發現那確實是一個讓人聽了一臉嚴肅的笑話。2017年1月,我就有關內容到北京大學哲學系資深教授樓宇烈先生的家中請教,樓先生說:國內其實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對于“封建社會”一詞的使用已經到了婦孺皆知、約定俗成的地步,已經很難按其歷史原意糾正回來了!
孔夫子有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筆者認為在事關中華歷史事實和尊嚴的問題上,我們尤其要效法孔夫子的精神,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換不回”。如果“封建社會”這個概念不能在國民中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糾正回來,它至少會產生以下三個嚴重的后果:
一是整個社會上大部分炎黃子孫對中華上古史的認識始終是扭曲的和錯誤的。這會導致中華文化在源頭上被丑化、在時長上被短化、在真實性上被虛化,絕不利于中國人民“文化自信”的真正建立。因為所有中華文化的開創性原典的主旨思想都是在夏商周時代傳承下來的,如《易經》和《黃帝內經》;或者在傳承的基礎上“創新”出來的,如《道德經》和《論語》。
二是錯誤的歷史觀會嚴重影響文化觀和價值觀。歷史觀里面包含著國家觀和文化觀,體現著世界觀和價值觀,決定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人生觀。歷史如果僅僅是記錄著的歷史,那么“史學”就不必存在。歷史恰恰是因為不同的觀念解讀,從而產生了“學問”,影響著國家的凝聚力和發展方向。對歷史的解讀,反映著一個民族的心靈、境界和智慧,顯示了該民族的自信程度、反省能力和覺悟狀態。正確的解讀可以凝聚民心、增強自信、挖掘價值、提高智慧、拓展生存能力,這是國家強盛和長治久安的思想基礎,是文化上的國防;錯誤的解讀能夠瓦解民心、毀掉自信、扭曲價值、降低智慧、削弱發展能力,毀壞的是一個國家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基礎。
三是對當下中國的文化繼承造成傷害,對未來中國新文化的生成造成障礙。錯誤地解讀歷史,就不會正確地繼承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就不可避免地在發展中重復先人已經犯過的錯誤,造成國家和民族整體利益的本可避免的巨大損失。
二、中華史觀的客觀性與獨特性
按照許多史學研究者的看法,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稱呼被廣為傳播的源頭起于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其對中國史學研究的影響,是開始用西方的進化論機械史觀來“套”中國的歷史,使中國的歷史形態按照“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觀被解讀成了一個個原本并非如此機械進化的固形階段,喪失了中國古代史學傳統,遮掩了“合道而興,悖道而亡”的中華史觀下歷史演變規律。比如,按照道家傳承的判斷,和宋代邵康節先生在《皇極經世》中關于社會發展階段的認識,華夏文明的“午時”是在堯舜的時代,其衡量標準是“人類生活與天道自然的和諧程度”,而不是物質技術的發達和物質財富的多寡。也就是說,按照古代的中華史觀,社會的文明程度是按照“天人合一”的道德程度來衡量,而不僅僅是按照技術的先進程度或者創造財富的多少來衡量。這顯然與現代西方歷史觀的認知標準相差太大,社會化大生產下的分工與合作顯然要比手工時代的分工與合作效率高多少倍。進化論下的歷史觀,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一個比一個“先進”。
但是西方進化論史觀中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漏洞,就是為什么在思想覺悟的境界上,西方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都無法超越所謂“軸心時代”的大師?壽命長短是檢驗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按照西方史觀,原始社會是生產力極其低下的社會,茹毛飲血,野蠻落后,可是為什么在中國堯舜禹以上時代的天子壽數都在百歲以上?而春秋諸子除了非正常死亡的韓非子都活過了70歲?就古代社會而言,宋代的富庶是全世界公認的,為什么北宋諸子除了程顥一人活過70歲而其他人都命不長久?顯然,中華歷史中有一些精華性的東西沒有被大眾認識和傳承。如果我們錯誤地看待了歷史,歷史的經驗就不能為我們造福。而少數了知此中道理的人卻可以從中獲益,如唐代的孫思邈、呂洞賓,宋代的陳摶,明代的張三豐,都能道法自然,身年過百,壽數堪比上古天子。
依據中華史觀,被西方史觀稱為“原始社會”的時期其實是中華文明“圣王治世”時期,在“體悟天道”或者“道法自然”方面,它們是華夏文明的一個高峰期。雖然在“物質文明”方面比現代社會遠為落后,但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后世望塵莫及的,例如《易經》和《黃帝內經》等中華文明原創經典的核心精神,至今無法超越。在《漢書》中,從伏羲到黃帝之間,有數十位在古今人物表位列“賢人”的天子。按照《史記》的記載,黃帝之前有八代神農氏為天子。黃帝時期,各地其實是“諸侯國”,不是西方史觀下洪荒野蠻的“原始部落”。
黃帝有明確的國號“有熊”。黃帝之后,各位圣王皆有其號。顓頊帝國號高陽,帝嚳國號高辛,帝堯的國號陶唐,帝舜的國號是有虞,大禹的國號是“夏后”。在殘存的《尚書》中,《周書》之前有《商書》,《商書》之前有《夏書》,《夏書》之前有《虞書》,《虞書》之前應該還有根據國號或者朝代命名的“書”,可惜原本3000多卷的《尚書》散失了,現在只能看到《虞書》以“堯典”為開篇起始。
現在沒有了痕跡,不等于原來不存在。即使沒有念過書的人都會知道,我們不能因為八輩子以前的祖宗不存在了,就認為我們沒有過這些祖先。我們更不能容忍別人惡意侮辱我們的祖先,例如19世紀一些日本學者說堯是板凳,舜是蠟燭臺,禹是爬蟲。即使以“科學”的名義,也不能妄說我們的祖先就是“類人猿”。按照中華史觀,“人”這個物種的存在,要比類人猿的歷史長了不知有多久。如果說“類人猿”和“人”在生理特征上有某些相似之處,并不能“科學”地證明人就是從類人猿進化而來,因為在自然界中,“進化”與“退化”同時存在,“科學”上也存在另一種可能:“類人猿”是從“人”退化而來。人類社會的孩子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落入“狼孩兒”的境地,也能說明人可以退化為具有某種野獸特征的生物。
上古國號和姓氏的具體關系,現在尚不得而知,但是一定是文明訴求的結果。要想讓國民正確地認識中華原創經典的重要,就不能順著西方“原始社會”的觀念,稱呼上古諸侯國為“部落”。試舉實例說明,西方哪個原始部落可以鑄鼎?而黃帝重新統一華夏之后,就曾經鑄鼎以宣明德。能夠鑄造大型的青銅寶鼎,能夠在鼎上鑄造文字以記錄其事,能夠了知人體十二經三百六十五絡與天地四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對應變化關系,這樣的文明程度怎么能說那是野蠻、愚昧、落后的原始社會?是真的無知還是別有用心?“欲滅其國,先去其史”,我們不能不警惕。
中華史觀具有如下特性:
(1)建立在天人合一觀念基礎上。相當于現代的表述“世界是普遍聯系的”,人與自然是息息相關的,自然環境和國運興衰隨著人的心念和行為而改變。
(2)衡量社會歷史形態的標準是統一的。比如以道德水準為衡量標準,輔以經濟繁榮程度。而西方史學觀念衡量社會發展史的標準是不統一的:“原始社會”的定義依據是生產力低下;“奴隸社會”的定義依據是人身隸屬關系;而“封建社會”的定義是“分封建國”,是國家政體和資源分配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定義依據是決定資源分配的要素。
(3)無論個人、家國還是天下,都是“合道而興,悖道而亡”。《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大舜德行深厚,孝悌圓滿,寬以待人,贊嘆懿行,不譏他過,感動了萬民,紛紛在他居住的周圍安家落戶,結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周武王發動革命之前,周文王在西岐已經憑借德行“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后世雖然武力征伐,但是沒有足夠的合道,都不長久。天下以德而有,因敗德而失。夏桀、商紂、周幽王、秦始皇、唐玄宗、宋徽宗都是因為悖道或亡或衰。
還給大眾中華史觀,和還給天下一個地道的經濟理念一樣重要。沒有正確的史觀,也無法正確地評估當下和正確地展望未來;沒有正確的經濟理念,會使整個社會倒退回唯利是圖、物欲橫流、寡廉鮮恥的野蠻社會。沒有道德,物質再繁榮,也不能稱作是文明社會。
三、中國古代社會的再研究與再認識
中華文明也稱“華夏文明”,這一稱呼本身表明,中華文明在至少4100年前,已經達到了“華服盛美”的程度。夏代的衣服目前沒有出土的物證,但是夏代青銅冶鑄技術的實物卻可以在河南洛陽博物館一睹真容。1975年在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夏朝乳釘紋銅爵,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青銅酒器,被稱為“華夏第一爵”,表明夏朝青銅鑄造技術的高超。史學界認為當時的青銅鑄造已經不僅僅是為了容器,而是使用者身份、地位、文化的象征。
但是,更具有象征意義的不是爵,而是鼎。根據《左傳》魯宣公三年記載,夏朝初年,大禹根據施黯的報告,下令把九州州牧所貢之銅,用來鑄造九鼎,以九鼎象征九州。此后,九鼎便成了歷代傳國之寶。夏亡之后,鼎遷于商都;商亡之后,鼎遷于周都,表明天命之所歸。秦亡之后,九鼎下落不明。但是從禮儀規模上推測分析,大禹所鑄之傳國寶鼎,一定遠遠重于目前最大的出土實物“司母戊”大方鼎,器型巨大而莊嚴。而且這些鼎上根據《山海經圖》刻有當時全國各地山川奇異之物的圖形,對鑄造工藝和技術的要求遠比“華夏第一爵”所需要的技藝復雜得多。所以,一旦未來九鼎出土,或者原本《尚書》出土,華夏歷史就絕不再是按照西方史觀羅列出來的機械順序,而應該是按照中華文明內在的邏輯和觀念重新梳理。
一般認為,把中國古代社會按照西方進化論史觀進行階段劃分和社會性質定義,也是起始于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本書被認為是最早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的名著。它突破了以歷史文獻為研究對象和依據的局限,將研究視野拓展到地下出土實物,把《詩經》《尚書》《易經》里面的歷史性記載,和甲骨文記錄的卜辭、周朝金文里面的地下出土材料,熔于一爐,得出他所謂的“社會發展之一般”。從研究方法上看,這種方法本來就是歷史研究應該有的方法。但是問題在于,科學的方法卻未必一定產生正確的科學邏輯判斷。
郭先生的著作被稱為唯物論史學研究的典范,可是他的結論卻在史實和邏輯上存在諸多顯而易見的漏洞和錯誤。例如《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的第二部分標題是“二 殷代——中國歷史之開幕時期”,就特別值得商榷。說中國歷史的開幕時期是在殷朝,顯然是“只有爺爺活過的證據不見曾祖的痕跡就不承認曾祖的存在”!這種把“出土文物”作為唯一證據推斷文物所在朝代為華夏文明起始的觀點,和19世紀日本學者否認堯舜禹存在的觀點如出一轍,貽害無窮。
至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四部分的“第一章 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隸制的推移”和“第二章 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也都是“管中窺豹”和“盲人摸象”式的以局部妄斷全體的結論。另外諸如“周代彝銘中無井田制的痕跡”和“周代彝銘中無五服五等之制”,更是犯了“把必要條件當作充分條件”的邏輯推論錯誤。如果周代彝銘中有奴隸制度,難道周代就是奴隸制度?明代、清代也有數不清的文獻清晰地表明奴隸制度的存在,難道清代和明代就是奴隸社會了?同理,美國南北戰爭是因為奴隸制度的存廢而戰,19世紀了,美國還處于奴隸社會,那么按照該書的歷史“科學發展”的邏輯,美國結束奴隸制度,所進入的“新社會”階段,應該是“封建社會”才對,怎么就是“美帝國主義”了呢?
這些僅僅在物象上對社會發展階段的判斷,是不能準確認識歷史的。中華文化的奇特之處,在于創造了“華服盛美”物質文明背后的獨一無二的“精神文明”。此文明與其他文明的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在誕生的初期就達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中國原創經典當中的文化精髓,包含著基于天人合一觀產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它對世界的解讀是由本質到現象、由一到萬逐層展開的:性、心、身、家、族、國和天下。性是自性、道體、本體或者天道,是一切生發的根本,卻是超出二元對立和所有形象,由于無形無象無可名狀,非切身體悟證實而不能得知,所以在人們心中逐漸由樸素真實變得難以捉摸,“玄之又玄”,是以《論語》中記載,孔門高足子貢說“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從中華文字的原意上看,“性”是能夠“生心”的“那個”,本來混元一體,圓覺貫通,涵容萬有,所以不能以任何實物或者臆想來比擬,“說似一物皆不中”。但是由于本質和現象存在著“性相不二”的道理,所以通過現象可以覺知。本性生發出來的心理和身體,反映著當事人對本性的覺知境界和印證程度,例如男性的心理和身體反映著當事人印證到的本性是“男”的部分,女性的心理和身體反映著當事人印證到的本性中可變現“女”的部分,說明本性可生男也可生女。有道之人和普通人的區別就是,既不執著男,也不執著女。既然本性可男可女,那么顯然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非人,可以是飛禽也可以是走獸,舉凡生物界一切生靈,甚至可見和不可見,都不出本性、自性、天道、天性、天命。“身”是心的作品和工具,覺悟本性的心可以主動選擇身,迷失本性的心只能被動接受身。了知中國古代這種天人合一的觀念,就可以真正理解為什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為什么“心正”之后才能“身修”,“身修”之后才能“家齊”,“家齊”之后才能“國治”,“國治”之后才能“天下平”。這也是堯傳舜、舜傳禹的“心法”、“正統”和“政治交代”:天之歷數在爾躬(天運的好壞就在你身上)。四海困窮(如果你把天下治理得一塌糊涂,人民窮困不堪),天祿永終(那么你即使貴為天子,你的好運也到頭了)。
綜合古代的典籍和如今可查見的古物習俗,我們發現《尚書》和《大學》省略了對現代人理解中國古代社會運行非常重要的兩個物象:祠和社。祠是祠堂,同宗族的人在祠堂面前解決“家族內部事務”,在“家法”之后有“族規”,是中國古代社會治理體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環。社是社壇,對于國家是“江山社稷”的祭祀場所,對于普通大眾來說,是在族規之外,處理沒有血緣關系的“陌生人”之間事務的場所,是在告官之前,按照“天理良心”評理的地方。所以,不同宗族姓氏的人在“社”前“會”集,其“主義”含有“集體尋求天理、公平、公正”的意蘊。是以“社會主義”一詞雖是外來語翻譯詞匯,可是在漢語中的本義就是全體人民可以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集體決定事務的是非曲直、解決辦法和發展方向。在這樣的社會中,其“先進文化”是一切符合人與自然(天)、人與人(倫)、人與物(和)本質的文化,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不例外。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中國自古傳統中一貫努力堅持和傳承的華夏文化的現代演變與發展形態,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偕行、生生不息的結果。而“馬克思主義”看上去雖是百分百外來的“舶來品”,可是他的核心精神翻譯成漢語,是“實事求是”,語出《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也就是說,認真學習以前的優秀傳統文化,每一件事都要找到他的本質屬性和規律。
由此,我們確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本質上可以涵融現代學術思想觀念,只要透過古今文字的表達障礙,進入貫通的境界,歷史與現代可以順利地“接駁”。
四、中國近代史學的思想獨立性缺陷與時代性局限
最初,基于中華史觀的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再認識不太容易令人相信。因為郭沫若先生當時被奉為“史學泰斗”、“甲骨四堂”之一,怎么會在如此重大的史學判斷上如此“局限”?蘇東坡曾經說過,笑前人者常常復被后人笑也。我們自然要警覺自己是不是更加“局限”。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容易發現那是時代造成的。
我國在近代國力衰弱、生產力落后、飽受侵略,學界在文化自信丟失后的史學研究,充滿了否定自我、追模西方、言必稱希臘的特征。無論在冷戰時代學習蘇聯老大哥搞計劃經濟,還是在改革開放時代學習歐美搞市場經濟,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大體上處于模仿、翻譯、仰視的狀態,是缺乏自信甚至是沒有自信和獨立的研究。正因為這樣的境況,才導致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在學術命題、學術規范、學術成果和學術話語權方面亟待提高。如果我們以往的研究充分地展現了“文化自信”,那么我們現在就不會提出“文化自信”的要求。
20世紀中國史學界依賴考古發現的資料,對于甲骨文和商代卜辭的研究代表了史學的重大成就,卻顯然沒有意識到非常關鍵的一點:司馬遷即使沒有見過甲骨文,也不代表司馬遷所見到的關于商代的史實就是虛構的,中國古代的歷史觀就是沒有“科學依據”的。否認中國傳統史書的真實性和看輕中國古代史學成就,是當代史學不能獨立的重要因素。
五、中華文化自信立場下的當代歷史學構建標準
史學構建過程中,對人類社會自身發展過程的認識,有兩個基本標準,一個是生產力發展水平,另一個是精神的覺悟境界。把生產力發展水平作為唯一標準,最終會在社會形態認識方面導致機械進化論,在社會精神方面產生“物質崇拜”或者“物欲橫流”,恰恰走向了文明的反面。
中華文明是高度“早熟”的文明,它對人和自然和諧關系的認識至今都讓后人無法超越。如果只是按照唯生產力論來對待,就不能夠反映上古社會在認知世界和生命本質上的巨大成就!錢穆先生和季羨林先生認為“天人合一觀”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最大貢獻,而早在距今4700—6400年前這種觀念就明確產生了,現代社會形態劃分標準沒有體現這一核心文明成果。
中國是目前唯一還有連續的遠古傳承的文明。這種唯一性決定了中華文明及其歷史是獨一無二的,以西方史學觀念來“套”中國的歷史,尤其是古代史,不但不能準確地記述中華的歷史,還會把形成這一歷史的文化精髓掩蓋和淹沒。所以,中國的歷史必須用中華史觀來論述。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李學勤.史記五帝本紀講稿[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3]余英時.群己之間[M]//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4]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5]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6]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8]屈萬里.尚書今注今譯[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
[9]班固.漢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0]徐芹庭.細說黃帝內經[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11]馬克垚.世界文明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12]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M].吳象嬰,梁赤民,董書慧,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3]湯恩比.歷史研究[M].郭小凌,王皖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歐陽哲.胡適學術文化隨筆[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
[15]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M].趙月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溯水源深 血脈永恒——《雷鋒精神與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簡介
《雷鋒精神與中華傳統文化傳承》一書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于2013年3月出版,是作者鐘永圣博士應出版社的邀請,為“中國榜樣:永遠的雷鋒”大型叢書所作的關于雷鋒精神和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的學術思想性研究著作。該套叢書是為了紀念毛主席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五十周年而組織出版的系統性著作,由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和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聯合推薦。
雷鋒精神誕生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現在社會上很少有人認為雷鋒精神會和中國傳統文化有聯系,甚至認為二者“風馬牛不相及”。可是通過閱讀本書,讀者會感到雷鋒真的越來越鮮活,雷鋒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越來越密不可分,雷鋒精神其實是中華傳統文化精神在新時代的表現和概括。
鐘博士在收集和閱讀大量古代歷史材料的基礎上,精心選擇,細密論證,有力地說明了雷鋒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傳承關系。該書的一大特點在于,按照《黃帝內經·本神第八》的有關內容,設計了全書的邏輯論證框架,一共包括九章。第一章道德精神的本質:天之在我者德也;第二章熱愛學習:學而時習之;第三章心懷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第四章念在為人民服務:仁者愛人;第五章思在時常反省:吾日三省吾身;第六章意在忠誠敬業:君子終日乾乾;第七章志在無私奉獻:貨力不必為己;第八章行在勤儉節約:成由勤儉敗由奢;第九章身在光耀千秋:茍利國家生死以。眾多讀者反饋,開始以為該書會很“無聊”或者“生搬硬套”,讀過之后開始相信,沒有中華傳統文化的土壤,雷鋒精神可能難以產生。
2017-01-29 作者簡介:鐘永圣(1973-),男,博士
1671-7031(2017)01-0063-06
K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