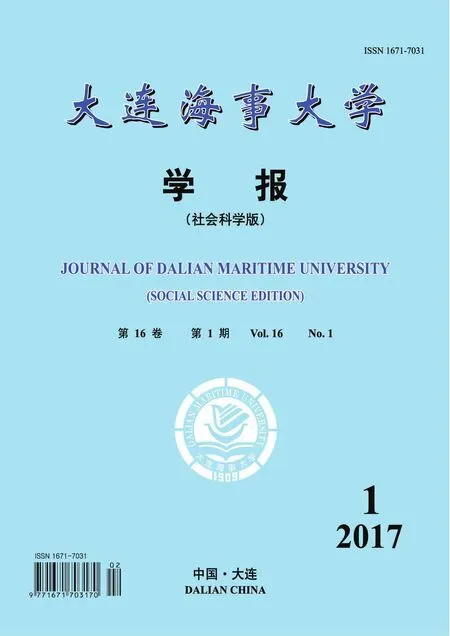世界文學史視域中的納博科夫形象及其創作密碼
崔永光,韓春俠
世界文學史視域中的納博科夫形象及其創作密碼
崔永光,韓春俠
(大連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遼寧大連 116023)
從不同的文學史去觀照納博科夫其人其作,可以客觀地看到納博科夫在各國文學史中的敘事話語策略,從中可以看到這位頗受爭議的作家的多元面孔,進而確立他在世界文學史中的位置、作用及影響。中外幾部文學史從納博科夫的移民身份、流亡生涯、詩性世界、詩學及美學品質等視角塑造了納博科夫的詩人、作家、譯者以及文學批評家的多重身份,同時呈現出其藝術世界中的“多層次性、多色彩”的藝術特性。而納博科夫的獨特創作密碼體現了一種“納博科夫精神”,這種精神的內核就是其藝術世界中的文字游戲、詩性語言及其彼岸世界主題。
俄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世界文學史;納博科夫;創作密碼
在我國納博科夫研究學者劉佳林看來,西方學界對納博科夫的研究起源可以追溯到1916年俄國一位新聞記者對納博科夫的早期詩歌未公開發表的一篇評論。到2016年,國內外學界對納博科夫的研究已經長達一個世紀之久。一百年來,從早期俄僑批評家對納博科夫作品的形式、美學和詩學批評,到20世紀80—90年代的倫理的和形而上的批評視域,再到21世紀近十幾年的跨學科和跨文化研究,納博科夫的文學聲名經歷了漫長的生長期,至今國內外學界對其人其作研究依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納博科夫的多重身份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讀和闡釋,納博科夫在世界文學史中的多重身份和形象也得以確立和認可。
截至2016年,國內學界有多篇論文對納博科夫作品及翻譯研究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梳理和評介。然而,研究發現,國內學界還沒有論述納博科夫在世界各國文學史中的研究成果*本文將以《俄羅斯僑民文學史》《20世紀俄羅斯文學》《劍橋美國文學史》《世界文學史》等文學史為研究文本,探究不同版本下納博科夫的多重形象及其創作密碼,并揭示國內編著的文學史對納博科夫的誤讀現象。。這為納博科夫研究述評開辟了一條嶄新的研究視角。從國內外不同版本的文學史去觀照和梳理納博科夫其人其作,可以客觀地看到納博科夫在各國文學史中的敘事話語策略和藝術創作密碼,從中讀者們可以看到這位頗受爭議的雙語作家的多元面孔,進而確立他在世界文學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
總體而言,中外幾部文學史中從納博科夫的族裔身份、流亡生涯、作品主題、詩學及美學等視角塑造了納博科夫的詩人、作家、譯者以及文學批評家的多重身份,同時呈現了其藝術世界中的“多層次、多色彩”*列捷尼奧夫在《俄羅斯僑民文學史》的第十四章“納博科夫”中,提出了納博科夫創造的藝術世界的主要特征是其多層次、多色彩。小說題材的多樣性、作品的多元主題為讀者解讀納博科夫其人其作提供了可能性。列捷尼奧夫指出,在納博科夫的筆下總是與對重點始終一貫的關注結合在一起的,這重點便是人類意識的復雜規律性問題,對人類生活事件進行主觀解釋的多樣性問題,人類認知的可能性和邊界的問題。的藝術特性和創作密碼。幾部中外文學史以整體論的敘事方法詮釋了納博科夫獨特的創作密碼和藝術精神。然而,由于國內部分研究者治學不夠嚴謹等原因,對納博科夫及其作品解讀存在不少的誤讀和誤譯現象,需要國內學者予以批評、指正和重讀,以還原納博科夫的真實客觀形象。
一、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是誰?
對于他的身份問題,納博科夫敏銳地意識到讀者及評論家對他形象的塑造。在一次訪談中,他本人回答到:“事實上,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出現一位對我作出新評價的人,宣稱我遠不是輕浮之徒,而是一位嚴峻的道德家,旨在驅逐罪惡,銬住愚昧,嘲弄庸俗和殘酷——而且施無上的權力于溫厚、天資和自尊。”[1]可以說,納博科夫的文學聲名在一個世紀的歲月中被打上了美學家、魔術師、文體家、游戲高手等種種標簽。然而,這些形象僅僅是單一維度的,評論家仍在繼續發現納博科夫的多重身份。“近些年來,納博科夫創造的令人敬畏的知識遺產,如對他作為鱗翅目昆蟲學家的研究新視角,已經開始備受關注。”[2]在由朱莉安·康納利編寫的《劍橋文學指南——納博科夫》(TheCambridgeCompaniontoNabokov,2005)一書中,康納利在本書的引言中重點評述了納博科夫的多重面孔,收集了納博科夫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storyteller)、一位俄羅斯作家、一位詩人、一位從筆名為西林(Sirin)轉向納博科夫的雙語作家等多篇代表論文。除了以上的多重身份,納博科夫還有傳記和自傳作家身份的研究視域。
納博科夫的小說創作中具有傳記文學的影子。如其長篇小說代表作《普寧》和《微暗的火》對國內納博科夫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納博科夫的這兩部作品本身就具有自傳性的特征,因而具備傳記視野研究的可行性。而國內研究從傳記視野對納博科夫的藝術創作進行文學解讀的嘗試不多,研究似乎只落在傳記翻譯的層面上,進行深度解讀的不多。納博科夫認為,解謎是人類最純粹、最基本的心智活動。因此,從其傳記的視野走進納博科夫的文學世界去感受其文學思想的愉悅與震顫將是打開納博科夫創作之謎的另一扇窗戶。時至今日,國外已有幾位傳記作家為納博科夫作傳,如《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人生與藝術》(Andrew Field, 1986)、法國作家布洛的《蝴蝶與洛麗塔——納博科夫傳》(Jean Blot, 2010),以及最近出版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一種藝術人生》(David Rampton, 2012)等,都對納博科夫的藝術創作人生作出了積極的探索和概括。
納博科夫研究的權威與集大成者當屬新西蘭知名學者布萊恩·博伊德(Brian Boyd)。其最負盛名的學術成果不僅包括兩卷本傳記《納博科夫傳》(俄羅斯時期和美國時期)*劉佳林分別于2009年和2011年將兩卷本傳記譯為中文。《納博科夫傳:俄羅斯時期》和《納博科夫傳:美國時期》填補了國內納博科夫傳記翻譯的空白,為國內納博科夫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參考。,還包括納博科夫經典英文小說《微暗的火》《阿達》的學術研究成果:《納博科夫的〈微暗的火〉:藝術發現的魅力》(1999)和《納博科夫的〈阿達〉:意識之地》(2001)。兩部專著里,博伊德都走進小說文本世界里,對納博科夫的藝術世界進行了詳細而又深刻的發現。此外,2011年由哥倫比亞出版社出版的新作《跟蹤納博科夫》以論文選集的形式對納博科夫最優秀的英文小說及其無與倫比的自傳《說吧,記憶》重新進行了梳理和解讀。對所有的熱愛納博科夫的讀者來說,納博科夫的作品永遠擁有謎一般的魅力和誘惑。因此,納博科夫的傳記和自傳作家身份也不容忽視。
納博科夫處處讓博伊德充滿著驚喜與驚奇,而博伊德也沒有讓納博科夫失望。兩卷本的《納博科夫傳》為這位文學大師寫下了精彩的人生注解。傳記一經出版便受到評論界的一致好評,諸如“一部細節豐贍的傳記”、“一部非凡的讀者指南”等。這位文體大師終于找到了一個配得上他的技法高超的傳記家,去追蹤其人生中每一個迷人的峰回路轉。
通過納博科夫的多重藝術身份,讀者們意識到以史學的敘述視角去審視納博科夫的人生和藝術世界,會發現納博科夫作品中的多層次性和多維度的藝術特性。通過解讀不同版本文學史中對納博科夫研究的敘事話語和策略,讀者們可以探究到納博科夫的史學形象及其獨特的創作密碼和藝術精神。
二、俄羅斯本土文學史中的納博科夫形象
劉文飛在其撰寫的《納博科夫國際研討會側記》一文中對1999年為紀念納博科夫誕辰一百周年而舉辦的“俄羅斯文學與世界文學中的納博科夫”國際研討會進行了述評。在側記中,他對冷清平淡的研討會與十年前同樣在莫斯科舉辦的聲勢浩大的紀念帕斯捷爾納克誕辰一百周年研討會做了對比,感觸頗深,同時分析了經濟危機、文學失落等種種原因。然而,本次會議也在某種意義上反映出納博科夫與其“俄羅斯性”和“非俄羅斯性”的矛盾與沖突。這位使用雙語(英語、俄語)寫作,很早就加入美國國籍的作家對俄國一直有著深深的懷舊情結。流亡的歲月里,納博科夫“心中懷藏的對過去的思念是對失去了的童年的一種極度復雜的感情”[3]。在詩中他寫道:“在我的美利堅的天空下懷念俄羅斯的那獨一無二的地方。”[3]然而,俄羅斯人面對納博科夫也出現了某種矛盾:一方面,他們認為納博科夫無疑是20世紀最偉大的俄語作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面對納博科夫的“美國作家”頭銜。[4]或許,對于納博科夫而言,生性孤傲、低調創作的他不會太多計較他的自我形象和作家地位,然而,為世界文學創作了文學瑰寶的納博科夫應該擁有自己的位置和評價。納博科夫畢竟不僅屬于美國,他也屬于俄國,也屬于世界。[4]因此,從俄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以及世界文學史中的敘事與評介去審視納博科夫的藝術創作,可以為揭開納博科夫的創作密碼,進而走進其獨特的藝術世界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路徑。
納博科夫與文學史有著歷史的淵源。他曾經寫信高度贊揚德·斯·米爾斯基(1890—1939)編著的《俄國文學史》(AHistoryofRussianLiterature),認為“這是包括俄語在內的所有語言寫就的最好一部俄國文學史”[5]。這部俄國文學史分為上下兩卷,概述了從11世紀古俄羅斯開始到20世紀初俄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遺憾的是,時代的局限性未能讓納博科夫走進這部文學史,讀者們更想知道米爾斯基對納博科夫及其藝術創作又該作出何種評論呢?
但是,由弗·阿格諾索夫編著的《俄羅斯僑民文學史》中的第十四章(列捷尼奧夫撰寫)對納博科夫在俄羅斯僑民文學第一次浪潮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較為深刻的闡釋。納博科夫創作生涯的涵蓋面、使用英俄雙語創作出的文學瑰寶以及對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弘揚與傳承等三方面原因確立了納博科夫在俄羅斯僑民文學中占據的特殊地位。可以說,“納博科夫的創作保證了當代俄羅斯文學與二十世紀初期文學之間的連續性”[6]。同時,“他為西方真正地開啟了一扇大門,讓他們了解到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俄羅斯經典作品,尤其是普希金的創作”[6]。
尤為珍貴的是,在本部文學史中,著者在文章后面列出了20世紀80—90年代俄羅斯學界對納博科夫研究的重要文獻成果。成果涵蓋了納博科夫俄語小說文集、英俄語傳記、納博科夫與俄羅斯文學傳統、俄羅斯性與非俄羅斯性之間的關系、作家世界觀和詩學特征、元小說寫作范式、對《死刑邀請》《天賦》《洛麗塔》等作品形式手法及其審美解讀。
在另一部由阿格諾索夫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一書中的第19章,分三個部分對納博科夫其人其作進行了評述。從內容上看,該章同樣是由列捷尼奧夫撰寫,增加了對長篇小說《死刑邀請》的詳盡、深入評論。第一部分以“浸透著俄羅斯骨血的一生”為標題,作者開篇便詮釋了納博科夫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占據特殊地位的三個原因,駁斥了俄羅斯僑民文學圈子里視納博科夫為“世界主義者”作家的論調,認為他“不僅獨立于俄羅斯文化之外,而且毫無俄羅斯骨血”[7]372。為此,國內學者以此為研究視角探究了納博科夫與俄羅斯文化的密切關系。第二部分揭示了納博科夫“只有現實的眾多主體形象的藝術世界”[7]373。作者深刻地解讀了納博科夫所創造的藝術世界的“多層次、多色彩”的特征,同時其所有的作品具有一種完整統一的品質。
三、《劍橋美國文學史》中的納博科夫創作密碼
納博科夫在煌煌八卷本的《劍橋美國文學史》中的位置位于第七卷散文作品(戲劇和小說 1940年—1990年)中的第三章(在路上與離路行:作為青年叛逆的局外之人)。劍橋版的美國文學史以較少的篇幅賦予納博科夫更多的是流亡意識與懷舊情結。流亡成為研究納博科夫不可忽視的動因之一。窮困潦倒的歲月、昔日的光彩、“失去的童年天堂”主題、語言的分離,在納博科夫的自傳體散文《說吧,記憶》中“飽含著懷舊的情感,充滿了精神的力量”[8]230。可以說,納博科夫在俄羅斯僑民中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但是最具詩性和回憶品質的。“在《洛麗塔》一書里他把回憶和向往,把懷舊之情和無法實現的渴望結合起來,從而獲得了極大的感染力。納博科夫的自傳是開啟他所發表的全部作品的一把鑰匙。”[8]230
納博科夫是幸運的。記憶中的歡樂時光、父親慘遭暗算的家庭變故以及遠離故國的種種不適沒有讓他沉浸在無盡的歡樂或是悲傷之中。相反,他用詩性的語言、蝴蝶、鏡子和迷宮等種種隱喻和意象勾勒出一個獨特復雜的藝術世界。“與其他俄國流亡知識分子相比,納博科夫更富有創造性和超越性,他把流亡的無法彌補的損失化為藝術靈感,輸入自己畢生的創作之中,從流亡的痛苦和損失中創造了一種文學風格。”[9]可以說,“藝術是納博科夫用來重現往昔,使之完美無缺、永恒不變的一種方式”[8]230。其中,他善于使用的蝴蝶意象以及夢蝶情結成為國內外學者解讀其作品美學思想的重要手段之一。*從中國知網上可以看出,國內學者何岳球、趙君、王凱鋒、張嘯等在文學核心期刊上發表多篇文章闡釋納博科夫的蝴蝶情結及其美學思想。其中何岳球提出:納博科夫采用精確絢麗的語言、精妙新穎的藝術手法把他對蝴蝶狂熱的迷戀貫注在他的作品中,并把這種迷戀濃縮為一種揮之不去的蝴蝶情結,使作品閃爍著超現實的激情,達到了寫實性與詩意性的雙重效果,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美學意蘊。詳見文獻[10]。在納博科夫看來,大作家總歸是大魔法師。他將寫作藝術與自然的魔力相比較,認為兩者“都是一種任憑錯綜復雜的魅力與障眼法來玩的游戲”[8]230。為此,納博科夫總會因其作品中的藝術形式、語言制造術和文字游戲而受到誤解,仿佛“納博科夫就只是一個玩弄噱頭和花招的魔術師,一個醉心于純形式的作家”[11]74。
然而,時間將成為揭開納博科夫藝術作品的密碼,而時間與回憶又是納博科夫作品中的重要主題。從《劍橋美國文學史》的敘述話語中可以看出,《洛麗塔》中亨伯特的回憶與向往、《說吧,記憶》中納博科夫對過去時光栩栩如生的回憶,卻“不帶絲毫傷感的強烈情感”,這都賦予了納博科夫的藝術世界極大的感染力,飽含著懷舊情緒和精神力量。因此,對納博科夫的研究無法回避其海外流亡者的身份,其多部作品表達了對失去的俄國昔日歲月的深深眷戀:《瑪麗》中加寧對初戀情人的那段令人神魂顛倒的愛情、《洛麗塔》中亨伯特對那個精明的小仙女所代表的心中往昔的渴望,以及《說吧,記憶》中對失去的童年的復雜感情等都反映了納博科夫創作中的流亡作家身份及流亡話語策略。該文學史鮮明地指出,寫于1948年至1955年間的《說吧,記憶》《洛麗塔》和《普寧》“組成了描寫海外流亡者內心生活的三部曲”[8]232。
該文學史尤其對《洛麗塔》進行了多層次、多視角的剖析,涵蓋著20世紀50年代美國文化的主題及亨利·詹姆斯式的國際主題,賦予其道路小說、偵探小說、元小說以及“一部后現代主義小說家的自省之作”等風格特征。[8]239后現代主義小說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特點使得這部小說具有黑色幽默、諷刺戲仿、政治寓言等多元闡釋話語和藝術策略。更為深刻的是,編者還對《洛麗塔》與《麥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看不見的人》等作品進行了對比研究,凸顯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文化變遷對社會發展及自我解放的深刻影響。
總之,《劍橋美國文學史》中對納博科夫的評介重點闡釋了納博科夫的流亡意識、懷舊情結和回憶主題,同時對《洛麗塔》背后的后現代寫作特點及其深刻的文化主題進行了客觀、詳盡、有力的解析。但遺憾的是,該部文學史對納博科夫的其他重要作品和詩歌都未做進一步的評論,缺失了對納博科夫作品較為全面的評介和解讀。
四、《世界文學史》:誤讀與重讀
納博科夫的自我形象的確在國內學界因其作品受到嚴重誤解。《洛麗塔》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世界級的禁書”、“非道德小說”,甚至是“色情小說”而被不斷地誤讀和誤譯。從國內學者張德明編著的《世界文學史》中,筆者發現,盡管給予納博科夫的介紹不到兩頁的篇幅,卻對《洛麗塔》的故事情節描述存在不小的錯誤。如認為“亨伯特在惋惜之余開槍打死了她的男友,被判死刑”[12]388。“他把早年戀人的變化歸罪于她的丈夫。但他不知道,當他開槍企圖殺死這位丈夫的同時……”[12]389這種介紹嚴重地混淆了原著中的人物關系,因為亨伯特最后殺死的是奎爾蒂(Quilty),而并非是她的丈夫。而這種概論式、淺顯的評介難以讓讀者們正確地理解納博科夫在世界文學史中的地位。因此,盡管納博科夫的文學聲名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的生長期,國內學界仍需要重讀納博科夫其人及其作,客觀準確地確立納博科夫在世界文學史中的形象和地位。
劉佳林在《納博科夫研究及翻譯述評》一文中對中國的納博科夫翻譯與研究現狀做了一個概括性的評述。他運用翻譯實例對譯者翻譯納博科夫作品中的誤讀和錯譯進行了梳理和批判。正如作者所言,“要真正提高中國納博科夫的研究水平,必須首先在翻譯上重新投入大量的精力”[11]80。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譯文出版社自2005年12月陸續推出納博科夫作品系列,組織了國內著名的翻譯家和納博科夫研究學者,如梅紹武、主萬、蒲隆、王家湘等進行翻譯,從而保證了譯文的高質量。2013年,該社重新整理、編輯,以精裝形式推出的納博科夫文集,涵蓋了納博科夫的14部小說,整體風格典雅大方,從裝幀到內容都獨樹一幟。
然而,與西方學界對納博科夫研究的豐富文獻相比,國內學界對納博科夫的詩歌、短篇小說、傳記、書信以及代表研究文獻的翻譯仍有漫長的路要走。中國學者要開拓研究視野,需要付出精力、智慧和耐心將西方重要研究成果引進中國進行翻譯和出版,不斷推動納博科夫在國內的深入研究。
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一書中指出:“一個優秀讀者,一個成熟的讀者,一個思路活潑、追求新意的讀者只能是一個‘反復讀者’(rereader)。”[13]對于納博科夫的藝術作品同樣需要讀者反復閱讀,在其精心設計的迷宮里恣意探險與發現,最終體驗其藝術世界中獨特的“審美愉悅”。因此,要了解納博科夫的完整世界就要重讀其創作的每一部小說,因為納博科夫的所有作品具有一種完整統一的品質。“納博科夫的全部作品仿佛都在征求續集:它們就好似綜合的藝術整體中的片段。各種不同作品之間也是彼此相聯,就像同一部抒情系列或書中那些單獨的詩作彼此互相關聯一樣。”[7]374納博科夫所期望的就是優秀讀者借助豐富的想象力和藝術審美情趣去發現納博科夫的獨特創作密碼。
美籍華人,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英語系教授童明就是一位優秀的讀者。其所著的《美國文學史》(AHistoryofAmericanLiterature, 2008)中對納博科夫的闡述視角獨特,觀點新穎,見解深刻。他將納博科夫置于全書的最末一章:“美國文學的全球化:飛散作家”*“飛散”這一概念和術語是童明教授對“diaspora”的中文翻譯。他多次撰文從飛散的視角闡釋了世界優秀文學作品中的跨民族美學和文化批評的力量,其中就包括對納博科夫及其作品的“飛散”視角解讀。詳見文獻[14]~[16]。。在多元文化交融的全球化時代影響下,納博科夫、莫里森、拉什迪、奈保爾等一批作家“成為由跨國意識影響的快速發展起來的文學的一部分,他們對美國文學經典化中的傳統思維方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同時也為美國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活力”[17]364。童明將這些新類型文學歸類為飛散文學(diasporic literature)。童明從“飛散意識和文化輸出”的視角對“飛散”的詞源及其文化表征進行了周到的梳理,并提出了飛散寫作的七大主題特征。*童明教授從文化地域與有限空間、后殖民空間下的多元歷史、民族主義問題、文化翻譯、遭遇異域、反對同化意識、族裔文學等七大方面闡釋了全球化時代下的飛散意識和文化表征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闡釋的最具代表性的五位當代美國飛散作家中,童明將納博科夫放在第一位加以詳細評介。研究發現,童明教授在其文章中多次提及納博科夫流亡生涯的文化價值及其情感結構。他對納博科夫的短篇小說中的飛散主題有著獨到的見解和準確的定位。“小說中的人物,原有的生活被切斷,故國的往日已疏離,現實和夢交織或沖突,小說如泣如訴,欲愛而不能、自我錯位的思緒,逐漸深化為富有哲學思考的情感主題:詩人對殘酷極為蔑視,因而時時為生命中無所不在的仁慈所感動,藝術形成強大的生命力。”[15]154
在《美國文學史》中,童明主要評介了其短篇小說集中的幾篇代表作、長篇小說《洛麗塔》和《普寧》。在童明看來,納博科夫的小說背景有時設在美國、有時設在俄國,有時穿插于兩國之間,有時設在想象的國度。這種背景設置的不斷變換是與其作為一個飛散者的身份一致的。[17]369亨伯特和普寧作為飛散者的形象注定受到誤解。兩部作品都可以用其短篇小說中的主題進行更為有意義的詮釋,即通過殘酷的現實去再現疏離的過去時光。
五、結 語
21世紀背景下的納博科夫研究應該以更為開放的態度、多棱鏡的視角去重新審視納博科夫的多重身份及其多層次的藝術世界。然而,開放多元并不意味去誤讀和曲解納博科夫。任何一種解讀都不可疏離納博科夫文學思想的基本內核和深層文化內涵。納博科夫的獨特創作密碼體現的是一種“納博科夫精神”——這種精神的內核就是其藝術世界中的文字游戲、詩性語言及其彼岸世界的形而上主題。正如納博科夫本人所言,重讀作品時真正需要的是“心靈,腦筋,敏感的脊椎骨”[13]。因此,讀者和評論家對納博科夫及其作品的解讀永遠是開放式、多元化的。納博科夫試圖要做的是邀請讀者們和他一起探險和創作,一起在其制造的迷宮世界里發現、思考和頓悟。而作為優秀的讀者需要走進納博科夫的文學文本,去做優秀的重讀者,在感受“審美愉悅”的同時,更要去領悟隱含在其文本中的獨特的創作密碼和文學精神。
[1]NABOKOV V. Strong opinion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193.
[2]CONNOLLY J W.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bokov[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1.
[3]納博科夫.說吧,記憶[M].王家湘,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69.
[4]劉文飛.納博科夫國際研討會側記[J].外國文學動態,1999(3):41.
[5]NABOKOV V. Selected letters, 1940-1977[M].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0:91.
[6]阿格諾索夫.俄羅斯僑民文學史[M].劉文飛,陳方,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435.
[7]阿格諾索夫.20世紀俄羅斯文學[M].凌建侯,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8]伯科維奇.劍橋美國文學史:第8卷[M].孫宏,主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9]崔永光.流亡話語與故國想象——納博科夫作品中海外流亡形象的心路歷程[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5(1):103.
[10]何岳球.納博科夫的蝴蝶情結與美學意蘊[J].當代外國文學,2007(1):104-110.
[11]劉佳林.納博科夫研究及翻譯述評[J].外國文學評論,2004(2):70-81.
[12]張德明.世界文學史[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13]納博科夫.文學講稿[M].申慧輝,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3.
[14]童明.飛散[J].外國文學,2004(6):52-59.
[15]童明.家園的跨民族譯本:論“后”時代的飛散視角[J].中國比較文學,2005(3):150-168.
[16]童明.飛散的文化和文學[J].外國文學,2007(1):89-99.
[17]童明.美國文學史[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本刊聲明
為擴大本刊及作者知識信息交流渠道,加強知識信息推廣力度,本刊已許可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在CNKI中國知網及其系列數據庫產品中,以及萬方數據——數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等,以數字化方式復制、匯編、發行、信息網絡傳播本刊全文。該著作權使用費及相關稿酬,本刊均用作為作者文章發表、出版、推廣交流(含信息網絡)以及贈送樣刊之用途,即不再另行向作者支付。凡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發表之行為即視為同意本刊上述聲明。
2016-11-20 基金項目:2016年度大連海洋大學社科聯重點課題(2016xsklzd-23) 作者簡介:崔永光(1981-),男,講師;E-mail:yongguangc@163.com
1671-7031(2017)01-0123-06
I712.06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