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美學(xué)談
——兼評(píng)《雙城記》新譯本
楊 佳,耿寧荷(.沈陽化工大學(xué) 外語系,遼寧 沈陽 04;.埃森哲信息技術(shù)有限公司,遼寧 大連 603)
翻譯美學(xué)談
——兼評(píng)《雙城記》新譯本
楊 佳1,耿寧荷2
(1.沈陽化工大學(xué) 外語系,遼寧 沈陽 110142;2.埃森哲信息技術(shù)有限公司,遼寧 大連 116023)
中國傳統(tǒng)翻譯理論歷來講究譯文的美。依照劉宓慶先生提出的翻譯的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即相對(duì)性、時(shí)代性、社會(huì)性和依附性,審視《雙城記》三個(gè)流行的譯本,主要從耿智和蕭立明教授翻譯的《雙城記》新譯本引例,來討論如何依照翻譯的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來實(shí)現(xiàn)譯文的美。
翻譯美學(xué);相對(duì)性;時(shí)代性;社會(huì)性;依附性
中國最早的翻譯理論就有講究譯文美的論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鳩摩羅什提出的“依實(shí)出華”[1]。所謂“依實(shí)”,就是忠于原文的思想,所謂“出華”,就是譯文要通順文雅。中國近代的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和維新運(yùn)動(dòng)直到后來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使翻譯活動(dòng)大大超出佛經(jīng)翻譯,而很快轉(zhuǎn)向文史哲和科技翻譯。在這一洪流中,起主導(dǎo)作用的就是嚴(yán)復(fù)“信達(dá)雅”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到了21世紀(jì),隨著外國譯論的引進(jìn)和中國自身的翻譯理論發(fā)展和深化,對(duì)翻譯美學(xué)有了更加系統(tǒng)的研究,如劉宓慶先生提出的翻譯的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即相對(duì)性、時(shí)代性、社會(huì)性和依附性[2]。狄更斯的《雙城記》有一二十個(gè)譯本。201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耿智教授和蕭立明教授翻譯的世界文學(xué)名著典藏系列的《雙城記》全譯本,這一譯著對(duì)想提高名著翻譯水平,提升翻譯能力的譯者而言無疑是部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這里主要將20多年來的兩個(gè)流行的譯本,即1993年版石永禮和趙文娟的譯本和2011年版張玲和張揚(yáng)的譯本,跟新譯本進(jìn)行比較,并按照劉先生的這些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來賞析《雙城記》的這個(gè)新譯本,進(jìn)而探討翻譯美學(xué)的問題。
一、相對(duì)性
翻譯是一種雙語活動(dòng),具體說來,就是將一種語言轉(zhuǎn)換成另一種語言。世界所有的語言按照其源流,分為七大語系。在同一種語系中進(jìn)行翻譯時(shí),語言模擬式的形式美可能多一些,而跨語系之間的翻譯時(shí),形式美往往難以模擬。因此,“雙語轉(zhuǎn)換則應(yīng)努力探求對(duì)應(yīng)式或重建式的形式美”[2]。英語屬于印歐語系,漢語屬于漢藏語系。因此轉(zhuǎn)換只能按照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相對(duì)性來處理。《雙城記》的開篇本身就是一段修辭十分考究的美文。這是一般讀者都很熟悉的文字,由于篇幅所限,這里只引出最后一個(gè)分句,來看三個(gè)譯本的處理方法。
—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1993年版的譯文:
——簡言之,那個(gè)時(shí)代跟現(xiàn)代十分相似,甚至當(dāng)年有些大發(fā)議論的權(quán)威人士都堅(jiān)持認(rèn)為,無論說那一時(shí)代好也罷,壞也罷,只有用最高比較級(jí),才能接受[3]3。
2011年版譯文:
——簡而言之,那個(gè)時(shí)代同現(xiàn)今這個(gè)時(shí)代竟然如此惟妙惟肖,就連它那叫嚷得最兇的權(quán)威人士當(dāng)中,有些也堅(jiān)持認(rèn)為,不管它是好是壞,都只能用“最”字來表示它的程度[4]3。
新譯本相關(guān)譯文:
——總之, 那時(shí)和現(xiàn)代如此相似,以至于在那些最愛大發(fā)議論的權(quán)威人士中,有些人硬要接受那個(gè)時(shí)代,雖說褒貶不一,但是為描寫那個(gè)時(shí)代,各自的措辭,無所不用其極[5]3。
比較三個(gè)譯本,第一個(gè)譯本完全按照英文的詞義直接譯出。按照英語語法,形容詞和副詞有三級(jí)比較,即同級(jí)、比較級(jí)和最高級(jí)。可是漢語是沒有這種語法規(guī)則的,漢語是用具體的詞語來進(jìn)行比較,例如:“一樣”“同級(jí)”“比較”“最”等等。第二個(gè)譯本過分使用了“它”。按照英語的消極修辭要求,也就是英語重形合。話語強(qiáng)調(diào)形式連接(coherence),代詞的照應(yīng)就是一種重要的形式連接手段。但是漢語是一種重意合的語言,過分使用代詞,就會(huì)影響漢語的流暢[6]。同時(shí)用“最”也不恰當(dāng),因?yàn)榍拔闹校饲皟蓚€(gè)分句外,并沒有用“最”來形容那個(gè)時(shí)代,而是用其他的詞語來形容,例如“智慧的時(shí)代”“愚蠢的時(shí)代”等等。相比之下,新譯本采用了對(duì)應(yīng)式的形式美,忠實(shí)地表達(dá)了原文的思想。
二、時(shí)代性和社會(huì)性
翻譯是隨著人類文明的進(jìn)程而不斷開展的,不同的時(shí)代就有不同翻譯原則,翻譯也就根據(jù)這些公認(rèn)的翻譯原則,給不同時(shí)代的社會(huì)帶來不同的譯本。前面說到了嚴(yán)復(fù)的“信達(dá)雅”,他所謂的“雅”,是文字的高雅。而那時(shí)是中國的舊文化時(shí)期,文言文被視為高雅的文字。以同時(shí)期的翻譯大家林琴南為例,他自己并不精通西方文字,與他人合作,翻譯了一百多部西方文典,譯文全都是文言文。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后,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時(shí)代不同了,社會(huì)不同了,林琴南的譯文對(duì)研究翻譯和研究近代文化的學(xué)者來說,可能還有很大的可讀性,但是對(duì)廣大讀者來說,已經(jīng)成了過時(shí)的東西。當(dāng)代人追求平易清新的文風(fēng)。狄更斯的《雙城記》是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攻打巴士底獄是小說的一個(gè)中心場面。平民出身的酒店老板德法奇率領(lǐng)平民造反時(shí)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Deep ditches, single drawbridge, massive walls, eight great towers, cannon, muskets, fire and smoke. One drawbridge down! “ Work! Comrades all. Work! Work, Jachques One Thousand, Jachques Two Thousand, Jachques Five-and-Twenty Thousand; In the name of all the Angles or the Devils which you prefer—Work!” Thus Defarge of the wine shop, at his gun, which had long grown hot.
再來看三個(gè)譯本:
1993年版的譯文:
深壕,單座吊橋,巨大的石頭墻,八座大塔樓,大炮,火槍,炮火和硝煙。一座吊橋放下來了!“干哪,同志們,干哪!雅克一號(hào),雅克二號(hào),雅克一千號(hào),雅克兩千號(hào),雅克兩萬五千號(hào);以一切天使和魔鬼的名義——你們愛用什么就用什么——干哪!”開酒店的德法日這樣喊道,一邊仍開著那早已發(fā)燙的大炮[3]204。
2011年版的譯文:
深壕溝,單吊橋,高厚堅(jiān)固的石頭墻,八座大塔樓,大炮,火槍,烈火,濃煙,一個(gè)吊橋攻下了。“干呀,全體同志,干呀!干呀,雅克一號(hào),雅克二號(hào),雅克一千號(hào),雅克兩千號(hào),雅克兩萬五千號(hào),以所有天使的名義干,或是以魔鬼的名義干——隨你們選擇吧——干!”就這樣,酒鋪的德法日一直守在大炮旁邊,那門大炮早就發(fā)燙了[4]240。
新譯本的譯文:
深的壕溝,單層吊橋,巨大石墻,八個(gè)塔樓,大炮,毛瑟槍,火和煙。一個(gè)單層吊橋攻下來了。“沖啊!同志們,沖啊!雅克一,雅克二,雅克三,雅克一千,雅克兩千,雅克兩萬五千,以天使的名義,或者以魔鬼的名義——隨你們以什么名義——大家沖啊!”于是酒店老板德法奇仍守在那尊炮前,那大炮早就發(fā)燙了[5]222-223。
對(duì)比三個(gè)譯本,前兩個(gè)譯本違背了語言的時(shí)代性和社會(huì)性。這里關(guān)鍵是對(duì)原文work的翻譯。根據(jù)《新牛津英漢雙解大辭典》,這個(gè)英語動(dòng)詞的本義是do work,engage in one′s job也就是“工作”或者“干事情”但是英語的常用詞往往是多義詞。這個(gè)詞的引申義還有make efforts to achieve something,move with difficulty into another position, typically by means of constant movement or pressure,也就是“盡力去做”,或者“奮力向前推進(jìn)”的意思。而在中國絕大多數(shù)戰(zhàn)爭小說中,在絕大多數(shù)的戰(zhàn)斗影片和電視劇中,這種戰(zhàn)斗口號(hào)都是用“沖”這個(gè)詞。再者,戰(zhàn)斗口號(hào)是口語,應(yīng)當(dāng)十分流暢,不能文縐縐的。相比之下,新譯本更加符合漢語的時(shí)代性和社會(huì)性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
三、依附性
翻譯不是創(chuàng)作,不能有譯者的主觀臆造,譯者只能以自己的審美認(rèn)識(shí)為依據(jù),去進(jìn)行審美的體驗(yàn)。換句話說,譯者必須對(duì)原文有深透的理解,也就是能把握原作者的審美意圖。這里有兩個(gè)層面,一是原語的思想層面,二是原語的修辭層面。小說的主要人物之一卡登是個(gè)偉大的利他主義者,有才華,有見識(shí),思想敏銳,道德高尚,但又不為社會(huì)所賞識(shí),只能屈身在皇家律師手下。他的性格被社會(huì)扭曲了,但仍然心地善良,為了自己心上人露西的幸福,甘愿自我犧牲,頂替情敵走上斷頭臺(tái),含著微笑,寧靜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這是作者塑造的人道主義的最美典范。小說的最后,是以描寫卡登臨刑時(shí)的心里活動(dòng)而結(jié)束的。作者用一系列的排比結(jié)構(gòu)勾畫了這種心理活動(dòng)。下面摘取排比的最后一段,原文如下:
I see that child who lay upon her bosom and who bore my name, a man winning his way upon in the path of life which was once mine. I see him winning it so well, that my name is made illustrious there by the light of his. I see the blots I threw upon it, faded away. I see him, foremost of just judges and honored men, bringing a boy of my name, with a forehead that I know and golden hair to this place…then fair to look upon, with a trace of this day′s disfigurement…and I hear him tell the child my story, with a tender and a faltering voice.
1993年版譯文:
我看到,她抱在懷里,用我的名字命名的那個(gè)孩子,已長大成人,在曾經(jīng)是我的人生道路上,憑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就。我看到他獲得那么大的成就,我的名字也沾他的名字的光而大放光彩。我看到我給自己的名字抹上的污點(diǎn)消失了。我看到他,最公正的法官和最受尊敬的人,帶著一個(gè)用我的名字命名的男孩,有我熟悉的前額和金發(fā),來到這里——那時(shí)看起來很美,一點(diǎn)也看不到今天這樣殘破的景象了——我聽到他用溫柔的顫抖的聲音跟他講我的故事[3]355。
2011年版譯文:
我看見,那個(gè)過去抱在她懷中,取了我的名字的孩子長大成人,在我一度走過的生活道路上攀登,節(jié)節(jié)成功。我看見,他的成功如此輝煌,因而我的名字也因他而顯得光彩。我看見,我在那條道路上留下的污點(diǎn)都褪盡消失。我看見,他,正直法官和堂堂男子中的佼佼者,帶著一個(gè)又取了我的名字、長著我熟悉的前額和金黃頭發(fā)的男孩,來到此地——那時(shí),此地看來很漂亮,沒有一點(diǎn)現(xiàn)今這種不成樣子的痕跡——我還聽見他以溫柔、顫抖的聲音,給那男孩講我的故事[4]417。
新譯本的相關(guān)譯文:
我看到,那個(gè)曾躺在她懷里,取了我名字的孩子,長大成人,在我走過的人生道路上前進(jìn),不斷成功。我看到他成績?nèi)绱溯x煌,使得我的名字增添了不少光彩。我看到,我在那條道路上留下的污點(diǎn),消失殆盡。我看到,他在正直的法官和堂堂男子中成了佼佼者,帶著一個(gè)男孩,也取了我這個(gè)名字,長著我所熟悉的前額和金黃的頭發(fā),來到此地——到那時(shí),這個(gè)地方會(huì)非常美麗,沒有現(xiàn)在這種殘破的痕跡了——我聽到他用親切而顫抖的聲音,給這男孩講我的故事[5]392。
這三個(gè)譯本,可以說,三者都注意到了原文的思想美和語言美。不過多讀幾遍,不難看出,新譯本更加注意到譯文的流暢和形式美。例如,新譯本用比較工整的標(biāo)點(diǎn)顯示出排比句式,讀起來更流暢。這就是依附原文,譯者追求譯文美的一種表現(xiàn)。
四、結(jié) 語
翻譯美學(xué)是翻譯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融貫中西的大師錢鐘書先生提出的“化境論”:“文學(xué)翻譯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zhuǎn)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xí)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qiáng)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fēng)味。”[6]本文比較了三個(gè)譯本,從小說的三個(gè)重要篇章(第一部第一章:時(shí)代;第二部第二十一章:腳步回聲;第三部第十五章:足音永逝)引例,經(jīng)過比較差異之處,體現(xiàn)出翻譯美學(xué)觀的重要性。筆者所要指出的是,這些差異并不存在于理解層面,而存在于語言轉(zhuǎn)換層面。可以說,不注意翻譯美學(xué)的譯文難稱上品,而運(yùn)用翻譯美學(xué)的譯文有可能成為佳作。
[1] 陳福康. 中國翻譯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
[2] 劉宓慶. 當(dāng)代翻譯理論[M].北京:中國對(duì)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216-217.
[3] 狄更斯. 雙城記[M]. 石永禮,趙文娟,譯.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3.
[4] 狄更斯.雙城記[M]. 張玲,張揚(yáng),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5] 狄更斯.雙城記[M]. 耿智,蕭立明,譯.廣州:花城出版社,2016.
(責(zé)任編輯 王莉)
OnAestheticsinTranslation——As a review on the new version ofATaleofTwoCities
YANGJia,GENGNing-he
(1.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Shenyang Liaoning 110142, China; 2. Accenture Enterprise Enablement of Dalian, Dalian Liaoning 116023, China)
In China′s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elegance is always stressed, from Kumurajiva′s norm (elegance based on the original) to Yan Fu′s criterion (faithfulness, smoothness and elegance). And that point of view has developed unti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today. This article, based on Liu Miqing′s standards of aesthetics in translation, namely relativity, times, sociality and anaclisis, discusses the aesthetics in translation by drawing a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popular translation versions ofATaleofTwoCities, mainly citing examples from the new version translated by Professor Geng Zhi and Professor Xiao Liming, and illustrates how to realise this aesthetics in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n translation; relativity; times; sociality; anaclisis
2016-11-24;
2017-09-13
楊佳(1980-),女,湖南長沙人,講師,主要從事翻譯理論與實(shí)踐研究。
2096-1383(2017)06-0625-04
H059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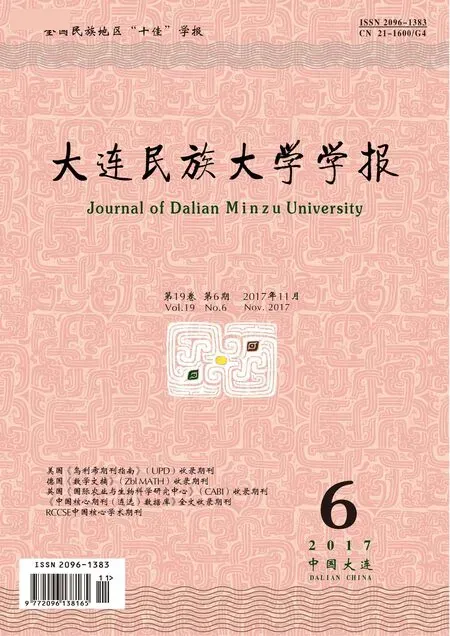 大連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7年6期
大連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7年6期
- 大連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藏族維吾爾族本科生英語學(xué)習(xí)動(dòng)機(jī)個(gè)案研究
——以大連民族大學(xué)為例 - 大學(xué)英語教學(xué)M-learning模式的SWOT量化分析
- 少數(shù)民族本土風(fēng)格在漢語文本中的還原與翻譯對(duì)應(yīng)
- 《寧古塔滿族薩滿神話》的文學(xué)解讀
- 會(huì)計(jì)準(zhǔn)則變革研究的主題、路徑與方法
——基于國際期刊2007-2014年的數(shù)據(jù)分析 - 遼寧省城市化與城市游憩環(huán)境協(xié)調(diào)度評(píng)價(jià)與優(yōu)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