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伯格
徐德林
1970年前后,英國電視臺BBC播出了一系列“藝術啟蒙”節目,造就了一批電視名人,其中之一就是日后享譽世界的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1972年,伯格在BBC出鏡主講了關乎藝術的4集系列片《觀看之道》,然后出版了脫胎于此的同名書籍。為了挑戰藝術史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三年前以歐洲白人男性視角主講的13集紀錄片《文明》,伯格挪用了沃爾特·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作為理論資源,探究視覺意義與詞語意義之間的關系。
啟迪一代人對待藝術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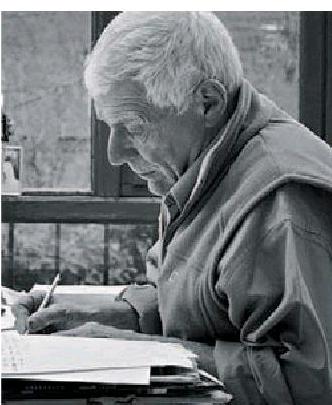
伯格指出,人們觀看事物的方式受制于其知識與信仰,人們只看見被注視之物,而注視卻具有選擇性,所以,人們將所見之物納入其能及的范圍,不斷審度物我之間的關系。通過對藝術與政治、女性作為觀看的對象、油畫自身的矛盾、廣告與資本主義白日夢等主題的實例闡釋,伯格道明了當代(視覺)文化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即現實是由其被感知的方式建構的。此間的伯格并未糾纏于被建構的現實真實與否,而是開宗明義地將廣告、媒體、宣傳等視為觀看之道的內在維度,將流行文化納入藝術批評的視野。
在伯格看來,物之物質性并不在于它是客觀或自然事實,而在于它表達某種內在結構、表現權力的存在。表面現象的深層結構是權力,這一“觀看之道”有效地保證了伯格在教人“觀看”的同時教人“反觀”,以新的方式和視角重新思考藝術和這個世界,雖然他的電視系列片被用作教學資料,他的頻頻參與現場辯論也功不可沒。伯格在關注藝術現代形式的同時,基于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關注藝術對現代資產階級的經濟價值,從而有效地融合了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促成了流行于彼時學界的各式結構主義批評,將其批評性閱讀拓展到非言語類媒體、文化之中。
固然,伯格并不是唯一以意識形態為視角考察視覺文化的人,但他是最早獲得大眾認可的人之一。無論你是否接受他的觀點,至少你會思考他的“觀看之道”,更何況他寫出了通俗易懂的藝術評論。所以,《觀看之道》的影響力是具有革命性的,足以啟迪一代人對待藝術的方式,伯格因此迅速成為了被廣泛推崇的著名藝術評論家。然而,我們必須知道,一如他在《肖像》中明確指出的:“我一直都討厭被稱作‘藝術評論家”,伯格更喜歡的身份是“講故事的人”,或者“散文作家”。這一方面是因為在機械復制時代,藝術評論家雖然勝過藝術品銷售商,但依舊是“令人討厭的人”;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故事既可以是虛構的,也可以是真實的。故事的存在是為了分享經驗,伯格感興趣的是一個人的主觀性和行為,他的命運和選擇,那些無法納入計劃和規則的謎,而他面臨的挑戰則是“解釋這些謎”,并“確保它們能被分享,不至于孤立”。
為此,“講故事的人”伯格習慣于“拒絕向前看,堅持活在當下”——“這是我從很早就養成的習慣,它是一種逃離,離開測算、預言和因果鏈”,其結果是伯格不斷嘗試以不同形式講故事。畫畫,辦畫展,后來寫藝術評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隨筆,以及眾多難以歸類的文字,但所有這一切對他而言都不過是形式上的差別而已,他只是一直在講故事。縱觀伯格所講的紛繁多樣的故事,我們不難發現,他為之寫作的“世間真正重要之事”既可能關乎政治、理念、藝術和文學,也可能關乎桌上的一餐飯、手中的一杯酒,或者一個手勢所引發的微妙情感、一個微笑所包含的共謀,而這些之中究竟什么能夠成為他的“世間最重要的事”,則關乎他在某一當下的好奇心和眼光。
關于自己的好奇心,伯格曾這樣解釋過:“作為一個常懷有好奇心的人,這種觀察方式對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我就像是船上的雜務員,做些不起眼的小活,也監測、望風,但我不是導航員,恰恰相反,我在船上閑逛,觀察奇怪的地方——桅桿、舷緣什么的——此外只剩下看海。”而伯格的眼光之敏銳,我們可以從如下比喻中窺見一斑:“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性別、自己的年齡,這和人口統計學沒有什么關系。羅馬是女性,敖德薩也是。倫敦是一個少年,一個頑童,而且,關于這一點,從狄更斯的時代開始就沒有什么變化。巴黎呢,我相信,是一名男子,正當二十多歲的年紀,卻愛上了一位年長的婦人。”所以,伯格總是能夠在自覺地與主流藝術評論保持距離的同時,“觸動讀者內心極為相似的詫異與經驗”。

“文學惡棍”
伯格的不拘一格講故事或者寫作難免會遭人詬病,比如英國馬克思主義小說家、詩人斯蒂芬·斯彭德曾批評伯格的作品不過是“大霧中的號角”,含混不清。但是,沒有人能夠否定的是,因為堅信寫作的力量,伯格不僅一直筆耕不輟,而且即使是在最為傳統的意義上,也可謂是一個優秀的作家。1958年,伯格出版了第一部小說《我們時代的畫家》,其題材來自他與居住在倫敦的幾個流亡藝術家之間所建立的友誼,他們大多數是從東歐和中歐流亡而來。小說主人公亞諾什·拉文是一個非常政治性的畫家,他生活、夢想在現代主義的遺產里,并思索在社會主義者的藝術和思想里迫切需要一個新的、批評的現實主義。小說結尾,在1956年事變之際,亞諾什從倫敦消失,回到祖國匈牙利,甚至拋下他最親密的人——他的妻子、小說的作者、讀者,他們對他所可能從事的行動,對他所可能遭遇的命運一無所知。這部小說極具說服力地展現了政治現實的復雜性,出版后同時受到了右翼和左翼的激烈攻擊。
1972年,伯格憑借講述“一戰”前歐洲某位浪子逐漸政治覺醒的小說《G.》獲得了布克獎和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獎。在發表布克獎受獎演說時,伯格譴責了布克獎贊助者食品貿易巨頭布克·麥康奈爾公司,抨擊其財富積累得益于130多年的加勒比海貿易,而“加勒比如今的貧困,就是這種或類似剝削的直接結果”。伯格當場宣布將一半獎金捐給激進黑人民權組織“黑豹黨”,并將其引為同路人;出格的舉動引得輿論大嘩,伯格因此被貼上了“文學惡棍”的標簽。另一半獎金幫助伯格完成了關于歐洲海外勞工的研究,見諸他在1975年出版的《第七人:歐洲農業季節工人》,以復雜、圖解的術語揭示了歐洲海外勞工受剝削的本質。
2005年,年近八旬的伯格出版了自傳體小說《我們在此相遇》,富有詩意地告訴讀者“我和你,我們都在這世上,為了修補一些已經破損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為何會出現的原因”。2008年,伯格憑借關乎“情欲的身體”的《A致X》,再次獲得了布克獎提名。2016年,伯格驚訝地發現自己的觀看之道有了些許變化,一是自己對手機短信的熱情,一是基于自己隱居經歷的紀錄片《昆西四季:約翰·伯格的四幅肖像》在第66屆柏林電影節的展映。不過,絲毫沒有變化的是,伯格依然“堅持活在當下”,一如他對英國脫歐的思考所暗示的:“在我看來,我們必須要回歸,我們要重述全球化的意義,因為這意味著資本主義,意味著世界金融組織變得有風險,不再擁有第一生產力的地位,政治家們幾乎失去了作出政治決策的力量,我指的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家。國家不再是之前的樣子。”
所以,透過伯格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寫作,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三個主題的持久關注:藝術、藝術家和政治的關系;視覺或者觀看本身的意義與歧義;當代經濟政治變遷中的農村和農民。貫穿這些主題的,是他通過延續“從D.H.勞倫斯到肯·洛奇的英國異議傳統”而永葆的批判精神和悲憫之心。作為“異類”,伯格非常擅長以簡單的方法闡述復雜的思想,讓自己的寫作充滿感性與詩意,雖然這樣的寫作會與學術論述大異其趣,造成學院體制接受的困難,但它賦予伯格的“公共性”卻讓他獲得了學院派作者望塵莫及的廣大讀者群,享有既有長度也有深度和密度的人生。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