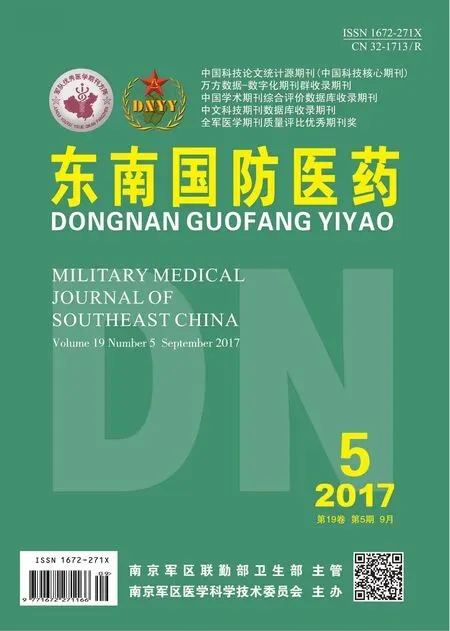骨質疏松性骨折預測方法的研究進展
王耿杰,倪連紅,馬良赟
·綜 述·
骨質疏松性骨折預測方法的研究進展
王耿杰1,倪連紅2,馬良赟1
跌倒的低能量創傷造成的骨折往往是骨密度降低所致的骨折,也稱為骨質疏松性骨折。骨質疏松性骨折是骨密度降低和骨的微觀結構退化的結果。老年人的跌倒風險與平衡能力、骨質疏松程度、年齡等相關。骨量和骨質量的致病、藥物、BMI、營養狀況、維生素D的攝入、新近的骨折病史、最近吸煙史、酒精的攝入量、運動情況、最近是否使用糖皮質激素、是否有類風濕性關節炎以及其他導致繼發性骨折的危險因素,均為骨質疏松性骨折的危險因素。文章就骨質疏松性骨折常見的骨折因素進行分析,并對目前國內外預測骨折的工具進行綜述。
骨質疏松;骨折預測;骨折風險
骨質密度降低,骨微觀結構改變,是骨質疏松的表現。年齡,性別,BMI,既往骨折史,糖皮質激素的使用,酒精及吸煙,基礎疾病均為骨質疏松性骨折的危險因素。目前國內外預測方法較多,使用最為廣泛的是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開發的骨折危險評估工具(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ol)。合理有效地對骨折傾向患者進行評估,具有重要意義。
1 跌倒導致的骨質疏松性骨折
1987年,kellogg國際老年跌倒預防工作組將跌倒定義為:無意圖的摔倒在地或更低的平面上,但不包括暴力、意識喪失、偏癱或癲癇發作所導致的跌倒。跌倒是老年人骨折的主要誘因,而骨質疏松是老年人骨折的一個關鍵因素,除少數情況下,如脊椎的骨折可能是由于自身重力作用、咳嗽或用力排便而發生椎體壓縮性骨折。在大多數情況下,骨質疏松性的老年人,一旦發生跌倒,往往預示著骨折的發生。低能量的創傷,或生活活動導致的骨折,稱之脆性骨折。對于老年人,骨質密度明顯降低,骨質微觀結構退化,輕微的損傷甚至在平地行進中的跌倒均可誘發骨折。老年人的跌倒和骨質疏松性骨折的發生被認為是衰老的標志,跌倒和骨折往往互為因果關系,即可因為跌倒而骨折,亦有可能因為骨折而發生跌倒或既往骨折史導致跌倒的頻發。骨質疏松性骨折是骨功能衰竭的一個重要表現[1]。
跌倒所致的骨折部位與跌倒時的體位,常見的骨折部位包括:①股骨頸骨折和股骨粗隆間骨折,也稱髖部骨折;②腕部骨折;③脊柱壓縮性。骨骼功能的衰退,常有骨質疏松癥或者骨質減少,發生骨質疏松性骨折的概率較高,而在跌倒性骨折中,主要是下肢骨折[2]。在所有發生骨折的部位中,髖部骨折是最受人重視且后果最為嚴重的一種骨折。
對衰老的骨骼功能,可用骨強度進行評估。而骨強度的評價指標包括:骨密度,骨幾何學(骨的大小和形狀),骨礦化程度,股微觀結構以及骨轉化。骨密度的檢測是目前用來評估骨骼強度的最好方法,其代表了70%的骨骼強度。骨幾何學可用平片來評估,在骨折患者中或疑似骨折的患者中,需對患者的幾何學進行評估。骨礦化程度及骨微觀結構的評估需要生化指標檢測、骨活檢、微觀CT或MRI檢查,而這些因特異性不高、有創性檢查及價格較為昂貴等在臨床上不易推廣。骨轉化可由骨轉化生化標志物包括骨吸收標志物和骨形成標志物,對于絕經后的女性骨質疏松的患者,絕經前的骨吸收標志物超過正常上限,已被認為是獨立的骨折危險因素[2]。除此,其他能夠增加骨折的危險因素包括:年齡的增加,既往骨折史,接受糖皮質激素治療,家族的骨折史,當前的吸煙史,飲酒史以及類風濕性關節炎史等。因而,治療措施干預的時間以及干預方式會隨之進行改變。
2 骨密度與骨折風險
無論涉及到怎樣的檢測技術,骨密度的降低均直接關系著骨折風險的增加。如上文所述,骨密度代表著70%的骨強度,在臨床上,雙能X線骨吸收測定(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是用來對骨質疏松進行診斷分類的檢測技術。DXA是測定骨密度應用最為廣泛的一種方法,能夠直接提供與臨床相關的骨骼部位較為準確的測量結果。1994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了骨質疏松的診斷標準,定義為患者與同性別同種族年輕成年人參考人群的骨密度之間的標準差T值≤-2.5,-2.5≤T值≤-1診斷為骨含量減少,T值≥-1為正常[3]。
近期的一些研究認為,全身骨骼中,骨密度變化最為敏感的部位是股骨頸,因此,骨質疏松的診斷標準也應基于股骨頸的T值。Kanis等[4]研究顯示,每降低1SD≈10%~12%的骨量丟失,因而建議骨密度低于-2.5SD或減少30%的以上者診斷為骨質疏松。骨密度每下降1SD,被檢測骨骼區域的的骨折風險增加1.5~3倍[5]。且WHO目前對骨密度無“骨折閾值”等標準。反復DXA骨密度檢測對于骨密度進行性降低的高齡患者預測骨折風險意義較小[6]。通過骨密度與骨折風險的相關性預測骨折風險仍然是一種相對的危險,即一種總體的風險,不能體現個人的絕對風險。所以,需在測定骨密度外引入其他因素,這些因素在老年人跌倒性骨折中也在產生重要的作用,目前國內臨床上,考慮到骨密度的價格因素,較少使用骨密度考慮骨折的風險,但將其作為骨質疏松的一種評估工具。
3 骨質疏松性骨折的臨床風險因素評估
3.1年齡 韓國的一項前瞻性研究發現,年齡對于骨折風險的骨密度有獨立貢獻的因素,年齡改變的重要性相當于7倍的BMI、新近骨折史、吸煙飲酒史、類風濕關節炎史、激素用藥史等[7]。既往研究認為,T值相同的人骨折風險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如T值為-2.5的女性患者,80歲患者的骨折風險50歲患者的5倍[8]。但是,Kannus等[9]的研究發現男性高發期為50~59歲,而非年齡越高,骨折風險越大。另有研究發現,絕經年齡越晚的女性患者,首次髖部意外骨折發生的危險越高[10]。
3.2性別 Alswat等[11]評估了8262例患者的一項回顧性研究發現男性的骨折疏松的概率低于女性。而在其另外一項研究發現,相比于女性,男性的髖部骨密度(BMD)較高。且男性較女性失去骨質的年齡更晚,速度更慢。與男性相比,50歲以上的女性骨質疏松癥發生率高出4倍,骨質減少率高出2倍,5~10年的骨折往往較早[12]。
3.3BMI 有研究表明,BMI是僅次于年齡之后第二重要的影響因素[9]。BMI被認為是老年人骨質疏松性骨折的獨立危險因素。低體重(≤58 kg)與老年人的骨質疏松性骨折風險增加相關。女性50歲的身高縮短會增加老年髖部骨折的風險,而增加體重能減小風險[11]。無論男女均可用身高簡單而有效的預測髖部骨折的風險,身高降低5 cm以上者,男性髖部骨折的風險增加50%,女性增加34%,具有較強的相關性[13]。
3.4既往骨折史 既往低能量骨折史(跌倒性骨折)在臨床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是50歲以上患者的骨折,是獨立于骨密度的骨折危險預測因子。Kains等[14]在meta分析中表明既往骨折會增加骨折的風險,這個風險超過了BMD所能解釋的范圍。在4005名澳大利亞男性和女性隨訪16年的一項前瞻性研究中,既往存在低能量骨折史的女性和男性,其再次骨折發生風險的相對比率分別為20%和35%[15]。
3.5高酒精量的攝入與吸煙 過量的飲酒和吸煙均會引起跌倒性骨折的風險性增加。Kim等[7]研究發現,過量飲酒會引起骨折的風險,但是過量飲酒引起的骨折風險中,男女無明顯差異。既往研究發現,吸煙會使骨密度降低,并引起跌倒性骨折的概率增高,吸煙時間越長,每天吸煙或被動吸煙的量越大,跌倒引起的骨折的風險越大。既往的研究認為,老年男性吸煙導致骨折的概率>女性,但在Kim等[7]的研究發現,韓國男性因吸煙導致的骨折風險顯著低于女性。亞洲人吸煙導致的男女性別差異目前還無相關證據,需要后繼的研究進一步探討。
3.6基礎疾病 類風性關節炎在任何類型的骨折中已被認為是一個顯著的危險因素。但是在kim等[7]的研究中發現,濕性關節炎導致的骨質疏松性骨折中,只有男性顯著,而女性則不明顯。其他如甲亢、炎癥性腸病,糖尿病、慢性腎功能不全等可能的原因是因為這些潛在因素,導致機體的內分泌功能紊亂、破骨細胞活躍、大量破壞骨質、骨密度下降。也有可能是吸收障礙,腎對維生素D的轉化利用障礙導致的對鈣離子的排泄障礙。但具體的研究機制目前尚無文獻報道。
3.7激素的應用 激素的使用會明顯增加骨折的危險性。美國的一項納入244 235名患者的回顧性分析表明,強的松7.5 mg/d或以上與高骨折風險相關[16]。Fujiwara等[17]發現開始口服糖皮質激素(GC)治療后的早期,易發生骨丟失,骨折的風險在3~6個月內迅速增加。停止GC治療后,骨折風險迅速下降。而De Vries等[17]卻發現間接使用大劑量口服GC(每日劑量≥15 mg,累積暴露<或=1 gm)可能導致骨質疏松性骨折風險小。而GC也會導致兒童骨折疏松[18]。筆者認為,骨質疏松性骨折的風險大小可能與激素的服用劑量以及規律有關。
3.8其他可能性因素 相關研究表明,運動、受教育情況,婚姻,職業,季節變化、藥物使用情況(干擾代謝的藥物,免疫抑制劑,抗凝藥,抗抑郁藥,安眠藥等),均是骨質疏松性骨折的影響因素[19-24]。
4 骨折的風險評估工具
4.1FRAX 當骨折發生時,過去常常使用骨密度來預測骨折發生的概率,由于骨密度無明確的骨折閾值,且骨質疏松和骨質低下用骨密度T值來測定時,骨質低下的患者遠多于骨質疏松的個體[25]。缺乏骨密度測量的地區及骨密度測量費用較高,明顯不能使用骨密度來評估骨折的風險,甚至影響治療的進展及展開。所以需要一種相對普遍而且費用合適的評估工具預測骨折。
FRAX是可用于評估患者10年骨折發生可能性的工具。FRAX模型使用了年齡,身高,性別,體重,脆性骨折史(骨質疏松性骨折史),家族性骨折史,目前吸煙行為,激素治療史曾服用腎上腺皮質激素,類風性關節炎史,繼發性骨質疏松癥和每日飲酒超過3單位(包括3單位),最后再加入股骨頸骨密度。根據FRAX推薦,低骨量和10年內髖骨骨折≥3%和骨質疏松引起的主要骨折≥20%的患者應及時進行藥物的干預。而目前我國缺乏大規模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研究顯示,盡可能多的納入臨床因素,預測跌倒性骨折風險的概率準確性一定程度上可提升。當然FRAX缺乏某些重要危險因子,如基礎疾病情況,骨轉化指標,個人受教育程度,只適用于未接受治療的患者,且嚴重受到繼發因素的影響[26]。所以目前仍需要進一步完善FRAX骨折預測工具。盡管如此,FRAX預測工具已經在世界普遍使用,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可根據所在的地區通過檢索相關網頁,輸入相關數據,獲取髖部及其他重要部位骨折的風向。
4.2Garvan nomogram 該法是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加爾文研究所基于國際著名的Dubbo骨質疏松癥的流行病學數據調查建立的。可評估個體5-10年發生骨折的絕對風險,但此方法只是基于60歲以上的澳大利亞人群。Sandhu等[27]對GarVan量表法和FRAX法進行了比較,發現雖然兩種預測方法在女性評價中均較為準確,但是對于男性Garvan nomogram評估法優于FRAX法。新近的一項研究表明,Garvan nomogram法同樣適用于挪威人群[28],但目前國內關于Garvan nomogram法的使用尚無研究報道。
4.3韓國骨折風險評分(Korean Fracture Risk Score,KFRS) Kim等[7]基于亞洲人種用來估計骨質疏松性骨折的模型很少,提出通過臨床危險因子的韓國骨折預測模型。共18 306名50~90歲的韓國人納入到這項研究中,并隨訪了7年。此模型納入的臨床因素包括年齡,BMI,新近脆性骨折史,缺乏規則的鍛煉,最近使用口服的激素,類風性關節炎,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二次型骨質疏松癥。在這個模型中,影響韓國人最主要的3個臨床因素是年齡,新近骨折史,以及口服激素。目前國內外尚無關于這個模型的最新進展。
4.4骨轉換標志物(Bone turnover markers,BTMs) 成骨細胞和破骨細胞在骨代謝過程中起著重要的核心細胞作用。成骨細胞是骨形成的主要功能細胞,負責骨基質的合成、分泌和礦化。這種骨質新陳代謝的過程稱為“骨轉化”。骨轉換標志物(BTMs)反應的是骨轉換的總體速率,其提供了一種研究骨折的非侵入性方法,且易精確測量。更年期婦女,BTMs增加,而高的BTMs水平意味著更快的骨丟失,因而這些人也具有更大的骨折風險[29]。然而,BTMs用作骨折預測的證據基礎尚不夠充分,因此BTM尚未納入骨折預測模型[30]。
5 結 語
合理的運用適當的骨質疏松性骨折的預測方法對預防骨折具有重要的意義[31];可指導臨床進行有效的治療骨質疏松和預警骨折事件的發生。充分利用骨密度、FRAX等預測骨折風險,同時注意防跌倒,從而使骨質疏松性骨折的風險和嚴重后果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通過危險因素的分析,可發現跌倒和骨折的危險人群,對高危人群的監護和干預是有效降低跌倒和骨折風險的有效途徑。
[1] 李澤佳,蔣宜偉,宋 敏. 骨質疏松性脊柱骨折的研究進展[J]. 醫學研究生學報,2014,27(10):1099-1102.
[2] Chopin F, Biver E, Funck-Brentano T,etal. Prognostic interest of bone turnover markers in the manage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J]. Joint Bone Spine, 2012,79(1):26-31.
[3] Wood WA, Muss H. Quantitation of individual risk for osteoporotic fracture[J]. Oncology (Williston Park), 2010,24(8):753-755.
[4] Kanis JA, McCloskey EV, Johansson H,etal. A reference standard for the description of osteoporosis[J]. Bone, 2008,42(3):467-475.
[5] Melton LR, Thamer M, Ray NF,etal. Fractures attributable to osteoporosis: report from the 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J]. J Bone Miner Res, 1997,12(1):16-23.
[6] Hillier TA, Stone KL, Bauer DC,etal. Evaluating the value of repeat bone mineral density measurement and prediction of fractures in older women: the study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s[J]. Arch Intern Med, 2007,167(2):155-160.
[7] Kim HY, Jang EJ, Park B,etal. Development of a Korean Fracture Risk Score (KFRS) for Predicting Osteoporotic Fracture Risk: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Korea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J]. PLoS One, 2016,11(7):e158918.
[8] Siris ES, Chen YT, Abbott TA,etal. Bone mineral density thresholds for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fractures[J]. Arch Intern Med, 2004,164(10):1108-1112.
[9] Kannus P, Niemi S, Sievanen H,etal. Fall-induced fractures of the calcaneus and foot in older people: nationwide statistics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13 and prediction for the future[J]. Int Orthop, 2016,40(3):509-512.
[10] Chen FP, Hsu KH, Fu TS,etal. Risk factor for first-incident hip fracture in Taiwanese postmenopausal women[J]. Taiwan J Obstet Gynecol, 2016,55(2):258-262.
[11] Alswat K, Adler SM. Gender differences in osteoporosis screening: retrospective analysis[J]. Arch Osteoporos, 2012,7:311-313.
[12] Alswat KA. Gender Disparities in Osteoporosis[J]. J Clin Med Res, 2017,9(5):382-387.
[13] 黃公怡. 跌倒與骨質疏松性骨折[J]. 中華骨質疏松和骨礦鹽疾病雜志, 2011,4(3):149-154.
[14] Kanis JA, Johnell O, De Laet C,etal. A meta-analysis of previous fracture and subsequent fracture risk[J]. Bone, 2004,35(2):375-382.
[15] Center JR, Bliuc D, Nguyen TV,etal. Risk of subsequent fracture after low-trauma fracture in men and women[J]. JAMA,2007,297(4):387-394.
[16] Kung AW, Lee KK, Ho AY,etal. Ten-year risk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s in postmenopausal Chinese women according to clinical risk factors and BMD T-scores: a prospective study[J]. J Bone Miner Res, 2007,22(7):1080-1087.
[17] Fujiwara S. Glucocorticoid and Bone. Fracture risk of steroid-induced osteoporosis[J]. Clin Calcium, 2014,24(9):1295-1300.
[18] 楊 曉,夏正坤,樊忠民,等.糖皮質激素所致兒童骨質疏松的診斷和治療[J]. 醫學研究生學報,2014,27(2):203-206.
[19] De Vries F, Bracke M, Leufkens HG,etal. Fracture risk with intermittent high-dose oral glucocorticoid therapy[J]. Arthritis Rheum, 2007,56(1):208-214.
[20] Tveit M, Rosengren BE, Nilsson JA,etal. Exercise in youth: High bone mass, large bone size, and low fracture risk in old age[J]. Scand J Med Sci Sports, 2015,25(4):453-461.
[21] Pluskiewicz W, Adamczyk P, Czekajlo A,etal. Influence of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occupation, and the place of living on skeletal status, fracture prevalence, and the course and effectiveness of osteoporotic therapy in women in the RAC-OST-POL Study[J]. J Bone Miner Metab, 2014,32(1):89-95.
[22] Solbakken SM, Magnus JH, Meyer HE,etal. Impact of comorbidity, age, and gender on seasonal variation in hip fracture incidence. A NOREPOS study[J]. Arch Osteoporos, 2014,9:191.
[23] van Staa TP, Leufkens HG, Cooper C. Utility of medical and drug history in fracture risk prediction among men and women[J]. Bone, 2002,31(4):508-514.
[24] 徐若男,王丁丁,朱小蔚.預防和治療骨質疏松癥的常用藥物[J]. 東南國防醫藥,2011,13(6):540-541.
[25] 方 巖, 朱 濤, 劉文斌, 等. 影響骨質疏松性骨折的危險因素和評估方法[J]. 中國骨質疏松雜志, 2011,17(10):925-932.
[26] 俞海燕, 唐 偉, 王 堯. 骨質疏松性骨折風險預測方法的研究進展[J]. 中國骨質疏松雜志, 2015,3:372-375.
[27] Sandhu SK, Nguyen ND, Center JR,etal. Prognosis of fracture: evaluation of predictive accuracy of the FRAX algorithm and Garvan nomogram[J]. Osteoporos Int, 2010,21(5):863-871.
[28] Ahmed LA, Nguyen ND, Bjornerem A,etal. External validation of the Garvan nomograms for predicting absolute fracture risk: the Tromso study[J]. PLoS One, 2014,9(9):e107695.
[29] 張進城,肖占森.絕經婦女全身骨密度與慢性牙周炎的關系探討[J]. 東南國防醫藥,2015,17(3):278-280.
[30] Vilaca T, Gossiel F, Eastell R. Bone Turnover Markers: Use in Fracture Prediction[J]. J Clin Densitom, 2017. pii: S1094-6950(17)30113-0.
[31] 王桂華,趙建寧.骨質量的影響因素及其檢測方法[J]. 醫學研究生學報,2011,24(10):1095-1098.
R195
A
1672-271X(2017)05-0513-04
10.3969/j.issn.1672-271X.2017.05.016
2017-03-28;
2017-07-05)
(本文編輯:劉玉巧)
362000 泉州,解放軍第180醫院,1.胸外科,2.眼科
倪連紅,E-mail:nilianhong@126.com
王耿杰,倪連紅,馬良赟.骨質疏松性骨折預測方法的研究進展[J].東南國防醫藥,2017,19(5):513-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