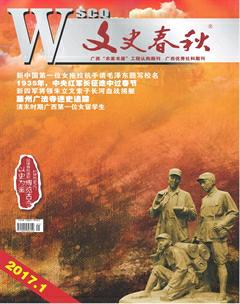官場圣人范仲淹(連載11)
肖亮升
第五章 復姓歸宗
21復姓歸宗
等各項事務稍微穩定下來后。范仲淹又想到了復姓歸宗的事情。
自從當年范仲淹從醴泉寺回朱家取米糧那次得知自己是姑蘇范氏子孫后,心里就萌生了復姓歸宗的念頭。只是當時他不敢向父母提起,他怕傷害母親的心。也擔心會讓繼父傷心,就只好作罷。但多年來,復姓歸宗的念頭一直深藏心底,從不曾忘記。
多年來,他知道自己是范仲淹,是范墉的兒子。卻不能光明正大地以范仲淹的名義生活在這個世上。因為他的名字叫“朱說”。心里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多年來。他以“朱說”之名去應天書院寒窗苦讀。吃粥咽菜;以“朱說”之名金榜題名,進士及第,打馬游汴京;以“朱說”之名步入仕途,為國效力,為民謀福。“朱說”之名早已深入人心,“范仲淹”卻無人知曉。
如今,母親已在身邊由他奉養,他已長大成人,再也不用依靠朱家的任何人。他雖然依然官職卑微,俸祿微薄,但足以養家糊口,孝養母親。于是經過左思右想,反復權衡利弊之后,他決定復姓歸宗,堂堂正正地做一名范氏子孫。
他打算找個時間先跟母親說說這事兒。先征得母親的同意之后,再回蘇州老家去跟范氏族人商議。
母子連心,沒等范仲淹跟母親開口,母親便主動跟他提及此事:“淹兒呀。娘這陣子反復在考慮。你應該改回你原來的名字。認祖歸宗。”
“孩兒也是這么想的,孩兒正想找個時間跟娘稟報此事呢。”范仲淹誠懇地說。“雖然繼父對孩兒有養育之恩,但孩兒畢竟是范氏子孫。孩兒相信繼父若是泉下有知,也會同意我認祖歸宗的。”
“嗯,”謝觀音點頭道,“‘仲淹這個名還是你滿月的時候。你爹在成德軍營帳賜給你的。”回憶當時范墉給兒子賜名的情景,謝觀音滿臉的幸福,“你幾個范氏兄長的名中都有水,你爹便也想給你取個帶水的名,最后就想到了‘淹字。你爹希望你長大后能成為一個學識淹博之人,更希望你能人朝為官,建功立業,光宗耀祖,聞名天下!”謝觀音看著兒子微微笑道。“你爹對你的期望已經實現了一半。接下來就看你如何建功立業、光宗耀祖、聞名天下了。”
“感恩爹娘給了孩兒生命,感恩爹賜的名……可惜爹已不在人世,無法看到孩兒金榜題名、入朝為官……”范仲淹說著就流下了眼淚,“要是爹現在還活著,看到孩兒的樣子,不知道該有多高興。”
“唉!你爹他陽壽太短,跟我們的緣分太淺……”謝觀音幽幽地說,“你爹雖然滿懷抱負,清正廉潔,但時運不濟,懷才不遇,一輩子只能輾轉各地做些小官,到死那天都未能獲得提拔重用,一輩子郁郁不得志……想想他也真是可憐。所以他才希望你日后能夠建功立業、光宗耀祖、聞名天下啊!”
“孩兒定當不懈努力。發奮圖強,繼承爹的遺志,建功立業,光宗耀祖!”范仲淹淚眼婆娑,“過幾天孩兒就回蘇州老家與范氏族人商議復姓歸宗之事,爭取早日改回爹賜給孩兒的大名……娘您知道嗎?孩兒在夢里都聽見有人喊我范仲淹!”
范仲淹處理完手頭的緊要公務,給下屬做些布置和交代。向通判楊日嚴告了假,便專程返回老家蘇州吳縣去跟范氏宗親商議他復姓歸宗的事,不料卻遭到了范氏族人的拒絕。范氏族長對他說:“你這事非同小可,非與族人開會商議不可。”
過了兩天,族長對范仲淹的答復是,族人一致反對他復姓歸宗。理由有三:一是此事來得太突然,族人對他身份的真偽尚不能明確,他是否范墉之子,有待考究;二是就算他真的是范墉的兒子,也不能輕易讓他復姓歸宗,因為這對他同父異母的兄長范仲溫是個威脅,范墉在蘇州的祖業已由范仲溫繼承,族人擔心他會回來瓜分祖業;三是他自幼隨母改嫁朱家。從小就改名換姓,二十多年來從未與范氏族人謀過面。族人對他無任何感情,某些族人甚至認為他是大逆不道、數典忘祖。如今他雖然長大成人,也有功名,但畢竟只是個從九品上的小官。地位和俸祿都不高,所以族人普遍懷疑他此番專程返鄉要求復姓歸宗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
族長傳達完范氏族人的意見后,搖搖頭對范仲淹說:“我雖然是一族之長,但像你這種認祖歸宗的大事,也只能聽從大多數人的意見,不可擅自做主。實在是抱歉呀。”
“侄兒能理解八叔的難處。”族長跟范墉同輩,族人都叫他八叔,于是范仲淹也稱他為八叔。
八叔說:“你能理解就好。畢竟你這是認祖歸宗的大事,非一般小事。”
范仲淹說:“族人反對我復姓歸宗這三個理由,我能否跟八叔解釋一下?”
八叔擺擺手說:“你先不忙著跟我解釋。我看你也是一番真心,我給你指一條路你去試試看。”
“八叔請講。”
“你先去找你三哥仲溫說說,如果他同意你認祖歸宗,我就再召集族人開個會,你再當面跟族人解釋。你看如何?”
范仲淹覺得這條路可行,趕緊拱手道謝:“多謝三叔成全。我這就去找我三哥。”
八叔叮囑道:“你可別讓你三哥知道是我給你出的主意。”
“八叔請放心,這個分寸侄兒還是明白的。”范仲淹說完便去找他三哥范仲溫去了。
讓范仲淹沒想到的是,范仲溫對他認祖歸宗的事也不置可否,只是說了幾句不痛不癢的話:“這事你自己看著辦。跟族人商量著辦吧。”
范仲溫的夫人在一旁看不過眼,插話道:“范仲溫你這話不是說了等于沒說嗎?你讓仲淹自己看著辦,你們不同意,他還能怎么辦?你讓他去跟族人商量,商量什么?你這個當哥哥的都不給他說旬公道話,誰還能給他說公道話?”
范仲溫馬上呵斥夫人:“家族大事,輪不到你一個婦道人家插嘴!”
范仲溫夫人毫不示弱地說:“我看你這個堂堂男子漢連我這個婦道人家都不如呢!”
范仲溫陰沉著臉。甕聲甕氣地問:“你這話啥意思?我怎么了?”
范仲溫夫人說:“族人反對你弟弟認祖歸宗還可以理解,難道你這個哥哥也反對?難道你真的擔心像他們說的那樣。仲淹會回來跟你搶家產?我看仲淹也不是那種人。再說了,仲淹既然是爹的兒子,就算分走一份家產也無可厚非。”
范仲淹沒想到三嫂說話如此深明大義、通情達理,不禁有些感動:“多謝三嫂信任。三嫂說得沒錯,我絕對不會回來分家產的。我范仲淹就算再怎么落魄,也不會落魄到回來跟三哥搶家產的地步。如果三哥不相信,今天當著三哥三嫂的面,我可以對天發誓:我此次回來只是想復姓歸宗,以盡孝道,別無他求。”
“你看弟弟都這么說了,你還有什么意見?”范仲溫夫人看著丈夫說,“你再不為你弟說句公道話恐怕就說不過去了。”
“既然這樣,那我就同意你認祖歸宗吧。”范仲溫看著范仲淹說,“不過光我說了還不算數,還得族長跟族里的長輩們同意……這畢竟也不是小事。”
“族長和族里長輩那邊我再去想辦法。”范仲淹拱手對范仲溫說,“多謝三哥能夠接納小弟。”
范仲溫微微一笑。推心置腹地說:“其實我何嘗不想多一個弟弟?只是突然冒出個弟弟來,我也得有個心理準備吧。你說是不是?”
“三哥說得有道理。”范仲淹轉頭對三嫂說,“所以三嫂你要理解我三哥。三哥他是個老實人。說的都是實話。”
范仲溫夫人嘟著嘴說:“你三哥他就是太老實了,才老被人欺負。我就想往后有了你這個當官的弟弟,也好有個人照顧著點兒,他倒好,找上門來的弟弟都不想認。”說著便用手指頭戳戳丈夫的后腦勺,嗔道,“你說他這顆腦袋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范仲溫憨厚地笑了笑:“認兄弟也不能病急亂投醫是吧?大街上滿街都是人,你干嗎不去拉一個回來認兄弟姐妹?呵呵。”
“看你這說的是什么亂七八糟呀!仲淹是大街上隨便拉回來的嗎?”范仲溫夫人搖搖頭,一副無可救藥的表情,“仲淹你看……這就是你三哥……我都不知道該怎么說他才好。你可別跟他一般見識啊。”
三哥三嫂的樣子讓范仲淹忍俊不禁:“我怎么會跟自己哥哥計較呢?三哥三嫂,那我先去找族長了。”
范仲淹心里明白。正如三嫂所說。三哥是個老實人。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平日里應該話也不多,而且家里大抵也是由三嫂做主。三哥之所以不敢答應讓他認祖歸宗,估計也是擔心族人非議,并非怕他回來跟他分祖業。正因為三哥為人憨厚,過于老實,估計在當地也常受人調侃甚至算計,所以三嫂才說想讓他這個當官的弟弟日后多關照著點。
唉,可憐父親懷才不遇,一輩子不受重用,郁郁而終。幾個兒女不是早天,就是老實巴交。只有他這個小兒子進士及第,有些出息,卻又被拒之范家門外,無法認祖歸宗。看來自己這次無論如何都要說通族人,一定要盡早復姓歸宗。繼承父親的遺志,發奮圖強,建功立業、光宗耀祖。
在范仲淹的請求下,族長終于再次召集族里長輩開會商議他認祖歸宗的事。族長清清嗓子說:“上次我把族人反對朱說改名換姓、復姓歸宗的三條理由轉告于他。他說想當面跟族人做個解釋。所以今天我就再把各位召集來。大家一起來聽聽他的解釋吧……好吧,朱說你來說說吧。”
范仲淹起身給各位長輩鞠了躬。又拱手作揖一番,才說:“仲淹此番回家,確實有些突然,這是因為仲淹復姓歸宗心切,所以才告假返鄉專程辦理此事。至于族人對本人的身份真偽心存疑慮,甚至懷疑本人是否范墉之子的問題,本人深表理解。為了打消各位叔伯、長輩們的顧慮,仲淹特意將當年朝廷調任我父親為武寧軍節度掌書記的樞密院鈞旨帶了回來,這是父親留下的遺物,請各位過目。”
范仲淹說完便從身上摸出那份樞密院的鈞旨遞給族長。族長看完后又遞給幾位長輩過目,幾位長輩這才頻頻點頭認可,紛紛說:“嗯,這東西應該假不了。”“沒錯,這確實是朝廷調任范墉的東西。”“他手中有這個東西,應該是范墉的兒子。”
族長把手往下壓了壓,道:“好了,各位先靜一靜。讓他接著往下說。”
“各位長輩,各位叔伯。”范仲淹朝各位長輩拱手作揖了一圈,開誠布公地說,“族人擔心我復姓歸宗另有圖謀,甚至會回來跟我三哥爭家產。請各位長輩放一百二十個心,仲淹絕對不是那種人。仲淹復姓歸宗的目的只是要表明我是范氏子孫。盡到對我親生父親及列祖列宗的一份孝道,僅此而已,絕無他意。”說到此處,他眼睛突然一熱,哽咽著說,“各位長輩可曾知道,我父親是在赴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的路途中病倒的,還未來得及上任就病逝于驛館……我父親為人正直,廉潔為官,卻因為時運不濟,懷才不遇,一輩子只能做些小官,空有一番抱負卻無法施展……每每想到我那可憐的父親,我就忍不住想哭……我就告訴自己要繼承父親的遺志。盡早復姓歸宗,發奮圖強,建功立業、光宗耀祖!各位長輩,你們可曾知道,‘朱說這個名字我用了整整二十五年啊!自己明明是范氏子孫,卻只能姓朱,明明叫范仲淹,卻只能叫朱說。寒窗苦讀、結交朋友、進士及第以及現在身為一名朝廷命官。處處都只能以‘朱說的名義出現,我甚至連做夢都想早日復姓歸宗、早日被人稱作‘范仲淹呀!各位長輩,各位叔伯,你們雖然沒經歷過改名換姓的滋味,但你們能否理解一個在范家門外等候了二十五年的范氏子孫的迫切心情?理解我為了復姓歸宗而朝思暮想、夜夜夢里回故鄉的心情?今天當著各位長輩的面,我可以向大家保證:我范仲淹復姓歸宗后,只會為范氏宗親辦好事、謀福祉,絕不會做任何傷害家族聲譽和利益的事情!”
范仲淹這番話說得人情人理,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讓人聽了無不為之動容。在場的族人長輩都深受感動,有幾個甚至還掉下了眼淚。經過族長和長輩們商議,最終同意他復姓歸宗,恢復范姓。
雖然過了范氏族人這一關。但這并不意味著范仲淹從此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恢復范姓了。由于他畢竟是有功名之人,改名換姓當然不像平常百姓那么容易。要想真正地改名換姓,他還要上奏朝廷。征得皇上的同意才行。
回到家后,范仲淹當即揮筆上表朝廷,向皇上奏請復姓歸宗。他在奏請中不僅有事實有依據,還特意寫了一副對聯:“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
這副對聯引用的是兩名范氏先祖的典故。
一個是先秦時范睢的故事:范睢在魏國大夫須賈門下做門客,有一次與須賈出使齊國,齊王因賞識他的才華而賜他黃金十斤,他不接受。須賈卻認為齊王之所以對他那么好,肯定是因為他向齊國出賣了魏國的秘密,于是回國便將此事告訴丞相,丞相就派人打斷了范睢的肋骨,打掉了他的牙齒,差點將他打死。后來他在鄭安平的幫助下,隨秦國使者王稽逃出魏國而投奔秦國,改名張祿,人秦拜相,顯赫于后世。
另一個是被后人贊譽為“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的范蠡的故事:范蠡輔佐越王勾踐,為勾踐出謀劃策,使得勾踐臥薪嘗膽二十年之后終于打敗吳國,一雪會稽之恥。功名顯赫的范蠡卻認為高處不勝寒。在功成名就之后便激流勇退。化名姓為鴟夷子皮,乘舟泛湖而去。期間三次經商成巨富,卻三散家財,世稱“陶朱公”。后世人將他當做財神供奉。稱他為“商圣”。
范仲淹引經據典,善用典故,引用這兩個范氏先祖的典故巧妙地表達了自己復姓歸宗、恢復范姓的要求,皇帝因此而恩準了他的請求,準許他恢復范姓。
自此之后。范仲淹終于結束了以“朱說”為名的生涯,開始堂堂正正地啟用父親從小給他取的名“仲淹”,同時,他還為自己取了字“希文”。
復姓歸宗后的范仲淹還特意寫了幾封信告知關中的王鎬、同年進士滕子京等幾位好友,以及湖南安鄉縣興國觀的司馬道長、長白山醴泉寺的慧通大師,跟他們分享他復姓歸宗后的喜悅。
范仲淹雖然已經復姓歸宗,但他對朱氏兄弟依然關懷備至,情同手足。復姓歸宗后不久,他還專程回長山看望了朱氏兄長,拜祭了繼父朱文翰的墳塋,將自己已復姓歸宗、改名為范仲淹的事告知九泉之下的繼父,請繼父理解他的做法。同時告慰繼父的在天之靈,日后他會用實際行動來表明自己雖然已經改名換姓成為范氏子孫,但繼父對他的養育之恩他沒齒難忘,銘記于心,他會一如既往地像對待親生兄弟一樣對待朱氏兄弟。
一日上午,通判楊日嚴突然對范仲淹說:“范大人,咱們不能在一起共事了。本人馬上就要調離了。”
“啊?什么時候走?”驚訝的同時,范仲淹有些遺憾,跟楊日嚴搭檔以來,彼此相處融洽,從未發生過爭執,而今楊日嚴卻要調離了,真是可惜。
楊日嚴說:“后日一早就啟程。”
“這么急啊?”范仲淹馬上說,“那今夜我請大人吃飯。”
楊日嚴笑了笑:“就不麻煩了吧?”
“大人別客氣,”范仲淹真心誠意地說,“下官當初來赴任。是大人親自為下官接風洗塵。而今大人離任,下官也略備薄酒為大人餞行,略表心意。此地一別,還不知何時才能與大人再見。”
“既然老弟這么說。那楊某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其實楊日嚴也想跟范仲淹喝個臨別酒,兩人再好好地敘敘舊。他跟范仲淹共事的時間雖然不長,卻相見恨晚,彼此相處得也很融洽。兩人雖然是上下級關系,卻能夠彼此尊重,工作上相互支持,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像他們這種一見如故、惺惺相惜的上下級關系在而今的官場上是極為罕見的,甚至是沒有的。據他所知,上下級是很難成為真正的知己朋友的,除了上司與下屬的關系,很多都是利益關系。不管是何種關系,上司與下屬很多時候都是貌合神離,虛情假意的。像他和范仲淹這樣既能夠坐在一起談知心話。又能夠一起把公務搞好的關系,是很不容易的,估計他以后永遠也不可能再遇上了。
范仲淹提前在衙門附近的富貴酒家訂了個包間,先點好菜,吩咐店家在什么時辰做好上菜的準備。然后才將地點告訴楊日嚴。約定晚上再見。富貴酒家的生意好得出奇,吃飯還要排隊,來晚了根本沒位子,上菜也慢,他這么做是以免讓他們久等,等楊日嚴一到就能開桌吃飯。
傍晚,范仲淹在酒家門口親自迎接楊日嚴,楊日嚴開心得眉開眼笑的樣子像一尊彌勒佛,對范仲淹拱手不止:“老弟你太客氣了。”
范仲淹扶著楊日嚴上了樓,說:“大人對下官的知遇之恩,下官沒齒難忘。”
“哪有什么關照,”楊日嚴說,“你才華橫溢,能力超群,到哪兒都是英雄豪杰。”
范仲淹不動聲色地說:“就算再有才華和能力,也得遇上懂欣賞、善任用的好上司才行。好上司能將一塊頑石變成美玉,不好的上司卻能把黃金變成破銅。大人就是那種能把頑石變成美玉的好上司。”
范仲淹的這番比喻讓楊日嚴樂得合不攏嘴,嘴上卻謙虛地說:“過獎了,老弟過獎了……你本來就是一塊美玉,我只不過是讓你發揮美玉的光芒而已。”
范仲淹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怎么說大人都是下官的伯樂。”
楊日嚴笑著說:“你不光是千里馬,更是一匹汗血寶馬!”
范仲淹拱手道謝:“多謝大人抬愛。”
當夜,范仲淹和楊日嚴推杯換盞。相談甚歡。酒過多巡。楊日嚴打著酒嗝說:“我走后,不管誰來任通判,你都要像跟我搭檔一樣。好好跟下任通判大人搭檔……不要強求再遇到像咱們這種關系的知心朋友。”
范仲淹說:“大人的話下官謹記于心。下官一切隨緣便是。”
楊日嚴推心置腹地說:“你還年輕,仕途才剛剛開始,凡事要沉得住氣,不要急躁,不要冒進,要穩得住自己……你要相信,像你這種德才兼備的官吏,遲早都會受到朝廷重用。”
“錢多錢少,都有煩惱;官大官小,沒完沒了。”范仲淹微微一笑道,“我從入仕那天起,就告訴過自己:要把名利看淡些,看輕些。無論官大官小,都一樣是為朝廷效力。哪怕是在最卑微的位置,也要做出最有價值的事情。”
“你的心態很好。我最佩服你的就是這一點。”有幾分醉意的楊日嚴煞有介事地說,“不瞞你說。我就沒你這么好的心態……我雖然已官至通判,卻還不知足,老覺得自己懷才不遇,時運不濟,官位太小。有時甚至還在內心里埋怨朝廷目不識珠,不任人唯賢,經常有消極怠工、得過且過的想法。”
楊日嚴的話讓范仲淹有些驚訝。眼前這個自己一向敬重的上司,這個工作敬業、平易近人的通判大人,竟然也有著如此復雜的內心?真是看不出來。看來確實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下屬有下屬的煩惱,上司也有上司的難處。身在官場,人在江湖,恐怕就沒有哪個人是內心徹底清凈、心態平和的。他覺得自己也是如此,他雖然多次在心里告訴自己無論身在何職都是為朝廷效力,要淡泊名利。但他骨子里還是想盡快升遷。當上大官的。其實這也能夠理解,既然身為朝廷命官,又有誰不想身居高位呢?只要念頭是正確的,不是自私自利的。有當大官的想法又何嘗不可呢?就像佛家說的起心動念間已有善惡之別。只要自己的起心動念是正念、善念,就算他想有朝一日位極人臣、當上宰相,那也不是非分之想。因為如果是心存君國。胸懷百姓的官員,當上宰相不是更能為國效力、為君分憂、為民謀福嗎?初任廣德的時候他已深刻體會到官職卑微的滋味。自己本來是想為民辦些實事,起心動念都是善念,但由于自己官位太小,人微言輕,很多時候自己苦心經營多時的一個好想法,被上司三言兩語就打發了,甚至一口回絕了,沒有上司的支持,很多時候就算你有再好的思路、再好的想法,最后都只能變成海市蜃樓。竹籃打水一場空。那種滋味,只有親身體會過的人才知道。
“我今天的話也……也許讓你感到驚訝,怎么連楊日嚴這么道貌岸然的人也是表里不一的人?”
楊日嚴的話把范仲淹的思緒拉了回來。范仲淹趕緊說:“不不不,我從來就沒覺得大人表里不一……其實大人想高升也在情理之中啊。像大人這種清正廉潔、德才兼備的官員。如果能夠官至封疆大吏甚至朝廷要員。那也是百姓之福啊!”
“只怕百姓沒這個福咯。”楊日嚴說著就獨自喝了一杯悶酒,言語中有幾分失落,“我自認為自己還算是個忠于職守、清正廉潔的官員,所以也想趁現在還年富力強,想為朝廷效力,為皇上分憂。可惜這都是自己一廂情愿的想法而已。出仕多年。來來去去都只能做些不上不下、不痛不癢的小官……唉!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想的。別說我等芝麻綠豆官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實現,就算在朝廷那邊,讓誰做什么、不讓誰做什么,很多時候甚至連皇上都不一定能夠左右……唉!每次想到這些煩心事,我就覺得干活沒勁……咱們在這種窮鄉僻壤整天想著為朝廷效力、為皇上分憂,可曾想過朝廷需不需要你效力?皇上需不需要你分憂?咱們的想法是不是很可笑?是不是有些自作多情?”
從楊日嚴現在說的這番話來看。范仲淹知道楊日嚴今晚確實是喝多了,要不他怎會跟下屬說出這種牢騷話?平日里就算再怎么交心。再怎么言語投機。他斷然不會跟別人說這種消極之詞,就算他有天大的怨言、滿腹的牢騷,平日里表現在世人面前的也是一個工作敬業、平易近人的楊日嚴。
今夜,也許是自己跟他言語投機,也許是他酒醉吐真言,或許是因為他即將離開此地,回首往事,觸景生情,百感交集,才忍不住說出了深藏內心多時的想法。
想到這里,范仲淹甚至為楊日嚴的前程擔憂,如果是被居心叵測之人聽到楊日嚴剛才那番話,去向他的上司甚至朝廷告密,那后果可想而知。別說升遷,弄不好連現在的官帽子都保不住。
看到眼前的楊日嚴,范仲淹心里不禁感慨萬千:看來佛家將飲酒作為一條戒律是有道理的,酒能迷糊頭腦,使人昏沉,酒量一旦失控,不是失態,就是失言,總之弄不好就會誤事,甚至出大事。為此他暗自提醒自己:今后還是不飲酒為好,就算是遇上非飲不可的應酬場合。也要少飲。萬不可像眼前的通判大人一樣開懷暢飲,喝個酩酊大醉之后便什么話都和盤托出。
想到這里,范仲淹便對楊日嚴說:“大人。下官不勝酒力,不能再陪您喝了。”
“本官不……不用你陪……本官自己喝便……便是……”楊日嚴說完又將半盅酒一飲而盡,然后搖頭晃腦道,“假……假以時日,老……老弟你定能……能成大器!要是哪……哪天老弟你位極人……人臣。你可得舉……舉薦老……老哥呀……”
范仲淹不動聲色地說:“下官現在不過是個區區節度推官而已,大人已是通判。以大人的能力和德行,前途肯定在下官之上,日后還要大人多多關照下官才是。”
“不不不……本官心中有數的……本官雖……雖然虛長你幾歲,比你多……多任了幾年虛職,但后生可畏,你比本……本官有前途。”楊日嚴搖晃著起身道,“今夜謝……謝謝你的好酒好……好菜,咱們后……后會有期……”說完便東倒西歪地給范仲淹拱手作揖。
“大人慢些走。”范仲淹怕楊日嚴摔倒,趕緊上前扶穩他。楊日嚴一步一個踉蹌。走路像跳舞一樣,讓范仲淹扶起來很吃力,他想背著楊日嚴走,因為楊日嚴太肥。又背不動,只好連拉帶拽、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楊日嚴送回家去。
楊日嚴夫人一看丈夫這副爛醉如泥的樣子,馬上就皺起眉頭說:“又喝成這樣!官不大,酒量也不大,還偏要喝!”
楊日嚴看著夫人,嬉皮笑臉地嘟囔著:“就……就是官小……酒量小,才要多喝,喝……喝多了酒量自……自然就大了……酒量大……大了,官位自……自然就大了……”
“什么亂七八糟的!滿嘴酒話!洗臉睡覺!”楊夫人趕緊將楊日嚴扶進了房間,不想再讓他當眾出丑。她雖然是個婦道人家,但也知道禍從口出的道理。
看到楊日嚴喝成這樣。范仲淹心中感慨萬千,唏噓不已。甚至有些愧疚,后悔自己不該讓他喝那么多。但想想又覺得并不怪自己,自己只是好心請他吃頓飯,也不怎么勸他的酒,只是他自己好酒貪杯,借酒澆愁。非要將自己灌醉。
翌日。酒醒后的楊日嚴只字不提昨夜醉酒一事,一如既往地跟范仲淹點頭微笑,拱手作揖,一副平易近人的樣子。他甚至還煞有介事地告訴范仲淹,早在前幾天他就寫好了舉薦信,要在臨走前向上級官府推薦德才兼備的范仲淹。
范仲淹聽了心里十分感動。不管楊日嚴說的話是否真假,他都要感謝他。心想楊日嚴雖然好酒貪杯,但確實是個關心下屬的好上司,臨走還不忘推薦下屬,這樣的官員并不多見。人要有感恩之心,今后無論自己身處何地、身居何職,都不能忘記楊日嚴這種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上司。
楊日嚴離開集慶的那天清晨。范仲淹早早地趕去為他送行。兩人不停地拱手作揖,揮手作別,直至楊日嚴夫人再三催促,楊日嚴才依依不舍地離去。
范仲淹望著楊日嚴離去的背影,突然想起唐代詩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兩句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楊日嚴昨夜為何喝得如此盡興?以至于爛醉如泥,大概也是覺得自己離任集慶后,再難相遇他范仲淹這樣的知己,所以才決定放縱一回吧?
想到這里。望著早已看不到楊日嚴的前路,范仲淹不禁有些心酸,兩行清淚從臉頰悄然滑落。想到漸行漸遠的楊日嚴,他在心中默念唐代詩人高適的《別董大二首》中的兩句詩為他祝福:
莫愁前路無知己:
天下誰人不識君。
22報國心切
天禧三年(1019年),三十一歲的范仲淹授官從八品秘書省校書郎。
秘書省監掌古今典籍、國史、實錄、天文、歷數等,校書郎在秘書省屬下負責校勘典籍,訂正訛誤等事務。范仲淹雖然被封了個小官,卻只是掛個虛職而已,沒有實際到任,仍守官集慶。
翌年。范仲淹曾短期去京城秘書省校勘書籍,原以為自己由此可以留在京城,不料很快又返回集慶,依然原地踏步。這不禁讓他有些失望。在他看來,雖然校書郎也只是個不痛不癢的小官,但如果能留在京城,至少離皇上越來越近,機會自然也就多一些,可惜他不能如愿。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調任泰州,擔任西溪鹽倉監官,負責當地的鹽稅及專營事務。雖然官職已由集慶的從九品上提升為從八品,但對于心有遠大抱負、報國心切的范仲淹而言,他覺得這樣的升遷速度還是太慢。因為照此發展下去,距離自己成為良相的距離還是遙不可及。
想到這些,范仲淹心里也常常覺得自己懷才不遇,甚至有些悶悶不樂,便利用工作之余去西溪各地游山玩水,甚至與當地百姓談天論地,以求沖淡心中的煩心事。真是不出去走不知道,出去了幾次才知道小小的西溪竟是個藏龍臥虎之地,竟然已走出兩位名震朝野的大員:五歲就能作詩、十四歲以神童身份參加殿試的晏殊。以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的呂夷簡。
范仲淹的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一次在游覽當地名勝后,他揮筆寫下了一首《西溪書事》來表達自己胸懷大志、報國心切的心情:
卑棲曾未托椅梧,
敢議雄心萬里途。
蒙叟自當齊黑白,
子牟何必怨江湖。
秋天響亮頻聞鶴,
夜海瞳嚨每見珠。
一醉一吟疏懶甚,
溪人能信解嘲無?
(未完待續)(連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