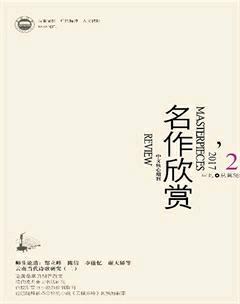喧囂背后
李佳憶+鄭立峰
摘 要:“70”后女作家映川以智性思考跨越物欲時代“身體寫作”的陷阱,自覺關懷女性生存立場,探尋個體精神異變,追求兩性和諧發展,以迥異于商業化欲望化的獨特書寫,開辟了消費語境下女性寫作的新天地。
關鍵詞:消費語境 女性寫作 兩性關系 異化
在“70”后女作家群中,與消費時代一同生長的楊映川走出了一條暴曬欲望與直書理性的別樣之路。她的小說沒有如衛慧們一般縱情于個人情感的宣泄與估價身體的狂歡,成為與市場合謀滿足大眾窺視欲望的消費文本,而是執著于在同樣浮華的都市背后追尋個體生存境況的異化,探求現代社會兩性關系的新變。自覺翻越幽閉私語高墻的創作意識,使得映川在眾語喧囂的新世紀文壇中得以避開身體敘事的陷阱,在消費語境里構建新的話語體系,呈現出女性寫作的嶄新風貌。
一、陷落的符號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開始全面轉型——標榜自由開放的消費社會來臨了。對于在傳統年代個性精神遭受禁錮乃至消解的廣大作家而言,全新的文化語境使私人化的個體敘事替代宏大的民族寓言敘事成為可能。在此種潮流下,林白、陳染、衛慧、棉棉等女性作家紛紛從長期被壓抑的文化禁忌的暗處“浮出”,她們在創作中將自我身體從隱秘之域推至公共空間,暴露于市場及大眾視野之下,用戰斗的姿態將男性統治的倫理規范盡數瓦解,在都市物質的叢林中肆意歡笑,引來社會的一片嘩然。然而她們沒有料到,“消費主義文化仿佛一道雙刃劍,在推進了中國女性自我解放的同時,又設置了一個新的話語陷阱”①,淪為符號的女性及其身體在反抗男性的同時又滿足了男性窺探欲的本質,“看”與“被看”組成了新的消費關系。如何從“身體敘事”中轉型,打破市場探視下女性寫作尷尬的困局,成為女作家們思考的議題。
映川無疑是屬于思考與探索并進的一類作家。盡管時刻警惕著市場設下的陷阱,但消費社會生產的一些意識形態早已進入文學文本,稍不留神,作家便會有意無意間與消費社會“合謀”,成為支撐消費環節的一名“共犯”。在早期作品《做只鳥吧》中,映川塑造了兩個追求理想愛情的少女形象,果果和樹子。果果沉醉于樹子描繪的童話世界里,而童年目擊父親出軌的陰影令果果決然地關上與物質世界接觸的大門,自始至終她都抗拒著功利主義化身的男性與外界誘惑對自我空間的侵入,企圖與同性的樹子之間保持“純粹的愛”。另一個女主角樹子卻沒有像果果般守住最后的陣地,被肖確攻克后的她逐漸在消費社會中沉淪并走向毀滅。兩個起初同樣眷戀童話的少女,卻由于異質社會的介入而走向不同的結局,可以說作者這樣安排飽含深意。映川想用個人退守至烏托邦的精神理念來對抗物欲世界消費的本質觀念,但遺憾的是兩人都沒有達到預設目標。果果無論如何驕傲,也沒能擺脫消費社會帶給她的審美趣味——唯美主義的同性情愛正是當今社會最常消費的美學元素。而樹子的形象還隱含著另一層悲劇:文中身為畫家的果果曾以樹子為模特繪制了一幅真人大小的肖像畫,畫中樹子赤裸的身體是至高的藝術,但后來這幅私人的創作被掛在大街上成為供看客消遣的廣告形象。樹子從真身跌入物質的漩渦,到最后連虛擬的身體都成為一個商品化的符號,這似乎道清了一個現實:“女性固有的生存困境并不因時序變遷而徹底改觀,改變的只不過是與現實的遭遇方式。商業化市場化時代以更為隱蔽詭譎的伎倆明目張膽地對女性進行無情而無恥的掠奪。”②盡管初次的嘗試沒能逃開消費話語意識的遮蔽,但映川從早期童話式的愛情描寫中敏銳地感悟出了個體與社會之間的距離,她不再用消費性的符號來逃避或對抗消費的社會,這只是一個理想的期望。她開始嘗試發現,并揭露社會中存在的那些正緩緩掉入陷阱的符號,個體身處巨大的游戲場中已是既定事實,映川的高明之處在于將注意力轉移到這些下陷的個體本身,借對人物心靈困境及自我遭遇的反復挖掘,傳遞其在當今消費語境下的獨特思考與警示。
《女的江湖》是映川少有的長篇,榮燈在顧角遠赴新加坡后獨自一人在物欲橫流的情感江湖里游戲人生,直到有一次同事李京氣急敗壞一語驚人:“你以為你是圣女貞德?沒人有時間陪你玩……”榮燈終于明白在男性菲勒斯權力中心的社會里,誰也不會在乎自己的靈魂,別人要的只是自己的身體。女性作為狩獵的符號是如此孱弱無力,盡管榮燈高高在上嘲弄那些權錢并有的裙下之臣,卻仍不能掩蓋女性作為娛樂消費品的蒼白。《意殺》講述的是看透消費社會男性本質的蘇物麗讓所有接近她的男人立誓,楊正也不例外,他在激情時刻許諾永遠不欺騙她,否則房子就會垮掉。然而獵艷成功的楊正最后還是消失了,蘇物麗沒有意外,楊正的誓言被倒塌的大樓壓成一頁廢紙,從她內心的空間徹底刪除,她迅速開始新的生活。故事結尾,朋友有意給蘇物麗介紹對象,她的反應很平淡,說見見吧,見見又沒什么損失。在人海中兜兜轉轉一圈,最后還是回到了原點,就如文中副院長勸誡蘇物麗的話:“趁年輕,找個人嫁了,女人還是要靠著男人的。”③不論男人如何肆意踐踏誓言,蘇物麗們心如明鏡,也只能在意念上殺死對方,現實中仍逃不過依附男性的結局,這是現代女性面臨的尷尬困局。她們在消費大眾眼中,更多的是有別于男性的性別符號,女性的身份使她們艷光四射的同時又被隨意觀賞。消費的欲望催生了強大的獵手,在他們的緊逼下,女性苦苦頑抗仍不能減緩下墜的速度。看清消費時代下女性的處境,并以筆揭示給大眾,映川的目光穿透了浮華的身體語言,用理性編織自己的故事。
二、異化的人心
提起當下消費時代的繁榮,人們不禁會昂首挺胸,目光所及之處定是鱗次櫛比的大樓、琳瑯滿目的商品、徹夜狂歡的酒吧……這是屬于大都市的浮華光景,可以說,都市的繁榮標志著消費文化生存空間的確立。人作為都市消費語境中的主體,在享受優異環境的同時,也時刻受到消費意識形態的改造,消費文化思想的滲透使構成社會基礎主體的“人”的深層意識產生了一定的斷裂與扭曲。越來越多人在現實與狂歡的夾縫中向欲望投降,對物質妥協,現代人所要面臨的不僅僅是快節奏的高壓生活,還有精神上的異變危機。
對于消費都市中人和人之間關系的變幻,女作家們無疑是最為敏感的。早期衛慧、棉棉等美女作家借“身體寫作”為大眾勾勒出了喧嘩城市里為物欲所累的男女群像,他們對品牌與消費的崇拜是商業大潮洗禮后的精神遺渣。相比她們文中大量名品羅列、酒吧放縱的輕奢生活,映川筆下的人物則拋棄了繁華的外衣回歸世俗的庸常。一件件瑣事的交錯碰撞使華麗背后隱匿的人性暗區浮出水面,暴曬在世人眼前。
《零食》主講一個愛情讓位給現實的故事,篇幅不長,卻對都市人的“物化”有著較為獨特的描寫。靠維修電腦養家的譚文為了讓女友鐘楚梅過上更美好的生活,想方設法為她找尋新的對象。而鐘楚梅對于男友異想天開的做法也由一開始的氣惱漸漸轉化為習慣甚至于到最后的接受,因為她發現了無關情愛的另一種生活:“這段時間與陳立交往,她一半是賭著氣的,賭著賭著也領略了生活的另一面,她不得不承認自己是虛榮的,她喜歡漂亮的衣服,名牌化妝品,喜歡坐在咖啡廳里聊天,喜歡坐小車而不是擠公交車回家……”④最終現實與譚文“合力”讓鐘楚梅與條件優越的盤城走到了一起,而鐘楚梅也反過來為譚文介紹了同樣條件良好的對象,譚文開始了新的追求。在這篇小說里,愛情充當了等價交換物,曾經的一對戀人將自身作為籌碼,用他們認為微不足道的愛情換取了更為穩定優渥的生活,雖然在物質方面他們取得了勝利,但這是在消費社會重壓之下精神領域的一場潰敗。譚文是思想上的委頓者,男性的雄風被消費高昂特權林立的城市打擊得蕩然無存,他迫切想為鐘楚梅找到一個像樣的男友把自己“替換”掉,他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崇高的事,而絲毫沒有發現將女友“轉讓”的行為已是不負責任的逃避。鐘楚梅的反應則更為現實,盤城能帶給她譚文不能給的,這就已足夠,何況是譚文在“撮合”兩人呢?“自以為是”與“心安理得”造就了本篇看似合理實則扭曲的價值觀,都市人面對消費社會的震蕩與誘惑時的自我迷失是映川為之擔憂的。
同樣值得憂慮的不僅僅是個體精神的變異,襲承自古老中國互愛友善的人與人之間交流的紐帶也在消費時代的大語境下面臨“失語”的尷尬。《最后的朋友》通過皮樂山用金錢“施恩”素不相識的張和達成臨終托付秘密的目的這樣一個故事,揭示了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冷漠、孤獨與缺乏信任等危機。皮樂山與張和原本是陌生人,卻通過對張和的金錢援助彼此有了很深的聯系,皮樂山憑借有恩于張和,不僅毫不避諱自己包養小三的事實,更將張和當作敷衍妻子探查的“幫兇”,幾乎將所有的老底曝光在張和眼下。而相對于外人的張和,本該是最親密的妻子卻是皮樂山的“敵人”,皮樂山與妻子僅靠兒子維系著家庭,根本談不上信任。在家庭信任缺失的情況下,張和成為皮樂山托付秘密的首選,看似合理實則異常,兩個陌生人之間的相互托付標示著現代人心靈深層的悲哀。《為你而來》則又是一個家庭內部價值觀在消費環境下的異化。袁方是擁有金色履歷的家族中的“異類”,他活得雖不光鮮卻自由自在,瀟灑坦蕩。反觀身為成功人士的一家人,二哥對課題狂熱卻失去歡愛的基本興趣,二嫂在壓抑痛苦之下自殺未遂,姐夫在外偷情放縱……“許多看上去光彩照人的東西里頭沒準早霉掉了……”⑤人性指向的是人的自然感性和物質欲求,成功立足社會的生活卻讓他們失去了身而為人的一部分道德與情感。家庭內部只看地位相互攀比,外人看來風光無限,卻失去了生活的本真。“家”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由一家之隱憂反觀社會之現狀,映川犀利的筆鋒讓讀者不得不在憂慮中反視自我,解析都市背面的陰影。映川對人生境遇的反撥與消費時代都市人群精神困境的深層關懷,可見一斑。
三、藩籬的突破
在全球化與商業化的消費語境中,兩性之間應該是怎樣的一種關系?對于這個疑問,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同類型的女作家給出了不一樣的回答。林白、陳染進行著從男性身邊逃離的“一個人的戰爭”;衛慧、棉棉用女性物化的身體嘲弄對抗男性的強權。映川早期的寫作也不可抑制地有過這些路子的痕跡,但很快她收斂了“戰斗”的鋒芒,雖然一些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仍有美化的跡象,但對男性的刻畫不再過于負面與平板。誠然社會對女性的消費是貪婪而巨大的,但誰能確保男性慣來超然的地位呢?
正如賀紹俊批評中的一針見血:“我們這個社會的消費胃口越來越巨大,它不僅消費女人,也要消費男人。”⑥當消費主義浪潮席卷全球時,傳統的性別優勢承受了世人難以想象的重擊。后現代社會的到來,打破了以傳統兩性關系為基準的性別分工模式,帶來了兩性關系的深刻變革。男性不再是掌握絕對話語權的霸主,稍不留神,他們也會被所謂弱勢群體的女性甚至社會拋棄,暴露出軟弱、無奈的一面。《宋響的玫瑰》描繪了一個天才少年走向自我毀滅的過程。宋響的一生刻下了三個女人的痕跡。第一個女人是他喝藥自盡的母親。宋雪夢的臨終遺言讓宋響早早跨過貧窮窩囊的父親,讓他決心自己塑就可掌握經濟大權以對抗消費社會的男人形象。劉飛飛是帶有過客性質的第二個女人。通過接近劉飛飛,宋響成功拜師劉鎖王學成了開鎖的技術,這是宋響選擇偷盜的資本,也意味著他與“讀書正道”的劉飛飛等普通人以及背后秩序社會的決裂。第三個女人是宋響心中的夢幻,也是喚醒他男性沉睡的“征服”因子的一點光亮。這個宋響入室盜竊時偶然遇見的女人讓宋響質疑自己當初的選擇,質疑自己偏離軌道的生活,“如果他沒有學開鎖,沒有成為一個小偷,如果他好好讀書,上大學找一份正經的職業,他是有機會認識這樣的女人的,還可以娶她們做老婆”⑦。可惜這個社會從沒有“如果”,宋響重回偷竊現場尋找女人的舉動使他落入圈套,慣犯的身份足以使一個天才夭折。宋響的悲劇不僅僅是底層人物生存困境的悲劇,更是現代男性急于立足而遭受無情打擊的悲劇。宋響遭遇了女人和社會的雙重圍剿,宋響反擊的路塌陷了,陌生女人不是指引他的救贖之光而是燒灼他的煉獄之火,宋響倒下了,看似獨立的他也許需要的正是異性的一句溫暖的鼓勵。可惜命運中三個女人所對應的三個轉折點讓宋響在叛離社會的異途上越走越遠,直至被現實吞沒。
男性霸權的動搖使女性主義運動狂飆突進的同時也由激烈的對撞變為理性的平和。面對愈發洶涌的消費主義巨浪,在兩性問題上,或許逃避與對抗都不是最好的選擇。女性只有直面男性,雙方攜手并進,才有可能超越傳統性別角色中“兩性殘缺”的狀態,達到“兩性融合”的極致,達成文明社會和諧的最終目標。這是一條別于傳統的道路,映川正在前進的路上,她所做的就是翻越兩性角色之間豎起的高墻,為女性書寫開辟一片嶄新的園地。
于是《易容術》《掛在墻上的自行車》等小說相繼問世,這兩部小說都呈現了“性別拯救”的特質,這正是映川企盼達成“兩性融合”的一種嘗試。《易容術》中青琴為了拴住優秀的丈夫過分追求容貌以致走火入魔,其間肖魚劍一直容忍著妻子的疑心,安撫她的不安,盡一切努力幫助妻子走出自卑,可惜偏執的惡魔占了上風,肖魚劍的努力沒能挽救妻子的自我毀滅。《掛在墻上的自行車》里的陶亦追求完滿的愛情,她無法忍受優秀的男友簡之同近乎病態般收集前女友物品以此懷念過去的做法。最終兩人的互不相讓使一段感情破裂,陶亦沒能“喚醒”沉浸在過去的簡之同,簡之同也沒能消解陶亦潔癖性的占有欲,故事以遺憾收場。兩部小說分別展現了兩性之間“單向調和”與“雙向互救”的特點,雖然均以失敗告終,卻為“兩性融合”的終極目標指明了方向。映川在創作試驗中意識到,只有男女雙方跳出傳統性別的窠臼,實現開放式對話,相互調解,才有希望真正意義上突破性別的藩籬,建立兩性和諧的文化秩序。《不能掉頭》《我困了我醒了》《淑女學堂》等作品正是進一步的嘗試,映川以冷靜的自省與敏銳的感知一步步開拓著兩性書寫的嶄新道路。
在這個“身體解禁”的時代,“消費”和“物欲”已成為支撐社會存在形態的兩大指標。文化語境的轉變使得女作家必須走出各種一廂情愿的幻影式自欺,跨越大眾狂歡的陷阱,打開女性書寫的新局面。由自閉走向自審,由暴露轉向理智,映川以其清明深遠的獨特創作于喧囂背后,展露別樣風采。
① 岳斌:《在詩意和塵囂間游移》,山東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第134—135頁。
② 王侃:《九十年代女性文學的主題與修辭》,《文學報》2000年7月6日,第003版。
③ 映川:《意殺》,《青年文學》2010年第3期,第85頁。
④ 映川:《零食》,《中國作家》2012年第13期,第40頁。
⑤ 映川:《為你而來》,《廣西文學》2006年Z1期(第5-6期合刊),第18頁。
⑥ 賀紹俊:《男性可堪拯救?——讀映川的小說》,《南方文壇》2005年第1期,第69頁。
⑦ 映川:《宋響的玫瑰》,《作家》2004年第11期,第76頁。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5級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廣西籍女性作家影響研究”的成果
作 者:李佳憶,玉林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2013級漢語言文學本科生(卓越班),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鄭立峰,文學博士,玉林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編 輯:趙紅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