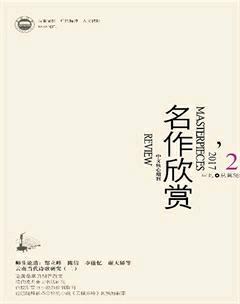論黃詠梅的邊緣文化審美問題
邱舒馨+鄭立峰
摘 要:黃詠梅從“人”的維度來審視邊緣文化,結合個人經驗、文化差異構建城市邊緣群體的精神世界,現實與精神失衡,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文化碰撞融合,使邊緣文化具有雙重性與斗爭性的特點。在邊緣文學創作中對人物底層、事件底層進行敘述化,擺脫個人經驗的蒙蔽性,重塑“日常經驗”,對邊緣群體進行苦難敘述,透過個人表層,溫情注視這一群體的精神,講述“出走”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無法回到故鄉的“漂泊”命運。
關鍵詞:邊緣文化 苦難敘述 精神世界
“邊緣文化”特指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外,是相對弱勢的、占少數的非主流意識形態,產生的理論依據是“共生”思想和“邊緣效應”,一般情況下表現為片面的、非重點的。在經濟和文化呈多元化發展的態勢下,“邊緣文化”的存在便具有客觀必然性,其主要表達的對象是邊緣群體,即以中下層和底層群眾為主,屬于社會的弱勢群體。黃詠梅從文化審視角度深入邊緣文化,結合精神與環境,構建了一系列與社會現實斗爭的人物形象,以低調平和的姿態平視邊緣群體,表同情于悲慘命運,對邊緣群體進行“底層敘事”,塑造在苦難環境中仍然努力追求夢想的精神,探索能夠在城市立足的外在力量與精神力量,哪怕精神在社會的重壓下走向麻木甚至破碎,都是探索之路的成功者。
一、構建邊緣人孤獨悲苦的精神世界
黃詠梅筆下的邊緣群體有從農村到城市謀生的勞動者,也有在城市轉型過程中被拋到底層的市民,盡顯社會“優勝劣汰”競爭法則。采用“全知全能”的敘述方式,筆調客觀細膩,文章為多線型結構,線索明晰,善于對日常小事進行冷峻再現,以悲憫之情,扯掉現實外衣,揭露藏匿于后的精神堅守,將對苦難的吶喊藏在心底,對命運做隱忍式抗爭。
作為當代底層敘述的先覺者,黃詠梅較早地關注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者以及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被擲到生活底層的小市民,“直面都市底層人物的精神遭遇,將他們的愛情、親情及友情中的痛感描寫得細膩溫婉”{1}。從“人”的主題出發,溫情維護人的尊嚴,由現實空間上升到精神追求維度,表達試圖超越現實的渴望,在迷茫探索過程中尋求解脫之路。《表弟》中對表弟的成長分為了三個轉折點,第一個是在跆拳道表演時搭檔臨時改變動作,讓表弟在臺上被打倒在地出糗。受挫后的表弟如眾多青少年般沉迷于網絡世界,游戲中獲得的自我滿足蒙蔽了虛幻與現實的判斷力,于是帶著所向披靡的姿態回到現實與他人進行斗毆,不料被拍成視頻放到網上,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批判,這個熱血事件就是表弟的第二個轉折點。自尊的挫敗感讓人逃離到游戲帶來的快感里,最后崩潰的極點在“裝睡哥”事件上,表弟因坐公車時睡覺沒有給老人讓座,又被人拍下來放到網上,由此來自各方面的道德倫理枷鎖扼住了表弟的喉嚨,重壓之下表弟選擇了“薩克雷”式一躍,結束了年輕的生命。表弟存在逃避現實的自我蒙蔽心理,渴望疏離現實,逃到可以釋放孤獨產生濃烈熱情的“江湖”,構建一個與現實對立的虛擬精神世界,然而質樸的本性在回歸現實后被現實侵蝕,不得已選擇最決絕的方式表達對現狀的不滿與反抗。與表弟相似的還有《單雙》中的李小多,數數這一天分給她帶來些許的尊嚴滿足,博弈勝利帶來的快感使她沉迷在自我世界,隨之不斷加大籌碼,最后把生命賭給了上天。表弟和李小多二者都渴望超越現實,逃離到自我存在得到滿足的虛擬維度,對現實的幻想破滅后陷入絕境,歸于虛擬的精神世界,對生命探索缺乏經驗,脫離社會,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在迷茫探索后,都用生命來反抗現實。
超現實努力的失敗,或以命為終,或歸于生活,繁瑣的日常經驗,隱藏著人物精神的追求與變化,黃詠梅用冷靜的筆調,將時代犧牲品在過渡時期的頑強心理發揮到極致。《契爺》里,夏凌云用書信與外界聯系一事敗露后,在封建傳統與現代化沖撞交匯中,契爺是舊文化的代言者,夏凌云則是時代轉換縫隙中的犧牲者,從國道而來的司機黎變搞大她的肚子又離她而去,她只得生下女兒自己撫養,在路旁的蒙古包里賣糯米糍粑度日。另一個人趙想想則在個人努力下實現了“出走”,坐上開往省城的末班車,頭也不回地離開。經濟的一體化發展,打破了各地區孤立的狀態,在城市現代化發展的夾縫中,有不少像夏凌云企圖逃離卻掙脫不了現實只得妥協回歸,也有如趙想想帶著與故鄉決裂的堅定實現“出走”,逃離追夢,但是從黃詠梅筆下邊緣人命運看來,趙想想“出走”后的留白,隱藏著妥協或潰敗的未明意味,個人也好,整個邊緣群體也罷,若想要從本質上完成現代化蛻變,需要積累足夠的力量,才能獲得社會話語權。
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犧牲者,還有《檔案》里管理檔案的小職員,《瓜子》中從管山到廣州的保安,《特定時期的愛情》中沒有正經工作又不愿回家鄉的小每,等等,這一類人,沒有資本積累,沒有一技之長,只有廉價勞動力,由于對金錢、虛榮與繁華的渴望,縱使因都市的排外性而被歧視孤立,也不愿離開令人沉醉的廣州,更不愿回到故鄉,最后都走上“漂泊”的道路。
黃詠梅在講述人物時,透過人生經驗,直擊他們千瘡百孔至麻木的精神深處。他們急切地渴望脫離故鄉,摒棄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精神財富,被金錢物欲蒙蔽,竭力賺取金錢來填補精神上的空虛,在盡力融入城市的過程中,理性追求被一點點磨滅,在被排擠的苦難邊緣地帶中生存,即便如此,他們也不愿回歸故鄉。底層群眾雖占社會的大多數,但其自身在經濟、政治和文學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故沒有足夠的力量轉變身份,缺乏話語權。
生活在現代城市的弱勢群體,個人奮斗似乎并不足以讓人實現轉換社會地位,欲望與現實拉大了追求與得到的心理落差。《把夢想喂肥》中“我媽”身殘志在,是殘疾人的典范,在梅花州是殘疾人三輪車群體中的“領袖”,為了“把夢想喂肥”,她毅然決然來到了廣州,滿腔熱血,卻始終抵不住現實的消磨,夢想破滅后死在廣州區里的一條臭水溝里。殘疾人在生理上本就處于弱勢,冷酷的現實更是撲滅了追求希望的火焰,在此黃詠梅并非只是對殘疾人生活遭遇的苦難進行單一重現,而是塑造了一個另類的勵志典型,在絕境中依舊激情,對明天充滿向往的“大姐大”。黃詠梅追求的精神世界,與現實接軌又超然于現實。人的欲望分為物質欲望與精神欲望,往往精神會大于物質,暗藏了邊緣群體追求與得到的不平衡,側重于追求過程的場景再現,憑借著原有的精神財富抵抗現代化城市帶來的攻擊,雖然人物超現實的行為失敗了,但是精神卻成功了,與一貫標準化的人物追求不同的是更注重人物在追求夢想過程的心理變更,從有聲追尋到無聲隱忍,感情逐漸變得固板,最后選擇妥協或者用生命之重痛訴社會現實的殘酷。
二、孤獨的“漂泊”者
因中國現代化城市的畸形發展而產生的“都市癥”,在文學作品中流露出孤獨、焦慮、寂寞的“現代情緒”。謝友順認為進入“新世紀”后,文學的消費主義浪潮以較快的速度興起,在這一浪潮的影響下,作家內心對敘事探索的熱情消減了不少,“作家們似乎輕易就卸下了敘事的重擔,在一片商業主義的氣息中,故事和趣味又一次成了消費小說的有力理由”{2}。寫作對象有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者,因原有的精神文化與城市現代化現狀產生隔閡,他們變成城市孤獨的漂泊者,還有原本就生活在城市的底層群眾,在前現代精神文化和現代精神的文化沖突中,邊緣群體只能在城市邊緣尋求存在感。許多作家持憐憫的目光,以俯視的姿態進行單一的揭露、批判和控訴,空洞地進行道德呼喊,極力表明道德立場,為邊緣群眾硬性代言,看似積極,實際上受市場性影響,邊緣文學的“文學性”被削弱,以至于故事情節模式化,人物形象僵化,缺乏精神底蘊,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里,將農村與城市二元化地對立起來,重視物質經濟,淡化了文學對人倫理、道德精神的作用,雖揭露邊緣群體的苦難,也只是停留在表層。而著眼文學魅力脫離時常桎梏形成的“文學場”,來看待現代作家的邊緣文學創作,則反映了邊緣文化的獨特魅力。
當代文壇主流作家遲子建的作品自新時期以來很難被歸入到某一思潮中,近幾年出現的“底層文學”為她的作品提供了新的維度。遲子建以溫情著稱,關注社會邊緣弱勢群體,遵循道德倫理審美標準,迷糊善惡分界,從二元對立的模式中跳出,有豐富的精神內涵,細膩的筆觸,溫情的目光,看待邊緣地帶的苦難生活。《起舞》以全知全能角度對時空進行靈活轉換,以老八雜的拆遷重建作為切入點,講述老八雜底層貧民生活的現代化變遷,和蘇聯專家在“起舞”中受孕成為齊如云命運的轉折點。小說圍繞半月樓的女主人齊如云和丟丟展開,到老八雜變成龍飄花園,映襯出哈爾濱從20世紀初到現代的風雨悲歡,回遷的貧窮市民和新住來的富人相比,他們的粗衣糙布與現代化的高級小區顯得格格不入,沒有了溫情,剩下的只是鋼筋水泥的冰冷蒼涼。遲子建和黃詠梅都屬于溫情敘事,用悲憫的目光注視邊緣群眾的苦難,關注“人”的主題,從表層深入溫情注視邊緣群體的內心精神世界。雖然城市現代化發展迅速,但底層精神蘊含仍然扎根在傳統文化中,從語言到思想,邊緣群體不可能完全擺脫先輩傳承下來的精神財富,而一下子進入到社會中心位置。
黃詠梅并沒有割裂城市“漂泊者”與精神文化源地的聯系,反而在尋求身份認可過程中表現了與故鄉的羈絆,帶著這份不變的精神堅守,“出走”到都市,根植在鄉里。對此黃詠梅很少直接寫家鄉,她的小說大多數以廣州為背景,但其中蘊藏著深厚的梧州地域文化底蘊,在都市生存本相的關注下,給人物世俗層面上增添地域文化的審美空間。梧州自然景觀鴛鴦江、潯江、系龍洲等常在其作品中出現,人文景觀也不少,如:多寶路、騎樓、白馬等,這些不是單純的地區標號,還是文化地域的標識。小說《騎樓》以衰落的騎樓文化群為背景,以“我”與小軍的愛情為線索,結合“茶文化”和“騎樓小吃”勾畫了梧州特色圖景。“茶文化”反映了梧州人生活的悠閑恬靜,“騎樓小吃”則有酸筍紫蘇的味道,人們聚集在一起品味鮮美的螺肉,喝掉碗里“最要緊那啖湯”,“啖”在梧州方言中是“一口”的意思,除此之外還結合了廣州粗話,如:“丟那媽”“耍花槍”和“曬命”等,方言俗俚和“省罵”交叉,黃詠梅從飲食文化汲取營養,將語言作為切入點表現城鄉文化的融合性,充實作品人物的傳統屬性,強調精神之魂駐扎之地,對“根”的執著,人物就算在衣著、語言和行為等方面與城市人如出一轍,其“出走”都是不徹底的。人們存活在社會邊緣、罅隙中拼命賺取作為社會人的權利,經濟落后導致思想固封,發達繁榮催促精神走向“超現實”,父輩以懷念故鄉的姿態把勞動力供奉給城市現代化建設,子輩在城市中被“欲望”改變,流亡于城鄉斷層,失去了先人留給他們的精神歸宿,大自然的純真熱情,城市的僵硬冷漠,與母體的羈絆無法割離,又不被城市所接納,只能成為時代激蕩中的犧牲品。創作中以梧州為人物故鄉的原型,看得出作者即便是“出走”到廣州,對故鄉仍有醇厚思念與文化扎根,廣州與故鄉的生活經驗,在邊緣人身上體現為現代和傳統兩種文化精神的沖撞及融合。
城市的“漂泊者”,他們生活于城市卻被城市隔離,逃離故鄉又無法徹底否決歸宿,在城市與農村的邊緣罅隙中“漂泊”。作品中原有的精神財富就是漂泊者的根,對于現實生活的展現,黃詠梅自己承認:“寫作給我帶來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我過另外一種生活,能讓我實現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不可能性,甚至讓我成為一個現實生活的客人。”{3}故其作品中的人物具有強烈且獨特的自我意識,不作為作者的傳聲筒存在,而實行自我發聲,相應地抒情性便有所減少,透過生存境遇反映精神世界,突顯追求與精神,揭示在社會轉型期,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被現代工業文明孤立的“漂泊”命運,“走出去”和“走回去”似乎都成了不可能,只得在農村與城市的邊緣地帶生存。《瓜子》刻畫了一群從管山到廣東的打工者,以瓜子為主線,穿插兩代人與兩種文化的碰撞交融。開成鱉攜女兒到廣州生活,希望女兒能轉變為徹底的“廣州人”,自己因刺殺孟鱉后被捕入獄,女兒只得隨大伯回故鄉,不料女兒在途中逃離火車,獨自徒步又向廣州的方向走去。女孩成長過程中被學校乃至社會排擠,導致心理扭曲,雖盡力融入廣州,不愿“歸去”,但又無法擺脫管山文化及其精神印記,盡卑微之形在廣州漂泊。女孩選擇反叛式出走,隱喻由“瓜子”二字形成的“孤”,可見作者諷刺之意。作者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處于底層的弱勢者的生活境遇及內心世界進行探索,并予以同情。父輩與子輩、農村與城市,相互共存,相互影響,同時也存在審美沖突。社會發展的歷史性與階段性,突出了新舊力量此消彼長的斗爭性,在這種背景下,邊緣過渡地帶的人們具有雙重性,黃詠梅則抓住這一特性,構建了不愿回歸又不被接納、處于城鄉邊緣群體的生存環境。
寫作來源于經驗,或直接,或間接。黃詠梅在《把夢想喂肥》的自序中說道:“我知道經驗的重要性,也知道了經驗的蒙蔽性。因而寫小說的時候,我總是在跟經驗談判,跟經驗拉扯。”{4}在寫作與經驗的拉扯中,提出了經驗的蒙蔽性,這也是她創作的獨特性所在。她細膩、冷靜地對生活進行諷刺式的敘述,透過溫情悲憫的目光,與現實經驗的蒙蔽性作斗爭,以直視隱藏的情感與精神,立足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看底層人群在邊緣中、掙扎中的情感堅守與破滅。
從農村到城市的打工者以及在現代化轉型中被拋到社會底層的小市民,黃詠梅撥開經歷的表層,由苦難敘述揭露隱藏的內心世界,看當代人的夢想追求與精神堅守,構建原有精神文化和現代化精神的沖突交融的精神世界,體現傳統精神本源和城市現代化生存本相,構成了黃詠梅對邊緣文化的獨特審美。詩化的語言、方言俚語和粵方言的嫻熟轉換,為底層敘述增添了溫情和嶺南地域文化特色,這也是黃詠梅對邊緣文化的獨特審美。
{1} 孫春等:《南方文學崛起的希望——“嶺南文學新實力”作家創作現狀筆談》,《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第19頁。
{2} 謝友順:《重構中國小說的敘事倫理》,《文藝爭鳴》2013年第2期,第96頁。
{3} 黃詠梅:《文學的氣場》,《文藝報》2015年4月8日,第002版。
{4} 黃詠梅:《把夢想喂肥》,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