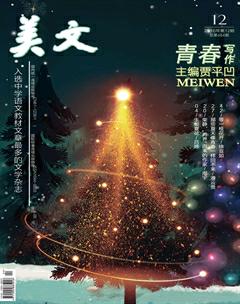你,獨一無二
董偉瀟
困難選擇了他,他卻選擇了詩意的生活。他用心體驗大自然賦予他的一切,用毅力充實著自己的智慧,完善著自己的人生,甚至還可以笑著寫出《病隙碎筆》。他詩意地生活著,收獲著。他的名字叫史鐵生。他是我最欽佩、最喜愛的一位作家。
1980年,由于敗血癥住院接受搶救治療后,史鐵生問柏曉莉大夫他還有多長時間。柏大夫對他說:“你大約還有十年時間。”可三十年之后,他仍然頑強地活著,于是柏大夫問他:“那十年,你有沒有倒計時的感覺?你當時是怎么想的?”
史鐵生說:“從感覺上,當時沒有太相信我只有10年的時間,但也想過這個問題,但無論是5年還是10年,你都改變不了,那就不如使這10年精彩起來。人生只有一個過程,過程使你獲得一切,而并不是你在終點得到什么。10年是一個過程,你把這個過程弄的很糟糕、很憂慮、無所作為、沒有價值,何苦呢?不管它是幾年,先干著再說。”柏大夫問:“就是我給你倒計時的時候,你也特別坦然,活一天就要過好一天?”
史鐵生說:“是的,而且現(xiàn)在也是這樣。這么多年,我堅定了一個信念,就是既然是一個過程,那么不管怎樣,我盡力而為。人生有時像打牌,雖然你抓的牌很糟,但你不能不打。任何一把糟糕的牌都有一種最好的打法,你找到了最好的打法,你就算贏了。只有在過程中才能顯示你的力量、你的美、你的智慧。運動員常說如果以最好的方式去對待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你就會有最好的結果。這等于說你最好的過程就是你最好的結果。”
他是一個殘疾人,但是他從生命的殘缺中體會到了人生的價值,在信仰的廢墟中重建理想,熱愛生活,超越宿命。他是智者,是強者。他的思考早已超越了殘疾,跨過了生死,向著更深遠更廣闊的層次里邁進。史鐵生認為,世間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殘缺的,都是有所遺憾的,可正是因為生命的殘缺,卻反而為人們超越自己,超越困境和證明存在的意義敞開了可能性的空間。他在《我與地壇》中寫道:“假如世間沒有了苦難,世界還能夠存在嗎?”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就像尼采所說的那樣,沒有巖石的阻擋,哪能激起美麗的浪花?沒有挫折的考驗,也便沒有不屈的人格。他在《我的夢想》中說:“我希望既有劉易斯一樣矯健的身體,又有個了悟人生意義的靈魂,后者卻又要在千難萬苦中獲取。”史鐵生讓我明白,要敢于接受即使不如意的命運,不要抱怨,不要悲傷,抬頭仰望,微笑向陽,努力學習,努力生活,要相信,畢竟山的那一頭總會雨過晴天,那時的天空會透明如洗,山坡上會春暖花開,迎面而來的會是和煦的春風。
帕斯卡爾說,人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雖然它十分脆弱,但因其會思想,所以脆弱如蘆葦的人就能發(fā)出人性的迷人光澤。史鐵生就是用他那殘缺的身體,詮釋了他最為健全而豐滿的思想。他體驗到的是生命的苦難,表達出的卻是生活的明朗和歡樂。人生漫漫,世事難料。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和困難周旋的過程,但我們能夠做的,應該做的,就是如何將手中的“牌”優(yōu)化組合,并力求把每張牌打好。
我很佩服史鐵生,他在面對問題和挫折時,不是一味地抱怨,而是能夠適時調整好自己的心態(tài),用“愛”的方式來戰(zhàn)勝苦難,詩意地生活。
這也是我喜愛他的原因。
他就如我人生路上的一盞明燈,不斷地指引我向前,哪怕前方的困難再多,我也不會放棄,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