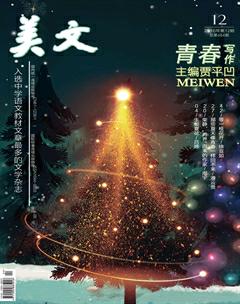只為途中與美相遇
林頤
喜歡歐游的人不少,謝哲青也是其中之一。他不僅是一個旅行者,還是一個藝術欣賞者,他的歐洲游記同時也是一次美的記錄。這一本《歐游情書》,仿佛情不自禁曬出的戀愛心境,款款情深,喃喃“藝”語,傾訴與美的一次次相遇。
當然,這些相遇需要時光沉淀,在那之前,他必須要做好足夠的準備。謝哲青大學畢業后,成了一個頂尖的導游,走過80多個國家。他還求學英國倫敦亞非學院,取得了考古學與藝術史雙學位,并曾任大英博物館研究助理、拍賣會策展人。中國臺灣電視節目《關鍵時刻》主持人劉寶杰大呼:“我們找到寶了!”原本只是偶爾的一次嘉賓邀請,謝哲青的藝術素養卻折服了熒屏前的寶島觀眾,一位知性誠懇的“藝術說書人”從此誕生。
如何介紹歐洲的悠久傳統呢?學院式綜合論述的形式固然翔實有用,但是卻難以表情達意。朱光潛說:“美是物的形象,或者美是意象。”物的形象如果不能喚起意象的共鳴,又何必來談美呢?謝哲青的筆致溫雅深情,在一次次珍貴又倏忽消逝的邂逅時分,他挽留住了某種獨特的東西,讓讀這本書的人分享了“美”。
這種獨特的東西就是濃郁的人文氣息。謝哲青選擇的藝術家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具備挑戰時代桎梏的勇氣,坦然地表達自我對世界的理解。
謝哲青說,喬托是第一個站在“人”的角度看待耶穌的畫家。謝哲青寫過《重返文藝復興》,重點講述達·芬奇與米開朗琪羅兩位大師的巔峰對決,可惜其他人物旁涉不多,《歐游情書》彌補了先前的一絲遺憾。文藝復興時期熱情洋溢的藝術創作,是一種長時間壓抑的欲望的真正爆發,它本身就是一次美的勝利。
凝視《阿波羅與達芙妮》,泛著瑩白光芒的柔美的女性胴體,還有男性有力的肌肉虬結的臂膀,這種理想化的美和欲的形象背后,是歐洲藝術一直以來對人性的追求。謝哲青說貝尼尼“根本就是個魔術師,不但讓石頭有了欲念,也讓石頭有了絕望的情緒”,而他從這個故事中生發出來的對“愛的執念”的闡述,叩響聆聽者的心弦。
席勒的《家庭》——最哀傷的全家福,畫作底色沉郁黑暗,不祥縈繞在人物周圍。孩子、媽媽、爸爸,一個倚靠著另一個,一個擁抱著另一個,宣示著無言地層層保護。親眼目睹懷孕的妻子痛苦離世,同樣承受著病痛的席勒在三天后也隨之而逝。謝哲青說席勒畫出了幸福生活的普世價值,那是家庭之于我們的義無反顧的責任。
一路行走一路沉吟,帕多瓦、塞南克、馬德里、佛羅倫薩、巴黎、羅馬、維也納、莫斯科……26個觸發思緒的旅行地,謝哲青目光所及、足跡所至,有畫作、雕塑、遺跡,也有城堡、宮殿、墓園。這樣一種漫漫而游的姿態,并非到處都合適,而歐洲無疑最是佳地。
謝哲青寫新圣母福音教堂,落筆不在視覺而是嗅覺,描述香氛氣味之神奇,“召喚遙遠塵封的歲月”。舒國治也有類似的說法:“氣氛,有時不是感受于當時,而是滲露于久遠的后日。”他們都有著敏感細膩的心思,出入塵世而不滯著,故能體味常人忽略之細處,一如蘇軾在《記承天寺夜游》里所說的,何處無月,何處無松柏,但少閑人閑心而已,現代的人們大多數還少了點閑錢和時間。
如果說新圣母福音教堂是療愈生命之所,在謝哲青看來,蒙帕納斯墓園則展露了“對生命的依戀”。墓園,大概是人間最特殊的地方,連接著生死,溝通著陰陽。死亡是所有旅人的終點。里斯本的老電車悠悠晃蕩,在時鐘之外,是歐洲依然存留的慢時光。這時候,你會記起木心和“從前慢”嗎?“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克羅齊說:“藝術即直覺,直覺即藝術。”藝術與直覺都是情感的表現。謝哲青避免了術語和理論,他的闡述都是主觀性的感受,不同的欣賞者當然會有不同的體味,未必就要去贊同他的看法,只是在聚精會神的這些時刻,讓我們漸漸地沉靜下來,遐想遠方,與美來一次不期而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