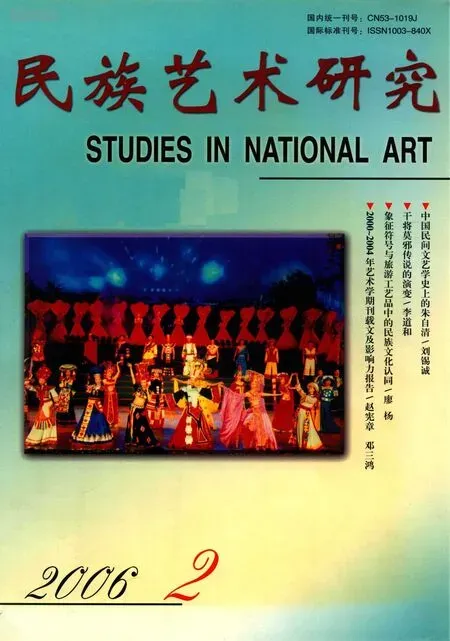脫離與沉浸
——舞蹈劇場中前沿科技創作觀念探索
劉 春
脫離與沉浸
——舞蹈劇場中前沿科技創作觀念探索
劉 春
編舞家們以新技術探索身體的感知方式,電腦工程師以舞蹈作為連接和打通所有藝術的鑰匙。身體在劇場科技中將獲得新的形態?技術如何完成自身開發,產生意義;身體如何與新技術共處?藝術家對于新技術的態度,以及他們的創作探索將舞蹈拓展到身體藝術的整體觀念,甚至重驗舞蹈自身的藝術規律和動作原則。未來的劇場是否因為前沿科技的運用,人不再成為表演的主體?人將身體和動作的原則以技術化的方式,促使整個劇場環境成為“合成”的表演者。編舞家和數字藝術家在使用新技術時所呈現的創作觀念和宣言,也是21世紀藝術家們在重新思考藝術邊界和創作者身份時面臨的責任和挑戰。
新媒體與舞蹈;舞蹈劇場;前沿科技;舞蹈媒介;投影與身體;實時互動;舞蹈與技術的共生隱喻
一、科技與舞蹈的“互動”重建劇場幻覺的原則
新科技被劇場逐漸地接納,激發全新觀演感知,舞臺的夢境因為技術的進步越來越真實。因技術與身體的相互依存,出現了虛擬影像與真實表演者的混合。“混合表演化的投影”、實時互動等新鮮景觀,使整個舞臺影像技術的進化過程充滿爭論但又令人興奮。身體在虛擬環境中刷存在感,新技術卻正在營造改變觀演者心智的環境。
新科技讓藝術家能夠延展身體,甚至產生脫離身體的狂想,得到某種時間的延續和空間的折疊。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創造了創作者沉浸內省和編織更大幻覺的機會。表演者的動作被捕捉進而由技術變為虛擬的數據,肉身得以在數字化中“永生”,表演者的動作與風格也可能轉化為新的生命,就像“人們通過機械連接重新獲得對生命的幻想”。一方面“脫離身體”的時空造夢手法提供了現實舞臺上的數字化儀式,以技術的手段企圖觸碰精神的世界,讓表演者與數字環境互生意義,重建個體;另一方面,對其浸入的體驗讓觀者失去了時空的確定性,隔絕與劇場外真實世界的關聯,讓觀者徹底相信環境的唯一和故事的真實性。
互動技術等更多前沿科技的出現與使用,不再局限于意義和內容。投影演變為了角色,增強了幻覺空間的存在感,同時這個“角色”也擁有了獨特的生命。
投影在劇場中所創造的角色,產生一種幻覺的力量,營造出現實存在卻又看不見的空間;有關內容、意念的產生,是多維度,同時發生的。因為互動技術的加入,投影可能成為“演員”,是夢中不同層次幻覺的呈現,也可能成為記憶的碎片,肉眼無法識別的數碼流,以及我們正在面臨和應對的數字化生活的影像喻示。投影在劇場中具有很強的“身份性”,無論是機器設備、操作者,還是與劇情有關的影像。
視頻設計、表演者、導演、研究者……作為劇場影像探索進程的參與者,我曾不斷轉換身份。這種身份的轉換也是劇場科技發展帶給很多從業者的另一種影響,在與技術的合作中,站在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反思和學習,彼此推動,同時也提出問題。劇場中,前沿科技和現場的表演者,誰在影響誰?哪個更真實?同時也質疑目前投影創作的潛力遠遠沒有被開發,突然爆發的、模式化的商業投射掩蓋了技術本身拓展的可能,以及“沉思”的機會。
目前劇場中投影的趨向,從投影和身體之間的隱喻關系和意義層面分析,涉及重身、鏡像、復制、內省、隨動。倫敦奧運會視覺設計約翰·曼諾在長期的舞蹈、秀場、演唱會、裝置藝術的創作中,曾總結了“動作響應Reactivity、實時互動Interactive、立體映射Projection mapping”三種類型,從“動”的角度,從設計空間角度,從投影和表演者的關系上,重新思考。Reactivity是反應式的、對位的,其表演主體可以感知所處的環境,并通過動作行為響應并適應環境,表演者與預先設計好的影像運動配合,形成一種假定的互動方式,更像是精心編排的調度,需要大量的排練。立體映射Projection mapping則是突出了投影介質結構本身帶來的視幻,影像附著在身體上,附著在舞臺建筑結構上,視覺設計不僅制作內容,更參與舞臺空間結構的設計,讓影像空間和物理空間來講述故事。實時互動Interactive l ive,強調現場實時采集身體數據,跟蹤身體動作,表演者不再用精準的走位來應和環境,行為更為自由,表演的環境具有了生命感,整個表演過程是觸發式的:身體觸發投影環境的變化,投影環境因為與表演者的互動關系,仿佛成為某種有機的生命體。
動、被動、互動,“動”本身在劇場影像的探索中,已經超越了身體的概念。“互動”成為劇場“整體幻覺”的文本形式。“電腦系統感應舞者的動作,舞者影響著電腦系統做出圖形投射反應,兩者共同塑造出一個立體的、虛擬的,充滿變數的幻景。每一場舞蹈和影像的互動因為實時反應,彼此的配合,即時的影像不可能完全地相同,互動表演變得唯一,不可完全復現。”[1]
二、數字技術環境下表演主體的模糊化
技術時代,觀眾被放置到不再舒適和穩定的觀演環境中,無論是科技造夢,還是數字化影像成為演員,觀眾都需要調動所有感官去體驗和辨識現實與夢境,由此不僅技術,觀眾也成為演出的重要部分。新科技在舞蹈創作和表演中正在逐漸形成新的表達語匯,以現場性、互動性、立體性來重組數字時空。視覺藝術家、編舞家、劇場導演、軟件編程設計師身兼表演者,開始新一輪的“映射”(projection)。他們的劇場投影創作中所傳達的觀念,正是新科技時代中的人與新科技形成共生或是持續矛盾的狀態,以及新科技如何在與“人”的互動中完成進化。
“我們都是由夢構成的”(stuff that dreams are made on),這是來自于《暴風雨》中的一句臺詞,朱生豪先生翻譯的版本是“我們都是做夢的人”,400年前莎士比亞的夢想,加拿大4D藝術團體已以全息的方式將其轉換到了數字化的舞臺之上。1983年成立于蒙特利爾的勒密·皮頓四維藝術團(l emieux pilon 4d Art)由表演藝術家米歇爾·勒密和錄像藝術家維克多·皮頓組成,兩人在2015年執導太陽馬戲團《阿凡達——第一次飛翔》,成就了一場超大尺寸的現實夢境。在太陽馬戲的介紹中,兩位藝術家以跨越融合戲劇、電影、詩歌、舞蹈、裝置、視覺藝術、音樂等藝術門類營造了全新的劇場世界。他們把劇場轉換成了魔術場,場中虛實難辨的影像、復合媒體投影、配合動作跟蹤系統、精致的動畫影像改編了表演者的空間,以詩意和幻覺疊加出更深的夢境。無論是莎士比亞的作品《暴風雨》(The Tempest),還是以動畫大師為靈感的《諾曼》(Norman),將流行文本進行影像夢魘解讀的《美女與野獸》(l a Belle et la Bête),大多數以投影中的演員、數字化的對手戲、影像的表演和真人的表演為主,從而實現了現實與夢境的對話。獨創的視覺環境系統,以全息的投影方式,在舞臺上立體呈現動畫、數碼粒子的陣列,真人大小的3D影像、夸張的頭像,舞者穿過自己的影像,全息的“演員”爬上真實演員的身體和自己的影像角力,動畫的符號隨著舞者的動作起伏……其中向動畫大師致敬之作《諾曼》,讓舞者在立體空間中跟隨諾曼·麥克萊倫的動畫音樂和影像起舞。其編舞完全根據諾曼·麥克萊倫的動畫片動作來設計,其影像成為編舞的靈感和主導動機,影響了其調度和動作風格,身體動作和影像動作在不同時空中成為統一的敘事。預制的影像,圍繞、附著、籠罩著舞者,舞蹈因為影像的跟隨,喚醒了身體的記憶,復活了諾曼動畫的精神。
全息投影以“消失的屏幕”,打破電影、劇場的界限,模糊了真人演員和虛擬演員(錄制真人而非動畫制作的演員),兩位創作者曾這樣介紹,“虛擬現實探索版本的《暴風雨》:舞臺的雙重宇宙圖解了現實和幻想之間的移動邊界。真實的演員扮演著島上的居民,他們的生活卻被虛擬的影像角色所攪亂,演員被投射在舞臺上,沒有使用任何可見的屏幕!”
劇場和電影,新媒體技術疊加出的空間,形成了解不開的“夢”。布滿危險,不確定性,更多的是怪誕和夢魘,夢成為兩位作者的創作觀念的原點,虛擬影像完成了重身、分身,靈魂與真身的對話,形成了抽絲剝繭的空間謎團,令觀者沉浸到夢境之中。
奧地利多媒體藝術大師克勞斯·奧伯邁爾(Klaus Obermaier)的頭銜很多,媒體藝術家、導演、編舞、作曲,其作品以視覺分型、變體、破碎、重組方式來表達身體的觀念,探討科技營造空間中的表演主體,以視覺、光影來改變動作的原有形態。在1999年,他曾提出“視頻投影、身體表演、聽覺環境,能夠融合出一種共生狀態,從而創造出他們自身新的現實性。”[2]
20世紀90年代,奧地利多媒體藝術大師克勞斯·奧伯邁爾(Klaus Obermaier)開始使用一系列數字媒體的硬件和軟件,開始對人體投影、實時互動進行研究型的創作。在《技術空間中的表演主體,由虛擬到現實》的書中,曾有章節以克勞斯·奧伯邁爾的作品《幻象》展開討論貝爾納·斯蒂格勒的技術哲學,以貝爾納·斯蒂格勒的關鍵概念個體化、器官學、藥物來解讀奧伯邁爾十年作品中所不斷呈現的視聽隱喻。評論稱“《幻象》把電腦技術提升為共生表演狀態的同伴”。
作品“幻象”(Apparition,2006),呈現了兩個層面的內容,數字投影系統作為表演同伴,沉浸式的動態空間。作品揭示了一幅未來或是正在進行的圖畫,人類與技術環境之間的糾纏,賴以身存和自我毀滅?“他和電子藝術未來實驗室(Ars Electronica Futurelab)合作,利用多方資源開發互動技術,以移動追蹤系統,通過電腦的計算,把演員移動時的輪廓或形狀,從背景中抽取出來,以不斷更新的采集數據轉換成肢體投影,以及運動力學的定性計算,例如速度、方向、沖力、體積等,再把這些計算得到的數據以動態的方式,編制成實時發出的投射影像,或直接回到演員的肢體上,或放大后成為背景的投影。這樣,準確同步的投影把整體擬真運動空間化成現實,影像是流動的,又可以停滯,可以做出延展、收縮、波動、屈曲、變形的特效,來回應演員或影響演員的動作。克勞斯曾說:‘舞者不能決定電腦的操作,但能夠影響電腦的反應,而電腦也無法決定舞者的動作,他只是舞者的一個‘舞伴’,一個深具潛質、變化無窮的舞伴。’應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節委約創作互動3D版《春之祭》,是目前最科技化的《春之祭》舞蹈版本。觀眾帶著3D眼鏡看立體的《春之祭》,現場的獨舞女舞者Julia Mach的舞蹈通過立體攝像機采集,放置到電腦實時生成三維立體的虛擬空間之中,觀眾看到的則是舞者在虛擬環境中的身體冒險,32個麥克風采集的現場樂隊樂音,也將影響動畫影像的模式,舞者和樂者,動作和音符不僅僅是表演和呈現,而是創造和改變著整個演出。”[3]舞者的身體在虛擬環境中,完整的身體消失了,手腳分離身體,單獨地行走,代之以萬花筒式的身體器官組合,無限復制的女性舞者,延長了變形肢體的舞者。
這場《春之祭》在虛擬與現實中間挑選了那個“祭獻者”,在高科技和古老信仰之間,人類有新的方式去達成其和自然、精神的互動,這場祭祀有關不確定的未來,當觀者也帶上3D眼鏡,進入到祭祀者的空間時,這場人性的角逐才剛剛開始。而在最近作品《經顱》(TRANSCRANIAl,2015)描述為“科學家利用電磁脈沖通過改變神經元的電流,造成對大腦活動的故障。這種故障會導致肢體的分解感覺。身體表達思想,還是思想導致身體的表達,作品以新科技對現場表演進行器官學的探索。”[4]
克勞斯在《幻象》的創作筆記中回顧了新媒體與劇場現場表演的重要人物,網站上提到兩位先驅人物:捷克舞臺設計約瑟夫·斯沃博達(1920-2002)結合電影和現場表演,營造了動態的空間;美國編舞家埃爾文·尼古萊(1912-1993)曾以多媒體劇場全新的演繹方式去探索劇場空間和動作形態。特別是埃爾文·尼古萊神秘主義的創作美學,挑戰當時的編舞規范和樣式,其風格影響了眾多的藝術家。看得出來,在這些作品中,新科技與現場表演已經有緊密的結合,無論是技術上還是美學上的。他更是列舉了日本、加拿大、西班牙、英國、丹麥、德國、美國等地的藝術家,以持續增長的媒體與現場互動的探索團體,來說明他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而且正在等待新的轉折。“按照我的經驗,我會花很多時間等待怎樣以恰當的方式使用技術,能夠按照我的想法隨心所欲地使用……我知道技術所能夠做什么,我需要做的是在劇場通過編程、開發,工程師將技術突破自身原有的功能和設定,從而找到新的解決方式。”[3]所有新技術對于他來說,如果不能夠促進、激發演出,就沒有任何價值。
三、“身體化”的技術開發和使用
德國軟件工程師弗里德·韋斯(Frieder Weiss)和澳大利亞的當代舞團“分割運動”(Chunky move)跨界合作,讓該舞團成為澳洲舞界的先鋒。弗里德·韋斯曾宣稱:“我設計的軟件其實沒有做過什么有用的事情,也許這可以作為一種審美的宣言。”這種無用之用的宣言既是對技術本身的進化期待,也懷著對舞臺藝術創作者,無論是導演還是編舞的合作期許。“技術不被開發,就失去了本身的意義。”[5]
2013年,弗里德為音樂劇《金剛》設計了視頻和實時互動部分,“金剛”運動實時跟隨的數字軌跡,造就了互動舞臺的奇觀,讓這個巨大的生物獲得生命的能量。作為自由工作的電腦工程師,它長期專注于舞蹈、音樂、電腦藝術的“實時”互動。而他設計的Eyecon互動軟件則長期放在網站上,開源共享,便于其他使用者和設計師進行開發和創新。
澳大利亞舞團總監吉迪恩·歐巴札奈克(Gideon Obarzanek)和弗里德·韋斯創作了“發光”(Glow,2006),單純的獨舞和動作感應軟件交織互動,演化成“長達27分鐘舞者與科技的雙人舞”。創作者在兩者關系的探索中,讓舞者創造出一種“生物技術的科幻片”感覺,“光”仿佛有了生命,舞者的動作決定了光區的大小、形狀、方位。“發光”以數碼夢境中不確定性涂寫行走,描繪了原始的恐懼、孤獨和內心欲望的斗爭。“發光”是人體和機器之間的圖形博弈,舞者在地面舞過之處出現無數的線條、影子、光線,人在坐標之上移動漂移,人體之外是無盡虛空。投影機安排在劇場頂部,攝像機做動作跟蹤系統,事先預制的圖形,全黑的演出環境,一切依靠舞者的動作影響光,影像的起落、明暗、消長……作品使用了紅外線攝像機和帶有Kalypso軟件的PC電腦,弗里德為劇場應用專門設計開發了這個軟件,也是系列作品“可感知身體”軟件開發的延續,以不同計算方式來跟蹤表演者的動作。相反對于表演者來說,編導認為“數字化像素環境像是延伸了動作以及內在世界的視覺化,甚至這種環境成為自我完善、貌似真實的棲息之所。”[6]《致命機械》(Mortal Engine,2008)承接了“發光”的互動系統,配合激光,傾斜舞臺的裝置,讓演出驚心動魄,游蕩在數字的黑洞和夢魘的邊緣,與舞者相伴的線條和光暈變成了發散的黑色粒子,隨著動作開合聚散,塵歸塵,土歸土,身體仿佛是無數偶然的組合……編舞吉迪恩·歐巴札奈克將數字化和原始狀態混雜在一起,把舞者推向了新科技的未知領域。其實驗伴隨著不確定方向和冒險,有評論說,《致命機械》的藝術性遠沒有技術觀念本身有趣,令人昏昏欲睡。但實驗探索總會面臨經歷大多數的失敗,然后獲得一點點的成就。
日本舞蹈家梅田宏明曾提到,“數字技術激進地改變人類的感知。我相信存在另一種維度的審美領域,呈現出數字化控制下時間與空間的精致。藝術家使用數字化設備去延展和縮減人類身體的尺度……像技術更新一樣更新我的思想。”[7]一個人,一面數字影像墻,突然的靜止,突然的喧鬧,瘋狂的速度,瞬間的空白,在充滿無常的重復中,舞臺的“動作”以令人窒息和迷人的緊張感去提醒觀眾當代人擁有怎樣的生存現狀。身體觸發機器的動作,機器的永動讓人成為機器的一部分。這是日本編舞、視覺藝術家梅田宏明(Hiroaki Umeda)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景象。不會重復的“重復”散發著科技與身體融合的魔力,將觀眾推向未知的黑洞,猶如過山車般,內心尖叫著,期待著下一個重復。
梅田宏明放棄了攝影去跳舞,戲稱“攝影太貴,跳舞便宜”。他成立了舞團,舞團只有他一個人。作品中,大多數時候是他一個人面對巨大的數字環境,整個作品都在做一件事。他創作的《同層》、《觸·覺》(Haptic,2008)、《適度變異》(Adapting for distortion)不斷上演著身體和影像的戰斗。街舞和視頻躁點,光譜網格與每一個動作都精準的牽連,身體被無情的淹沒,舞臺上甚至難以辨別他的身體,而這場戰爭將無休止地進行下去。評論曾說:“極簡而又激進,微妙而又暴力,抽象但是充滿細膩,令人驚嘆的身體動作。”垂直的線條和水平的線條將身體切割、分解、變形,讓觀者看到的不僅是身體,而且也是一種現象,來自異時空的生物,卻又無比貼近我們所處的數字生存境遇。
他自己完成音響、數字媒體、舞蹈編排,而看起來復雜的科技,其實都是梅田宏明使用一臺電腦,來控制影像、聲音、燈光跟蹤。正如他所言:“我的電腦使用水平和人們日常使用電腦一樣,我沒有使用高科技去尋求表現形式的渴求……我不做技術展示。”梅田宏明不是舞蹈科班出身,卻決心創造“不同”的舞蹈。他創造舞蹈和運用能夠完成他美學理想的數字技術的方式都極為理性,要找尋“運動”本質和原則。他先是發明了“動力原則”,以“站立、移動、流動”三個階段來確立重新開發不同舞種的動作規律和原則,然后在進行與數字化技術的創作,尋找融合的、相互影響的運動規律。
2009年開始,他歷時10年的編舞計劃“超動”,嘗試創造一種即使沒有舞者也能夠在舞臺上表演的舞蹈,結合所有舞臺上所有動態的元素,由燈光和聲音構成的舞蹈。以數字化手段衍生出的“時空的人工作品,這個作品如同巨大的有機體將擁有生命……”[8]或者說,影像中粒子的運動,聲音的波動,身體的微小變化,燈光的明暗,都是這個巨型舞者的肢體,梅田宏明的編舞,是為這個有機體編舞。梅田宏明稱這個計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研究“動力學運動”,從與不同背景的舞者(街舞、芭蕾、當代)的合作中,通過在不同舞者動作特性中以梅田宏明特有的“動力原則”調整,尋找多樣化的動態語言。第二個階段創造“系統”,去組合所有數字環境的節奏、呼吸、速度,他稱之為“編排時間”;第三個階段的內容是確立“秩序”,是在確立了舞者身體原則之上的技術融合和添加,形成整個空間上的“秩序。”
在新科技的開放性中,每個人都可以使用技術完成自己的藝術內省,或是以技術思考身體本質,運用自己的觀念。這種技術是能夠幫助完成傳達的,或是有能夠傳達的特質和潛能。以數字化媒體來外化內心的原始性,或是凈化,或是喚醒。互動技術、投影內容、噪音頻率、身體動靜,形成了新的感知模式,梅田宏明認為“回應”是人與技術之間基本的溝通原則,舞臺上他將“人”消隱身份屬性,作為引起“回應”的媒介,但隨之帶來了“觀者、體驗者和表演者高度興奮的感知狀態,不是敲擊,而是冷的灼傷。”觀眾接受到的不僅是舞者動作,影像變化,音頻逐漸升高。脈沖帶來的張力,而是對于整個空間的感知,轉化為了對于自身存在的覺醒。
技術與身體,現實與虛擬,作為表演者的人與人作為視覺形式的元素,在梅田宏明的創作中,如同每天日常的身心變化,或是我們共同面臨的宏大與渺小。正如日本媒體藝術家Shiro Takatani曾在作品《靜止》中談到的,“真實的影子在想象的時間中上演,想象的影子起舞在真實的空間中。藝術與科學是否真的能夠表現這個沙漏般的世界,每一個沙粒震顫所發生的細小變化?”[9]數字化媒體與現場每一個的牽制,互動,其實都是宏大世界中的每個微小個體一次冥想的試探,只不過我們這次嘗試用此時此刻的“技術”。
四、全球化視覺沉浸中的舞蹈媒介
技術發展將極為個體的創作和感受,放大為全球化的交互。舞臺正在成為屏幕,幻覺正在變為真實。舞蹈,在所有與新媒體技術交融、碰撞的藝術門類中,最“身體”,形成最為直接的對話。舞蹈自身的屬性在這個進程中反而越來越清晰。作為“人”與技術的接觸,舞蹈的能量轉換、時空關系也啟發了技術如何產生意義和延展,舞蹈正在從藝術形式,轉換為與科技跨界和交流中的媒介。“1800年,法蘭西學會成立了一個致力于研究全景畫的專門委員會。該委員會一致認為,全景畫的主要影響在于制造了一個‘幻覺整體’,他們在報告中指出,通過與科學的結合,藝術無疑更加接近了完美幻覺的終極目標。”[10]他們不曾想到,21世紀以來,世界似乎成了一塊大屏幕,一幅令眾生沉浸的全景畫。人們總會需要更大的屏幕,更多的投影,更真實的沉浸,更大的空間來制造視覺奇觀。這能否被看作是一個信號呢,互動的探索正在公眾化,被悄然地認同。索契冬奧會使用了約120臺投影,里約奧運會使用了約110臺投影,無論是空間體量上,還是內容設計上,無論是硬件的含金量,還是軟件的換代升級,前沿科技正在將劇場空間,詩意,戲劇引向更多的公眾。
自北京奧運會大面積使用投影技術后,奧運會成了數字投影和新科技以及無數個體的互動平臺,這塊大屏幕不斷地投射出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符號和歷史軌跡,巴西奧運會的跑酷人與地面投影樓房的互動,北京奧運會的絲綢之路影像與人的歷史行走,索契冬奧會的歷史滄桑和壯闊詩意畫面與舞者的互動。這一切不再是投影的簡單呈示,這個過程永遠需要人的介入,因為人的介入,這些畫面才變得有生命,無論是哪個國家的文化符號還是歷史。互動,對話,交換感知,相互感應,才有了流動的生命,歷史才會繼續下去。拉茲洛·莫霍利·納吉在20世紀20年代曾預言,“目前的機械裝置與未來的照明技術的結合將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場舞臺革命,這場革命將為口頭表達和通過身體使時空形象化的舞蹈創造新的環境。”[11]正如法國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所言,“我們是技術的存在者,我們是象征的存在者。”[12]今天,藝術家們正在用數字技術、人工智能來繼續著變革、唯一不確定的是我們將迎來怎樣的新表演者和新的環境。
(責任編輯 唐白晶)
[1]劉春.互動未來——劇場舞蹈中的影像互動[J].舞蹈,2009,(3).
l iu Chun,Interactive Future:the Image Interaction in the Theatrical Dance,Dance,No 3,2009
[2]Neill O Dwyer,The Cultural Critique of Bernard Stiegler:Reflecting on the Computational Performances of Klaus Obermaier,Palgrave Macmillan UK,2015
[3]Annamaria Monteverdi,K laus Obermaier the Strange Dance of New Media,http://www.digicult.it/digimag/issue-023/klaus-obermaier-the-strangedance-of-new-media/
[4]Klaus Obermaier,http://www.exile.at/transcranial/
[5]布萊恩·阿瑟.技術的本質[M].曹東溟,王健,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Brian Authur,The Natureof Technology,trans.by Cao Dongmin and Wang Jian,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ress,2014
[6]Gideon Obarzane,http://www.frieder-weiss.de/works/all/Glow.php
[7]Hiroaki Umeda,http://hiroakiumeda.com/artist. htm l#1creative
[8]HiroakiUmeda,Choreographic Project“Superkinesis”,http://hiroakiumeda.com/artist.htm l#3choreographic
[9]Enrico Pitozzi,SHIRO TAKATANI,The extension of visible,http://www.digicult.it/news/the-extension-of-visible-shapes-of-time-acoustic-imageschromatic-figures/
[10]魯道夫·弗里林,迪特爾·丹尼爾斯.媒體藝術網絡[M].潘自意,陳韻,譯.上海: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R.Freling and D.Daniels(eds),trans.by Pan Ziyi and Chen Yun,Media Artistic Network,Shanghai:ShijiWenjin/Shanghai People's Press,2014
[11]拉茲洛·莫霍利·納吉.運動中的視覺[M].周博,朱橙,馬蕓,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laszlo Moholy Nagy,trans.by Zhou Bo,Zhu Cheng and Ma Yun,Vision in Motion,Beijing:CITIC Press,2016
[12]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愛比米修斯的過失[M].裴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Bernard Stiegler,trans.by Pei Chen,Technics and Time:The Faulty of Epimetheus,Nanjing:Yilin Publishing House,2000
Extraction and Imm ersion:Exploration of the Notion of Frontier Technological Creation in the Dancing Theatre
Liu Chun
The choreographers use new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sensing methods of human body,and the computer engineers use dance asa key to connect and relate all arts.Will the body acquire new forms in the theatre equipped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How will technology develop itself andmakemeanings?How will the body co-exist with new technology?What are the attitude artists have on the new technology,as well as their creative exploration which extend dance to a holistic notion ofbodily art,even re-verify the artistic rule and action principle of dance?Will human no longer be the subject of performance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the use of frontier technology in the theatre?People use the principle of body and action in the manner of technology so as to make the theatrical environment as a“synthesized”performer.The creative concepts and manifesto that are displayed by choreographers and digital artists when they are using the new technologies can be seen as respon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artists in the 21stcentury face when they rethink the artistic boundary and the identity of being a creator.
new media and dance,dance theatre,fronti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dancemedia,projection and body,real-time interaction,the symbiosismetaphor of dance and technology
J714
A
1003-840X(2017)02-0135-07
劉春,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北京 100029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2.135
2017-02-20[本刊網址]http://www.ynysyj.org.cn課題基金:本文系2016年度文化部文化藝術研究項目“新媒體與舞蹈藝術研究”(項目編號:2016FE00054)階段性成果。
About the author:l iu Chun,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nd Post-graduate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of Choreography of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Beijing 100029
The paper is funded by the follow ing:Phased results of the 2016 Ministry of Culture Cultural and Artistic Research Project New Media and Dancing Art Studies(No 2016FE0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