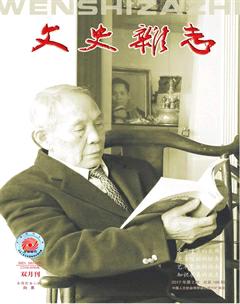向熹先生的語言學研究及學術思想述略
俞理明+孫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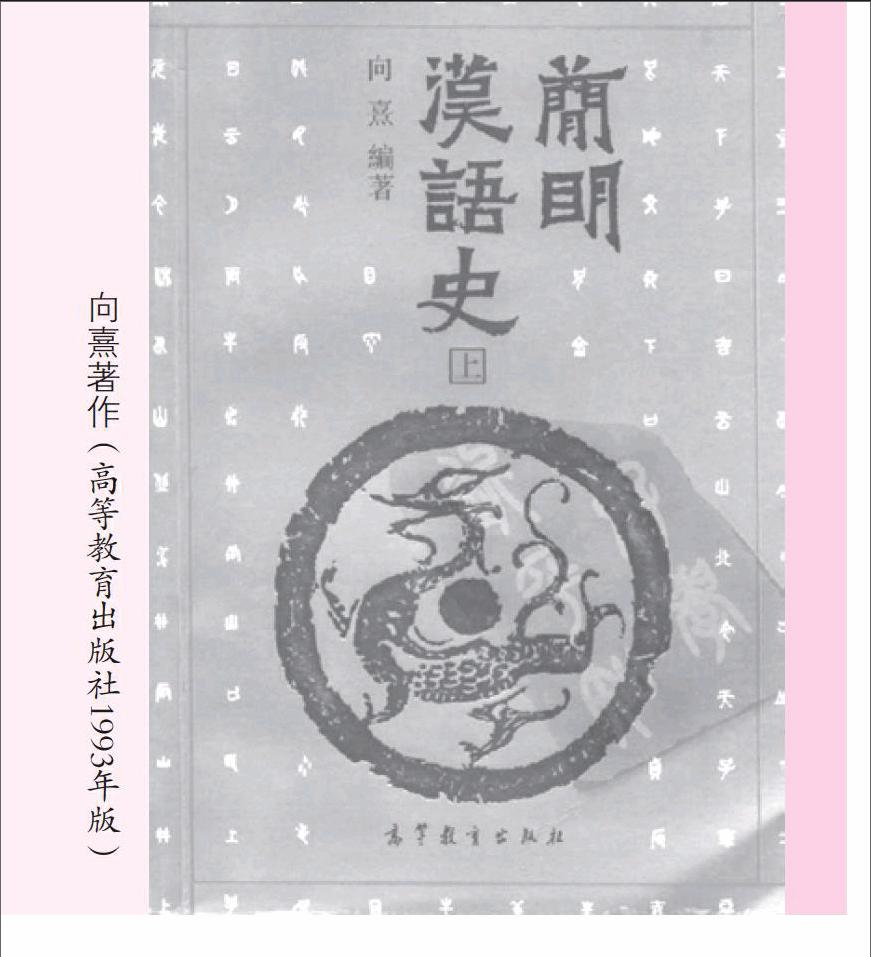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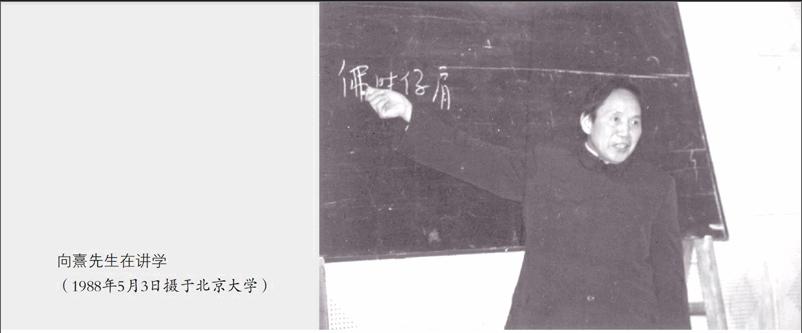
摘 要:向熹先生的學術研究的主線,在于繼承傳統小學,立足現代語言研究的理論方法,從斷代描寫的角度,對漢語歷史展開全面描寫,著成《簡明漢語史》。他的《詩經》語言研究,為漢語史的描寫奠定重要的基礎,與《詩經詞典》《詩經譯注》等系列研究構成了《詩經》研究的理論體系。他堅持教學與科研相結合,從教學中發現學術問題;并注重把艱深的學術研究與滿足公眾語言學知識需求結合起來,開展辭書編纂的理論和實踐研究,為古漢語知識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向熹;漢語史;詩經研究;辭書編纂
向熹,1928年生,祖籍湖南省雙峰縣,中國當代語言學家、漢語史學家,現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
向熹先生畢業于湖南春元中學高中,擔任過半年小學教師,l950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l954年本科畢業,留校繼續攻讀漢語史專業研究生,受業于王力、魏建功、高名凱、袁家驊、呂叔湘、陸志韋、周祖謨諸先生,其中導師王力先生對其學術影響最大。1958年秋,向熹先生研究生畢業,分配到四川大學中文系工作。向先生先后給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了“現代漢語語法”“語文和寫作”“漢語史”“古代漢語”“《詩經》語言問題”“《馬氏文通》導讀”等10多門課程。在幾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先生孜孜不倦,教書育人,為國家培養出許多語言學教學和研究人才。他善于從教學中發現問題展開研究,又利用研究成果促進教學,教學相長,學以致用,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研究特色。向先生的學術研究主要圍繞三個領域展開:一是《簡明漢語史》的編寫,二是關于《詩經》的研究,三是辭書的編纂。這三個領域的研究集中體現了向先生的主要學術思想。
一、漢語史研究及漢語史劃分的理論框架
20世紀50年代,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出版,這是漢語通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向熹先生求學期間受教于王力先生,專攻漢語史,確定了自己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向。向先生任職四川大學以后,從1961年秋起,給本科生講授“漢語史”課程,在師承王力先生漢語史研究思想的同時,并未簡單照搬老師的漢語史系統授課,而是嘗試自己編寫講義,安排教學內容。他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和對講義多次改寫補充,于1991年完成了以分段研究為特點的《簡明漢語史》的書稿,199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榮獲國家教育委員會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這是繼王力先生《漢語史稿》之后的第二部研究漢語史的力作。2002年到2006年期間,向熹先生又對全書進行了修改補充,201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修訂本,被教育部列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范教材。
《簡明漢語史》全書分上、下兩冊,包括漢語語音史、漢語詞匯史、漢語語法史三編,各編又按上古、中古、近代三大時期對漢語發展的歷史進行整體描述,另有“緒論”五節、“結論”二節與主體三編互相呼應,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分時段的漢語史體系。
漢語文獻記錄了漢族社會文明發展的歷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對于漢語這樣的世界上可溯歷史最久、保存文獻最豐、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描述它的歷史,不僅對于了解漢語本身和漢族的文明史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對于了解人類的語言、人類語言發展的規則都有著無可代替的價值。從“小學”的文字、音韻、訓詁到現代語言學的語音、詞匯、語法,歷代學者一直在漢語這塊土地上辛勤耕耘,留下了大量寶貴的財富。漢語通史就是要把歷史上積淀下來的豐富的語料與前人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作系統的描述、綜合的印證,說清漢語發展的歷史。《簡明漢語史》就是這樣一部勾勒漢語3000多年發展演變脈絡的著作,集中體現了向熹先生的漢語史學思想。他在《簡明漢語史·緒論》中說:“研究漢語史,就要弄清漢語在不同歷史時期語音、詞匯、語法的基本面貌,了解漢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變化,探索這些發展變化的特點和原因,揭示出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這也概括了本書的中心思想和內容。全書三編的描寫、論述都是為了解決以上關于漢語史研究中提出的問題。圍繞“史”的觀點,向熹先生提出:l.必須充分反映漢語的時代特點;2.區分語言事實現象的通例和特例;3.揭示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的相互關系。他指出,漢語史的研究,應立足于客觀的語料分析,綜合全面地看問題,進行科學的漢語史分期,才能建立起一個科學、系統的漢語史體系。歷史是“根”,做好漢語史的研究,對我們進行現代漢語研究、漢語方言研究和普通語言學理論的研究等都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就漢語史的描述與揭示,向先生提出了三縱三橫的理論框架,將語言的共時體系和歷時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種漢語史的描述理念,充分體現在《簡明漢語史》之中。所謂三縱,就是從歷時的角度,把漢語史視為語音史、詞匯史、語法史三位一體的綜合系統,再從上古、中古、近代三個共時層面,分別做歷史斷代考察,總結各時期漢語語音、詞匯、語法的概貌和特點,敘述其從上一時期到下一個時期的發展演變,對漢語發展史中紛繁復雜的現象作系統的歸納和整理,形成漢語史的總體描寫,勾勒出一個漢語史的框架體系。
向先生認為,揭示漢語史重在語言實證,要有大量的語言事實;但對歷史文獻中的語言事實,并不是越多越好,應從浩如煙海的語言材料中,去偽存真。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區分常例和特例”,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不能因為一些特例而懷疑語言發展演變的普遍規律,也不能因為常例而忽視語言發展變化普遍性中蘊含的特殊性變異。向熹先生本人就漢語史不同時代的語言現象做了大量前期的專題研究,從各歷史時期的各種文獻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同時也充分注意學界前賢時哲的研究,必要時兼及不同意見,根據歷史的語言事實取舍折中,提出自己的觀點或論斷。他認為,漢語有大量的古老的文獻,可以提供許多直接的實證材料;但漢語史的描述,還應吸收充分的旁證材料進行說明和印證,二者有機結合,體現證據材料的全面性和充分性。向先生描述“上古漢語語音系統”,討論上古漢語的聲韻調,每個聲母、韻部和聲調都舉出了大量的例字,更舉出每個韻部所屬的諧聲偏旁,并用大量《詩經》原文押韻例句作進一步說明。他在描述漢語語法史時,為了講清楚漢語各個語法成分、語法結構、句法等的發展情況,用了近萬個例句;詞匯部分的用例更是數不勝數,每一個論點的提出都來自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整理、歸納,避免用少數似是而非的材料作論證的依據。
對于漢語史的描述,向先生還提出一個基本原則:說史務必通俗淺出,重在敘史而不做過多議論和不必要的修飾;對語言現象和規律的揭示,應實事求是,用豐富的材料和細致的分析闡明觀點,也不故作高深;遇有不常用的術語應隨文做淺出的解釋,方便讀者理解。先生的《簡明漢語史》確實名副其實,體現他對敘史的“簡明”觀點。樸實的風格、簡明的語言、豐富的史料,勾勒出漢語3000年發展的清晰輪廓。
從宏觀上全面地研究漢語的發展史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它需要研究者全面掌握漢語史的各個分支和各時期的材料。在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過程中,要耗費研究者無數的時間和精力;沒有堅忍不拔的毅力、扎實深厚的學術功底和踏實穩重的學術作風是無法完成的。在幾十年治學生涯中,向熹先生堅持把自己的研究和教學相結合,長期開設漢語史課程。他通過自己的研究編寫講義,開展課堂教學,又在教學中尋找不足、發現問題,再通過研究加以彌補,提高水準,不斷地豐富其中的內容,使之日臻完善。《簡明漢語史》是向熹先生“教學要與科研相結合”的理念的最好體現,代表向熹先生的最高學術水平。
二、詩經研究
把《詩經》作為漢語研究的素材,起始于漢語通史研究的前期準備。向熹先生說:“最初只是為了編寫《簡明漢語史》須要掌握上古漢語第一手資料,才去研究《詩經》。接觸多一些,產生了興趣,于是下決心寫《詩經》語言研究方面的書。”他通過對《詩經》多年的全面系統的考察和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陸續出版了五種關于《詩經》語言研究方面的論著。
l.《詩經詞典》(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次年修訂再版,1998年再次修訂重版)。這是向熹先生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學術專著,也是我國第一部音義兼備的專書詞典。該書“收錄《詩經》里出現的單音詞2826個作為字頭,同時收錄復音詞近1000條、305篇的題解和有關《詩經》研究的術語300余條,總計1318條”(《詩經詞典》后記)。修訂本又把異體字獨立列出,字頭增加為3336個;另外,合并義項近500處,增補材料3000余條,還審訂了每個字頭的字音。書中義項解釋準確、精煉、通俗,除名物解釋外,一般采用古今對譯的方式,注音則兼用漢語拼音和反切兩種方式。在釋義內容的選擇上,向熹先生的原則是“首出己見,擇要兼收”,每個字頭下先列自己的解釋,然后擇要收錄眾說,用“一說”“又一說”的方式表明,意在把古今學者《詩經》訓詁研究的精華都匯集在《詩經詞典》里,以便讀者參考。該書出版以來,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好評,成為閱讀《詩經》必不可少的工具書,榮獲1988年第二屆王力語言學獎。近10多年來,向熹先生又對《詩經詞典》再作修訂,補充了材料1000余條。新版的《詩經詞典》已于201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詩經語言研究》(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本書是向熹先生在“《詩經》語言研究”選修課講義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為《詩經詞典》的姊妹篇,是我國第一部研究專書語言的著述。全書共六章,分別介紹了前人研究《詩經》的概況,討論了《詩經》的文字、音韻、詞匯、句法、修辭和章法,對《詩經》中的語言現象作了全面系統的分析和論述。夏傳才先生在《二十世紀詩經學》中評論說:“該書是80年代《詩經》語言研究的總結性著作,既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經著者歸納分析、覃思精研,不但條理分明,而且理論上又有精進,可以說該書代表了《詩經》語言研究的時代水平。”[1]
3.《詩經古今音手冊》(1988年南開大學出版社)。該書收集并注明了《詩經》所有單字的今音(漢語拼音)、反切、中古音和上古音,把每個字的字音從古到今貫穿起來,供讀者閱讀《詩經》和研究上古漢語音韻時參考使用。全書按拼音字母次序排列,不收錄《詩經》里未出現的字音,書末附有《詩經》上古音分部和入韻字表。《詩經古今音手冊》是一部研究《詩經》時期語音的專著,其中古今音的對照又為研究漢語語音的演變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4.《詩經語文論集》(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該書收錄了向熹先生關于《詩經》研究的論文15篇。這些論文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關于《詩經》語言研究的論文,分專題研討了《詩經》語言的性質、歧義的分析、異文、通假、注音以及詞匯、通韻和合韻等重要課題;其中有的是《詩經語言研究》沒有涉及的問題,如“歧義的分析”,有的問題在《詩經語言研究》中討論過,《論集》又進行更深入、詳細的論述。另一類是關于前人研究《詩經》成果的研究論文,包括從漢代到清朝研究《詩經》的幾個重要成果的研究述評。與《詩經詞典》和《詩經語言研究》匯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同,《論集》主要闡述了向熹先生自己的觀點和態度。
5.《詩經譯注》(200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本書原為1995年許嘉璐、梅季先生主編的《文白對照十三經》叢書中的一種,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單行本經劉曉翔先生設計封面,典雅質樸而富有創意,被選為“2009年中國最美的書”。2010年在德國萊比錫世界圖書評比中,從634種參選圖書中脫穎而出,獲得“2010年世界最美圖書”榮譽。《譯注》每篇詩包括原詩、題解、今譯、注釋、韻讀五部分。題解介紹詩的主題,力求簡潔,主要立足文本自身內容。今譯以直譯為主,緊扣原文,化繁難為平易,采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七言句式,并押大體相同的韻。注釋簡明扼要,擇善而從,表明今譯的依據,解釋不易理解的古代名物詞語,標明異文,為難字注音。韻讀按照《詩經》時代的韻部標示該詩的韻腳和韻部。《詩經譯注》是向熹先生多年研究《詩經》成果的集中體現,原文、題解、注釋、韻讀都是作者采集各版本和各家之長精校而成。
《詩經》是中國文學和語言方面的源頭性文獻,其中保存了大量治學不可或缺的寶貴材料。自古研究《詩經》的學者眾多,先生對《詩經》的研究從語言方面切入,充分繼承前輩在音韻、文字、訓詁各個方面的成果,博覽眾說,綜貫各家,擇善而從,保留異見,并以詞語為綱,編成《詩經詞典》,為學界在《詩經》的深入研究方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為自己在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其中,《詩經古今音手冊》是這項研究的字音部分。因為技術原因,其出版稍后,但卻是《詩經詞典》的前期成果。整體來看,《詩經詞典》是從語言的角度對《詩經》的微觀研究,而《詩經語言研究》則是在微觀調查的基礎上,從宏觀的角度把握《詩經》的語言特點,依托對《詩經》語料的窮盡性的考察,通過文字、音韻、詞匯、句法、修辭和章法等多個方面展開專章分析,總結歸納《詩經》語言的主要特點,描寫它的整體面貌。研究一種古代文獻的用語,微觀的觀察與宏觀的分析雖然角度不同,但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應該說,弄懂字詞的意義有助于我們理解文獻中的句子的篇章,了解句子和篇章內部的結構和邏輯關系,也有助于我們求得字詞的確詁。
借助古代文獻研究古代語言,包括編寫古代的專書詞典,在取材的時候,往往采取抽樣的方式,即獲得適當數量的語料之后就戛然而止了。這樣做,可能忽略了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語言現象,但是,也可以借此回避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而采用窮盡描寫的方式編寫詞典和考察各類語言的現象,使一種文獻中所有的問題都突顯出來,必須直接面對,無所逃遁。這樣做當然增加了工作的難度,但是,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現問題、迎難而上,才更能推進研究的不斷深入。
古代文獻由于距離現代時間久遠,古今漢語的差異,導致今人在閱讀古代文獻的時候,往往有一種可以意會卻不能言傳或似懂非懂的感覺。很多時候,讀者大體看懂了文獻中文句的意思,但是,未必理解文句中的每一個字,或未必理解句子的語法結構的詞語間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對文獻的理解,存在著某種“猜 ”的成分,所謂的理解,最多是“八九不離十”,大概知道而已。向熹先生的功勞,正是將這“八九不離十”,轉化成句句坐實,引導讀者從“不求甚解”進入到“游刃有余”的自由境地。《詩經》是萬古流傳的文學經典,愛好者眾多,歷來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研究《詩經》、解讀《詩經》的人也很多。向熹先生運用自己對《詩經》語言的深度了解和掌握,譯注《詩經》,深入淺出,要言不繁,字字落實,為《詩經》的傳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也為古代文獻解讀作出了表率。
三、辭書編纂及詞匯學說
20世紀70年代后期向熹先生與張永言、杜仲陵、經本植、羅憲華、嚴廷德等教研室同仁共同編纂了《簡明古漢語詞典》。這是一部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讀者學習古代漢語、閱讀古籍參考的中型語文工具書。其從通行的古代文學作品中,搜集現代人不易理解的詞8537條加以解釋,從選詞到釋義,都充分考慮讀者的需要,目的對象明確,針對性強,適用度高。這之中向熹先生撰寫了大約五分之二的初稿。該詞典于198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重印十余次,暢銷不衰,深受語文工作者歡迎,還于1999年出版修訂本。1988年,本書獲四川省人民政府頒發的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
20世紀80年代,向熹先生還主編了《古漢語知識辭典》。這是一部全面介紹古代漢語相關知識點的辭書,包括總論、詞匯、語法、音韻、文字、訓詁、詩詞曲律、修辭、文體、重要的語文著作、重要的語文學家等11大類,共收條目1619條。向熹先生撰寫了其中語音、詞匯部分的一些條目。本書雖然不是專門研究,但它注重實用,系統介紹古代漢語研究的基礎知識,方便備查,對于推廣學術、引導后學,有很積極的意義。本書198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再度出版修訂本。
另外,從1987年開始,向熹先生倡導組織了幾位青年后學展開《漢語稱謂詞典》的編寫工作。該詞典定位為歷史詞典,即為讀者提供各個漢語稱謂詞比較完備的歷史資料。詞典從歷史詞匯研究的角度,廣泛搜集漢語歷代文獻中出現的各類稱謂詞,搜集各稱謂詞的來源和歷史變化等有關材料,為讀者展示這些稱謂詞的歷史面貌和演變過程。這項工作從漢語稱謂詞的歷史調查入手,通過對歷史文獻中稱謂詞的廣泛深入的調查,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經過10來年的努力,寫成初稿。嗣后又幾經修改刪訂,現在已經初步定稿,即將出版。
辭書編纂涉及面廣、工作量大,要在辭書編寫中體現研究性和學術性,更是難上加難。因此,若沒有足夠深厚的知識積淀和握有豐富的各類語料,辭書編寫將寸步難行。向熹先生參與多部辭典的編纂工作,對編寫辭典的難度是深有體會。他在許威漢主編《古漢語詞詮》序中談道:“要求詞書編寫者不僅有真才實學,而且要有非常嚴肅的治學態度”[2]。這也是向熹先生編寫辭書的原則。
在從事以上三個方面的研究工作、撰寫和編纂了不少著作和辭書的同時,向熹先生還在文字、音韻、詞匯、語法、方言等方面寫有大量論文,包括關于文字方面的如《〈古代漢語〉文字上的幾個問題》《簡化漢字大有必要》等;關于音韻方面的如《〈廣韻〉入聲韻同非入聲韻中的重出字》等;關于詞匯方面的如《陰陽五行觀念和漢語詞匯》《王力先生對漢語詞匯研究的貢獻》等;關于語法方面的如《〈水滸〉中的“把”字句、“將”字句和“被”字句》《略論訓詁和語法的關系》《論〈馬氏文通〉的句法研究》《古代漢語教學語法體系芻議》等;關于語言和文化的如《避諱與漢語》(一、二、三)等;關于方言的如《湖南雙峰縣方言》等。
結 語
據向熹先生回憶,1957年末反右運動行將結束的時候,北大研究生舉行了一次“交心運動”。當時年輕的他在會上坦陳了自己人生的目標,那就是“當教師,寫10本書,發50篇論文”。畢業后50多年來,盡管遭遇了許多波折和坎坷,他一直沒有放棄這個目標,勤勤懇懇地在教書育人、科學研究這條道路上默默前行。作為導師,先生以身作則,對學生在思想和生活方面慈心相向,寬大包容,呵護有加;而在學術上鼓勵學生積極主動的思考,放手支持學生科學探索,大膽開創,熱情鼓勵學生在學術研究方面努力進取;同時嚴格要求,強調重事實、重材料,不輕率結論,不急于求成,踏踏實實,寫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著述。
先生說,人要有自我定位,我的定位有兩點,一、我是中國人,是農民出身,因此要做到三點:一要對得起祖宗,二要對得起祖國,三要對得起子孫;二、我是教師,作為一個大學教師,一要好好教書育人,二要做科研,我算不上是聰明人,也不會廣泛交際,但只要盡自己的努力,在專業上爭取做到更好,就滿足了。先生常常說:“我們普通人,能夠做到‘立言,就算得上是做了有意義的事了。”他也希望他的學生后輩們能真正沉下心來,不要急于求成,而是踏踏實實,寫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著述。
如果從1950年進入北京大學算起,向熹先生在語言學領域已經耕耘了60多個年頭。這60多年的時間里,基于現代語言學思想和理論的漢語史研究,從當年的萌芽狀態逐漸發展,形成了現在枝繁葉茂的繁榮局面。先生置身其中,力圖創新,致力于漢語史的研究工作,并以梳理漢語通史、撰寫全面系統的漢語史為己任。在漢語史研究這條主線指引下,先生首先把《詩經》作為上古漢語源頭性的語料,展開全面的研究;進而將《詩經》的研究從上古漢語的語料的角度,擴展到全面研究《詩經》,編寫《詩經詞典》和《詩經譯注》,以及組織和參與一系列詞典的編寫。先生在堅持學術研究的同時,面向社會,把精微深奧的專門研究與面向公眾的社會需求相呼應;又在從事深入的專業研究的同時,努力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專業服務。先生是農民子弟,出身貧困,秉承前輩刻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在王力先師的指引下進入學術研究。他深受先師宏大學術視野的感染,在研究中不畏大、不懼全、不怕難,量力定制,認定目標,則心無旁顧,孜孜以求,終至于斯。
注釋:
[1]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學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頁。
[2]許威漢:《古漢語詞詮》,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 俞理明: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孫 琳: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