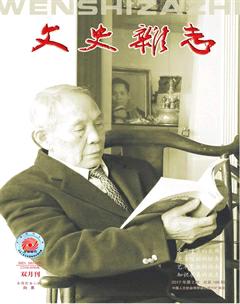從陳寅恪的諷諭詩讀他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上)
子規

陳寅恪現存詩歌三百余首,以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收羅最夥。陳寅恪在文化上尊宋,因為宋代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集大成者:最完備、最豐富、最具美感、最富人格精神與自由價值;但其在詩歌創作中,卻并不以宋詩、宋詞為宗,亦學唐詩、崇唐詩。就這點而言,他與父親“同光體”詩派領袖陳三立大有不同。
唐詩中,陳寅恪最服膺白居易與元稹,特別是白居易。趙翼《甌北詩話》說:“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這是講,元、白能夠用平易近人的語言表達大眾想要表達(卻未必能表達出來)的聲音。陳寅恪的詩,已達到“言人所共欲言”的境界。這里趙翼所講“坦易”并非文字粗糙,內容平淡;至于陳詩,則是勁爽而蒼樸,格調高,意境深,每每蘊含豐贍,耐人尋味。羅韜先生甚至認為,在這方面,陳詩已然超越了元白。羅韜在為《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所寫序言中說:“義寧(指陳寅恪)之壓倒元白者,以其詩關乎天意,所寄宏深,傷國傷時,最堪論世。義寧常自比元祐黨家子,而胸羅中古興亡之跡,撐持天坼地解之際,獨立于禮崩樂壞之時;責己以文化托命之大,諷世在士節出處之微。故其詩秉國身通一之義,造今古交融之境,望之氣沈郁,捫之骨嶙峋,史識詩情,盤屈楮墨。每讀之,未嘗不掩卷低回,愀然而嘆:此變風變雅之音也。”此言甚確!
陳寅恪同歷代優秀知識分子一樣,關注民生、更關注國家民族命運,憂國憤時,疾惡如仇;又以中國文化托命之人自勵,立足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試圖以一肩之力,力扛近世頹落的中國文化大閘,并將其賦予新的生命與活力。他的詩歌,便傳遞出這樣的思考,反映出這樣的心聲。我們看他于1916年所寫《寄王郎》,1929年所寫《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1930年所寫《閱報戲作二絕》,1938年所寫《藍霞一首》諸詩,均反映出他在民族危急、國家危急之時的焦慮不安和奮拔之狀。他的《藍霞一首》系七律,全文如下:
天際藍霞總不收,藍霞極目隔神州。
樓高雁斷懷人遠,國破花開濺淚流。
甘賣盧龍無善價,警傳戲馬有新愁。
辨亡欲論何人會,此恨綿綿死未休。
按“藍”指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以代指國民黨;“霞”(紅色)則指紅軍,以代指共產黨。盧龍,在今河北喜峰口附近,典出《三國志·魏書·田疇傳》。據胡文輝的解釋,舊時用“盧龍”指割地,出賣國家利益,但此處指共產黨向國民黨委屈求全,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戲馬,即戲馬臺,在江蘇銅山縣南,原屬徐州府,此代指徐州。陳寅恪寫此詩時,正值日軍發動徐州會戰之際(1938年5月)。其時國民黨四十萬軍隊在徐州陷入日寇南北夾擊的合圍中,形勢岌岌可危。陳寅恪獲此消息,心急如焚,祈愿我軍能全身而退;更祈愿國共兩黨能捐棄前嫌,共同對敵,否則,必將造成亡國之禍,遺恨千古。陳寅恪此詩,既反映出當時國人、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又有高出他們的更深刻認識——這從其以“藍霞”冠題可見隱秘。盡管陳寅恪同國統區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不甚了解,以為其對國民黨“委屈求全”不過是實用主義而已,但他對國民黨的態度則嗤之以法西斯主義,憂慮共產黨不是其對手。所以他的“此恨綿綿”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側重于對國民黨的警惕與責難。《吳宓日記》在1938年5月有段記述,很能說明問題:“因憂共產黨與國民黨政府不能圓滿合作,故宓詩中有‘異志同仇之語,而寅恪又有《藍霞》一詩。”之所以對國民黨多有責難,是因為對其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手法了解頗深,對剛艱難輾轉、萬里長征才至延安,卻又風塵仆仆、立馬走上抗日前線的共產黨殊為惜憐。陳寅恪在1936年7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不久,寫有《吳氏園海棠二首》呈吳宓,后者即在其手跡后加附注云:“寅恪此二詩,用海棠典故(如蘇東坡詩)而實感傷國事世局(其一即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書之內容——‘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本描寫紅軍長征的書,就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于1936年6月—10月訪問陜甘寧邊區后的長篇報告文學《紅星照耀中國》。陳寅恪《海棠》詩之一有“蜀道移根銷絳頰,吳妝流眄伴黃昏”句。胡文輝箋釋說,其時“紅軍處在國民黨軍隊的追剿下,顯得前途黯淡。故陳詩當是以海棠移植后紅色轉淡比喻共產主義赤潮的低落”。陳寅恪于此詩流露的“親共”情緒是很明晰的。再回過頭來看《藍霞》一詩,自會對陳氏同情看似弱者的紅軍、責難處于強勢的國民黨而心有戚戚焉。
《藍 霞》中的“樓高”猶言“高樓”,謂最高當局。《杜甫》《登樓》云:“花近高樓傷客心”即此。1940年3月22日,陳寅恪作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之一,與竺可楨等在重慶應蔣介石之邀赴蔣官邸晚宴,“寅恪于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有負厥職”[1]。陳寅恪返回在渝所寄住的妹夫俞大維宅后,遂有《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抒懷,中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句,顯示出對身居最高位的蔣介石的不屑與憂懼。
無須諱言的是,陳寅恪同國統區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對抗戰的前途比較悲觀——這也大量地表現在其于這一時期的詩作中。不過,這絲毫無損陳寅恪的愛國立場。他1940年在寫給傅斯年的信函中說:“弟素憂國亡”。他當時對抗戰前途之所以感到悲觀,一是缺乏對國際大勢的通盤把握;二是缺乏對中國共產黨的深入認識;第三,也是最重要一點就是對蔣介石法西斯式的獨裁政權徹底失望。陳寅恪于1932年所作《和陶然亭壁間女子題句》詩中寫道:“鐘阜徒聞蔣骨青,也無人對泣新亭”,就是對蔣介石政權無力阻止日本并呑東三省,更無力掌控全國大局的批評。在先,1929年5月,陳寅恪有《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詩,其“讀書不肯為人忙”句,則是對國民黨欲在包括大中學生在內的全國人民中推行所謂“三民主義教育”,以實行思想統一政策的不滿與嘲諷。
注釋:
[1]吳學昭整理《吳宓詩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60頁。 (下期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