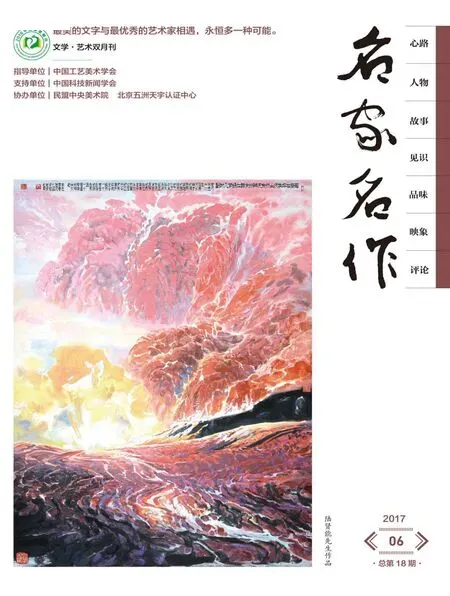好一個書法創作者
寧志榮

自作詩《馳哪》 劉維東/作
高鐵如梭追日月,中國速度世人奇。尖端領域空間闊,快意雄風泰岳移。
認識劉維東以前,就被他的諸多頭銜搞暈了,真不知在這些令人羨慕的光環下他是如何工作的。素有耳聞,他是一位頗有能力的書法家、學者、社會活動家,近期通過幾次接觸,終于印證了業內的評價。
一
兩個月前,我領受了采寫劉維東的任務,通話時他說比較忙,需過些時日才能見面,這一等就是六十多天。到正式見面時,但見在座的盡是文化界的腕兒,讓我大開眼界。握手言歡,細說原委,他確實很忙,教學任務、管理任務,這樣那樣的社會活動,最近還在趕寫一本專著……何況他屬于古道熱腸之人,只要是涉及書畫藝術方面的事情,總會熱心張羅,極力奔走宣傳,樂得為他人作嫁衣裳而無怨無悔。
席間劉維東說,他很少讓人寫自己,現在還不是總結的時候,與心目中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他不是一個全力投入技法錘煉的書家,但他堅信會迎來屬于自己的輝煌未來……我忽然感到,他和我以前接觸的書法家不一樣,他的心很大,他要創意、創新、創造,力爭成為一個提升書法藝術審美的推動者。
他的書法甲午集《縱橫有象》中就有這么一批作品,充分反映出他的上下求索、創新求變,無論從視覺上還是感受上,均讓人耳目一新。如由四部分組成的《察賾闡幽》,其“察”和“闡”取榜書體勢,又有繁復疊加之妙,給人凝重神秘之感;“賾”字左邊鑲嵌一小組行書,一團漆黑中尤為醒目,右邊如月夜幽谷,時隱時現,正合賾字本義(深奧玄妙),又讓人想起《易·系辭上》所言:“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幽”字三豎如山峰聳立,中間筆畫如山道陡峭、盤桓向上,真是曲徑通幽。整個作品把書法、繪畫、抽象藝術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渾然一體,妙趣橫生。又如他的獨字作品《龍》(星空),蒼茫的北碑筆意下斬釘截鐵,左邊部分高高聳立,右邊部分橫向伸展,頂端筆畫以紅色五星點綴,使這件作品平添了更多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意味。再如《中庸為至德》,以篆書結體,融合了甲骨文、鐘鼎文、小篆之特征,具有金石效果和古雅特征,顯得雍容和雅,格局廣大,既可獨立成篇,又橫貫為一,確系不可多得的當代佳構,難怪被德國的一家國際畫廊所收藏。

高眉細眼安然坐,不畏端詳為寫真。怎奈丹青無本色,心香一瓣化梅身。《自作題畫詩》 劉維東/作
我十分訝異于這些作品的形成機制,因為它們遠遠溢出了書法的常規面貌。忽然,我想到劉維東還是一個畫家,今天很多人都已經不清楚他的這層身份——這正是他近些年刻意隱逸的結果。觀賞其近來畫作《有胡子的風景》《失學女童》更讓我找到了答案:前者逸筆草草,連環滾動、撕扯扭結的線條構成有如連綿的遠山,意象簡約,筆墨跳宕,頗有歐美大師的風范;后者依形生發,走筆潑墨,既能生動概括人物對象的特征,又將草書筆法發揮得酣暢淋漓,真是一件暢意絕妙之作。李苦禪先生說:“書至畫為高度,畫至書為極則。”劉維東多年的繪畫體悟,使他的書法構思開闊、意趣無窮;反之,他的書法理解也使繪畫筆墨暢達勁爽,深富底蘊。可以說,正是書畫的相得益彰,使劉維東在藝術的道路上雙槳劃動、擊楫中流,徜徉于更加波濤洶涌的藝海之中。
二
劉維東追求創造,但他并不放棄精研諸體書法。無論是《縱橫有象》所刊,還是其他作品,都可以領略到其滿紙云煙之氣象、縱橫捭闔之氣勢,讓我們充分感悟到書法的無窮魅力。
清代朱和羹《臨池心解》云:“結體之功在學力,而用筆之妙關性靈。茍非多閱古書,多臨古帖,融會于胸次,未易指揮如意也。能如秋鷹博兔,碧落摩空,目光四射,用筆之法得之矣!”欣賞劉維東的《祭侄稿兩組》,草黃信箋,縱筆豪放,蒼勁流暢,頗得顏真卿書風,讓人禁不住遙想平原書帖之時,心情疾痛慘怛、哀思郁勃;欣賞他的《自敘帖印象》,借筆牽絲,筆勢連綿,有疾速而動蕩之感、平正見險絕之象;欣賞他的《王羲之尺牘印象》《古詩四帖節臨》等,都可以發現劉維東對書法經典的用情之深、用意之厚,真可謂鐵杵成針、金石為開,功到自然成。

《祭侄文稿一》 劉維東/作

《四個奈何》 劉維東/作
正是通過長時間的執著追求,劉維東的書法藝術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和特征,真正成為創作的藝術。他擅長多種書體,均達到了一定造詣。小楷是書法的基本功,最見功力。蘇軾《論書》道:“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劉維東的小楷《萬里茶路賦》,參差錯落,疏密有致,沉著中正,遒美健秀,頗得《爨龍顏》《鄭文公》《石門頌》諸碑之長,受到書界同仁贊譽;其魏碑大字作品,骨骼健朗,結構精絕,具有雄渾凝重又風姿飄逸的特點;他的行草博采王羲之、張旭、懷素、顏真卿諸家之長,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采眾長,镕冶一爐,達到了醇厚而靈動的境界;觀賞其草書《蔡邕筆論句》,但見整篇奮力引毫,筆走龍蛇,妙得奔雷墜石之奇、絕岸頹峰之勢。無獨有偶,我更欣賞他的一件草書冊頁《沁園春·雪》,其筆意連屬若大海之潮綿延不絕,通篇彌漫著驚鸞乍飛、邈邈翩翩、云鶴游天、直達碧霄的體勢,可謂體象卓然、氣勢磅礴。
三
我沒有機會去聽劉維東的課,或關于書法的演講,但相聚時的談鋒,讓我對他的語言魅力頗有感受:他談書論道,據典引經,幽默機智,妙語連珠,顯見他的口才和學識非同一般,真有“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圣稱避賢”之神采。
劉維東從小生活在農村,耕讀傳家,庭訓嚴格,自幼習書。他回憶,打小就在紙上涂鴉、寫仿影,稍長便幫著左鄰右舍寫春聯,在學校里出板報、刻蠟版。成長過程中,書寫讓他獲得了充分的認可和自信,也成為其不懈向上的動力。他曾說:“人的一生中能堅持做下來的事情并不多,也不需要多。”只要專注和堅守,定能收獲人生的碩果。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堅持,使他從鄉村一路走來:先考入山西大學國畫本科,后又攻讀碩士,師從著名書畫家李德仁教授,研究中國書畫技法與理論,繼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中央美院博士,師從邱振中教授,研究書法理論,兼攻草書。正如屈原所言“被明月兮佩寶璐,登昆侖兮食玉英”(《九章·涉江》),劉維東幼年就涉獵書法,長大后遨游在知識的海洋里,孜孜矻矻,含英咀華,樂而忘返。大風起兮云飛揚,困苦之后終有大成。多年的刻苦用功和師從名師,使劉維東的書法具有了堅實的功底和理論儲備,書法研究和創作也踏上了更加開闊的平臺。

《沁園春》 劉維東/作
他寬博的知識構架,不僅僅在于熱愛書畫,而且在于他的文學積累和大量閱讀。據說,他當年上本科住進美院學生宿舍,書架上擺滿了《詩刊》、文學著述,以至于同學懷疑他是中文系的學生。書法首先考量的是學問修養,其次才是技能。劉維東熱愛古代文學,浸淫傳統文化多年,汲取著中華文明的滋養,這些必然對他的書法理論研究和人生格局帶來莫大的影響。
縱觀古代史,許多書法家都是詩詞家、學問家,書法只是他們信手拈來的余事。歐陽詢以初唐大家名世,翰墨之外編有《藝文類聚》百卷;蘇軾是名滿天下的詞人、散文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王陽明筆精墨妙、字勢宕逸,卻是明代大哲學家、政治家。劉維東作為大學書法的專業導師、知名學者,他在學術領域也取得了可喜成績:他研究北宋叢刻《大觀帖》,闡幽發微,澄清了稱謂、版本等諸多問題;他還是清代大學士祁寯藻的研究專家,先后撰寫論文達十余萬字;他的書法評論,可謂生花妙筆、深刻文章,被專業人士競相傳閱;出版、主編書法教材、叢書多部,待出版的書稿有四部……他還是書法活動家和倡導者,除了一手開創了山西大學的書法學科外,近年來陸續策劃、舉辦了“中韓書法交流展”“德中藝術家作品聯展”“中日書法作品交流展”等國際藝術活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于促進山西書法和國際書壇的交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宋人朱文長《續書斷》中說:“其志一于書,軒冕不能移,貧賤不能屈,浩然心得,以終其身。”這句話直可奉與劉維東分享,他時常一襲唐裝,溫文爾雅,恂恂有儒者相。他教學創作之余,雅好交友:或天朗氣清,談書論道,品茗暢懷,心游萬仞,抒發天地之浩氣;或細雨紛紛,天地茫茫,感慨流光,思接千載,興嘆人生之苦短;或酒酣之際,興濃之時,濡墨揮毫,心手相契,若蘭亭之盛會,金谷之雅集。
記得那天酒酣耳熱之際,劉維東氣概豪邁,宣稱自己要做的是書法創作者。“創作”二字,表面淺顯,卻道出了藝術的真諦,也彰顯出劉維東的學術追求和高遠目標。他正當盛年,假以時日,定會在藝術的征程中登臨理想的高度,那時再看他激揚文字、盡領風騷!

劉維東簡介:
劉維東,別署龍池子、聞道齋。1969年生,山西孝義人,美術學(書法理論)博士。現為山西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所長、山西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藝術學會會員,兼任文化部國家藝術基金項目評委、山西省書協主席團成員(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山西省青書協副主席、山西省美協漆畫藝委會副主任、山西東方美術研究院副院長、山西省佛教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祁寯藻研究》副主編等職。學士、碩士就讀于山西大學美術學院中國畫方向,師從李德仁教授。博士就讀于中央美術學院書法理論方向,師從邱振中教授。目前主要從事書法教學、創作與研究,兼事美術評論、活動策劃與教育管理工作。曾獲全國大學生書法指導一等獎、中國書協全國征文三等獎、山西省社科聯論文二等獎等。作品入選全日本書會展、中韓書法展、赴德藝術展等國際活動,且被中外藝術機構、國際友人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