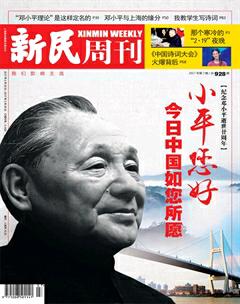樂震文:煙云物外,筆墨供養
王悅陽
“我從前作畫時,從來沒有料想到畫畫和經濟有關系。直到有一天,我的畫被標了高價,我就意識到一種威脅,金錢很容易讓藝術家斷送掉,刻意炒作藝術創作是一種絕對的傷害。我聽到周圍有人說,訂家出錢少,那就少用功,出錢多了,才好好畫。如此心態,怎么對自己負責呢?”

云山浩渺,飛泉煙嵐,平淡天真,一片江南。每每欣賞著名畫家,上海覺群書畫院院長、上海海事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院長樂震文的作品,總有一種置身自然、清和雅致的妙韻撲面而來的感覺。儒雅、敦厚、親和,一如樂震文的為人,一派謙謙君子之風。
丁酉新春,“煙云物外——樂震文藝術展”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開幕,這是作為畫家的樂震文有生以來最大的一次個展。展出作品60余件,時間跨度達30余年,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清晰勾勒出樂震文山水畫風格形成的軌跡,融合山水、花鳥、城市景觀等諸多題材于一堂,筆墨精到,色彩雅致,氣韻生動,意境深遠且不乏時代精神,民族派頭,充分反映了樂震文“為祖國山河立傳”的藝術雄心和“樂氏山水”的藝術全貌。
不僅如此,60歲的畫家還將足以代表自己創作生涯至今全部心血與結晶的60幅藝術佳作,一次性捐贈給了劉海粟美術館以作收藏、研究之用。從此,這批畫家平生“最為心愛之物”就永遠被國家級美術館妥善收藏起來,不僅豐富了劉海粟美術館的館藏,而且完整、精彩、全面地展現出樂震文數十年來的孜孜以求與藝術探索,成了畫家人品、畫藝與精神最完美的體現,蔚為大觀,也為當代海派藝術家群體的弘揚、研究,打開了一條全新的道路。正如樂震文本人所說的那樣:“我們這些海派畫家應該為上海做些事情,增加海派作品的庫存量,讓有志于做研究的后人可以在這里找到完整的資料。”因此,樂震文認為,相比建個人的藝術館,將藝術精品捐贈給國家,無疑是保存自己作品的更好方式。

心心念念,必有回響。在整個春節期間,劉海粟美術館所迎來的觀展群眾突破新高,展覽日期也因此延續了好幾天,成為今年春節上海文化界的一大熱點。毋庸置疑,無論是專業藝術家,還是普通老百姓,大家都被樂震文精到、細膩、傳神的筆墨功夫與藝術造詣所折服,同時也深深感受到了畫家的一顆赤子之心,面對藝術,面對傳統,面對自然的真誠之心,敬畏之心,煙云物外,筆墨供養。這也印證了一條真理——優秀的藝術作品,必定是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才能成為廣大群眾普遍喜愛的經典之作。
漲價不漲價
跟藝術家沒有關系

不知是誰說的,如今的時代,是藝術家所遇到最好的時代。或許真的有一番道理,當今的書畫市場異常火爆,但在風格多元、百花齊放的局面下,卻也難免人心浮躁,利益當先。對此,樂震文深有體會,“我從前作畫時,從來沒有料想到畫畫和經濟有關系。直到有一天,我的畫被標了高價,我就意識到一種威脅,金錢很容易讓藝術家斷送掉,刻意炒作藝術創作是一種絕對的傷害。我聽到周圍有人說,訂家出錢少,那就少用功,出錢多了,才好好畫。如此心態,怎么對自己負責呢?”為了靜心養氣,樂震文在書房里掛著吳昌碩的一幅八尺行書作品,對他來說,這一方面是滋養,另一方面也是鞭策。“畫家容易迷失自己,看看這些東西,提醒自己山外有山,有幸臨摹過大師的真跡,太清楚前人的段位是什么樣的。消去幾絲張狂,要知道早有先人在前頭。”
不僅嚴于律己,樂震文也不斷告誡學生們,漲價不漲價跟藝術家沒有關系,看著金錢作畫,藝術生命也就終結了。“我現在很懷念早前的狀態,畫作并不售賣,也沒有人來預訂什么,都是用自己的思維和內心做創造。”他毫不諱言地表示,自己是從傳統中出來的畫家,在臨摹傳統與寫生里成長起來的,他繪畫的養料幾乎都是從這兩方面汲取的。“傳統的繪畫是最經典,上追宋元,前溯明清,都是遙不可及的奢望。現在再看比如傅抱石、李可染、陸儼少的畫,因為大家有著深刻的寫生經歷,運筆才是這般通靈。”
可以說,樂震文是一個永不滿足的藝術家,他說在自己的目標里,既要堅持中國繪畫講究筆墨的傳統,又嘗試用新的藝術語匯為中國山水畫開拓新境界。“如果不探索,我們就完了,因為我們的作品是要給將來人看的,要與時代產生共鳴。”縱觀此次展覽的每一幅作品,都可以折射出一段真情,一個故事,乃至畫家的一分感動。此情此景,無關金錢,卻有真情。因此,《新民周刊》記者與樂震文老師的對話,也就由此展開。

《新民周刊》:說起樂老師的此次展覽,真可謂盛況空前,熱鬧非凡。是怎樣的機緣促成了此次展覽?如何想到要把自己的藝術精品捐贈出來的呢?
樂震文:可以說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一次展覽,作品是我從1980年代至今30多年的積累。回看展覽作品,很多是我上世紀80年代起參加展覽會的作品,展出結束后就存放在家。可以說,這些作品是我的成長見證,但個人的保存能力畢竟有限,這次重新托裱后捐給國家美術館,也是這些畫的最好歸宿。而事實證明我的決定是對的,劉海粟美術館也是非常重視,這60幅畫全部數碼掃描,存放倉庫,用一套科學的方法保存。我想,這些畫如果拿出去賣,不僅會流失分散,甚至還會成為了別人的牟利工具,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60歲捐60幅畫。我覺得也是對自己繪畫的一個階段性總結。回顧60年的這些畫,似乎回歸了初心,也提醒我身上的責任不僅是繼承,還要開創,為后代留點我們這代人的風采。
《新民周刊》:決定捐贈作品是不是因為受了諸如吳湖帆、謝稚柳、唐云、程十發等老一輩海派藝術大師的影響?
樂震文:說實話,有些老畫家知道后反而建議我不要捐,還不如自己弄個藝術館。也有人說現在市場火爆,你的畫行情這么好,為何不去賣掉?我不想賣畫,但這些畫保存在家里我沒時間打理,不如交給劉海粟美術館,至少有機會跟大眾見面。上海的藝術館中應該有一個海派藝術館。我們這些海派畫家也應該為上海做些事情,增加海派作品的庫存量,以后讓后來的研究者在這里找到完整資料。我希望劉海粟美術館成為研究海派的藝術館。

《新民周刊》:您為什么會提出“一個藝術家應該將他創作全盛時期的最好作品捐贈給國家美術館”?
樂震文:現在一些美術館、博物館可能對收藏古代、近代或者現代藝術家中已有名氣的藝術品更有興趣。不少當代畫家的優秀作品都流失在市場上,國家機構收藏的作品數量十分有限,如果現在不花精力研究收藏當代畫家的優秀作品,今后再要收藏可能時過境遷,未必能夠尋覓得到。
我一直想,當今社會名利的東西太左右一個畫家的心境。記得我當初學畫時還比較純粹,我們看到大畫家就像現在年輕人看到明星一樣。大畫家如果對你的作品指出問題,自己回來立刻畫個通宵,覺得畫好了比什么都開心。通過捐畫,我好像又回到了那個時代,回到了初心,對名和利都不那么在乎。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畫家是學畫條件最好、受到重視程度最高、物質條件也最豐富的,已經享受這么好的條件,也應該給這個時代留下些什么。
畫家不要框死自己
樂震文與畫有緣,從小愛畫的他因為機緣巧合,拜師海上花鳥畫名家喬木老師,打下了扎實的筆墨功底。每每喬老給他的畫稿,一周不到,就臨摹得像模像樣了。后來,因為工作的關系,樂震文得以大量接觸宋元傳統繪畫經典,一下子入了迷,手追心摹,孜孜不倦,逐漸將興趣引向了山水畫。而親身接觸到的大量張大千、吳湖帆、謝稚柳等大師的真跡,更使之對于傳統中國畫的正脈,有了清醒的認識,奠定了未來的發展基礎與方向。
傳統的滋養,加上多年的山川游歷,甚至走出國門,東渡日本,大自然的山山水水給了樂震文巨大的養分,也形成了典型的“樂家云水”畫風。他從中國傳統山水畫起步,追尋于李唐、范寬,覓跡于遠山、幽谷、寒江、暮雪和煙村;他從“江南作品”時期的酣暢、靈秀和靜美直入“黃土作品”時期的陽剛、蒼茫和高爽;他從磨礪傳統筆墨到兼顧現代構成,又從注重水墨技巧到尋求文化激勵。正如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所評價的那樣:“從畫理上說,他在探索山水營造與綜合視覺的結合、傳統筆墨與現代構成的并重、繪畫語匯與藝術哲學的相兼、自然節奏與人文節奏的統一。”
可以說,讓“智慧”拓展畫徑是樂震文作為一名當代中國畫家的文化守望與精神信仰,因此,在他的山水作品中,永遠洋溢著“寧靜”和“智慧”:在氣格中見風骨,在含蓄中見清奇,在婉約中見豪放,在張弛中見節奏, 在景語中見“情語”,在飽滿中見“空靈”……縱觀樂震文數十年來的藝術道路,出入傳統,走進自然,關照內心,堪稱解讀其藝術心路歷程的“不二法門”。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樂老師并非書畫界“科班出身”,但從小愛畫的您就以自己的天分與勤勉,與畫壇前輩結緣,很早就得以嶄露頭角了。
樂震文:我十幾歲開始學習山水畫,22歲(1978年)開始臨摹真跡,同時也開始搞創作,當時我就讀的繪畫班在1978年底辦了個畫展,我創作的山水畫被日本畫商欣賞,邀請我去日本深造,由此改變了命運。
《新民周刊》:上世紀90年代初,正當您在畫壇嶄露頭角之時,您去了日本學習深造。海外世界的繽紛色彩,東鄰繪畫的細膩柔美,都促動著您創作的欲望,在以“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為自己座右銘的同時,您以“構成”取代構圖,層層暈染、層層深厚,從博大沉雄的兩宋繪畫飛騰變化,滋養和開創了自己的藝術創造。但也有人覺得您畫水、煙、云的方法中吸取了日本畫的養分,是這樣么?

樂震文:1987年,我去了日本,很多人以為我繪畫風格的形成吸收了日本繪畫的元素,實則不然,在日本對我影響最大的依舊是中國的兩位畫家,一個是南宋僧人畫家牧溪,他在日本卻被推崇為畫圣。我在東京博物館看到一套牧溪的《瀟湘八景》很是震撼。另一個是清中期的畫家龔賢。現在大家對他們倆還是比較熟悉的,但在80年代末,我在日本看到他們的畫觸動很大。
此外,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一些畫也讓我震撼。比如橫山大觀,傅抱石《九歌》里的仕女就借鑒了他的畫,包括嶺南派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人也“摹借”了日本畫。所以,我大量買明治維新畫家的畫冊,也常去展覽會看他們的原作。但在日本我并沒有學他們畫畫的風格,倒是學到了他們認真的態度,現在叫作“工匠精神”,具體到繪畫上就是一張畫不要輕易結束,要不斷求索,精益求精。可以說,日本藝術界對傳統繪畫藝術的精神、態度,對我的觸動很大,而不是技法上的。
《新民周刊》:回國后,您開始執教于上海大學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在帶領學生臨摹、寫生、創作的過程中,您自己的作品也發生了變化。從青、藍、綠色為主的“江南時期”走進了以黃、紅、赭色為主的“黃土時期”。
樂震文:1990年代回國之后,我開始大量觀察生活,畫城市風景,還沒建好的延安路高架、城市高樓、電話亭都畫過,這些題材現在被叫做“城市水墨”,但當時鮮有人畫。
我覺得畫家不要框死自己,要“不擇手段”地把打動自己的東西呈現出來。在此期間,我比較多畫的是江南山水,也得到了一定認可。但到1990年代末我在上大美院帶畢業班寫生,去了黃土高原,山西、陜西、內蒙……一路走去,與平時看到的山水截然不同,一開始也犯怵,這怎么畫?半個多月下來,逐漸摸索出來,不斷看,不斷畫,不斷拍照,回來就畫了一批作品。在畫上,我把習慣性的筆法都拿掉了,代之以短線條的疊加,通過渲染,表達黃土地的厚重感。恰好我那時在研究清代畫家龔賢的作品,于是把兩者結合了起來。這樣的鋪排、組合,畫得很難,也很累,但引起了不小的關注。我自己也覺得畫這種畫很有勁,至少沒有第二個人畫成這樣。可以說,通過寫生與創作,我逐漸理解了“畫畫要有生命”這句話,在黃土中的生長出的四五棵樹,兩三間房,一條小溪就是生命……我畫的“北方山水”也是大山大水里小點景。這也構成了我繪畫的一種新形式。
《新民周刊》:人生度過了一甲子,藝術生涯也走過了幾十年,回顧您的創作求索之路,您對于山水畫藝術的追求是什么?
樂震文:我的追求就是,畫任何一幅畫,都要有畫外之意,內心之言。要逼著自己追求畫外的東西。比如畫一塊石頭,如果能賦予它畫外的東西,境界、氣氛,畫面的神秘性……思考到這樣的程度,就能畫出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山水會有習慣性,會被用筆帶過去,但如果能給予畫更多的內涵,就會不斷創新,吸引觀眾。程十發先生在“海平線”畫展上曾經表揚過我,他看了我的畫說:“樂震文畫得好。一般的畫里,山會畫得像三夾板,沒有前后關系,但他畫出了前后關系,他的山是有深度的。”我想,程先生所說的深度,就是指畫外的東西。另外,我對于畫面空白的地方很當心,哪怕是留白,也要讓觀眾看出你表達的是什么,所謂的虛實,虛的東西也很重要。所以我特別注重畫云、霧、煙靄、水,因為留白也要賦予內涵,要有厚度。
山水畫有特殊性,它不牽涉到教化作用,而是一種修養,畫家到了一定程度,就會表現出來。我覺得這與技術無關,與修養有關,胸懷、善惡、道德、品位等等,都是修養。
借傳統山水之心,
觀當下萬千氣象
古老的中國畫藝術傳承、發展到今天,日趨風格的多元化走向。同時,很多人一談到國畫的現代化,就以為是傳統的失卻,這或許是一種誤讀。縱觀樂震文的繪畫藝術,傳統筆墨,現代構成,清新用色與淡墨渲染,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現代感絕對不是純粹西方式的,而與中國傳統相依相存,畫出了時代性與獨特性。特別是他作品中所表達的意趣,歸根到底還是一個“雅”字。這也是中國山水畫非常重要的境界,寧靜、雅致、深邃、幽遠,成就了一種山水精神,一股君子之風。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您在畫中特別注重養育山水精神。讓山水的精神在時空調遣、歷史敘述和大自然的組合中表達得時而坦露、時而含蓄、時而躍然紙上、時而隱匿于煙云漫涌之中。然而,不管是畫得顯山露水、層巒疊嶂,還是云遮霧障、山色蒼茫,山水精神依然蕩漾,人文精神依然清晰。
樂震文:的確,近年來,我特別希望在作品中加強對中國山水畫的理性梳理,在追求筆墨精致的基礎上關注“經典生成”,在強調局部深入的同時更注重宏觀駕馭,要進行筆墨、構成、色彩、節奏、韻味、意境的綜合思考與實踐,增長繪畫發展的文化原動力,更要傾力于內涵因素的構建。既守望筆墨的精神家園和丹青的民族自豪,又在積極嘗試用新的藝術語匯解讀歷史、吸納經典、展示文明、拒絕浮躁。讓中國畫以更純真的藝術精神留駐筆墨,讓山水、花鳥畫以更智慧的方式走進大眾。
《新民周刊》:欣賞您的作品,發現一個顯著的特點,在扎實的傳統筆墨基礎上,您特別注重對自然山水的寫生。不僅如此,您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全景式構圖,而是深入山川內部,注重細節的刻畫,一樹一石,煙靄云霧,甚至留白,都十分講究。
樂震文:有時候看傳統的畫,有臨摹的沖動。但傳統那么經典的東西,畢竟是人家的東西,如今我們的社會發展了,身在其中,沒有辦法擁有當年那些畫者的心境了。我試想,不妨用另一種眼光去觀察,借傳統山水之心,觀當下萬千氣象。比如,某一個部分風景打動你的時候,把打動你那部分畫出來,一棵樹擋住一棟房,旁邊還一條曲徑,山環水繞,碧溪潺潺……風景里的筆墨、濃淡、空間、疏密,正是一石一峰的堅挺,讓整幅山水畫的氣脈相通;正是一樹一草的相守,讓整幅山水畫的情懷感人——寫生中如果還不去體會,心中的山水就會淪為了概念的山水。
我對于山水寫生的追求,源于年輕時的想法。那時很年輕,一直想動腦筋形成自己的繪畫風格,可怎么都不成功。最后只好老老實實回到傳統,去仔細分析一些前輩大師、老先生們的成功經驗,特別是李可染、傅抱石兩位,我發現他們都是從寫生里來的。于是就有了外出寫生的愿望,記得那時一出門就是兩個月,但真的很有效果。一開始束手無策,完全不知道怎么畫,時間長了,有了畫畫、思考,甚至與古人作品對比的時間,于是漸漸找到了門道。
當時我們是沿著長江一帶,一路畫下去,到了三峽都不坐船,全靠走,一路走一路畫,看了很多如今再也難見的美麗風景。峨眉山、青城山、樂山、九寨溝……真的是發瘋一樣地畫,先是鋼筆,后是毛筆,走的是李可染的路子。條件雖然很艱苦,但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開心。寫生越來越多了,就不再是以畫得像不像為目標了,而是通過描摹對象,把我的追求畫出來。比如我喜歡畫山路,通過寫生去研究透了,畫著畫著,自己的風格自然而然就這樣流露出來了。
《新民周刊》:轟轟烈烈的畫展取得了圓滿成功,但人生的全新探索還剛剛開啟。在今后的歲月中,您有著怎樣的打算與計劃?
樂震文:與老先生相比,現在是中國畫家最好時代,60歲對我而言也是新的起點,我想將來為“祖國山川立傳” ,可能會幾年選一座山,像當初古人深入山區一樣,除風景之外,深入了解山中的人文、生活習慣、當地風俗,因地制宜畫出帶有深度的寫生和創作,回饋時代,回報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