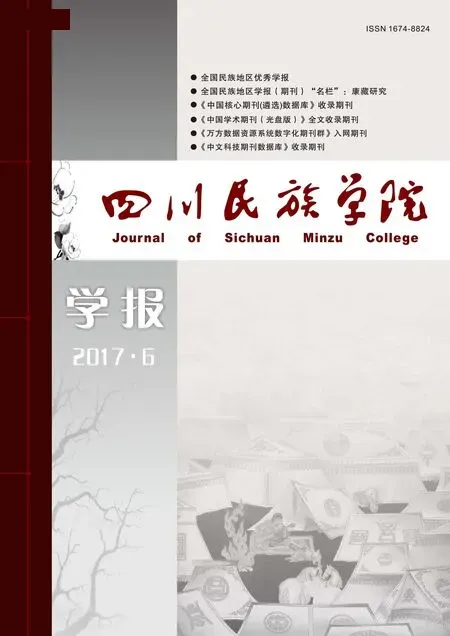教育人類學視野下的熱貢六月會教育價值探析
卓么措
熱貢,即現在的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 “熱貢,宋時譯為“一公”,亦譯作“一公城”。熱貢地區的范圍一般有不同的解釋,廣義的熱貢,包括青海的循化(及原屬循化的今甘肅夏河的一部分)、貴德、同德和貴南等地部分地區;狹義的熱貢僅指隆務河流域。[1]”現在,熱貢作為一個地理名稱,其范圍被公認為指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
熱貢六月會藏語稱為“周貝魯若”,意為“六月歌舞”,是隆務河流域藏族、土族村莊中盛行的大型民間祭祀活動,參與的村莊多達五十多個,定期于每年的農歷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舉行。主要通過拉則①祭、煨桑祭、歌舞祭、血祭等祭祀方式,敬獻神靈,祈求平安、福瑞、豐收,娛神又娛人。其大眾參與性與活動豐富性在全藏區都是獨一無二的,千百年來歷經滄桑變遷,依舊以蓬勃的生命力活躍在當地人民的生活中。2006年熱貢六月會入選民俗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一、祭祀儀式的主要活動
筆者在熱貢考察時,有幸參加了四合吉、郭麻日、森格雄、脫加四個村子的六月會。每個村子的六月會活動都各有特色,但基本的活動程序大多一致,現在按照時間順序,將熱貢六月會中的主要活動作一介紹。
第一步請神儀式,六月會正式開始的前一天,村莊里的眾男性在拉哇(藏語,神人的意思)的帶領下,到村子里的拉康(藏語,神廟的意思),四個年輕人把放置有本村的保護神的唐卡或雕塑的神轎扛出來,走村串戶,為村民祈福驅災。六月會上各個村子的神轎中供奉的神靈各不一樣,既有藏區的山神阿米夏瓊、阿米瑪沁等,還有漢地的二郎神、文昌帝君等,多種民族、宗教的元素在同一儀式中融為一體,充分體現了多元文化在熱貢地區的和諧共生。第二步拉則祭,六月會正式開始的第一天清晨,村子里的男子盛裝列隊、敲鑼打鼓、浩浩蕩蕩前往插在村子后山上的拉則,到了半山坡拉則處,人們煨起桑,用桑煙凈化木質的箭和矛。為了預示福瑞把羊毛纏繞在箭的頂端并抹上酥油。將拉則垛里已斷損的拉則取出,將新的拉則插進去,再往縫隙里插入枝頭綁有羊毛的樺樹枝。目前在藏區廣為普遍的拉則與藏族男性崇拜、尚武的民族精神與藏區先民的征戰歷史與軍事文化息息相關。第三步煨桑祭,村子里前往會場的小路上,人流不絕,人們紛紛端來供品,一盤盤、一籃籃,不停地往煨桑池中加著蒼翠的柏樹枝、酥油、青稞炒面、糖果、拋灑白酒……請神享用,很快堆成了一座小山。第四步歌舞祭,六月會從頭到尾貫穿歌舞祭祀表演,在不同村莊種類、內涵各不相同。主要分為“拉什則”(神舞)、“勒什則”(龍舞)和“莫什則”(軍舞)三大類。無論表演哪一種舞蹈之前,都要由拉哇念經,禱告請神,人們在舞蹈前都要恭恭敬敬地煨桑拜神。每一種舞蹈就是一道道獻給神的賞心悅目的供品,請眾神品嘗、享受。用敲擊銅鑼和單面羊皮鼓的聲音伴奏,在舞蹈過程中不間斷穿插有煨桑、獻供品、滑稽幽默小品表演、插口扦、插背扦、開紅山等活動。第五步血祭,在祭祀活動中,人們用自己的身體獻祭,以表示對神靈虔誠的崇敬的一種祭祀行為,是祭祀的最高境界。在熱貢六月會上最有代表性的血祭就是插口釬、插背釬和開紅山三種。開紅山是血祭的最高潮,拉哇用刀子將男性舞蹈者中的部分人的額頭劃破,鮮血不斷外流,舞蹈者任憑鮮血順著臉龐流下,在幾近癲狂的狀態下自由舞蹈,用自己的血虔誠地祭祀山神,以博其悅。涂爾干在考察阿蘭達人的儀式時總結道:“人用自己的血以及其中的神秘胚芽來保證圖騰物種生生不息……在阿蘭達,血似乎在儀式中起了主導作用。”[2]在熱貢六月會中,血也是用自己身體獻祭的最高境界,這個時候人和神的距離拉近了,人們的舞蹈比其他時候更加的狂熱、奔放、舒展,他們似乎看到了神在看著他們微笑。
二、祭祀儀式的結構分析
(一)場地
1.東
東面放置有從森格雄拉康中請出的神轎,神轎用翠綠的柳樹枝、五彩的綢緞、哈達裝飾,轎內供有森格雄的山神達加本森的唐卡畫像,即阿米武然、阿米木洪(二郎神)、阿米尤拉(文昌公)。神轎前面有一長桌,上面擺滿了村民敬獻的各種供品。靠著長桌,立有一幅看上去年代久遠的唐卡,上面畫的依然為達加本森,每年六月會村民都會把這幅唐卡從拉康請出來,參與到六月會的每一項活動中,去每戶村民家祈福,男子列隊去山上祭祀拉則,男子跳神舞時,人們都會高舉著唐卡。寓意著山神親臨會場,和人民一起歡舞、共娛共樂。
2.西
西面搭建了一個較為簡易的帳篷,只有立柱和頂棚,可以避免被高原上熾熱的太陽光曬傷。村子里較為年長的男子們三五成群盤腿坐在帳篷下,一邊聊天一邊喝酒一邊觀看歌舞表演。森格雄被譽為“藏族畫鄉”,村子里的男子各個都是繪制唐卡的高手,一般家里的農活和雜活都由婦女來做,男子則專注于唐卡的制作。家庭的收入多半來自繪制唐卡,男子的地位較高,在家中最有的威望,這點在六月會會場上的座位安排上就可以看出。
3.南、北
南面和北面為婦女和小孩的位置,她們大多從家中帶來小木凳。六月會是祭祀山神的盛會,也是女子們精心裝扮展示美麗和自信的機會。“不到六月會不穿綢緞顯耀,不到春節不將美食享用。”這句流傳在隆務河流域的諺語,充分表達了人們對六月會的重視和期盼。孩子們都更喜歡在媽媽身邊,除了看歌舞,他們更熱衷于要零花錢買各種小吃,對孩子們來說,六月會就像過年一樣熱鬧。他們在會場上來回奔跑,感受著六月會的濃郁氛圍,接受著本民族文化的點滴熏陶。

圖1 森格雄六月會上的會場安排
(二)人員
1.拉哇
拉哇,為藏語,意為神人。熱貢地區舉行六月會的每個村莊都有一到兩位拉哇。拉哇被認為是人與神的溝通者,能使神降臨附體,代神言事。在整個六月會祭祀活動中扮演著主持人、領祭人等特殊的角色。拉哇不是藏傳佛教的神職人員,因此他的生活完全是世俗化的。但祭祀活動開始前幾日,拉哇必須保持身體潔凈,不能接觸女性,并要到寺院里接受活佛們的洗禮,舉行誦經祈禱儀式。拉哇是整個六月會活動上的靈魂人物,祭祀活動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事必躬親,毫不懈怠。包括帶領眾人走村串戶的請神儀式,列隊到山頂上的拉則祭,會場上歌舞祭的領跳,不間斷的給神靈敬獻供品,拋灑酸奶、牛奶、白酒、煨桑。甚至連幫舞蹈者糾正舞蹈動作,整理衣衫,及村民的是否按時就位及遲到早退等細節也都在他所關注的范圍之內。祭祀活動的全民參與、秩序井然、規模壯觀是拉哇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2.舞蹈者
在六月會上參與舞蹈表演的大多為中年及以下男子和年輕未婚的女子。在每個村莊的六月會歌舞表演中,都可以看到幾歲一直到十幾歲的孩子都冒著酷暑參與到了歌舞表演中。在他們一張張稚嫩的臉上,似乎也能讀出對神靈的無限崇敬。民族文化的就是這樣潤物細無聲般地在人們的生活中,在民俗活動中,在祭祀儀式中做一代代地接力棒似的傳承。
3.觀眾
每年的農歷六月中下旬,地里的小麥、青稞還未成熟,隆務河流域的各個村莊正好處于閑暇時期。這個時間段也正好是學校放暑假的時候,村子里的小學生、中學生、乃至于在外地讀書的大學生都放假在家。因此,熱貢地區的六月會上,全體村民都自覺積極地參與到整個活動中。那些在外地打工或者城里工作的也大多迫不及待地趕回來參加一年一度的六月會,六月會上與家人團圓,和與兒時的伙伴歡聚是他們不管離家多遠的牽掛。
三、祭祀儀式的教育價值
熱貢六月會作為一種在熱貢地區極為盛行的民間祭祀儀式,其整個儀式中的活動及儀式結構蘊含了當地人處理人與神、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獨特價值取向。體現了民族認同的維系與凝聚、民族文化的宣揚與傳承、社會公德的規范與培育等教育價值。
(一)民族凝聚力的維系與增強
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在分析胞族間的紐帶聯系時指出,胞族間的團結與聯系,一是通婚,二是共同的宗教儀式。[3]在熱貢的六月會上,你就能清晰地感受到這種共同的宗教祭祀儀式產生的強大民族凝聚力。據森格雄的村民說,“他們的祖先是來自西藏藏科地方的的“吉果那吾”,他們是吐蕃時期在熱貢地區駐扎的部隊中留下來在本地安家落戶的一支。在森格雄的六月會上,森格雄上下莊和同處隆務河東岸的霍爾加、加倉麻四個村莊要一起跳,因為“霍爾加”以下一直到“頭莫”以上,都屬于“吉果那吾”,在遠古時期,需征戰出兵,是四個莊子一起出兵,如今跳六月會也一起跳。在六月會期間,在每天下午跳神舞的時候,領舞者要給全村人大聲說:“霍爾加”到“頭莫”地方的人,力量無窮,穩固如山,凝聚如海。出門在外個個都是英雄。”*受訪者:森格雄下莊 西合道(男,64歲,國家工藝美術大師);訪談時間:2010年8月5日下午;地點:森格雄六月會會場。這些吉利的話使村民們倍受鼓舞,大家一起高聲呼叫以示響應。內心深處對來年的生活更加充滿了希望。根據年都乎老人講,每年的六月會上,土千戶都要講:“我們的祖先是從東方來的,是皇帝派來守衛這里的。……這里是皇家的土地,是霍爾家的土地,好好的把草拔干凈……”[4]在隆務河流域,歷史上有這種族源淵源關系的村莊,在六月會上,各村的舞隊都會在拉哇的帶領下互相去別的村子的會場上串演,屆時都會被作為貴賓熱情接待。以六月會為精神紐帶,村子間的相互拜會及激勵人心的語言,堅定了他們團結一心、互幫互助的族群意識,具有維護部落情感、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教育價值。
(二)民族身份的標識與民族認同的強化
民族認同既包括對自己民族身份的認同和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也包括對他民族文化的認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體的成員將自己和他人歸屬于同一個民族,并對這個民族的包括價值取向、風俗習慣等在內的文化持親近態度。“文化的認同或民族的認同其實就是弄清自己,……而要認識自己,就需自別他者,就需在區別他者中認識自己,這便是所謂的'identification'。作為一個民族的主體性,認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由內向外的認同,而是一個民族自己的內部反思,找準一個民族從哪里來往哪里去,現在的主體精神是什么,在這樣的時代這一點尤其重要”[5]在熱貢六月會上,全體村民都以高度的熱情參與進來,年輕人是六月會的主力軍,他們往往都是舞隊成員,老人和孩子是他們忠實的觀眾,這種全民參與本身就是民族認同的一種外在體現。同時熱貢六月會也是一個展示民族文化的平臺,整個會場處處彰顯著本民族文化符號,神轎、唐卡、煨桑池、白海螺、羊皮鼓、哈達、隆達、烤饃、酸奶、青稞酒等等舉不勝舉,通過這場全民參與的盛會,民族的語言、文字、服飾、藝術、信仰都得到了最淋漓盡致的展現和宣揚,這些文化符號明確標識著在場每個人的民族身份,潛移默化中如潤物細無聲般讓年輕人和小孩,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直觀的認識,這也是民族意識深層次積累復制的過程,具有強化民族認同的教育價值。
(三)民族文化的弘揚與傳承
熱貢藝術是藏傳佛教藝術在青海安多藏區扎根發芽的一支,2009年熱貢藝術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隆務河河畔的森格雄、郭麻日、尕沙日等幾個村莊是傳承熱貢藝術的主要陣地,尤其是森格雄被譽為“藏畫之鄉”,擅長唐卡繪制。在森格雄六月會上自始至終都有唐卡的隆重出場,會場的東面的神轎中安放著村子保護神的唐卡畫像,神轎旁邊立著繪制有森格雄地方山神“達加本森”的唐卡,唐卡前方的長桌上擺滿了敬獻給山神的精美供品。他們是六月會場上的真正主角,山神唐卡畫像代表著山神真實蒞臨到了人們中間,接受人們的供養,觀看人們的歌舞表演,參與到了六月會的每一項活動。神轎對面會場西面,是成年男子的座位,這樣的安排充分顯示出對有成就男子的尊重,他們往往是繪制唐卡的高手,這無形之中對在場的年輕唐卡學徒也是個很好的激勵,他們也渴望像老畫師一樣取得成就,得到全村人的尊敬和愛戴。而只有靜下心、堅持每天刻苦勤練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唐卡畫師。可見,民族文化往往通過民俗、宗教等集體活動悄無聲息地代代傳承。除了本民族成員,熱貢六月會以獨特的魅力吸引著來自國內外的大批游客,這些絢麗多彩、獨具特色的文化符號,通過他們的鏡頭和即時通訊平臺被廣泛展示、傳播。
(四)社會公德的規范與培育
六月會進行到下午,在莊嚴肅穆的神舞表演之后,為了調節大家的情緒,會穿插一些即興小品表演。為村民自編自演,每個村子每一年的表現形式和題材內容各不相同,選題源自村民的現實生活并緊扣時代的發展變化,這樣就使民俗活動具有獨特的社會性功能。多用詼諧夸張的表現手段揭露社會不良現象,多為村子里的真人、真事。如:村子里的有些男青年不務正業、聚眾賭博的惡習;有些年輕的小兩口擯棄優良傳統,不孝敬父母的現象;有些男子拋棄老婆,在外面另覓新歡的現象,都可以成為即興小品所表現的內容。夸張的動作和人物造型,詼諧幽默的語言令全村人開懷大笑。在全村人都在場的特殊公共場域中,這些不良事件的當事人面紅耳赤,恨不得鉆到地縫里,對自己的行為愧疚不已。同時對所有在場者也具有生動的警示作用,讓人們明白什么是善與惡、是與非、榮與辱。貶惡揚善,提倡人們孝敬父母、鄰里團結、夫妻和睦。樹立了集體遵循的道德觀、價值觀。并對每個人以后的行為舉止也起著積極的約束作用。可見六月會中的所有一系列活動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傳統所規定的一整套行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動,這類活動經常被功能性地解釋為在特定群體或文化中溝通( 人與神之間、人與人之間) 、過渡( 社會類別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 、強化秩序及整合社會的方式”[6],對于規范全體村民的社會行為和道德意識具有重要的教育價值。
四、對民族學校教育的幾點啟示
目前我國少數民族現代學校教育的發展模式可概括為“模仿或照搬內地發達地區的教育發展模式”[7],又稱為“追趕式”“趕超式”。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當前一切以追逐經濟利益為目標導向的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指標亦成了衡量教育發展的風向標,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的教育發展模式,自然就成了全國各地教育發展模式的標桿。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地區的教育發展向發達地區看齊,照搬發達地區的教育經驗和模式,就成了縮短民族地區和內地發達地區教育發展水平的差距的主要途徑。這種功利化、狹隘化教育目標和考核標準,不但會破壞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還會產出沒有文化根脈的“邊緣人”,他們游離在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之間,無法融入主流社會,又無法回歸民族社會,將會帶來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缺失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反觀藏族民間祭祀儀式所具有的豐富文化內涵和多元教育價值,需要我們反思當前民族地區現代學校教育面臨的現實性困境,找到應對策略。
(一)民族教育的根基在于民族文化
民族地區現代學校教育的迅速崛起,強調現代學校教育的優越性而忽視了民族教育中的多元文化特性,導致民族傳統教育的式微。我國的很多少數民族,如藏族、回族、侗族、彝族都有扎根于本民族文化的傳統教育,藏族的寺院教育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藏族教育發展史上,寺院教育曾是主要的教育形式。“千百年來,藏族地區曾用寺院教育代替社會中的學校教育,寺院即是學校,喇嘛就是教師,佛教經典就是教材”。[8]藏區數量巨大的寺院就是各地的教育中心,“據不完全統計,解放時全國有藏傳佛教寺廟五千余座。”[9]1958年的宗教改革使藏族寺院教育遭受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寺院紛紛關門,僧人被迫還俗,寺院的教育中心地位漸漸被外來的現代學校教育取代。
民族教育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是豐富、多樣和立體的,可謂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藏族民間祭祀儀式及其教育功能的分析,向我們生動展示了一個民族獨特的社會文化生活在民族成員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因此,從事民族教育的研究者需要充分認識到,民族教育不僅僅只是學校教育,它還存在于學校外,存在于人類生活的每一處。被譽為比較教育學因素分析時代開創者的英國比較教育學家薩德勒(Sadler)早在上世紀初便已指出,校外的事情比校內的事情更為重要,并且它支配和說明校內的事情。少數民族現代學校教育是代表主流文化的年輕外來產物,只是少數民族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教育研究需要更加寬廣的研究視角,突破學校教育的圍墻,進入生活。“民族學校教育必須從民族其他方面的教育經驗中汲取必需的養分,最終使外發的現代教育系統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深深地扎下根,成為民族自己的教育。”[10]少數民族地區要辦出有自己特色的教育,必須扎根于自己博大精深、獨特的民族文化,需要充分考慮學習主體的多樣性需求和反映出民族文化的豐富性,這才是我們民族教育中核心的問題!民族教育的根在民族文化,多元文化是我國少數民族教育的基本特征。
(二)民族教育的功能在于傳承民族文化
少數民族現代學校教育中課程設置、課程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價、師資建設具有顯著的趨同化傾向,強調各個地區教育發展的共性而忽視了其各自的獨特性,這直接導致了民族地區學校教育以弘揚與傳承主流文化為主,強調了主流文化的傳承忽視了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幫助少數民族學生提升適應主流社會生活的能力,認同主流文化并融入主流社會是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學校教育在傳播主流文化的同時,并沒有如人們所預期的承擔起傳承民族傳統文化的功能,導致學校教育與民族社區、學校教育與民族傳統文化的割裂,學校教育成為民族傳統社區中的一片“文化孤島”。
“教育不始于現代民族學校的創立,這一點很容易被證明。否則,我們無法解釋一個民族的文化怎樣得以傳承、得以發展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不少民族早在現代民族學校教育系統在民族地區創立、推行之前就有了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而傳承和創造這些文化只能是與其民族文化相適應的民族教育。”[10]民族文化的傳承需要相應的教育來保證,而這種教育必須是能夠與民族文化共生的教育,只有這樣的共生教育才能起到傳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因此,民族教育應該充分關注到民族文化的多元特性,構建與多元民族文化相對用的學校教育機制,以便更好地發揮民族教育傳承和促進民族文化的功能。
(三)民族教育的價值在于促進人的發展
應對少數民族教育落后的現狀,學者們大多給出了政策傾斜、經費投入、扶持支援、硬件建設、教師培訓等應對策略。民族教育的發展寄希望于資金的投入和學校基礎設施的建設,強調硬件建設而忽視了學生的發展。誠然學校的基礎設施建設對于學校發展至關重要,但是如果在學校硬件建設過程中出現“重物不重人”“只見硬件不見其余”的問題,教學設備再先進、教學環境再優越,教學效果、教育水平一樣無法保障。
在民族教育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硬件建設是基礎、手段和途徑,其根本目的在于實現教育的真正價值。需要我們認識到教育是一個生命過程,教育的本質在于提升人的生命質量與價值,使生于斯長于斯的人們,在當地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中人性得到和諧發展。人是教育的出發點,也是教育的最終目的,受教育是人生存的需要,“只有以人為本,在一個由天地系統演化所構成的時空關系中發展具有適應性生存能力的人,才是教育的終極關懷,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時代背景下教育之道的回歸于價值重構。”[11]因此,必須從人的生存需要與人的發展的角度來界定民族教育的價值。民族成員需要教育來獲得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和更優質的生存質量,正如我國教育學家陶行知指出教育是“供給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們就教什么。是那樣的生活,就是那樣的教育”。[15]
[1]止貢巴·貢卻丹巴然杰著.吳均等譯.安多政教史[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82年,p292
[2]涂爾干著.渠東等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p437-438
[3]摩爾根.古代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7年,p237-238
[4]羋一之.同仁土族考察報告——四寨子(五屯)的民族歷史 [J].青海民族研究(內部),1985年,p150
[5]張詩亞.強化民族認同——數碼時代的文化選擇[M].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2005年,p53
[6]郭于華.儀式與社會變遷[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p1
[7]王鑒.我國少數民族教育跨越式發展戰略研究 [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p102
[8]周潤年、劉洪記.中國藏族寺院教育[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8年,p1
[9]李冀城.藏傳佛教[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p1
[10]張詩亞.祭壇與講壇——西南民族宗教教育比較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p4、p90
[11]倪勝利、張詩亞.回歸教育之道[J].中國教育學刊,2006年第9期,p5
[1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 卷)[M].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p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