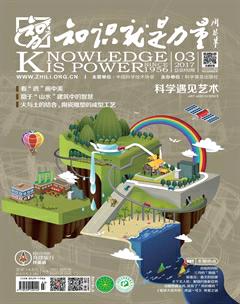湯斯:“幸運的失敗”引領成功之路
尹傳紅
激光發明人之一、諾貝爾獎得主查爾斯·湯斯的故事啟發我們:成功的路徑不止一條。具備各種理想的條件或環境固然很好,但即便沒有也不必泄氣,更不能自暴自棄,而是要審時度勢、揚長避短,努力闖出一條適合于自己發展的成功之路。
課余的求知探奇
查爾斯·湯斯一家并不富裕,經營農場的父親早年學習法律,是一位業余的博物學家;母親亦頗有知識——她修習了當地女子學院提供的每一門課程,然后上了通信課。他們的雙親對于勤做禮拜、行為得體和學校功課要求嚴格,但同時也很支持孩子們課余的求知探奇,他們是把教育當作一種自然和自動的義務來看待的。有一天,父親特意從一位鐘表商人租來的店鋪里,把一些壞了的時鐘帶回家去,讓湯斯和哥哥亨利鼓搗,為的是考一考哥倆能不能自己動手把它們修好,或者干脆拆出零件隨便做什么用。
就像他最早體驗到的一些野外活動那樣,湯斯把科學看作是探究宇宙的方式。他最初的玩伴和朋友是亨利和表兄弟們,以及在他們家周圍的各種蜥蜴、雀鳥、石塊和昆蟲。亨利天生喜歡生物學,他那種熱情最初也高度感染了湯斯。他們在室外建起了一個大的魚池,養著魚兒、蝌蚪和烏龜。他們的父母最終也容忍并習慣于在房子外面有一些養在籠子里的蛇,在孩子們的寢室里收藏著一些用來喂養毛蟲的葉片——孩子們想看個究竟:這些毛蟲如何變成蛹而且在最后羽化成蝴蝶。
課余或假期,湯斯經常跟哥哥亨利去遠足和探險,而且總是留意觀察雀鳥、魚類和其他各種生靈。他還喜歡翻開石塊,看看那底下有沒有在別處很難看得到的生物。有一年夏天,湯斯在祖母家附近的河里網到一條色彩斑斕的小魚。它看起來像是一種米諾魚,但在那些魚類的標準圖譜里都找不到這樣特別的一種。于是湯斯把它泡在甲醛里,寄去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斯米孫研究所,附上一封信問那里的人能不能鑒別它。后來他收到一封回信,被告知這條魚或者是一個新種,或者是先前不知道的一個雜種。信中還希望他抓到更多的稀奇的魚。這件事讓湯斯激動不已,久久不能忘懷。
了解事物是怎樣運作的
湯斯的人生目標并不是一開始就非常確定的。起初他跟哥哥亨利一樣,對生物學很有興趣。但感覺到亨利對生物學的興趣比他強得多,他就下意識地放棄了(亨利后來果真成了一名昆蟲學家)。而湯斯盡管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也仍然對生物學情有獨鐘。
排在生物學之后的數學,是湯斯最初的一個優先選擇,這可能由于教他數學的那位優秀教師是他遠房親戚的緣故。可湯斯最終還是選擇了物理學。在富爾曼大學學第一門物理學課程時,事情變得明朗了。物理學以它本身所具有的發揮數學邏輯的豐富資源,以及由于它看來同現實世界的聯系比數學更加緊密而吸引了湯斯。
雖然念的不是名牌大學,但湯斯學習非常認真、刻苦。“我清楚地記得在那個暑假里,我來到祖母在藍嶺山脈的小屋附近,坐在一塊覆蓋著青苔的石塊上,眺望著一條溪流。在我的膝蓋上攤著一本打開的書,書頁翻到了狹義相對論那一章,我非常吃驚地確信我發現了愛因斯坦在他的邏輯中犯了一個錯誤。在用過午飯,度過了精神亢奮的幾個鐘頭之后,我又回到那個地方,坐下來再次打開了書本。我終于判定情況并非如此,我弄錯了,而愛因斯坦的推導終究是正確的。”
盡管發生了那場誤會,但鬧誤會的那一刻真的讓湯斯激動不已。他被愛因斯坦僅僅從幾個簡單的方程出發就得出的、關于世界的那樣深刻和奇妙的結論迷住了:為什么高速運動的時候時間必定變慢,物體的長度必定收縮而其質量必定增大?
富爾曼大學的教學很靈活——學生們可以到任何一個系選修那些特別出色的課程。這使得湯斯在那里既拿到了一個物理學的理科學士學位,又獲得了一個第二學位——現代語言學的文科學士學位。在那些日子里,湯斯還通過做家庭教師、照料博物館,以及為他家的農場銷售蘋果而賺了一點錢。他在1999年出版的自傳中寫道:“我總覺得富爾曼給了我一種極好的廣闊的經驗。”
謀求自己真正
想要的東西
1935年,湯斯從默默無聞的富爾曼大學畢業。他希望能夠繼續深造,可他沒能從他發出申請的幾所有名的大學得到任何獎學金或研究職位。在當時也不是太知名的杜克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后,他向幾所名牌大學寄去的讀博申請,竟然也都被拒絕了。
沮喪之時,湯斯做了一個孤注一擲的決定:在事先沒有得到助學金的情況下,到美國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學院讀博。后來他在自傳里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去加州理工學院對我而言是一種失敗——我沒能從自己首選的幾所研究生院得到財政資助。但那卻是使我終身受益的一場失敗,一場幸運的失敗,因為它迫使我直接去謀求我真正想要的東西。”
博士畢業后,找工作又成了一個難題。關于這段經歷,湯斯是這樣敘述的:當時他的目標是去一家學術機構,一個致力于了解事物本源進而理解事物的地方,而根本無意于幫助某些公司制造物件或賺取錢財。當時在基礎研究方面還不怎么出名的貝爾實驗室派人到加州理工學院招募畢業生時,湯斯的研究顧問斯密特教授向招募小組做了推薦,說了不少他的好話。可不久斯密特就接到一個電話,大意是說:湯斯那個家伙是怎么回事?這是我們看到過的最馬虎和最潦草的申請表了。他看來對此沒有什么誠意。“斯密特很快就打電話給我說,我最好還是認真對待這件事。也許部分是因為他為我好而做出的懇切請求,我得到了我的任命。”
在那之后不久,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湯斯也被迫放下物理學研究去從事與軍事相關的工程設計工作。他其實真不想干,這也正是他害怕在一所工業實驗室里會發生的事情。不過,工作尚在進行之中,湯斯就被那樣的一種挑戰性吸引住了。他所承接的任務中的協作和試驗,教會了他怎樣運作復雜的計劃。而他們參與研制的幾種雷達投彈和導航系統所涉及的原則性與啟發性思路,對于他后來的大部分研究經歷,包括脈澤和激光研制、開發,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8年,湯斯和他的同行(也是他妹夫)阿瑟·肖洛發現了一種神奇的現象:當他們將內光燈泡所發射的光照在一種稀土晶體上時,晶體的分子會發出鮮艷的、始終會聚在一起的強光。根據這一現象,他們提出了“激光原理”,即物質在受到與其分子固有振蕩頻率相同的能量激勵時,都會產生這種不發散的強光——激光。尋著這樣一些思路,湯斯從對微波波譜學的開創性研究出發,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臺微波激射器,進而發明了激光器。
激光的發明是20世紀的一項劃時代的成就,對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被稱為“最快的刀”、“最準的尺”、“最亮的光”,在醫學、軍事和工業上許多領域都有重要的應用。1964年,湯斯與蘇聯的兩位物理學家分享了該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沒有得到第一流大學的職位,沒有進入自己理想中的研究單位,對湯斯來說可謂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晚年回顧往事時他說:“誰也不能預知什么樣的失敗背后隱藏著真正的成功,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簡單地去做在當時看來還算對頭的事情。深思熟慮然后再走向失敗是愚不可及的!無論如何,知道這一點是很有用的,當你心里懷著失敗的感覺時,后來的結果卻可能是非常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