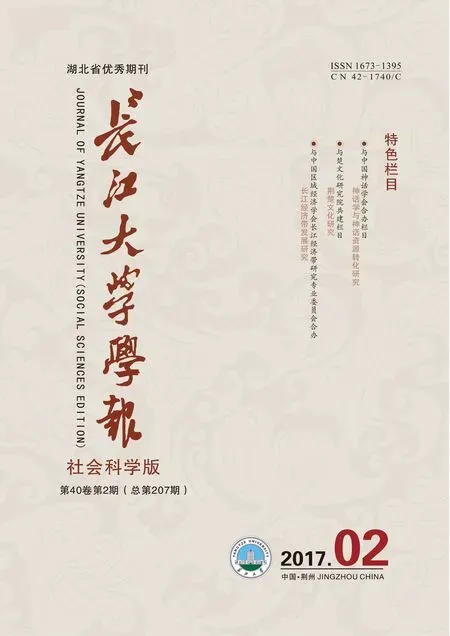施叔青小說中的女性書寫
盛開莉
(西北民族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
施叔青小說中的女性書寫
盛開莉
(西北民族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
施叔青小說中的女性群體,與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群體呈現出不同的特征:一面承受著來自家庭和婚姻的精神圍困,一面以出走的方式逃離。作者賦予這些女性以豐富的生命質地,改變了父權制話語下沉默的傳統女性形象,展現了女性獨特的生活經驗,對于女性的自我發現與生存拓展,具有一定的意義。
施叔青小說;圍困;出走;藝術結構
臺灣著名文學評論家施叔青的姐姐施淑,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施叔青的創作特點:“飛短流長成了藝術結構的特質。”[1](P2)毫無疑問,“飛短流長”指的是施叔青小說有著和張愛玲小說一樣的世俗化題材。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多為內囿沉默的,遭受凌辱壓抑和毀滅的女性。施叔青筆下的女人們,雖與張愛玲筆下的女人們一樣拘囿于家庭之中,但其命運和選擇卻有了新的可能。因此,揭示父權制家庭中女性受壓抑受迫害被奴役的現實,并試圖探尋女性的出路,就成為施叔青小說的重要主題。
一
“婚姻,是傳統社會指派給婦女的命運。直到今天,情形仍舊一樣,多數女子不是結了婚,便是結過婚,或準備結婚,或因未結婚而憂郁。”[2](P199)用西蒙·波娃的這句箴言來解釋大多數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命運,是極為貼切的。從張愛玲、蘇青到施叔青,雖經歷了歲月穿梭,世事變幻,女性的故事卻萬變不離其宗。施叔青繼承了女作家特有的立場,以寓言的語義化途徑,言說家中的天使被圍困的生存真相。被剝奪自由的婚姻或是情感狀態,及其所帶來的無力感和絕望虛無感,是施叔青小說里女性群體共通的生存狀態和感受。
施叔青小說對恩格斯有關父權家庭的理論總結——父權家庭將女性束縛于家庭中,做出了形象的闡釋。對這一本質的認識,是女性自我意識成熟的標志。當女作家從兩性關系入手,以顛覆父系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礎時,其寫作也就成為一種文本策略,具有了政治意義。在小說中,女作家以兩性關系為邏輯起點,袒露了房中的安琪兒的實際命運。在父權制意識形態下,女性是守護家庭的天使;而這聽上去美妙無比的稱謂,同時也成為遮蔽女性生存真相,模糊家庭權力關系的掩護。事實上,在溫馨的面具背后,家庭或許會呈現出一副壓抑囚禁女性身心的猙獰面孔。《困》中的丈夫像獄卒一樣冷漠,完全忽視了葉洽的情感需要,使葉洽成為一個對生命感到絕望的女人,最后在酗酒中,失去了對生活的感覺。《驀然回首》中的范秀美,像插翅難逃的蠅蝶,受困于無邊的黑暗里,看不到一絲可以逃遁的希望。在美國的她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逃回臺灣父親的家;但父親的家不僅沒有成為她避難的港灣,反而將她拼命往外推搡。無家可歸的范秀美只好求助于心理醫生,但心理醫生的冷漠與懷疑,卻逼得她想要發狂。在丈夫的家和父親的家,以及心理醫生所代表的社會合力構筑的森嚴壁壘下,絕望的范秀美走向了瘋狂。在這些作品中,家庭完全成為男性囚禁女性的場所,丈夫則成為迫害妻子的主謀,而瘋狂則是最仁慈的家庭中女性心靈空虛、精神萎縮的結果。《完美的丈夫》中的李素如同被判了終身監禁的囚徒,始終受困于婚姻的高墻里。《后街》中的朱勤是在大公司里打拼的獨立白領,年逾30而未嫁,在遇到蕭后,也同樣被困于后街。朱勤雖然沒有步入婚姻,但因為蕭對其身份的不予承認,她永遠也走不出后街。《尋》中的杜伊芳僅僅因為無法生育,就被丈夫打入冷宮,在無邊無際的冷漠里,如同死刑犯一般承受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
與張愛玲不同的是,施叔青小說里的部分女性人物打開了牢獄的大門,嘗試著進入社會公共領域。如果說,張愛玲作品呈現了女性的深層人格特征即內囿的話,那么,施叔青筆下的女性,則通過對不自由的反抗,以及對牢獄的逃離,呈現出與張愛玲筆下女性群體不同的特征,即對內囿的反抗。出走或者逃離,是施叔青中期小說中女性所普遍選擇的生存方式。《愫細怨》中的愫細,在發現丈夫有外遇后,不糾葛,不哭天搶地,而是坦然面對,主動選擇了離異,化身為精明強干的職場白領。《窯變》中的方月與姚芒的相識,緣于她對丈夫和婚姻的無望,而這本身就是對婚姻的逃離。隨后,當發現姚芒依然不能予她精神慰藉時,她再次選擇了出走,逃離了姚芒那個像博物館一樣的家。《票房》中的丁奎芳為了自己的藝術事業,放棄了丈夫和孩子,從大陸出走到香港。《困》中的葉洽,在發現丈夫無論怎樣都和自己是精神上的陌路人之后,選擇以酗酒的方式而獲得精神上的逃離。《常滿姨的一日》中的常滿姨,發現丈夫是個賭徒加嫖客之后,以出走的方式,從臺灣鄉下來到美國。這樣一個下層女傭,在以往的很多文學作品中,往往難以得到足夠的重視,而施叔青卻站在被人遺忘的角落,以敘述表層的若無其事,對其表達了令人動容的深層關懷。
二
女性出走,意味著走向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而與出走相伴的,則是女性精神內質的變化。因此,女性生命質地的豐富性,也成為作者在小說里所呈現的重要內容。在父權制文化模式的監禁下,女性長期內囿于家庭之中,被放逐在文化和知性的邊緣,沉默和貧乏是女性一直以來的標簽。“女性的沉默貧乏是女性心靈遭受壓抑的焦慮性表達。”[3](P4)女性長期被置于與男性代表的文明理性相對立的一面,被看作非理性、肉體和自然的代表。在男性文學作品中,長期以來,有知識的女性常常是令人厭惡的老學究、老處女。施叔青則通過一系列臺灣留學生婚姻小說和香港故事系列小說,以男性的沉默貧乏,反襯出女性的精神優越,呈現了女性豐富的心靈世界。
《愫細怨》中的愫細,是施叔青有意翻轉張愛玲作品中沉默貧乏的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留學美國的教育背景,使愫細以平等的精神價值,贏得了美國人狄克的愛情。與狄克離異后,她變身為德國公司獨當一面的設計主管。從婚姻里出局后,在父權制意識形態下,女性通常會遭到強有力的打擊,可是在愫細身上,離異所帶來的失敗感不僅全無痕跡,而且她還將這次生活的變故當作一次重生:“對新的自己凝視片刻……愫細恢復了她對自己的信心。”[4](P217)依憑職場復歸,愫細快速地重獲了對自我的認知與肯定。面對廣東鄉下來香港打拼的小老板洪俊興,愫細有著十足的優越感。她故意邀請洪俊興到她家里。發現書架上全是英文書后,“他抬起頭,和愫細挑戰的目光接觸,趕忙掉開去,訕訕的,臉都漲紅了。愫細有著目的得逞后的快樂”[4](P223)。愫細“譏笑他沒有邏輯觀念,缺乏學院訓練所說的話,永遠愚蠢可笑。憑著愫細起伏的情緒,洪俊興可以在一分鐘之內,從美妙的情人降至粗蠢的小老板”[4](P236)。愫細的教育背景、獨立的職業女性身份、富于智慧的談吐、有品位的生活,使得洪俊興只能暫時憑借物質來換取一點自信。洪俊興一廂情愿地以為,憑借物質,可以縮小他和愫細之間的距離;但最后,他還是在太過直白的物質換取中,被愫細徹底擊敗。而這一次,是因為愫細感覺到,洪俊興用物質威脅到了自己始終保有的精神優越感,故而她猛然抽身而退,捍衛了自己高傲的尊嚴,主動讓一場風花雪月戛然而止。傳統女性的蒼白貧乏,在愫細身上無跡可尋。愫細時時彰顯出強悍的個性,充沛的精神,豐富細膩的感情追求,獨立自主的人格。與之形成對比的,則是洪俊興的自卑、粗俗、乏味、謹小慎微。施叔青用女性話語,消解了父權制話語機制下傳統的二元對立模式: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物質,靈魂/肉體,社會/家庭。在父權制意識形態話語中,代表人類文明的男性,占據著社會公共領域,諸如政治、權力、軍事、科技等等;而女性則代表著相對低級的自然、肉體,隸屬于家庭領域。如此一來,在精神力量上,男性勢必高于女性,諸如沉默順從、無欲無求、精神貧乏,這些在男性身上可能被看作缺陷的品質,則被理所當然地看作女性的基本特征。但在《愫細怨》中,在與洪俊興的交往中,愫細不僅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且在精神層面上始終高于洪俊興。由此可見,女人的精神優越感,已成為該作品的敘事主線。而其小說《困》,也傳遞出同樣的意味。在小說中,葉洽的丈夫王溪山“是個極普通的人,有一顆極普通的心靈”[4](P121)。在作者的刻意強調和著力表現下,王溪山的普通,進而演化成無可救藥的乏味和平庸。比如,兩人在戀愛階段時的約會,談話內容乏善可陳,大半個晚上,統共沒講幾句話。靜默中的約會,尚可理解為此時無聲勝有聲;但當王溪山告訴倚在他肩頭的葉洽,他一個晚上都在數松山機場降落的飛機有多少架時,卻令人忍俊不禁。不僅如此,王溪山的住所也單調得索然無味,“客廳就像王溪山的人一樣,給人一種極貧乏的感覺,毫無情趣可言”[4](P122)。在精神上,王溪山無法與葉洽有任何共鳴相通之處。“你一直使我覺得自己一無所有”,王溪山在小說結尾處的悲鳴,讓人不自覺地想起了張愛玲筆下沉默貧乏的代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孟煙鸝,只是在施叔青的筆下,這一角色變成了男性。
曾有學者指出,在文學作品中,男性的魅力通常源于力量。這種力量既包括他對女性的征服和吸引力,也包括用武力統治世界,“而不是源于他自身某種豐富的、極富生命力的東西”[5](P234)。在優勝劣汰的商業社會里,男性的魅力常常源于他所占有的物質財富和社會資源,至于生命的豐富質地、精神層面的富有,則常常被認為是無用的東西而退居其次。施叔青卻在小說里有意展現這一層面:男性如果精神貧瘠,即便富可敵國,也無法讓女人真正折服。同時,作者又將作品中男性所缺失的豐富的生命質地,慷慨地贈予了女性。《窯變》中的方月,是個很有前途的女作家。在她眼里,闊綽的丈夫除了錢一無所有,富有的追求者就是只會用名牌包俘獲女人的獵艷高手。女性自我實現的愿望和對精神自由的渴望,使得她哪怕放棄男性給予的物質庇護,也要構筑自我精神家園——重新寫作。與小說里占有大量財富卻精神貧乏的男性相比,女性呈現出高人一等的精神力量。施淑認為,施叔青的作品“精力旺盛,血肉豐滿”,“這種在質地上的豐富、生命力,是可圈可點的”。[1](P2)這種質地上的豐富和生命力,無疑來自于她筆下的女性群體;而這種生命力的真正源泉,或許來自于她們對父權制意識形態下性別秩序的大膽僭越。《一夜游》里的雷貝嘉本是普通的公司職員,卻始終有著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愿望。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她斗膽向殖民地文化官員發起了攻勢。她有著強悍的主動進攻的精神,不甘心聽憑命運擺布的舉止,卻全無傳統女性柔順被動的一面。《情探》中的殷玫,雖然過著從一個男人到另一個男人的生活,但她有品位的裝扮,撐門面的作家頭銜,精明算計的手段,所有這一切,都很難讓人把她與那些沉默貧乏,只會肉體交易的傳統意義上的風塵女子相提并論。這些女性形象,如果以父權制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秩序來衡量的話,可能不會得到人們的肯定,因為她們對傳統性別制度所規定的女性氣質,如沉默、貞潔、柔順、犧牲等,常常并不認同,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她們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有了一種由被動變主動的氣勢和從容。這些女性形象,對于質疑父權制意識形態所規定的女性氣質,顯然有著積極的意義;對于女性沖破不公正的性別秩序所帶來的壓制,走向全面的個體解放,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三
女性主義批評家早就指出,女性有別于男性的人生經驗,勢必會影響到其對世界的認知及其思維模式;而女作家有異于男作家的思維模式,則直接影響到了其文本的藝術結構。自古以來,建功立業,開疆辟土,天然地成為男性的理想,故男性易于形成注重開拓與擴張的思維模式。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文學線性情節觀,即屬于吻合男性思維模式的文本結構觀。線性情節觀強調時間的連貫與情節的推進,注重結果與答案。女性長期生活于狹小的庭院之中,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勢必會影響到女性的思維方式,繼而對女作家的文本結構產生影響。施叔青的小說結構,就呈現為有別于線性情節觀的獨特格局。“施叔青的小說在形式上越來越走向一種分歧的結構。她的小說,在過完了青年期的夢魘階段后,經常是由一個可能的關注或激情的中心散文性地分歧出來。在這種敘述結構下,意念的發展或答案不是小說的重點。它的重點在熱熱鬧鬧的分歧本身,在它們之間的戲劇關系,以及與之呈現的問題,而這形成了她的小說在內容上的故事性的豐富和風格的多樣性。”[6](P2)情節的線性進展的確不是施叔青所喜好的,她甚至很少給小說以答案。男性小說的核心情節觀,是不斷探索新事物、新目標。在這一意義上,停滯是最大的敗筆。因“女性的思維過程更具關聯性,傾向于在相互的關系中考慮問題,在道德判斷方面更多地注入感情”[7](P28),所以施叔青的小說結尾多趨向于開放式,或者在某一個點上突然停止。
施淑曾從女性主義及精神分析角度,探討過施叔青作品中的禁錮與顛覆意識。她認為,施叔青作品中“濃烈矯情的象征,漫無節制的臆想,沒有出路的情節布局”,可以理解為“女作家對理性的、流麗的父權大敘述的質疑抗頡”。[8](P276)施叔青善于描繪龐大的人物群之間錯綜復雜的網狀關系,尤其擅長場景橫斷面式的鋪排。橫斷面意味著切斷了時間的綿延與流動序列,使時間停滯在一個點上,因而在形式上走向熱鬧的分歧本身。比如《票房》,從開頭到結尾,其場景都是上海票友聯誼會,就線性情節而言,幾無進展。小說四節猶如四幕戲,以從北京流落至香港的刀馬旦丁葵芳的期待開始,到她的最后被愚弄作結,展現了香港社會人們的勢利。小說從丁葵芳出發到另一個人物,再從那個人物回到丁葵芳,然后再以丁葵芳為基點,如蜘蛛織網般來回循環。作家著力刻畫了每一個出場人物的特征,準確而豐富,儼然舞臺指示。
“建立在女性的經驗和視野之上,施叔青的小說藝術不免于帶上被女性一向的社會角色所決定了的手工的性質。這個與日常事物和日常生活有著較直接和親密關系的藝術勞動,一方面使作品像日記一樣隱秘地、熱切地追逐著個人的生活;一方面產生了絮聒的,然而獨斷的全知敘寫觀點。”[6](P1)施叔青的小說藝術帶有女性社會角色所決定了的手工的性質,這顯然不是施淑的一己之見。其小說中將女性日常生活細節美學化的瑣碎描述,如時常不厭其煩地贅述沙發、餐桌、窗簾等室內陳設布置、服飾妝容等的搭配,以及意趣盎然地穿插的作者的審美趣味,使小說帶有濃厚綿密的敘述特征;而其所展現出的女性獨特的生活經驗,則無疑強化了其文本特色。
[1]施叔青.被顛倒了的世界再顛倒回來——《夾縫之間》自序[M].香港:香江出版社,1986.
[2](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3](美)艾萊恩·肖瓦爾特.婦女·瘋狂·英國文化[M].陳曉蘭,楊劍峰,譯.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
[4]施叔青.愫細怨[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
[5]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6]施淑.顛倒的世界[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7]陳曉蘭.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8.
[8]施叔青.施叔青集[M].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
責任編輯 韓璽吾 E-mail:shekeban@163.com
The Female Writing in Shi Shuqing’s Novels
ShengKaiIi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Nor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Lanzhou730030)
The female group in Shi Shuqing’s works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male group in Eileen Chang’s Novels:one side is under the spirit of the family and the marriage,and the way of "leaving".At the same time,the author gives women a rich texture of life,and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women in the patriarchal discourse.From this point of view,the creation of Shi Shuqing’s novels has a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women’s self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Shi Shuqing’s novels;siege;flee;artistic structure
2016-12-10
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YB019);西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重點項目(31920150139)
盛開莉(1980-),女,甘肅武威人,講師,碩士,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女性文學研究。
I207.42
A
1673-1395 (2017)02-005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