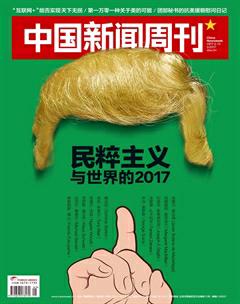團部秘書的抗美援朝慰問日記
彭總問我們:“你們希望不希望和啊?”有同志回答說:“希望和,我們大家都希望和平。”彭總笑了,他說:“我不希望和平,我愿做個‘戰爭販子,打下去,打垮它。”
1953年4月8日上午,丹東一所學校的操場上,176位20歲左右的年輕人身穿統一的灰色制服,披著土黃色斗篷式風雨衣,在寒風中整齊列隊,神情肅穆。
中午11點,赴朝慰問文藝工作團一團誓師大會準時開始。團長張云溪宣布:“出發!”176人登上大卡車,呼喊著口號,奔赴朝鮮。
此時,朝鮮戰爭已經進行到第4個年頭,曠日持久的停戰談判也進行了快兩年,三八線上處于膠著狀態。
慰問團一團團委會委員、團部秘書路奇也在其中。她的日記全程記下了這次慰問,這本日記成為經歷文革后她唯一保存下來的日記。27歲的她沒想到,自己竟然能親眼見證停戰的那一天。
入朝
晨5時50分到丹東。
下午聽我駐丹東空軍政治部王主任的報告。他說,三年來我們的空軍一天天在發展。去年全國人民熱烈地捐獻飛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例子,特別是文藝界常香玉一個人捐獻了一架飛機,給戰士們很大的鼓勵。
路奇的日記,開始于1953年3月18日。
慰問團全稱為赴朝慰問文藝工作團,成立于1953年年初,由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起。其中一團由北京和天津的劇團組成,西北區、華北區、華東區、中南區等大區的文藝單位則組成了其他分團。
出國門前,路奇奉命去沈陽為全團訂制了入朝裝備,包括襯衣、汗衫、褲衩、襪子、膠鞋、風鏡、口罩等。訂做制服時,她怕裁縫“吃布”,要求裁縫把衣服做得肥大一些,結果太肥了,大家穿著不太合身。
慰問團一團的任務是到志愿軍司令部、政治部、工兵指揮部、64軍駐地和朝鮮首都平壤演出,計劃演出130場。
根據要求,慰問團制訂了保密條例:絕不暴露本團及部隊番號、編制、行動方向等,不透露本人姓名和身份。對志愿軍的稱呼一律不加職務頭銜,不叫名字,只叫姓氏,特別是對首長。
4月8日,一團的車隊駛過了鴨綠江。
慰問團的路線是一條干線,從新義州,到定州,再到清川江。這是安全地帶,中國空軍的戰斗機活動多。安州、順州、承州是三個封鎖點,有敵機出沒。
與丹東隔江相望的新義州已經成了一片瓦礫,看不見一處完整的房子,只有斷壁殘垣。路奇的日記寫道:
一些朝鮮婦女和小孩在路上走著,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將往何處去。一路上常常遇見修路的人,也多半是婦女、老人和小孩,看不見青壯年。
由于敵機轟炸頻繁,車隊晝伏夜行。路上每隔一定距離就設置一個防空哨,由一個志愿軍戰士站在公路邊監視敵機。汽車經過時,若安全,就吹哨;若有敵機出現,就鳴槍。立即,汽車齊唰唰地滅燈,漆黑一片。
合唱團指揮金正平寫了一封給防空哨戰士的慰問短信,大家謄抄出很多份,連同一套背心、褲衩、毛巾、肥皂、布鞋捆在一起,每駛過一個防空哨,就投一捆到哨崗上,一邊喊著口號:“向志愿軍同志致敬,祖國人民問你們好!”
美國飛機經常會投下照明彈。中央實驗歌劇院的舞蹈演員李百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照明彈,“像兩百瓦的大燈泡”,恍如白晝,地面一覽無遺。飛機俯沖時巨大又刺耳的轟鳴聲,讓人感覺無處可逃。
慰問團幾次在過橋時遇到敵機。
按照志愿軍的要求,每輛卡車都選出了車長。一輛車坐15至21人,分成三列,整齊坐在背包上,坐車時不準睡覺。遇到突發情況,車長命令跳車。左右兩列從兩側翻跳出去,中間一列從后側跳下,幾秒鐘內疏散到15米開外。每人身上的土黃色斗篷式風雨衣解手時可方便遮擋,這時可用于偽裝。飛機去遠后再集合,清點人數報告。
司令部
4月10日早上,慰問團抵達了位于五圣山山洞里的志愿軍司令部。
這里原是一個年產18噸黃金的大金礦的坑道。洞口插著一些偽裝用的樹枝,洞子很深。洞中有很多鐘乳石,電燈一開,李百成覺得像寶石花一樣漂亮。
山洞寬約3米,右邊是通道,左邊是木板隔成的一間間小屋。沿著山洞走5分鐘,忽然燈火輝煌,這是一個可以容納800人的大石洞,被布置成了大禮堂。
慰問團被安排住進了小木屋。山洞潮濕陰冷,墻壁上總會滴滴答答地滲出泉水,睡久了關節會不舒服。
第二天晚上,彭德懷等志愿軍領導在大禮堂接見了慰問團和隨行記者。中央戲劇學院附屬歌舞劇院的舞劇編導叢兆桓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接見前傳達,彭總和志愿軍參謀長李達正在樓上下棋,要大家耐心等候。“首長下棋不是玩兒,下棋是運籌帷幄,是琢磨部隊怎么部署、怎么打,必有一場勝仗!”
終于等到彭總下來。不知是不是贏了棋,他看起來很高興,但一見到記者舉起的相機,他本來哈哈大笑的臉立刻板了起來。
叢兆桓聽記者說,跟了彭總幾年,照不到一個他笑的鏡頭,一照相就非常嚴肅。
慰問團成員都打了“四聯針”(預防四種傳染病)。每人得到一紙志愿軍的注射證,大家小心翼翼地保存起來做紀念。
慰問團分成了三個分隊,輪換演出,一個京劇分隊,一個歌舞和樂隊分隊(李百成和叢兆桓在這個隊),一個話劇、曲藝、雜技分隊(路奇在這個隊)。
歌舞隊先在“志司”(志愿軍司令部)演出。志愿軍里湖南、四川人居多,湖南花鼓戲《劉海砍樵》和川戲《秋江》最受歡迎。志愿軍副司令員楊得志是湖南人,每次看《劉海砍樵》都笑得前仰后合,聽多少遍也不膩。
楊小亭的魔術曾到蘇聯和東歐演出。他翻一個跟頭,一掀開長袍馬褂,就能抄出一盆金魚或者一碗熱湯面,讓觀眾驚嘆不已。有一次表演時,副司令員鄧華眼尖,看出他衣服下面有一根線,當場穿了幫。
叢兆桓除了跳蒙古舞、新疆舞外,作為戰地團支部宣傳委員,還有一項特殊的任務。他每天從“志司”的山洞出發,穿過幾里長的山溝,到“志政”(志愿軍政治部)的山洞去抄《最新戰報》,比如,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慰問上甘嶺戰士、為前線戰士洗血衣這樣鼓舞士氣的消息。
話劇隊先到“工指”(工兵指揮部),路奇兼任報幕。相聲演員常寶華的哥哥常寶堃也是相聲演員,參加上次赴朝慰問演出時在防空洞口被炸犧牲。這次常寶華和蘇文茂合說相聲,路奇每場報幕都會說:“上一次赴朝慰問演出的著名相聲演員常寶堃同志在朝鮮犧牲了,這一次他的弟弟常寶華同志又來了!”每次戰士們都會報以極其熱烈的掌聲。
在“工指”,司令員譚善和作報告說:“現在敵人的1307發炮彈才能殺傷我們一個人,這說明我們的工事在戰斗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我們的陣地已成了鋼鐵陣地,現在工兵可以在任何情況下保證交通暢通。每條河都有三五座橋,還在修筑水下橋。”
38歲的譚善和在路奇心中像一個傳奇,她在日記中屢屢提及他:
他每天一、兩點鐘睡覺,五、六點鐘起床。他一起來就要把同志們都叫起來。誰要偷懶就會揪著耳朵問他:“祖國派你干什么來了?” “抗美援朝來了!” “祖國派你抗美援朝來了,為什么老睡覺?”
4月25日,路奇帶隊去高射炮陣地一連演出。車還沒到,就聽到歡迎的鑼鼓聲。一連在一個光禿禿的山頂上,四座高射炮分別架設于四個方位。演出前有一個簡短的歡迎儀式,營教導員講話。
突然,一架敵機經過。連長立刻下達口令:“各就各位!”戰士們迅速奔向四個炮位。路奇和隊員們一時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戰士們提醒他們,原地坐下就行了。炮聲震耳欲聾,路奇看著一顆顆炮彈在敵機旁爆炸,敵機迅速飛走了。
演出結束后,每個人帶回一個高射炮引信的銅質“保險帽”作紀念。很多人寶貝似的保存了很多年,還有人把它改造成了花瓶。
64軍
一周后,慰問團移師64軍。行軍在晚上,越走,山越高。敵機轟炸頻繁,常看見火光在幾個地方同時亮起。
夜里一點,慰問團抵達64軍軍部。板門店就在64軍的防區,附近常有摩擦,但軍部距最前線還有一段距離。由于前兩次慰問團都有人犧牲,這次慰問團沒有獲準到最前沿。
第二天一早,天朗氣清。路奇站在山洞外,有一種恍惚之感,覺得這哪里是戰場,倒像是一處避暑勝地。只見四周松林茂密,巖石上長滿了金達萊。這是朝鮮的國花,天還很冷,但紫色的金達萊已開得滿山坡。
為了保護慰問團,64軍特別調來了一個高射炮營,并要求大家盡量不在室外活動,不要在外面曬衣服。
慰問團照例分成三隊,下到各陣地演出。演出一般在下午和晚上,演完即上車,夜里行軍,拂曉到達下一個團部,上午休息,下午繼續演出,每天如此。
路奇原是中央實驗歌劇院的大提琴手,除了報幕,也擔任伴奏,有時還唱歌。張魯作曲的《慰問志愿軍小唱》是保留節目。這支曲子的前兩句是:“緊打那個板兒來,慢拉琴,聽我唱唱可愛的志愿軍——”后面可以結合部隊的具體情況編寫一段新詞。戰士們聽后往往激動得像得了大獎章一樣:“怎么剛來就知道我們的事兒了?北京來的人都知道我們的名字!”如果有戰士沒有看成,慰問團臨走時會留下一封道歉信,并把慰問歌詞抄一份附上,簽上演員的名字。
路奇聽軍文工團的戰士說,眼下的生活和五次戰役時相比有如天壤之別。配給很豐富,每人每月半斤水果糖、9兩砂糖,有足夠的菜吃,兩頓飯改為三頓:早上米飯、中午面條、晚上饅頭。煙卷隨便抽。錢多了可以存入隨軍銀行,兩個月買一次有獎儲蓄。想買手表的,上級統一去買。
后來,路奇聽一位工程科科長談到五次戰役時的情況。那時敵機非常瘋狂,只能一早就上山躲飛機,晚上下山工作。國內運來的大批物資堆積在丹東運不過來。冬天沒有棉衣,1950年雪又下得特別大,很多戰士凍傷。頓頓吃炒面,因為缺少青菜,戰士普遍都患有夜盲癥。
歌舞隊走遍了“喀秋莎部隊”在朝鮮的九個團。蘇聯最新式的喀秋莎火箭炮是部隊的王牌武器,兩排共8枚炮彈齊發,最遠射程10公里。一天,歌舞隊在露天演出時,大雨傾盆而下。兩百多名戰士站在雨地里一動不動,慰問團當即決定繼續演出。
歌舞隊去190師演出前一天晚上,司務長專門坐著吉普車回丹東買菜,裝滿了一車的肉、菜、雞蛋、罐頭。回來的路上,離部隊只剩三公里時,遭遇敵機轟炸,年僅20多歲的司務長和司機當場犧牲。消息傳來,隊員們誰也吃不下飯。
好幾次,慰問團行軍途中,炸彈就落在附近。細碎的彈粒和掀起的塵土打在叢兆桓的身上,讓他深切地體會到,戰場上生死一線,今天還在談笑風生,明天就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再見。
條件最艱苦的一次演出是在一座軍工廠。大家進洞不久衣服就全都濕透了,碰到山洞的巖壁都燙手。朝鮮人民軍就在這近50度的高溫中作業。這是朝鮮唯一可以生產高炮的軍工廠,美軍飛機每次執行轟炸任務,只要有剩余炸彈,都會扔在這座山頭上。
5月27日是慰問團在64軍的最后一天。下午會餐時,軍長唐子安舉起酒杯,說:“我們把喂了一年的豬也殺了,我們說,不給祖國派來的慰問團同志們吃,給誰吃呢?我們把酒壇子也倒干了,我們說,不給祖國派來的慰問團同志們喝給誰喝呢?”臨別時,這位身經百戰的年輕將軍落了淚。
那一天,大家盡情暢飲,依依惜別,很多人都喝醉了。
平壤
5月28日,慰問團出發去平壤。經過中和、黃州、黃洞,車開出了山地,進入平原,平壤遠遠在望。
公路兩旁密布著炸彈坑,田野里倒臥著很多坦克和吉普的殘骸。路上行人越來越多,擔任防空哨的也換成了朝鮮人民軍。
慰問團的駐地在牡丹峰劇院。地面建筑已經被炸成斷壁殘垣,在瓦礫中順著石階往下走188級,就是地下劇場。
慰問團住在劇場的過道里,床鋪是像火車硬臥車廂一樣的三層鋪,人多擠不下,一部分人只能住在舞臺上。每天晚上,都能聽到飛機在頭頂扔炸彈,“咚咚的聲音像樓上裝修一樣”。
晚上,路奇出去散步。街道破敗,瓦礫中不時冒出炊煙,平壤的老百姓們都已經轉入了地下生活。
此后的幾天里,慰問團先后為朝鮮文藝界、朝鮮人民軍和朝鮮領導人演出。
6月6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斗奉在牡丹峰地下劇場宴請慰問團。這一餐非常豐盛,還有烤乳豬,食材都是從中國運來的。大家都是第一次見到烤乳豬,吃得很過癮。
傷員和戰俘
在平壤的演出結束后,慰問團回到了“志司”。
6月14日,話劇隊部分成員去慰問傷病員。前一天的傷員已經轉走,眼下又新來了40多位,大半是輕傷員,有七八位重傷員。輕傷員會被轉移到后方,重傷員則送回國內。
傷員都很安靜地躺著,聽不到呻吟。慰問團分散開去和傷病員聊天。路奇去看望重傷員,頭一位是右腿被截肢的。大夫壓低了聲音告訴他,祖國人民派來的慰問團同志來看你了,他睜開眼睛看看說:“同志們,你們辛苦了!”聽后,路奇難過得無言以對。
之后,為輕傷員唱了慰問歌,表演了大鼓、相聲、小唱。有的傷員哭了起來,說感到很慚愧,因為沒有立功。
一天演出時,路奇和禮堂門口的警衛聊天。警衛告訴她,很多戰士都看得很帶勁,看了還想看。路奇問他什么節目好,他說“都好”,就是不肯提意見。聊起朝鮮的戰況,他信心滿滿。
他說:“美國再打下去只有失敗。同志們現在情緒可高呢!有了任務都搶著要,要是不給,有的同志真哭呢!你要說危險,死就死,誰也不怕!”
6月16日晚上,路奇隨隊前往位于易洞金礦的俘虜營。這里關著一百多個南朝鮮俘虜和四五十個美、英俘虜。俘虜營所在的山上有明顯的標識,敵機不會來轟炸,朝鮮這最后一處完整的金礦才得以保存下來。
一位姓王的連長介紹,俘虜來了以后,衣服從頭到腳換新的,還發日用品。志愿軍每月的口糧中還有25%的粗糧,俘虜則完全吃細糧,并且和志愿軍一樣每月有津貼,但不給錢,發實物,每人每月還有半斤糖。每天早上出早操,有俱樂部,可以隨便打球、看畫報。參加勞動就是種菜自己吃,打柴自己燒,只要在規定范圍內,可以自由活動。王連長介紹,一般李偽俘虜轉化比較快,美俘很頑固。
路奇去河邊洗衣服時,看到俘虜都穿著整齊的藍色外衣、白色襯衣。有的還在河邊洗澡,看上去很悠閑。
第二天,協理員找路奇商量,能否也給俘虜演一場,她說要請示上級黨委,但想到很多志愿軍戰士還沒機會看上演出,內心極不情愿。上面來的一位處長答復可以演出,但演出時不要鞠躬,要顯出勝利者的姿態。
演出時,志愿軍坐前排,投誠人員坐中間,被俘人員坐最后,俘虜都自帶馬扎。演員們很自然地都板起了臉,表情嚴肅。路奇簡單地報了幕,略去了通常有的慰問話語。
她注意到,南朝鮮的俘虜反應較熱烈,前一排的幾個美軍俘虜連手也不拍。
演完雜技節目后,俘虜被要求退席。路奇再次上臺報幕:“親愛的同志們,現在為我們最可愛的人繼續演出幾個節目!”說著,她的眼淚幾乎流了出來。緊接著又表演了慰問歌、大鼓、相聲、小唱。
慰問團還參觀了俘虜營。南朝鮮俘虜的房間都收拾得很干凈,走廊里貼著墻報,一塊松木板釘在門框上,上面畫著畫,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門外有假山,栽著花。經過廚房,里面正在切肉。路奇心想,這哪里像俘虜營呢,簡直是在休養!
在美俘隊的圖書室里,路奇看到了美俘的尼龍避彈衣(志愿軍用槍試打過,不管用)。美俘都很年輕,悠閑地曬著太陽,卷著煙。在俱樂部里,有的在下棋,兩個白人在打乒乓球,一個黑人在撿球。協理員說,美俘有時打球會打起架來,還得給他們拉架。
停戰
6月27日,路奇和幾位隊員去“志司”參加功臣報告會,遇見了彭德懷。這一天,她的日記很長。
我們一行飯后走出洞口,剛好遇見彭老總在外面散步。任部長為我們介紹了,我們好像都有些拘謹。彭老總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先說話了,他問我們:“你們希望不希望和啊?”有同志回答說:“希望和,我們大家都希望和平。”彭總笑了,他說:“我不希望和平,我愿做個‘戰爭販子,打下去,打垮它。”
彭老總問我:“你說,用10年到15年的工夫過渡到社會主義算不算長啊?”我想了一下說:“我覺得不長。”旁邊另一位同志說:“10年到15年的時間不算短了。”彭總說:“10年到15年還長啊?改變一個社會制度,要是再短,我們就會犯錯誤的。”
7月27日上午10點,《朝鮮停戰協定》簽訂,當天晚上10點生效。
夜幕降臨后,李百成從“志司”跑了出來,周圍的山依舊都是黑的。
10點整,所有山頭瞬間燈光大亮,到處是歡呼聲。人就像突然從地下鉆出來的似的,幾乎每個山頭都站滿了人。
第二天,突如其來的安靜讓路奇很不習慣。之前的每一天,飛機的轟鳴聲一直在耳邊響個不停。傍晚,有人從山洞里把電線拉出來,在洞口裝上電燈泡看書。路奇十分驚奇,這是她入朝以來從沒有見到過的情景。
晚上,“志司”在地下禮堂舉辦了一場舞會,首長們全都到場了。副司令員鄧華舞跳得很好,他說:“今天要盡情地跳,不跳到天亮誰也不準走!”許世友恰好站在洞口附近,他說:“我站在這兒,把住洞口,誰也走不了!”逗得大家都笑了。
這時,彭德懷進來了,他坐在靠墻的一張椅子上,不跳舞。路奇被鄧華叫去陪彭德懷聊天,她坐在他身旁說:“聽說彭總剛入朝時也是吃的炒面和著雪。”彭德懷說:“我也是老百姓的兒子嘛!”路奇后來回憶起來,總覺得自己那時太年輕,說話不太得體。
慰問團沒有等到參加停戰協定簽訂慶祝大會的演出,于8月初乘悶罐火車回國。
離開的這一天,大批的志愿軍戰士到車站送別。上車后,戰士們還在喊著“再來一個”,有人剛唱了兩句,火車就啟動了。
鐵路兩旁,地面上布滿了重重疊疊的彈坑。路奇一邊請人掐表一邊數,一分鐘內路邊閃過70多個彈坑。
火車駛過鴨綠江大橋,離開了滿目瘡痍的朝鮮,前方亮起了丹東的萬家燈火,樂隊隊員田寶生吹起小號《歌唱祖國》,大家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回國后,李百成用赴朝近四個月的105塊錢工資,買了塊英納格牌瑞士手表。路奇和在朝鮮時交上朋友的一些志愿軍功臣、戰士一直保持著通信。那曲《慰問志愿軍小唱》,90歲的她現在還能哼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