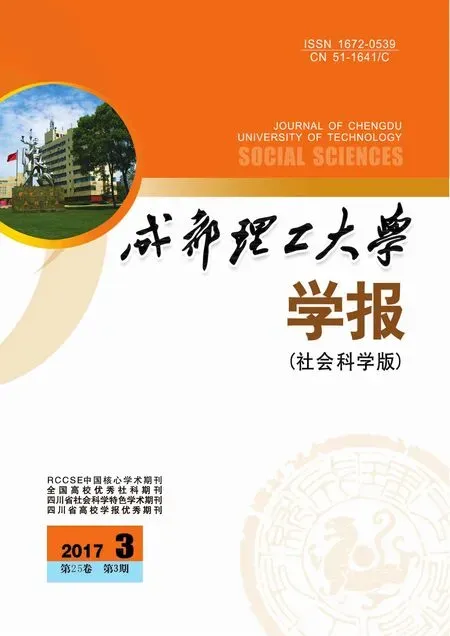《福》的互文性解讀:現代性建構與后現代解構
孫雨竹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071)
《福》的互文性解讀:現代性建構與后現代解構
孫雨竹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071)
《福》是對《魯濱孫漂流記》的改寫,因而兩部小說也建立了歷時性的聯系。文章從復調和對話性兩方面對文本進行內部研究,進而從廣義的互文性角度進行寬泛的文化研究。四個不相融合的聲音構成的復調性強調了個體的自我意識,在復調基礎上構成的對話以開放的自由言說創建著意義。兩部小說都與各自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構成互文性,《魯濱孫漂流記》的荒島故事體現了現代性建構的因素,而《福》反映了資本主義后工業階段對中心權威的解構。
《福》;《魯濱孫漂流記》;互文性;現代性;解構
庫切創作的《福》是對笛福《魯濱孫漂流記》的改寫,兩部作品之間也產生歷時性的聯系。對于《福》這部小說,中外學者主要集中于以下四點:第一,從后殖民的話語權利、他者、身份和邊緣化等角度對小說進行探究;第二,將小說置于南非的文化背景下,南非的殖民地、種族隔離歷史在小說創作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第三,從女性主義的視角探討《魯濱孫漂流記》中女性聲音的缺失和《福》中蘇珊·巴頓的敘述主體地位,批判父權話語體系中對女性的壓迫;第四,研究小說中的敘事聲音和敘事策略。然而,作為后現代時期對原著解構的小說,鮮有論文探究《福》中的復調和對話性,進而從互文性角度進行寬泛語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
巴赫金首先提出復調理論——“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不是眾多性格和命運構成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識支配下層層展開;這里恰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間不發生融合。”[1]4-5復調理論賦予了文本以生命,不相融合的聲音使文本有更多的言說能力。以此為基礎的對話理論進一步思考了不同聲音之間的互動關系,即通過“他者”來實現自身價值,“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1]340克里斯特娃發展了對話理論:在文本即書面語中不可能有主體的在場,因此主體間的對話關系不可能是直接的,只可能表現為話語與話語之間的聯系,她提出互文性來闡釋文本間的客觀聯系。由此可以看出,互文性是對對話性的豐富和發展,從強調文本中各主體的聲音到文本與文本之間,甚至更為廣闊的社會文化文本之間的互文。
一、《福》中的復調性
每個人在世上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位置,以及由特定時空決定的不可重復不可取代的意識和話語。如果意識和話語失去其獨立性,個人的主體性也被剝奪。在《福》中,文中并沒有出現一個權威的敘述聲音。雖然主人公蘇珊·巴頓是事件的絕對敘述者,但讀者在閱讀中能夠明顯地感知不相融合的聲音、意識所形成的多種頻調。
文中的女性敘述者是絕對的敘述主體。她尋找女兒,與克魯索和星期五在荒島求生以及尋求反抗男性話語,福先生敘述她自己故事的經歷都充滿探險精神。蘇珊·巴頓有著強烈的自主意識,不受他人干擾。因為自身的寫作能力,她將自己的海島故事口述給福并請求他真實地表達。但當她意識到福將她口述故事的重點改為她到荒島以前及尋找女兒的經歷以吸引讀者的注意時,她拒絕福來寫作,并嘗試自己的女性書寫。因此,她的女性書寫就構成對傳統男性話語和書寫的挑戰。
對比《魯濱孫漂流記》,《福》中克魯索的主體地位已經被剝奪,成為蘇珊·巴頓口中頹廢、安于現狀、沒有書寫自己歷史和控制他人欲望的“小島主”,由此產生的強烈反差賦予了克魯索豐富的言說空間。克魯索不用強制的態度要求星期五學習西方的語言以期賦予他“文明人”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觀念中,荒島是他自給自足的天堂,外面所謂文明世界的巴西到處都是食人族。他也不愿意構建自己的歷史,他相信“所有忘記的事情都是不值得被記憶的”[2]37。克魯索對法律制度有自己的理解,認為法律是用來節制欲望,而沒有欲望的小島不需要法律,這些觀點也體現了克魯索對現代國家契約精神和國家暴力的解構。
表面上看,星期五像是被控制和言說的人物,但實際上他卻用無聲的方式抵抗著權威。他的言說是組成蘇珊·巴頓故事真實性的重要部分。“星期五的舌頭可以言說很多故事,但真實的故事卻被埋藏在星期五中。我們將聽不到真實的故事,直到我們發現一種藝術的方式賦予星期五言說的能力”。[2]118而且,為了抵抗蘇珊·巴頓對他所謂的啟蒙,星期五用沉默、肢體語言和吹奏長笛的方式進行言說。然而這種神秘、原始的表達方式與被資本主義啟蒙觀念賦予的文明相悖。
《魯濱孫漂流記》的作者笛福從故事的權威敘述者變為故事的參與者。福先生不是荒島故事的直接參與者,卻因與星期五和蘇珊·巴頓的二元對立中白人男性的身份而擁有敘述權利。事實上,庫切似乎在暗示蘇珊·巴頓的敘述與笛福的創作存在著強烈的互文性,笛福似乎從蘇珊·巴頓的敘述中汲取材料完成了他稱之為史實的小說,克魯索是他筆下的魯濱孫·克魯索,而蘇珊·巴頓則是他故事中的羅克珊娜。
相對于《魯濱孫漂流記》中只有一個權威的聲音控制著人物,上述四種不相融合的聲音構成了《福》的復調性,每種聲音都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這種復調性是《福》的一個顯著特征,構成進一步探討對話性和互文性的基礎。
二、《福》和《魯濱孫漂流記》中的對話性
對話性發生在“地位平等、價值相當的不同意識之間,是它們互相作用的特殊形式。”[1]374《福》的復調性已經為對話性提供了多個不相融合的聲音,構成對話的基礎。在語義層面上,不同主體之間會產生對話,更進一步,巴赫金將對話理論滲透到句法層面,“對話語中任何一部分有意義的片段,甚至任何一個單詞,都可以對之采取對話的態度,只要不把它當成是語言里沒有主體的單詞而是把它看成表現別人思想立場的符號,看成是代表別人話語的標志。”[1]243對話也不限于主體話語和他者話語之間,巴赫金指出主體話語內部的對話性。“我們同自己說出的話,不論是整篇話語還是它的某些部分,以至其中個別的詞語,也都能夠發生對話關系。”[1]244對于《福》的讀者來說,魯濱孫·克魯索的故事已耳熟能詳,這就形成了一種前語境。
不同主體的不同聲音會產生對話。作為白人男性,克魯索的存在與蘇珊·巴頓代表的女性和星期五代表的黑人構成了二元對立。在這種二元對立的對話中,傳統的魯濱孫式的權威話語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幾個相互交織的平等聲音。《福》中的第二種對話出現在蘇珊·巴頓和小說家福之間,并占據著小說的大部分篇幅。兩人之間的對話實則是一場爭奪寫作話語權的斗爭。正是因為對話中二者的矛盾與相互依賴,對話性為個體的言說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如果將兩部小說對同一人物的刻畫看作內心兩種矛盾想法的沖突,那么人物自身就形成一種主體話語內部的對話。最大的不同莫過于兩個文本中對魯濱孫的描述:在《魯濱孫漂流記》中他具有資產階級頌揚的品質:冒險精神、勤勞刻苦、野心十足、追求財富。而《福》中,他拒絕離開小島,僅對小島進行簡單的改造,把荒島當作自給自足的終身王國。第二處體現于星期五,在《魯濱孫漂流記》中,他無意識地被殖民被馴化。而《福》中,他雖然被割去舌頭失去話語權,但卻用歌聲、身體、笛聲作抵抗,構成自我主體。對話性的文本并不追求終極的答案,在爭論過程中,差異與復調早已形成了足夠的理解、演繹空間。
話語的任何一部分都可能代表不同的思想、立場,個別的單詞就可能反映對話關系。蘇珊·巴頓不斷地向星期五教授的詞匯是主人(master),這一具有濃郁殖民色彩的詞匯似乎象征著她對星期五主體身份的界定。克魯索在與星期五的交流中并未出現有任何殖民色彩的話語,僅僅是簡單的生活交流用語。這種句法層面的詞語使用也構成了不同思想間的對話。
在巴赫金看來,所有的社會交往活動都是無限的、連續性的。在對話性中,不存在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因為話語向過去和未來延伸。“在對話發展的任何時刻,都存在著無窮數量的被遺忘的涵義,但在對話進一步發展的特定時刻里,它們隨著對話的發展會重新被人憶起,并以更新的面貌(在新語境中)獲得重生。”[1]391蘇珊·巴頓和福對于文本話語權的爭論最后也沒有結論,所有的意義都被后來者再敘述。《福》中最后一章描述了一個神秘的我發現了蘇珊·巴頓的尸體,而福和克魯索可能也在新的語境中獲得新的涵義,正如巴赫金所說任何意義都不會被時間沖走,它們只是在等待復活。
文本內部的對話性僅是狹義互文性的特征表現。作為后現代、后結構的標志術語,互文性“已轉向一種寬泛語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強調多學科話語分析,偏重以符號系統的共時結構去取代文學史的進化模式,從而把文學文本從心理、社會或歷史決定論中解放出來,投入到一種與各類文本自由對話的批評語境中”。[3]641因此,考慮小說創作的社會文化語境,更多文本將參與構建意義。
三、互文性:現代性建構與后現代解構
以互文性的角度來看,世界上的一切都文本化了,任何政治、經濟、社會、心理學、歷史或神學文本都變成了互文本。由此,文本的研究從封閉的文學內部延伸向更為寬泛的文化研究層面。
《魯濱孫漂流記》歌頌自由和啟蒙,對理性的強調與中世紀的蒙昧主義形成強烈反差。魯濱孫生活在笛福的年代,所以小說的背景與笛福生活的十七、十八世紀形成了互文性。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海外殖民的擴張和人文精神、清教主義的傳播,魯濱孫作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積極地探索財富。魯濱孫的故事雖然發生在荒島,但小說卻包含現代性裂變的因素。現代性主體意味著與中世紀的全面決裂,成為與傳統社會隔離的孤獨個體。魯濱孫被擱置在與世隔絕的荒島,這象征著個體在現代化過程中感受到的與傳統的疏離和孤獨感,海難的風暴也正是傳統的力量,它將個體卷攜,迫使他面臨新的環境來重新構建自我。現代國家注重法制、秩序,魯濱孫在荒島的第一件事就是進行空間的定位和選擇,劃分出居住區、種植區、狩獵區和危險區域。空間規劃和整合正是現代國家的標志性行為,通過規劃賦予混亂以秩序。鮑曼指出:“只要存在是通過設計、操縱、管理、建造而成并因此而持續,它便具有了現代性。只要存在是由資源充裕的(即占有知識、技能和技術)主權和機構所監管,它便具有了現代性”。[4]12魯濱孫從沉沒的船只上取出的種子、火藥、獵槍、簡單的工具成為他建立、控制現代性機構的基礎,他也成為海島機構的主人和絕對權威。
同時,現代性的經濟摧毀了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將整個世界變成一個市場。魯濱孫的大種植園在巴西,發達的海上貿易使非洲和南美洲的商品出現在英國的商店,這打破封閉民族的閉關自守,使落后的東方從屬于現代性的西方。理性和啟蒙使現代人擺脫了自然和上帝的雙重陰影,自然變成能為人的意志和能力改變的材料。魯濱孫依靠自己的雙手改造著自然:搭建住所,種植莊稼,制作面包和工具,打獵捕魚,馴養動物。清教主義相信財富可以被合理的獲取和積累。魯濱孫勤懇地在巴西開拓種植園,在荒島建造自己的王國,同時將錢寄回英國的委托人保管,這樣走向現代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到了現代性的成熟階段,它逐漸積累起來的形象就是疆域固定的民族國家、自由民主政制、機器化的工業主義、市場化的資本主義、主體—中心的理性哲學、權利和理性巧妙配置的社會組織,以及所有這些之間的功能關系,等等”[5]6。
然而,現代性的深層危機不斷突顯。“可在300年的擴張中,資本主義無時不在背離其許諾。與現代性的美好理想嚴重相悖,資本主義每個毛孔都散發著銅臭和血腥。它張狂進取,索求無度,每到一處都帶來曠世未有的沖擊震撼,以及隨之而來的戰爭、污染、異化和沉淪”。[3]641庫切站在當下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重新思考資本主義現代性。然而現代性中早已包含了后現代性因素,只是那些邊緣的走向了中心,中心的走向了邊緣。
《福》與庫切所處的后工業時代構成了一種廣義的互文。互文性作為一種敘事策略通過戲仿其他文本以達到顛覆、解構歷史文本的目的。首先在于對笛福的解構,笛福本名就為福(Foe),為了使自己的姓氏更加貴族化加上De,而De同時也為解構的意思。笛福在自身創作中不斷強調故事的真實性,而福先生對蘇珊故事的隨意篡改和拼貼暗示著小說的虛構性。這也體現了后現代作品對小說的真實觀和歷史觀的顛覆。在后現代語境中,解構中心,關心邊緣。克魯索不再是資本主義理想的開拓者,而是消極、墮落的保守形象。相反,原本被現代性男權隱沒的女性和被殖民者出現并參與敘事。創造意義已經沒有那么重要,解構意義才是后現代藝術的重點。
走出了現代性中人定勝天的思想,從人對自然改造的理性到人與自然的互動。魯濱孫對自然環境的改造曾標志著人類面對自然的祛昧,然而自大和面對自然的強權卻值得反思。被解構的克魯索已不再是“造物主”,他的房屋在自然的基礎上做簡單的改造,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他不過多地開墾荒地,種植的作物只有苦萵苣,這種人與自然的健康互動也體現了后現代生態觀。在現代性的構建中,男性被當作現代性的主體,而女性則被想象為未開化的自然。麗塔·菲爾斯基提出:“如果我們在考察現代性時, 不把男性體驗作為范式,而是將處于邊緣地位的女性體驗置于分析現代性的中心,那么現代性會呈現怎樣的圖景?”[6]10《福》中將蘇珊·巴頓這一女性形象作為敘述者本身就解構了以男權為中心的現代性。在大航海開啟的時代,女性似乎還被拘束為家中的天使,甚少踏足公共空間,很難想象庫切將蘇珊塑造為跨洋遠航的殖民者。庫切這一將女性置于現代性中心的思考也體現對男權中心的現代性的解構。
四、結語
小說的敘說形式作為內容的一部分也參與了文本意義的建構。《魯濱孫漂流記》描寫了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對中心權威的強調,所以全文由一個中心的敘述聲音來統領。而《福》中的解構敘事給予每一個人物言說的權利,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后工業階段解構中心權威的精神特質。
在《福》中,四個不相融合的聲音構成的復調性,強調了個體的自我意識,在復調基礎上構成的對話以開放的自由言說創建著意義。同時,在此基礎上廣義的互文將文本帶出了封閉的文學內部研究,轉向更為寬泛的跨文本文化研究。從現代性啟蒙到后現代的解構,文本跨越了三百年,體現了與政治、經濟、社會、心理學、歷史或神學文本的廣義的互文性的思考。《魯濱孫漂流記》留下的褶皺,等待《福》去填寫,這種改寫揭開了歷史的褶皺。通過文本與時代的互文性,讀者可以通過文本去觸摸一個時代的情感結構。不必再去追求故事的終極答案,書寫與闡釋才是文本生命的起源與延伸。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Coetzee, J.M. Foe[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1987.
[3]趙一凡.西方文論關鍵詞[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4]鮑曼.現代性與矛盾性[M].邵迎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5]汪民安.現代性[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6]Felski, Rita. Gender of Modernity[M]. Massachu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笛福.魯濱孫漂流記[M].郭建中,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編輯:魯彥琪
Intertextuality Interpretation of Foe: Modernity Construction and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
SUN Yuzh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Coetzee’s Foe is the rewriting of classic novel Robinson Crusoe,so the two novels are connected diachronically . This thesis makes research based on the text through polyphony and dialogicality, and further make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through broad sense intertextuality perspective. Polyphony consisted of four independent voices emphasizes each individual’s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dialogicality based on polyphony makes sense in open debate. Those two novels are intertextual with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respectively. Robinson Crusoe’s island story embodies the elements of modernity construction, while Foe reflects deconstruction of central authority in the postindustrial capitalism age.
Foe; Robinson Crusoe; intertextuality; modernity; deconstruction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3.019
2016-06-30
孫雨竹(1992-),女,黑龍江綏化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詩歌翻譯。
I106.4
A
1672-0539(2017)03-01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