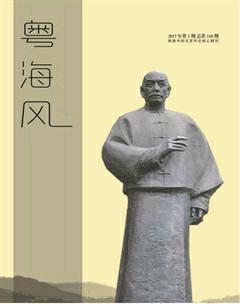現實主義與文化自信 (上編)
陳實+羅宏+譚運長
從《騾子和金子》說起
陳實(以下簡稱陳):今天我提議談一個話題,“現實主義與文化自信”。這個話題的起因,是從羅宏新近創作的小說《騾子和金子》,以及由這部小說所引發的系列文化現象說起的。我感覺到,我們廣東,至少是文學理論界、文學評論界,對于這樣一個創作現象,以及這現象所隱含的某種趨勢,不夠敏感,沒有從理論上來認識它。《騾子和金子》的熱度,在廣東似乎還不如在江蘇、浙江,他們是 小說一出來就知道了,就給予高度重視,我們這里實際上是不太重視的。《騾子和金子》這個小說出來以后,第一,它在讀者和閱讀市場上受歡迎的程度,其實反映了一種新的情況,這個小說是寫長征的,屬于我們一般所說的主旋律的作品。在這之前,所謂主旋律的作品,是從來不怎么受歡迎的,所謂叫好不叫座,大家不太喜歡。
譚運長(以下簡稱譚):就是能得“五個一工程獎”。其實“五個一工程獎”的評獎標準里面,是有對票房與發行量的要求的,但是實際上大多數都達不到。
陳:達不到嘛。這情形很普遍了,像電影,小說,都是這個樣子。甚至就是茅盾獎、魯迅獎,在這些具有官方色彩,體現國家意識形態要求的體系里面,一般來講就容易出現這種“叫好不叫座”的情況。也就是說,主旋律寫作是一個大問題。而這個《騾子和金子》寫主旋律,寫得在網上票選都能成為第一,這個很了不起。這本書放在購書中心銷售,開始是排在后面的,后來排名逐漸靠前,再后來排到暢銷書的名單里去了,完全是在市場里面受歡迎,讀者喜歡,才會這個樣子,對不對?第二個,它所引發的文化現象。這個作品賣了五六個版權,一個作品帶動了一群相關的文化產業,這也是過去少有過的現象。第三個,從我個人來講,我喜歡小說里邊對于中國革命,對于長征的這種思考,尤其是書中“二號首長”這個人物。現在聽說這個書準備翻譯到國外去,我估計到了國外,人家不一定看重的是騾子這個人物和故事,說不定人家更看重的是“二號首長”所代表的這種思想,說明中國的思想界、文化界,對長期以來所奉行的馬列主義,有了新的認識。這個東西,是當時的革命者為后人,為后邊的時代所提供的、很新穎的思想,我覺得這部小說的貢獻,最主要的是這個。以上三點,我是從現實主義創作這個角度來看的,而且羅宏本人有一個發言特別好,他解釋了現實主義創作現在碰上的挑戰,是在哪個地方的發言?
羅宏(以下簡稱羅):長安論壇上。
陳:就可以談談這個。所以我就覺得,第一,他這個作品對于現實主義的創作,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的經驗,比如說,羅宏沒有參加過長征,也沒有當過農民,是不是?他這里面寫農民,寫長征、革命,都不是他經歷過的。這個作為現實主義的創作來說,就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多話題。第二個,我們這個文學,從1980年代,就是我們叫做改革開放以來,受到外來文化各種思潮的影響,尤其是在文學創作中,實際上是變成了東不東西不西的一個東西了,詩歌也出現問題,小說也出現問題,各種體裁都在出現問題。而在這個《騾子和金子》里邊,起碼有一條,我感覺它基本上是把中國文學創作里邊的一些傳統類型的東西給復活了,比如說這種類型化、扁平人物。我們從1980年代以來都在批評類型化,批評“扁平人物”,要典型化,寫復雜人物,性格二重組合,等等。實際上也沒怎么寫出來,我看除了路遙的高加林,就沒有人能夠寫出多么復雜的人物來。這是一個。又比如說里邊的誤會法、巧合法,這都是很典型的中國小說的手法,中國古典的傳奇、話本,以及以“三言兩拍”為代表的,都是用的傳奇的手法,這是第二個。第三個,就是說主旋律,現實主義的作品,我們正兒巴經的這種精英文學,怎么和大眾文學結合的問題。《騾子和金子》能改編成電影電視,而且在電影電視里面它又那么受到歡迎,電影電視這些東西,實際上是大眾文化的一個骨干性的組成部分,為什么這個主旋律的作品能夠受到大眾的歡迎,這是給我們提出了很多值得總結和探討的東西的。我們現在的很多小說,老講到人民性、人民性。人民性,說白了就是人民歡迎,是不是?人民都不歡迎你,你還說有多少人民性在里邊,也就是你自己說說而已。所有這些,我覺得都是與現實主義話題有關的,就我看來都可以歸入到關于現實主義創作的討論,或者是現實主義創作在當今時代背景下的某種新探索、新經驗的討論里面。
另一個大問題,就是文化自信。為什么要談文化自信呢?對此可以擴廣一些來說。我覺得,習近平發表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后,在文藝界里面,似乎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雖然表面上看學習會開了很多,可是從文藝實踐來看,并不十分的理想。我思考其中的原因。我覺得,習總書記在講話里面,是已經看到了至少未來十年,甚至未來三十年,中國文藝應該走到哪一條路上去,我覺得他心里是知道的。但是文藝界也好,理論界也好,在解釋這些東西的時候,所能夠運用的理論武器太少。基本的理論,我們能夠用上的文藝理論,還是以前的那種文藝理論。我們大學學文科的,尤其是學中文的,那時的文藝理論教材,和現在大學里用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一套。
羅:在這個體系下還是有一些變化,但是變化不大。
陳:沒有本質的變化,在我來看。我認為,我們現在是叫做中國共產黨的新一代,它確實在文學藝術、政治經濟各個方面,都應該有創新的地方,這樣才不愧為現在的新一代。重要的是,各個方面的建設,能夠拿出一套東西來,至少應該像建國初那樣,有一個《新民主主義論》來指導,對不對?我覺得習總書記他是看到了這一點,而且他可能心目中也有這些東西,但是給他提供闡釋的這個理論,缺乏力度。我簡單的說,我們現在應該運用現代武器了,但我們的理論,還處在一個扛麻袋的時代,那不行。這個文學、藝術,它一般在文化里面是屬于最敏感的部分,它是看新東西看得最快的,連它都提供不了新的東西,那就不行。我們搞一個文藝座談會,那起碼要有給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新東西,才能夠指導下面。
回過頭來說,我們平時談文化自信,嘴巴上是自信了,骨子里還不夠自信,就是因為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一些新的東西出來。你看,好像是1962年,陳毅和周總理到廣州來開文藝座談會,直接就帶動了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思想,這才出現了六十年代中期的那種全國性的文化繁榮,特別是廣東,什么《三家巷》、《香飄四季》啊,以及軍區的那些創作,等等。包括中南戲劇會演,許多優秀的作品,都是那個時候出來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1962年在廣州搞的文藝座談會,一下把大家的思想照亮了。那個時候的文藝界人士,的確是足夠自信的。
講文化自信,還可以說一下所謂粵派,所謂嶺南文化的自信問題。前段時間討論“粵派批評”,我注意到,這個話題的發起人之一陳劍暉教授提出一個觀點,就是認為廣東人從不參與全國性的前沿問題討論,這說法明顯是不對的,可見即使在討論“粵派批評”的時候,嶺南文化也還是不夠自信。我覺得別的不說,就是兩個世紀之交的文藝思想,廣東都是處在全國前沿的。1992年在廣東開了一個理論研討會,那個會議很小,但是對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藝創作,可以說非常重要,非常有意義,其中出現的許多理論認識,在當時無疑都是前沿性的。那么,近年來,很多人認為廣東的文藝創造有點落后了,可是你看羅宏的這個《騾子和金子》,那就是一個新的東西,值得進行理論總結的。我的總體的感覺,實際上就是,廣東啊,每當有變化的時候,它都會把握到變化的脈搏,產生第一線的東西,這才是廣東的文藝界,或者廣東的理論界,應該提供給全國的貢獻,這才叫做文化自信。
譚:我插一句,我們講現實主義與文化自信,不一定是指對現實主義的自信,是不是,你的意思?
陳:首先是就提出文化自信的本意來講的,我個人認為。
譚:那就是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包括你剛才也提到對嶺南文化的自信,都是大題目。
陳:題目大,但我們可以從小處談起。比如說,在文藝觀念與文藝理論上,對一些比較適應中國國情,為中國大眾喜聞樂見的,同時也是我們的文藝家運用得比較得心應手、行之有效的一些文藝手法,要有自信,不要輕易丟棄。
現實主義面臨的挑戰與問題
譚:話題是從《騾子和金子》引發的,切入這個題目的話,我覺得可以請作者羅宏說一下,《騾子和金子》是不是現實主義?或者認為是現實主義在一種新的時代變化下,在面臨某種挑戰與問題的時候,所出現的一種新篇章、新經驗?
羅:可以這么說吧。去年8月份,我去參加中國文聯在西安和陜西省委宣傳部一起做的一個長安論壇。長安論壇的主題就是文化自信,一個大主題,分了三個組,中間有一個組就是討論現實主義的文化自信,我就被分到了這個小組里面。大概有20幾個人參加討論,只有半天時間,所以每個人發言限定五分鐘,很倉促。在現場我也看到一種“學界現象”,談現實主義,開始從庫爾貝講起,講到后來不斷地有人敲桌子打斷,但是他還是收不住,情愿他真正要講的東西講不完,也要把庫爾貝講完。最后他的主題還沒出來,就不得不結束了。我感覺這個學界的先生比較迂腐,好像他不從庫爾貝講起就講不下去了。于是到我發言,我就吸取前面發言人的教訓,講得比較直接。第一個,我說現在我們討論現實主義的概念以及它的源流,沒什么意思,應該直接地講:現實主義在中國是什么狀態。我們不要講它是怎么來怎么去的,那是另外一個話題。第一,現實主義在當下中國,它是主流創作形態,這是一個事實,為什么是這么個事實我們先不說了,不管是官方的倡導還是作家自覺的選擇,總之它是一個主流形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就講現實主義的基本價值,就是真理承諾。真理承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作者要告訴人們生活是怎么樣的,什么生活是應該的,什么生活是不應該的,歷史是什么樣的,什么才是歷史的本質,什么是歷史的假象。要告訴人們一個真實的生活,同時用這種真實的生活去感染人,教化人,引導人,用真理承諾去告訴人們生活的道理,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基本功能。現實主義不是為藝術而藝術,強調所謂的藝術形式,也是為了加強它的功能,而不是相反,這是第二個。第三個,我就講現實主義它有一個藝術上的原則,就是仿真性,你寫這個東西呢,你要寫出比較符合我們的經驗狀態中的生活來,比如說《紅樓夢》,就是屬于經驗狀態的,那《西游記》就不是。就是要求按照生活的邏輯去寫生活,寫得像生活,不是說不可以虛構,但要虛構出日常經驗生活的這種狀態來。然后再加上一個什么東西呢,恩格斯所說的,就是典型環境的典型人物,要以點帶面,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生活狀態,折射出種整體性的時代本質來,前提就是要真實,所謂的真實,當然是指仿真性意義上的真實,因為文藝作品本質上還是虛構的。我說這三點,目前都在面臨挑戰。第一個,現實主義作為主流創作形態,這個認識受到挑戰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各種各樣的方法,都可以實現文藝作品的功能,很難說將其定于一尊了。第二個,我覺得所謂的真理承諾,也受到考驗,現在我們的文藝作品,很大一部分功能不是讓人去受教育,去讀生活的教科書,而是當做生活的調劑品、娛樂品,是這樣去看待文藝生活的,很多很多的人在進行閱讀的時候,是把娛樂性、消遣性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來訴求的,而那種受教化的功能訴求減弱了。第三個,現實主義作品的仿真性,它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戰。比如說現在有很多抗日劇,從大的方面看好像也是仿真的,但是褲襠里掏雷啊什么的,顯然并不符合日常生活經驗,它有點傳奇性,但是總體上感覺在真真假假中間,還是以真為主。總而言之,現在說現實主義,就會遇到很大的尷尬,這三點都受到挑戰。原因是什么呢?現在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把文藝創作當作產業了,一旦產業化,它的邏輯馬上就變了。如果我們把它當事業的話,腦子里就會堅持一個指導作用和揭示作用,現在變成產業,等于是讀者和創作者之間是甲方和乙方的關系,一種契約關系,中心地位沒有了。包括對真理承諾的看法,也并不是說真理只有一個,真理的相對性加強了,而真理的絕對性減弱了,所以你的真理承諾,大概只能承諾一個有限的真理,是不是?真理性的東西,其普遍性、唯一性,大大的削弱了。而契約性強化了,對真理的看法,也要得到對方的認可才行。于是現實主義本體的那些東西,就受到了嚴峻的挑戰。這就導致現實主義很尷尬,通常的情況就是,你要是堅守現實主義,那你就全靠領導的支持,領導下行政命令買書、訂報、包場,然后領導給你評獎,用這種辦法去支撐現實主義。這當然不是現實主義的長久之計。我說現實主義要突圍,要靠自己來救自己。第一個,我認為,就是調整觀念,現實主義在今后的創作中間,不應成為唯一的創作現象,甚至也不一定非得自認是主流。人們用不是現實主義的方法、態度創作,我沒意見,是吧?但是我如果愿意擁抱現實主義,那我就要用現實主義的創作魅力去吸引人,我不是唯一,但我終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百花齊放,我是一朵花,而且我這朵花有人看,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怎么解決呢?就是這種真理承諾,我認為我們也要考慮。就是說,可能需要放棄那種對于真理的唯一性、普遍性、絕對性的看法,承認多元真理、局部真理、相對真理的存在。你只是寫你看到的生活,中間的那種所謂的道理的確定性,不要把它放大到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程度,在這個前提下締結與受眾的契約關系,我認為。這樣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談到第三點,就是說這種仿真性。我們怎么樣吸納很多很多的的民間元素,調動受眾喜聞樂見的手段,讓他具有真實感。于是我就拿出我這個《騾子和金子》的文本。這個《騾子和金子》,從它后面產生的社會效果來講,起碼可以說比傳統的一些文本更受到讀者的歡迎。我就講我在這里面采取了一些什么樣的手段,我向江湖靠攏,向底層靠攏,向老百姓的心態靠攏,就是找出了老百姓喜歡一些什么。比如說傳奇,說懸念。懸念的話,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吸引讀者的東西。而生活中處處是懸念,它是現實生活中客觀存在的。我就以懸念為核心來結構我的故事。這是可信的,也是仿真的,這里面還有一些巧合、傳奇等等的元素。我找到了這樣一些元素,它既符合現實主義的規矩,也符合我們現在大眾的需要。在某種意義上,它也可能會超出一些傳統認為的現實主義的范圍,但是如果你拿捏那個度拿捏得好,它就不犯現實主義的規。后來一位解放軍政治部的文藝局局長,叫汪成德,他就說我們有些題材很真的東西,卻感覺很假,而你這個東西一看就知道是編的,但是卻覺得很真。他這個說法大家也可以體會。我在這個文本里面,主要就是在一些技術上,在一些形態上,觀眾心理上,還有一個,就是從我們中國傳統的一些文學手法中間,找到一些行之有效,一些經久不衰的招數。把這幾個東西結合在一起,就產生了比較好的效果。所以我認為,當然我不能說我這個東西就是現實主義了,但是應該給現實主義創作起到一定的啟迪作用,或者是現實主義創作的一種可能性。
現實主義的各種可能
譚:聽你們倆剛才所講,關于現實主義,總的來說,就是說傳統的、本體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概念,受到了挑戰,《騾子和金子》,是因應這種挑戰所產生的這么一種具有探索意義的、新的文本,而這種探索,特別在當下這個處在各種變化之中的時代背景下,具有一定的趨勢性、啟示性的作用。從理論上對這一新的經驗進行總結、概括,其實涉及到與文化自信有關的問題。大概是這個意思。
首先,我覺得羅宏對現實主義問題總結的三個要點,很有意思。
羅:我不是講現實主義的源流、演化,我是講在中國的現實主義。
譚:中國的現實主義,我覺得有些地方可以討論。比如說在當代中國,或者說整個社會主義中國吧,現實主義是不是主流創作形態。當然從主流意識形態,從官方文件上看,我同意你的看法,這是一個事實。但是進入到實際情形上看,我覺得里面的問題還非常復雜,許多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理論關鍵,到現在都還沒有真正得到解決。比如說,我們建國以來對各種標榜為現實主義的文藝觀念,批判是不斷的,而不管是批判者還是被批判者,都同樣標榜為現實主義。我理解這就是為什么大家從感覺上一直認為現實主義是主流。你比如說文革時候的文藝,那時候現實主義口號應該是叫得很響的,但是八個樣板戲,是不是屬于現實主義的作品?我從藝術上看,不認為八個樣板戲是壞作品,也不認為在現實主義與好作品之間可以劃等號,好作品不一定非是現實主義的。八個樣板戲,我認為從藝術上看,不失為藝術的精品,但是它并不適用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理論來討論,當時的說法,是聲稱為經過改造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又有說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是這樣的。
現實主義概念,應該說它基本上是在十九世紀,在工業化,也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散文時代”背景下,所產生的。然后到了別車杜那里,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就已經非常成熟了。后面經過普列漢諾夫、盧卡契等等,進一步把它完善。到我們紅色中國以后,中國特色的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就產生了。但是這里面的斗爭是很激烈的。具體地說,胡風這一派的現實主義,它跟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形成的,后來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其實沖突得非常厲害,后來甚至演變成了很大的政治事件。胡風的現實主義,是相對來說比較接近于原始的、本體的現實主義理論的,他的理論的體系性、學術性,相對比較強,包括后面“向著真實”這一類的發展,都是他這套現實主義理論體系的邏輯的結果,并且與十九世紀那種批判現實主義,寫真實的這一類概念,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延安文藝座談會所形成的理論,它的實用性比較強,特別強調的是功能性,它首先要求的是對現實發生作用,而且是很明顯很快的作用。延安當時因為它是戰爭時期的文藝,像街頭劇一樣,要的是對革命有利的效果,是不是?所以首先從功能的角度來要求它。它不像胡風的那一套,是有很具體的方法論為基礎,并且是與傳統的本體的現實主義理論相聯系的。方法論跟功能沒關系,功能就是達到一個目的,所以當時特別強調為工農兵群眾喜聞樂見,這些都是從功能的角度來考慮的。所以你講到在中國的現實主義,我想至少也存在兩種現實主義的概念,一種是從方法論出發的現實主義,一種是從功能性出發的現實主義。應該說,這兩種在中國的文藝實踐中都是廣泛地存在,但不管是就其內容本身,還是就其為官方意識形態所接受的狀況而言,都是有區別,甚至有沖突的,不能籠統地說現實主義是主流創作形態。
另外還要說到一種現實主義概念,就是想要調和以上說到的兩種現實主義,抹平其中的矛盾、沖突的地方,這就是也曾遭到批判的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這種理論,是把現實主義看成一種總的精神,一種原則、態度,而不去管具體的觀念、方法的區別。這其實也并不是完全中國特色的,法國的羅蘭·迦洛蒂的“無邊的現實主義”觀點,就是這樣的。羅蘭·迦洛蒂的現實主義觀,實際上是現實主義理論進入二十世紀,面對現代派文藝的挑戰,所作出的調整。他就是要把畢加索、卡夫卡這樣公認的大師,統括到現實主義中來。卡夫卡說“文學是現實生活的避難所”,但迦洛蒂認為他也是現實主義的。
我1988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論文,就叫《現實主義是一種自信》,所以接到你這個題目,“現實主義與文化自信”的時候,我覺得很是親切。當時參加全國文藝理論學會的年會,這篇論文收進到年會的論文集里了。我主要就是從某種精神、原則、態度的角度,來理解現實主義的概念的,我把這種精神、原則、態度,概括為“自信”。主要觀點,大致就是你剛才說到的第二點,就是現實主義承諾給讀者提供真理,那是何等的自信,是不是?這具體的講包括兩個方面,一個就是在人和自然的關系當中,人的自信。現實主義相信人類是主體,人類是中心,人能夠認識自然并且改造自然,這是現實主義的一個基本哲學思維。這個就是馬克思講的主觀能動性,人是萬物之靈長,莎士比亞是馬克思最欣賞的,這就是典型的現實主義的態度。現實主義要提供時代精神,人相信自己能夠把握住時代精神的脈搏。當然再具體地說,實際上還有一個方法論和功能論的區別的問題,否則的話席勒化也是現實主義,就不需要強調莎士比亞化了,是不是?但我沒有細致地涉及這些更復雜的問題,只從態度上講,所以大體這篇論文的意思還是屬于“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的。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就是在人和人的關系中,在人類社會內部,在文藝與社會生活的關系中,文藝的自信。現實主義認為我提供的文藝作品,它能夠改造生活,參與生活,介入生活,就是說我的作品能夠使生活變得更好,不管你是批判的也好,你歌頌的也好,你塑造美,讓人們向真善美的生活看齊,是吧。它就是真正認為文藝作品能掌握善,掌握真,掌握美,然后提供給讀者。就是這樣。我當時說現實主義有很多人討論,它有很多很具體的世界觀,方法論,但是我覺得在這些之外它有一個總體的精神,就是認為人有能力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認為文藝作品有能力來使生活變得更美好,這個就是現實主義的基本態度。到現在已經快三十年了,我覺得從這個角度看現實主義的概念,并不過時。這既帶有一點方法論現實主義的因素,跟傳統的、本體現實主義有一脈相承的地方,另外它也強調功能的角度,是一種調和派、折中派。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包括全世界的現實主義理論,在對現實主義的本質的認識上,一直都在不斷的爭論當中,到現在都沒有定論。從無邊的現實主義,或者現實主義廣闊道路的說法看,那就是卡夫卡都算現實主義,因為它是從現實生活當中產生的,反映現實生活并且最終要對現實生活產生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解釋現實主義,那就幾乎沒有一部好的文藝作品不是現實主義的。當然也許作者的目的不是對現實生活發生作用,但是如果這個作品產生了影響,它一定會對現實生活發生作用。對現實生活發生作用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不一定就是只從文本本身的內容來看,比如說你這個《騾子和金子》,一定對現實生活發生了作用,它不可能對長征發生作用,但是他對受長征影響的人以及我們現在的社會生活,發生了作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它也是屬于無邊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那不是一條道路,很多很多道路都可以通向現實主義。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八個樣板戲也可以說是屬于那種無邊的現實主義。它里邊的內容,編造很明顯,人物高大全,但是如果這個作品最后能夠成立的話,我覺得它還是遵循一定的生活邏輯的,可能它的編造比較偏重于審美的邏輯,政治的邏輯,但是它還是有生活邏輯的基礎。我覺得從無邊的現實主義或者說現實主義廣闊道路的角度來講,它與“向著真實”的這種提法,那有區別。這就涉及到你講的仿真性。從功能的角度來講,傳統現實主義強調的具體性、形象化,也許并不是唯一的,它就不排除一種抽象的真實性。就是亞里士多德講的,他對真實有一個定義,他用效果來講,用心理效果來講,真實就是相信。文藝作品一定是虛構的,不可能是真正的真實,你去判斷它的時候,建立在對真實的一種經驗把握的基礎上,對吧。所以真實性一定是仿真性,它不可能是真實本身。所以亞里士多德關于真實的提法,我們可以稱之為真實的幻覺。要給你的文藝作品營造一個環境、氣氛,讓整體的真實感立起來。所以傳統現實主義理論講典型人物以外,還要講典型環境,營造整個的真實的環境,真實的氣氛。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高峰,就是在這方面最高明的,他是不厭其煩的從現象到本質,從局部到整體,把那種整個的真實感,真實的氣氛營造出來了。但是,這種具體的、形象的方法,我想并不是唯一的,比如樣板戲,他用舞美、燈光、舞臺調度等等綜合性的手段,以及與內容相配合的意識形態宣傳,讓觀眾相信舞臺上表現的東西是真實的,這種以階級斗爭為基本哲學的對現實的認識,指向的大概只能說是一種抽象的真實,但也許也并不違反現實主義所強調的仿真性。據說當時《白毛女》上演的時候,有觀眾中的戰士舉槍要向舞臺上的黃世仁射擊,可見其在營造真實的幻覺這一點上,是挺成功的。
羅:這里我先插一下,就是我寫東西,對于你說的“真實的幻覺”,我喜歡造成它所謂的質感。故事嘛肯定是編造的,但是我就把它放在歷史的框架上,使這故事有質感。那什么叫歷史框架呢,它有一個技術,比如現在有很多作家、編劇,他寫抗日戰爭,他寫日本人是壞人,中國人是好人,他就覺得真實了。但是具體地寫,比如寫大掃蕩,日本人為什么掃蕩,掃蕩的背景是五一大掃蕩呢,還是別的什么,他不計較這個東西,然后就一味地打。我基本上是這樣:這次掃蕩,它是平原的掃蕩,還是山區的什么掃蕩,這個掃蕩的指揮官是誰,部隊番號是什么,打的時候,和他發生接觸戰的是誰,是120師還是135師,是林彪的部隊還是賀龍的部隊,我覺得有必要說清楚。而我們現在好多抗日劇,開打的是哪個部隊,他不講究。我就比較講究這樣的東西,我認為做仿真感,營造真實的氣氛嘛,必須要有歷史的框架在。再比如說我最近寫的一個小說涉及朝鮮戰場上的一次諜戰。為什么出現諜戰?就是因為談判陷入僵局,陷入僵局的時候,李承晚和美國人,想的不一樣。李承晚是希望打,美國人希望談,于是李承晚希望把這個事情攪大,讓美國談不成,談不成就打。于是志愿軍的部隊,針對的間諜就應該是李承晚派出的間諜,而不應該是美國的間諜。我們很多人是不會編的,他就說是美國派來間諜,要暗殺李克農。那我說是,暗殺李克農,把他干掉了,談判就談不下去了,就只能打了。但這個絕對不能是美國遠東情報局干的活,一定是李承晚干的活,我把我的故事放在這個歷史框架里面去編,就有特殊的質感,好多人不講這個。
譚:你說的這個,可以把仿真性這一塊的討論,引向深入。剛才陳實講到,羅宏沒有經歷過長征,但《騾子和金子》,大家覺得很真實。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就我所知道的,比如我們廣東的作曲家劉長安寫的一首歌,《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這么傳唱經久,具有無限魅力,而且真實到令人神往的,對于海南島風物的塑造,大概許多人都想不到:劉長安當時根本就沒去過海南島。談現實主義,這可是繞不開的一個話題,就是跟真實性相關的,親歷性的問題。我以前與人討論文化散文。寫散文,大多數都是講真情實感的,對不對?散文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真情實感,但是歷史散文、文化散文,大家都沒經歷過歷史,作者的真情實感從哪里來?所以我講親歷性,有一種可以稱之為感受的親歷性,就是你的感受是真實的。那么你的這個感受的真實性從哪里來呢?你是真正進入了那個真實的歷史氛圍,你在讀歷史資料的時候,或者你在歷史古跡面前的時候,其實是把自己代入到了那個歷史資料、古跡所代表的環境里面,這種感受是親歷的。我想劉長安寫《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的時候,一定是把自己代入到了海南島的山水環境里了,這樣他才能想象出五指山萬泉河的形象,并表現出其中的熱愛。談現實主義,特別是談主旋律這一類“主題先行”的創作的時候,我認為“感受的親歷性”,這一從一般的真實性概念中分離出來的、更為深入一點的認識,很重要。所謂“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只有自己親口嘗一嘗”,記得讀書的時候我們討論現實主義,有人說: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寫殺人犯,他必須要自己去殺人嗎?感受的親歷性,某種代入式的親歷,可以解決這一疑問。
陳:這是怎么搞好現實主義創作的一些技術活,我更關心的,就是你們剛才發言所及現實主義的各種可能性的問題。比如你說胡風式的現實主義和其他的現實主義,包括和延安的現實主義,它是不一樣的。其實胡風也好,延安文藝座談會也好,它們都不是盧卡契的現實主義,實際上都還是以日丹諾夫這一類為主的。真正來講的話,相比胡風,延安文藝座談會里的東西,更多地把中國本土的許多成分加了進去,可以算是中國的現實主義。另外它在當時的文藝界看來,具有不少新的思想、新的發現,讓人眼前一亮。至少有一點,延安和西安比,它的文藝觀是不一樣的,它是有新的東西在里邊的。你比如說國統區的新生活運動,比較提倡風花雪月,那是從周作人就開始了。這種閑適文學,也是現實生活,而毛澤東那個時候強調的就是勞動大眾的生活,而且是革命的生活,而且是抗戰的生活,這才是真正的新生活。所以我覺得現實主義至少有三種區別。第一是有不同時代的現實主義,你比如說文藝復興時期莎士比亞的那種現實主義,和十九世紀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肯定是不一樣的,到蘇聯那時代,《靜靜的頓河》,又跟十九世紀的那個不一樣了。這里有個時代的差別。所以我們真正應該討論的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什么樣的現實主義,這是一個。第二個區別是什么呢?中國的現實主義和外國的現實主義,它也是有差別的。包括浪漫主義,你比如說我們中國一講浪漫主義,就是《西游記》,是不是?這種東西和雨果式的浪漫主義是兩碼事。所以中國式的現實主義和外國式的現實主義,我們對現實主義的理解是不太一樣的。我們中國的現實主義,我認為基本上應該就是《詩經》的傳統,風雅頌的現實主義。第三個呢,還有一個生活的現實主義和心理的現實主義的差別,的確是有差別的。比如剛剛講的“感受的親歷性”的問題,似乎也與此有關。所以我說,純粹的從理論上去討論,不是我們現在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真正所要解決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什么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現實主義。比如說我們現在的現實主義和延安時期的現實主義一樣不一樣,這個問題到現在都沒有解決。中間經歷了那么多的討論、爭論,甚至批判、斗爭,真正收獲的可以上升為現實主義理論的成果少之又少。我覺得之所以產生這么大的分歧,之所以到現在還這么爭論不休,就是因為理論界沒有對這個現實主義下一個大家相對認可的定義,有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沒有解決。
譚:具體一點說,比如現實主義和主旋律的問題,現實主義和生活陰暗面的問題,就是歌頌與暴露的問題,這些都困擾了幾十年,但到現在都還沒有真正解決。
陳:理論上沒有解決。往往是一出現大的爭論,就用行政命令給壓了下去。這樣爭論是平息了,但是問題并沒有解決,本應產生的理論收獲一點也沒有。我們的理論很滯后,就是這樣子的,這個是應該罵讀書人偷懶的。傅斯年1949年到臺灣之前,他講過一句話,他說我們的失敗不在于什么別的東西,就是讀書人太懶,不讀書。理論家們太懶,在新的理論上缺少敏感性,這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以你看習近平想把文藝搞好,但理論界來來去去提不出好的東西。
譚:比如剛才提到的現實主義和生活陰暗面的問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曾經有人寫過一篇文章《歌德與缺德》,反對寫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引起了極大的爭論。后來到電影《人到中年》出來,又有人以其揭露了陰暗面而反對給予授獎,就使這問題的爭論更趨激烈了。就此王元化寫了一篇長文:《論知性的分析方法》,這其實是對此一問題的極有價值的理論收獲了。可是沒有人對此進行梳理、總結,形成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系統表述。后來《人到中年》得獎了,要不要和能不能揭露陰暗面的問題也不爭了。但問題并不是王元化的文章解決的,而是有關方面打電話、發通知來解決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