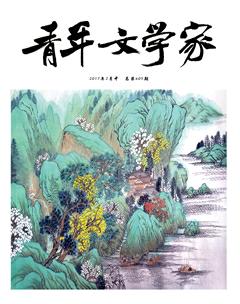文學自由與征服
余迪
摘 要:文學作為再現日常現實生活的話語結構,展現社會大眾生活方式和思想差異的一種文本。文學一方面與社會政治緊密聯系,不能單獨存在要通過文學家來創作,不可避免的帶有文學家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有著為政治服務的功利性一面;同時文學本身又具有自身特有的超功利性審美自由的一面,文學家與讀者之間是通過靈魂與情感的交流來完成文學作品與受眾者之間的文本對話。在世界文學多元化、自由化發展的今天,中國文學應當走向世界,這既不是迎合也不是征服,是將人類靈魂的文學傳承后世。
關鍵詞:功利性;超功利性;文本對話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02
一、文學應當追求審美自由還是功利發展
文學自由思潮最早在古希臘萌發,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以17世紀洛克的思想為標志,中國的文學自由主義萌發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當時的知識分子大多留學歸來,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嚴復《論自由》發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吶喊,開啟了中國文學自由主義的一扇門,繼而以維新派為代表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倡“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1],倡導人們成為完全自由的個人。在國家面臨存亡時,文學的審美特性被忽視,把文學當作救國救民之良藥,夸大其社會功利性。五四以后,中國的現代文學大體發展為兩個方向,一種是左翼文學,這個時期的文學以中國和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命運為題材,另一種則是自由主義文學,以自由的人生理念和文化本體論為文學理念的一種追求。這種思潮既反對當時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文學,也不贊成共產黨的左翼文學,主張文學應該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意識和自由不應與政治混為一談,反對把文學當作獲取利益的手段。
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對文學自由主義觀念最早闡述的是王國維。他認為文學是“天才游戲之事業”[2],文學活動是一種游戲,在游戲的進行中是超功利性的,既不受到自然規律的強迫,也不受到理性法則的約束因而是自由的。游戲本身并不能成為藝術,要通過人的行為創造使其升華為藝術,而大多數人并不具有藝術家的條件,雖然可以創造出各種各樣的文學,但只有具有一定天賦條件的人才能創造出真正的文學。其核心理論則是借鑒了叔本華的“生活之欲”的觀點,他認為“人之勢力,用于生存競爭而有余,于是發而為游戲……以發泄所儲蓄之勢力。”[3]人只能像鐘表一樣往復于由欲望所衍生的痛苦與無聊中,惟有超功利的文學美才能擺脫這一苦痛存在的根源。文學應該表現人的本質,把創造具有審美價值的文學作為文學創作的惟一目的,反對把文學當作政治輿論的武器,這就從根本上與傳統文學的“文以載道”、“寓教于樂”的觀點劃清了界限。無論社會還是藝術家如果把文學當作獲取功利的手段,那么最終只能導致文學失去其獨立存在的自由和價值。
文學應該以功利性為目的來發展,還是應該作為獨立自由的審美方式來發展,從文學自身演變的規律來看,二者并非是完全對立分割的,文學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本體自由存在的意義,但是在國家民族存亡的時刻,文學如果無視民族變革救亡的意識只單純去追求自身審美價值的完善,那么文學也勢必不會得到繼續存在的價值,勢必會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和合法性。文學的存在必然離不開人的存在,無論是以哪種目的作為文學創造的條件,都必須通過人這一真實存在來完成。現代中國社會的新的文化氛圍,決定了現代文學必須隨時代的演變而不斷調整自身文學結構和內容,承擔新的歷史空間下所賦予的使命與責任。因此,文學功利主義的盛行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日常生活本就有其功利性的一面和超功利性的一面,并不能說哪一方就是絕對的。
二、文學與政治誰征服誰
改革開放后對文學政策的放寬使文學發展有了更為廣闊的空間,提出中國文學應當脫離政治獨立發展,建立自身文學特性。這一觀念的流行“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4]他們認為二十世紀是文學史的世界,那么就必須有別于政治作為獨立學科發展,打破了文學史隨政治分期而分期的壁壘,使文學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保持自身民族文學的特點,從這一點來看,文學具有復雜性、多元性、獨立性,文學與政治是相互獨立而分開的。這在日本尤為明顯,日本文學的傳統就是超政治性,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往往是冷漠的,這些文學者們往往就是單純的文學家,而不用兼顧政治階層。即使在今天的日本,把政治帶入文學里仍被視為低俗。日常生活的超功利性一面,使得文學的創作發展轉為無功利性的審美方向,文學的這種無功利性集中表現在文學家的創作活動和受眾者的閱讀過程中都沒有直接的功利目的,并不要求文學家和受眾者得到利益的滿足,文學接受是超功利性的精神享受,真正的文學無疑是美的,以審美的角度來說文學與政治是各自獨立存在,但并不是絕對的獨立,文學本身是蘊含著“政治的性格”。
綜觀歷史,在中國從封建統治者、地主階級剝削人,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的三重壓迫,社會的階級關系和社會形態發生變化時,文學始終作為反映當時社會變化的特殊意識形態,即便是在當今社會,文學的創作也離不開時下政治格局的動蕩,文學總是被一條無形的枷鎖所桎梏,這條枷鎖就是政治。毛澤東就曾經指出五四文學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文學為政治服務。政治作為上層建筑的代表,是人類生活中覆蓋面最廣、最普通的現象,每個人的行為、環境、命運都與政治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文學又是依附于人的存在而存在,那么政治就很自然地要對文學的產生有影響,文學家盡管潛移默化的淡化文學作品里的政治意識,卻也仍舊在作品里有著自己鮮明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迎合當時社會的政治走向。另一方面文學又折射出政治面貌,文學也可以成為推翻政治的一把利刃。蘇洵在《六國論》里論述了戰國后期齊、楚、燕、韓、趙、魏這六國滅亡的原因,以此來告誡北宋王要需吸取歷史教訓,改變對契丹和西夏的妥協投降政策,以免重蹈歷史悲劇。在五四運動以及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的《藥》通過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才喚醒中國群眾的愚昧,為社會的政治變革帶來一劑強有力的藥。
那么文學與政治,誰征服誰也就因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而有不同的解釋和關系。在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文學與政治的每一方都在征服對方也被對方征服,這里的征服既可以是對對方的認同,也可能成為對抗性的,甚至產生二者之間的逃避、偏離、漠視的狀態。征服的前提是要認同對方的獨立存在,征服不是一方消滅另一方,而是在文學中有政治,在政治中有文學的一種相互滲透關系。從政治對文學的征服角度來看,政治作為上層建筑最有影響力的因素,自然要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一切社會意識形態做出征服,將文學納入政治的世界,文學自覺或不自覺對政治的這種征服做出認同或抵制;從文學對政治的征服角度來看,文學的征服是建立在審美超越性上來關照政治,文學不論是批判社會也好,還是頌揚社會也罷,都是從文學對政治的審美理想出發來評判政治,代表著對社會理想的高度完美化,因而在某些時期,文學會對政治做出否定性判斷并以此成為政治變革的一把利器。這也就是美國從對中國進行政治軍事征服策略轉變為文化征服戰場的原因。
三、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不意味著征服世界
改革開放國力日漸強盛,文學家們借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和開放的國策使中國文學有機會走向世界,這是一個很好的機遇。不巧的是,互聯網的普及,全世界的文學閱讀都走向了一個相對蕭條冷清的階段,以往看的報紙、翻看的書籍如今很多都以被網上電子閱讀所以替代。盡管隨著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世界對中國文學的關注驟然增加,掀起一股學習中國文學之風,但是中國推廣到世界的文學作品依然是有限,這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引領文學潮流的一大壁壘。就目前國際文化競爭中,中國文學還處于弱勢的地位,首先缺乏對自己文學的自信,別人說好的我們就認同是好的,一旦別人說不好就開始懷疑自己的作品,我們的文學作品是為了與別人交流,越是在不平衡的情況下越要保持我們對自己文學和文化的自信與信仰,如果自己都不能對自己的文學產生歸屬感、認同感,又怎能期待受眾者對你認同。正如魯迅所說:“那時我們的祖先對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根據,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心……決不輕易地崇拜或輕易唾棄。”[5]其次中國文學應回歸現實,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的角度結合在一起,莫言之所以能獲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他不避諱社會的黑暗和丑惡,只有寫到人的靈魂深處才能讓文學綻放光芒。每一個文學家的作品,都是一個文本,在這個文本中實現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不在場對話交流,只有讀者閱讀作品感受文本的靈魂才能實現文學的價值。
當前有一種論調認為中國的文學將征服世界,堅持這一論調觀點的往往是那些熱衷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們,又或許是因為西方所謂“中國威脅論”。無論是基于哪種原因,我卻并不認同一種文學可以征服世界。埃及文化源遠流長,但是埃及的文化也隨著亞歷山大帝國的建立而希臘化,而希臘文化被凱撒帝國占領后隨之又被羅馬化,最后又被阿拉伯人給伊斯蘭化。盡管中國文學早在漢代就已經開始與外來文學有了接觸,然后到了晉、唐時代佛教文學的不斷發展,使中國文學作為文化的一支分流部隊把中國文化帶到了亞洲,而且到16世紀開始逐漸走向歐洲,席勒還曾把清代小說《好逑傳》改編為劇本。盡管中國文化和文學在18世紀以前還處于世界文學的頂端,但是這個龐大的封建國家還是把這個國家和文化的所有走向了衰落。馬克思對此說道:“一個人口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而最現代的社會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人想也不敢想的奇異的對聯式的悲劇。”[6]中國文化和文學都受到了嚴苛的考驗,但也在這黑暗的夜空里,中國文學仍然發出新的吶喊使文學有了新的生存方向,那就是尊重個體生命價值和尊嚴。
近些年來,隨著新媒體的發展,當下的主流文學似乎從為政治服務的角度轉向為金錢利益,加上一些媒體的不健康價值觀宣傳,文學家受制于出版商和文化機構,使文學創作日趨低迷和庸俗。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還面臨著許多困難和難題,把中國的文學推向世界,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文學要迎合世界文學的口味,也不意味著用我們的文學去征服世界,而是讓那些人類靈魂深處的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價值作品能更為廣泛的得到世界的認識,這不僅是了解中國的文學,也是了解中國的文化和文明。
參考文獻:
[1]梁啟超.梁啟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29.
[2]佛雛主編.王國維學術文化隨筆[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214.
[3]姚淦明,王燕主編.王國維文集上部[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16.
[4]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漫說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9.
[5]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3.36-37.
[6]德 馬克思等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