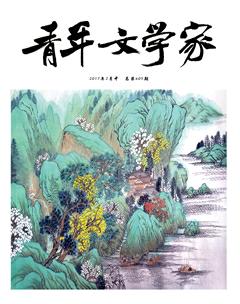從鴛鴦蝴蝶到雙重焦慮
課題項目:陪都時期重慶文化生態對抗戰文學創作的影響,項目編號:2011YBWX082。
摘 要:作為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家,抗戰前期,感時憂國和新舊文學交鋒的雙重焦慮迫使張恨水在創作上由強調小說的趣味性轉向體現抗戰時代的意識形態。本文以抗戰歷史為敘述維度,著重考察張恨水這一時期的創作特色及轉型原因。
關鍵詞:張恨水;抗戰前期;創作特色;雙重焦慮
作者簡介:劉瑜(1969-),女,重慶人,四川外國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女性作家作品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02
1938年,張恨水到達戰時首都重慶,在重慶特殊的抗戰時空里,感時憂國和新舊文學交鋒的雙重焦慮迫使善寫世情小說的張恨水的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轉型:抗戰題材開始成為小說內容的主要元素;由強調小說的趣味性轉為體現抗戰時代的意識形態;從非主流的現代性規范轉向主流現代性規范;以社會言情小說為主業的張恨水由對社會表達的疏離一躍成為中國“抗戰小說”創作量最多的作家。
一、感時憂國的焦慮
1937年,以“七七事變”為標志,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先后從南京移駐武漢,最后決定遷都重慶。伴隨著中央政權轉移的是洶涌而至的大規模的難民潮,“戰爭使人們喪失了在原居住地從事生產、維持生活的基本條件,無奈地告別原本平靜舒適的生活而遷移他鄉”。
張恨水南遷的歷程與抗戰政治中心的南移、抗戰難民的行蹤趨于一致:抗戰前夕,張恨水舉家遷至南京;1937年12月,張恨水赴武漢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第一任理事;1938年1月10日,張恨水奔赴陪都重慶。民族敗退遷移的悲愴、個人漂泊的流亡之感觸發了張恨水對歷史再次重演的隱憂與感懷,發之筆端,乃有《讀史十絕》,這些作為典型抗戰文本的詩歌幾乎首首詠懷國家危亡和南渡史實。
對于從舊文學陣營里走出來的張恨水來說,這些含蘊悠長的詠史詩將抗戰陪都的現實與南朝、宋明亡國南渡的故事微妙地對接在了一起,抒發了詩人內心深處擔憂亡國的思慮以及對國家前途懸而未決的渺茫情緒。與此同時,張恨水重操小說舊業,打通歷史與現實的關聯,于1940年初夏創作了《水滸新傳》。這部作為《水滸傳》續傳的小說明寫梁山群雄抗擊金人入侵,暗線則貫穿了四十年代全民抗戰的精神與氛圍,不難看出作者描寫異族欺凌和中國壯士抗戰的創作抱負。
此時的張恨水已然從鴛鴦蝴蝶派的綺思與輕愁中脫身出來,從他的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陸游、辛棄疾等憂國憂民的詩人的身影在晃動。很明顯,重慶時期的張恨水真正具有了自覺的國家意識,他以詠史詩來表達對國家危亡的擔憂和對政權抗戰不力的指斥,用新編歷史小說來鼓舞國民士氣,“不斷地考慮個人的行為,擴展和上升到國家—民族的意義網中。國家成為敘述關注的目的,而個人的行為則不過是承載這一目的的實體。在個人和國家之間,張恨水決定性地導向了后者,并且通過自己小說的敘述鼓勵了前者為后者而努力”。
從詠史詩和歷史小說可以看出,張恨水的國家意識是受過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反應,他們的憂患意識、“士人風骨”以及接受的儒家文化都使這種國家意識迥異于西方近代社會所形成的以“民族主義”為核心架構的國家意識。換而言之,以張恨水為代表的傳統型文人雖然接受了現代西方人道主義觀念的影響,但主要秉持的還是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將文學作為消閑、趣味的對象固然是大多數中國傳統文人的文學觀,但在民族氣節的問題上,中國傳統文人們絕不含糊。小說情節中只要涉及到國家民族的問題,他們的態度馬上會嚴肅起來,并常常將對國家和民族的態度作為衡量小說人物的人格是否完美的重要標尺。張恨水“抗戰小說”創作的根本驅動力也是來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氣節,其發出的“國如用我何妨死”的壯烈呼聲,正是傳統士人在二十世紀余光未絕的精神返照,也是張恨水國家意識和救亡焦慮最為重要的文化背景。
此外,一個不容忽視的歷史背景是,張恨水感時憂國焦慮的強化與殘酷戰爭的刺激也有著密切的關聯。張恨水是“重慶大轟炸”的目擊者、見證者,與重慶市民一道躲警報,鉆防空洞,經歷了在彈片橫飛、烈焰沖天、房屋倒塌中倉皇奔命的驚險,目睹了大轟炸給重慶造成的巨大破壞和慘痛景象。戰爭的殘酷將個人和國族的命運捆綁在一起,“激發了對現代民族國家的訴求和想象……加入到建構自己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之中”。正是對國家的強烈認同而產生的使命感和焦慮感促使張恨水在抗日的烽煙和炮火中將自己納入到民族國家的前沿陣地, 以筆作為武器表達著自己與國家共命運的意志和決心。他主編的《新民報》副刊“最后關頭”所載稿件都是直接或間接與抗戰有關的:“本欄名為‘最后關頭,一切詩詞小品,必須與抗戰及喚起民眾有關。此外,雖有杰作,礙于體格只得割愛”。他的作品除了正面表現抗戰軍民的英勇以鼓舞民族士氣外,還把那些間接有助于抗戰的問題和直接有害于抗戰的表現都寫出來,張恨水明確表示,“抗戰時代,作文最好與抗戰有關,這一原則是不容搖撼”,與抗戰無關的作品,他不愿拿出來發表唯恐干擾以抗戰為中心的寫作主題。
二、“新舊”文藝交鋒的焦慮
作家生活在特定的意識形態氛圍內中,無意識地接受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抗日戰爭這一特殊的歷史環境,要求作家和文學擔負起民族救亡的使命。就此,這一時期中國作家的文學創作出現了空前的一致性和傾向性:表現民族戰爭中新人的誕生、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與形成,熱烈地渲染昂奮的民族心理與時代氣氛。
處于國統區的重慶由于其陪都的特殊的政治與地理位置,它的文學色彩更加鮮明地打上了抗日救亡的烙印,體現出抗戰文學最為典型的格調與特色。1938年8月,戰時最為著名的文藝團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重慶成立,《抗戰文藝》《七月》《文藝陣地》《文學月報》等文學雜志先后在重慶問世或復刊,隨之文學界收獲了一大批反映抗戰生活的小說。戲劇方面,以“霧季公演”為代表的小劇場運動在重慶的大街小巷流行起來,或鼓舞精神,或抨擊腐敗,一時間街頭巷陌盡是宣傳抗戰的壯烈風景。由于報告文學靈活輕捷、直接迅速,重慶還出現了報告文學的競寫熱潮。與此同時,一大批戰斗詩篇紛紛涌現出來,詩人們用詩歌為民族唱起獨立自由的戰歌。
無疑地,抗日文學“救亡圖存”的主旨最大程度上體現或延續了中國傳統文學以及五四以來現代文學“文以載道”和“感時憂國”的特質。正如夏志清所論,新文學所要竭力表現的是“道義上的使命感、那種感時憂國的精神”,要求文學要有社會使命感, 著重關注文學作品的道德和政治社會意義。在現代文學語境中, 感時憂國著眼現實,密切關注歷史的發展和民族的振興,體現出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職是之故,胸懷家國天下的知識分子無法退守為書齋中的看客,不甘以局外人自居,只能自覺地投入到社會生活中去。
而眾所周知,張恨水的小說盡管在主題、文體和敘事技巧方面都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卻一直被文化精英所主導的主流文學界視為“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其小說所強調的“消閑”、“娛悅”不時遭到新文學人士的質疑和批判。這種質疑和批判固然有文學派別的齟齬的因素,但也不妨視作張恨水小說文本自身品性所折射出的淵源有自的某些特征和要素。從創作伊始,張恨水即和鴛鴦蝴蝶派結下了不解之緣,寫下了大量以曲折感傷的愛情悲劇為主要內容的“言情小說”,運筆所向多著墨于纏綿悱惻、婉約動人的世俗男女愛情故事和悲歡離合、光怪陸離的市井生活。就其早期作品而言,《春明外史》中的李冬青與《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側重于描寫舊式才女的憂傷、敏感、多情、孤傲與現世猥瑣殘酷遭際的捍格;《啼笑因緣》和《夜深沉》的女主角沈鳳喜、楊月容作為淪落風塵的名伶“戲子”的形象亦不乏曖昧的艷情的蠱惑;《秦淮世家》更選取了槳聲燈影里煙視媚行的秦淮河作為敘事背景,難免為人非議。與此同時,加之敘事主題內在的狹隘性,其小說內容不外三角與多角戀愛,結局非結婚即生離死別,個別細節處理如《春明外史》中對狎妓生活的描寫甚至帶有較多的自然主義色彩,以致把才子狎妓也當作真誠的愛情來加以美化。這些無論有心還是無意流露出的帶有鴛鴦蝴蝶派某些特征的小說都給新文學評論者造成了口實。以至于即使20世紀30年代張恨水的小說創作及其影響力達到巔峰之時,仍有以“正統”“主流”自居的新文學批評家們從“新”與“舊”、“先進”與“落后”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出發對張恨水充滿了深刻的偏見,并對他的小說作品及文學觀念展開了持續的圍剿。換而言之,新文學與張恨水為代表的所謂“舊文學”之間已然形成了一種二元對立結構的張力,存在著此消彼長的競爭的關系。
無可諱言,新文學作家營造的以“感時憂國”為基調的抗戰氛圍、所取得的累累碩果以及對抗戰所發揮的實際作用對張恨水的創作心態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在新文學“強勢話語”的重壓和刺激之下,尤其是在重慶這一抗戰中心的語境里,張恨水為了趕上時代的腳步,自覺地調整了寫作藝術風格:他逐漸偏離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為代表的“社會言情”小說的創作類型,摒棄了娛樂、消遣的趣味主義,形成了帶有獨特風格但又符合主流意識形態要求的國難小說和暴露小說系列。可以說,在這一場新舊文學的交鋒里,張恨水充滿了焦慮,他向五四新文藝傳統的“靠攏”充滿了無奈。然而,“靠攏”的結果卻使張恨水獲得了“主流”文學場域某種程度的認可,評論家們對張恨水的轉變也表達出善意的鼓勵和熱烈的歡迎:“恨水創作之可敬,就在于他能利用他的技巧跟著時代,不斷創造新的內容。他以‘鴛鴦蝴蝶派成名,卻能夠斷然舍去使他成名的舊路,描寫新的東西。這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
三、結語:從鴛鴦蝴蝶到雙重焦慮
在雙重焦慮之下,張恨水轉向后的抗戰小說應從歷史的角度加以肯定,但若以文學的標準衡量卻存在相當的弊病。正如論者指出的,張恨水的轉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小說原來所具有的豐富的現代性特征日漸狹仄和枯萎,張恨水在獲得某種“先進性”、“時代性”的同時,被一種充滿了深刻偏見和日漸“窄化”的“現代性”規范所收編和桎梏。具體而言,張恨水以“抗戰—國難”為主題的《瘋狂》《巷戰之夜》《潛山血》《游擊隊》《大江東去》《虎賁萬歲》等小說更大的功用是喚醒國人、鼓舞民氣。在這種寫作主旨的引導下,他不復強調小說的趣味性,加之作家本人對戰爭并無實際接觸,造成了小說結構的混亂、筆法的單調、除了枯燥乏味、毫無新意的戰爭場面描寫外,幾乎毫無“趣味性”可言,甚或有淪為“抗戰八股”之嫌。至于張恨水的暴露諷刺小說致力于尖銳地抨擊、全面地揭露國民政府抗戰時期的腐敗面。以《八十一夢》為例,這部多線敘事的小說以冷嘲熱諷,嬉笑怒罵的筆態,對抗戰時期消極抗戰的將軍、作威作福的豪門,巧取豪奪的貪官,囤積居奇的奸商,陰險下作的特務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與鞭撻,表現出左翼的、激進的、前進的政治意識。但由于放棄了自己的藝術個性,一改典雅而詩意的書面寫作,“平鋪直敘,急于說教,既有拘泥于生活真實而放棄藝術真實的傾向,又有制造巧合圖解觀念的毛病”,墜入了單純暴露、美感不足的兩難困境。
參考文獻:
[1]李潔非:《典型文壇》,武漢,湖北長江出版集團,2008年。
[2]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