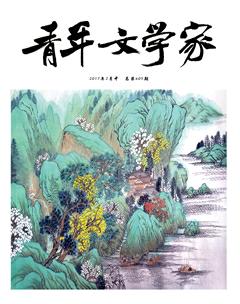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百合花》三元沖突與融合之淺析
摘 要:茹志鵑于1958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百合花》,不久,茅盾就高度評價其“清新俊逸”的風格和精密的藝術手法。[1]然而由于政治環境的影響,《百合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倍受爭議,直到后代評論家反復研讀,它才逐漸被奉為文學史上的經典。
關鍵詞:文學評論;藝術審美;政治
作者簡介:陸韻(1995.11-),女,漢,江蘇省無錫市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大三本科在讀。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02
然而,文學經典作品并非完滿無暇,《百合花》亦是如此。在時代環境、作者個人經歷與創作心態等諸多條件影響下,《百合花》既有藝術審美性上多方面的優點,又有待歷史真實性上的考證,亦不免在政治正確性的大框架下存在突破與含混之處。本文主要圍繞《百合花》政治正確性、藝術審美性和歷史真實三元的碰撞,與《山地回憶》展開比較分析。
一、政治正確性:作者的突破與讓步
1957年,毛澤東發表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使得許多文藝問題與學術問題進入政治領域。茹志鵑寫作《百合花》的時間是1958年3月,正值反右派斗爭緊鑼密鼓之際。茹志鵑一方面對政治局勢大為憂慮,另一方面又對丈夫極為思念,“《百合花》便是這樣,在匝匝憂慮中,緬懷追念時得來的產物。”[2]無疑,《百合花》也必然符合政治正確的大框架。無論是在作品表層的用詞方面,抑或是在作品深層中男通訊員與新媳婦的關系處理上,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性。
首先,在描繪敵軍的用詞方面,作品雖然著墨極少,但貶義極濃,在和諧的文本中顯得突兀,帶有勝利者回憶戰爭時居高臨下的姿態。“要不是敵人的冷炮,在間歇地盲目地轟響著,我真以為我們是去趕集的呢!”,這樣一句感嘆諷刺意味濃烈。“我們的總攻還沒發起。敵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燒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轟炸,照明彈也一個接一個地升起”,解放軍還未開始戰斗,“忌怕”“盲目”等詞以及具現恐懼心理的軍事行動,已經大力貶低敵軍,顯示其在勇氣、策略上的低人一等。通過零度的敘述自然而然彰顯寫作對象的特點,會更具有藝術感染力,然而在政治正確的框架中,作者直接跳入文本中,用褒貶明朗的詞句判定對錯,便失了幾分審美意味的悠長。
其次,主人公之間的情感關系則更服務于政治正確性。茅盾將《百合花》中年輕的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的關系評價為深刻的主體思想,稱其為“軍民魚水情”。然而,這種男戰士與女孩子之間的感情沖突不存在微妙之處嗎?在文本中,作者沒有直接敘述通訊員向新婦借被子的場景,而是側面描寫“我”去借被子時,通訊員的別扭和新媳婦的笑。“她臉扭向里面,盡咬著嘴唇笑。”后來,“她也不作聲,還是低頭咬著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這是一個剛過門沒幾天的新婦嬌俏的笑,糅合著年輕婦女的愛意。全文中新媳婦的笑一共出現五次,這種笑是嬌羞之愛的符號。另一方面,年輕通訊員面對娶親問題“飛紅了臉”。新婦要為他縫衣,他“卻高低不肯,挾了被子就走。”這是一個未經過愛情的年輕人對于愛情問題青澀的回應。[3]但在作品本身中,這種男女之間情感的描寫,卻始終如霧里看花,被做了模糊甚至含混的處理,而刻意地向“軍民魚水情”的恢弘主題靠攏,忽略了人性中隱秘而美好的情感流動。誠然,作者能刻畫出這樣兩個含有愛意的軍民形象,已經屬于同時期文學創作中一大突破,但依然被政治正確性束縛了手腳。
同樣的,《山地回憶》也描寫了戰爭時期男戰士與女性間的情感碰撞,這種沖突更為明顯,但依然被解讀為“軍民魚水情”。從最初的河邊爭吵,到后來妞兒要為“我”做襪子,她先低聲問“不會買一雙?”,后來主動提議說“我給你做”。側面描寫細節處也很多,借大伯之口,“我們妞兒剛才還笑話你哩!”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嗎? ”從大伯的話語中,可以明顯觀察到妞兒對“我”的敬仰和嬌羞的愛意。可最后,這種被慢慢渲染出來的情感卻倉促收尾,“當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發了。”作者始終沒有對他自然描繪出的情感氛圍作出處理,而服務于意識形態,最后歸于軍民魚水的大旗下。
二、藝術審美性:文本細讀尋真味
孫犁的《山地回憶》創作于1949年12月,帶有詩意的娟秀,融合了傳統寫意和現代敘事。這種獨具一格的藝術審美性“影響了一大批派外作家”[4],其中包括茹志鵑。《山地回憶》是以一雙襪子作為敘事的線索,《百合花》則以新被上的百合花作為象征,在結尾還刻意點出“這象征純潔與感情的花”,在藝術技巧上不如《山地回憶》來的自然渾厚。但是,在表現手法方面,《百合花》仍然受到孫犁風格的影響,具有審美品評的價值。
首先,在主人公的人物塑造方面,作者用了正反映稱和徐徐而進的筆法。主人公通訊員不再歌功頌德式的人民解放軍形象,他不完美但人性豐滿,有毛頭小伙常有的急躁和嬌羞,在談到娶親問題時,他“飛紅了臉”“出了大汗”。而在借不到被子時,他還會懊惱急切地罵一句“死封建”。這種急躁懊惱的情態,不僅沒有折損他的形象,而增添了濃郁的人情味,使他的性格更為立體,也為他的正面形象起了反襯作用,使后來他的可愛與可敬便自然地凸顯出來。同時,通訊員的形象也不是突然映入讀者眼簾,沒有通過一開始的外貌描寫來展示,而是通過一個個小情節一筆一劃慢慢勾勒出來,直到最后他“棕紅的臉,現已變得灰黃”,我們才算看清了一些外貌,但實則早已剖析過內部的人性美。
其次,作者善于細節描寫和前后呼應,雖然顯出些許刻意,但仍可稱為經典。作品中的細節與呼應有多處,包括新婦前后對待新被的態度、反復提及的通訊員肩膀上的破洞、通訊員給“我”開飯的兩個干饅頭等等。以通訊員肩膀上的破洞為例,破洞產生于通訊員求助“我”借到新被后,“慌慌張張地轉身走”時勾到的,新媳婦要笑著為他縫補,他死活不讓。第二次提到“我”看到布片“在風里一飄一飄”,“真后悔沒給他縫上再走。”最后則是在通訊員被抬回來后,他的肩膀上仍有大洞,高潮處也在這里產生,新媳婦一改嬉笑和嬌羞的情態,一針一線縫補這個洞。這樣一處細節,把通訊員、新媳婦、“我”三個人物都串聯起來,透露出三個人物之間的情感流動。
再次,《百合花》敘事結構精巧,節奏緩急得當。作者多處避免了平鋪直敘,而用他人的視角展開側面描寫。例如作品并沒有直接描寫通訊員第一次向新媳婦借被子時的沖撞,而采用“我”的視角寫通訊員罵“死封建”的惱怒和新媳婦的笑,留給讀者充分的想象空間,也使后來新媳婦縫補破洞時候的感情迸發顯得更有沖擊力。茹志鵑的著墨處重在生活情景和人物情態的刻畫,擅長簡樸自然地刻畫出可愛的性格,例如“他決定以后,就把我抱著的被子,統統抓過去,左一條、右一條的披掛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這種描寫細致入微的憨態感染力更加勝于恢弘、直接的謳歌,作者在平緩的節奏和清新的敘事中,把褒貶評價的權利留給了讀者,也以這種審美性打動了讀者。
三、歷史真實與歷史縫隙
作者只有真正了解自己作品中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并且有可觀的親身體會,才可能通過歷史真實和細節真實打動讀者。茹志鵑1943年參加新四軍,曾經在部隊文工團工作,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作品寫的是1946年中秋,她自己說過,“小說里描寫的戰斗,以及戰斗的時間地點都是真的,是蘇中七戰七捷之一,總攻海岸線的時間確實是1946年中秋”[5],確切地說,是七捷中的第四戰,目標是收復海安縣城,時間是1946年8月11日夜次日下午。她當時確實在包扎所工作,對戰爭形勢有一定的了解,所以盡管她寫的不是真的人物和情節,卻在寫作中展現出誠與美。
同時,通訊員的形象也有兩位原型考證。一位是萊蕪戰役中一位年輕戰士領著茹志鵑前往包扎所,不敢靠得太近也不能甩得太遠,所以文本中通訊員領“我”去包扎所那一段才寫得極為生動。另外一位則是茹志鵑跟隨汪歲寒戰斗時,深夜臥談認識的年輕戰士,他在提及婚嫁時極為羞澀。這兩位原型考證可見于茹志鵑在80年代的回憶敘述。[6]
但是,茹志鵑寫作的歷史真實僅僅停留在包扎所內部,她對于軍事戰爭的細節和軍人規則也存在不明之處,這種不明朗反映在《百合花》中,使筆者發現兩處存在疑問的縫隙,以作分析。
第一,通訊員向槍管中插入樹枝花朵。文本中出現兩次,先是,“肩上的步槍筒里,稀疏地插了幾根樹枝,這要說是偽裝,倒不如算作裝飾點綴”,其次,“他背的槍筒里不知在什么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樹枝一起,在他耳邊抖抖地顫動著。”這兩處一直被看作描繪通訊員可愛形態的典型之處。但是問題在于,這種行為既不符合軍人心態也不符合軍隊規則。首先,無論一個軍人如何年輕稚氣,軍人不會拿自己的槍進行這種無謂的裝飾,這是軍人的原則問題。其次,軍隊規則也要求軍人珍惜槍支,年輕的通訊員正是因為年輕,更會尊奉軍事紀律,又怎么會產生這種矛盾行為?這處歷史縫隙也體現了作者戰爭經歷的有限。
第二,通訊員撲向手榴彈犧牲到被抬到包扎所這一段沒有任何敘述。當然,出于藝術審美性的考慮,這種交代也許不必要,但卻存在縫隙。可以試想,在激烈的巷戰中,一條狹窄的小巷中有十幾副擔架,敵人從屋頂扔下一顆手榴彈,手榴彈在擔架隊伍當中被通訊員撲擋,這樣一條擔架隊伍也就被阻塞了。擔架隊員查看通訊員傷勢、尋找擔架來抬通訊員、調派人手后,還繼續前進,他們是如何全身而退的?這樣一段時間扔下那枚手榴彈的敵人何不趁勝追擊嗎?解放軍中有一句俗語,“打傷一人兩人抬,打死十人一人埋。”手榴彈的軍事功效在于打傷對方拖延時間,從而一擊致命。敵人怎么會任由這么長的擔架隊伍離開的?這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通訊員的尸首能否回到包扎所,直接影響了《百合花》的小說高潮能否發生。但作者沒有進行任何交代,所以讓被文學情節感動的讀者又對真實性產生疑慮。
在《百合花》中,政治、藝術、歷史三元始終相互碰撞與融合。政治正確性的大框架無疑削弱了《百合花》的藝術審美性,使得其思想情感存在含混,褒貶過明減損了悠然詩意;藝術審美性的需要和作者個人經歷的局限,也使得作品在展現歷史真實時留有縫隙,讓讀者剛剛進入故事情節,又不得不跳出小說之外,存在對于真實細節的疑慮;政治環境和歷史背景又是小說產生的最初養料,斯人斯事都誕生于這種特定的政治和歷史中,成為藝術作品誕生的源泉。在這三元的碰撞和融合中,《百合花》較之同時代的作品,無疑作出了巨大的突破,在思想情感關系、藝術表現手法、清新平實的語言風格方面,和孫犁的《山地回憶》有諸多相近可比之處。《百合花》歷經波瀾起伏的褒貶,我們還需結合政治、歷史、讀者個人經歷、文本細讀研究等,以“知人論世”之法,對其作出公允的評價。
參考文獻:
[1]茅盾. 談最近的短篇小說. 人民文學,1958,(6):4-8.
[2]茹志鵑. 漫談我的創作經歷. 新文學叢論,1980.
[3]茹志鵑. 我寫《百合花》的經過. 青春,1980,(1):47-48.
[4]余志平. 孫犁“荷花淀”風格小說對當代文學的影響. 江西社會科學,2007,(5).
[5]熊坤靜. 短篇小說《百合花》創作的前前后后. 黨史博采(紀實),2014(8).
[6]茹志鵑. 我寫《百合花》的經過. 青春,1980,(1):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