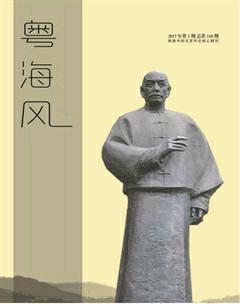紐約所見中國人
譚家健
2010年夏,在紐約探親,小住數(shù)月。接觸附近一些中國同胞,大多是留學(xué)生,博士、碩士;或探親老人,教授、醫(yī)生、工程技術(shù)、教育界人士。經(jīng)歷各不相同,各具個人色彩。幾年過去了,至今記憶猶新。
順風(fēng)順水的陳小姐
到美國第一個認識的中國人是陳小姐。從飛機場到住所的地鐵車廂里,陳小姐坐在我們旁邊。她從我和家人談話的口音中聽出我是湖南人,是從北京來的,便主動問訊并自我介紹,她也是湖南人,北京大學(xué)畢業(yè)的。我說,咱是同鄉(xiāng)又是校友,便遞給她名片和電話。
幾天后,我與家人到附近公園散步。看見陳小姐牽著幾歲的男孩走過來招呼:譚教授,咱們又見面了。接著介紹她的丈夫謝博士,從復(fù)旦大學(xué)到麻省理工,目前在美國著名的高盛公司任職,恰好我兒子也在該公司不同的部門。謝老先生是上海某工廠退休職員,每年到美國半年照看孫子。湖南的外公外婆接著來美國輪替。謝家寓所與我家相距不足三百米,所以互相很快就熟悉起來。
陳小姐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看到我的介紹,真誠地表示要討教。她說,一直對文史有興趣,然而在北京大學(xué)是物理系,到耶魯學(xué)理科,如今一邊工作一邊在耶魯兼讀歷史文化學(xué)博士課程,才開始不久,大約需要五六年時間。她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了解到我出版過中國文化史、中國散文史方面的書,問我哪些書有電子版?我告訴她:八九十年代出版的都沒有電子版,近十來年出版的書,有幾本有,有幾本沒有。最近的是馬來西亞出版的《中國散文簡史》,我的筆記本電腦里有電子版。她想看,我便發(fā)送過去。
不久,她指出書中文字有誤。引《論語·先進》篇“冠者五六人,童子七八人”,應(yīng)是“童子六七人”。是排印錯了而未能校正。后來,她陸續(xù)提出一些問題: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當(dāng)時孔子不過一介民間教師,《春秋》不過一本私人著作,真的能使“亂臣賊子懼”嗎?我舉齊有太史簡、晉有董狐筆,竟使得生殺與奪,不可一世的崔杼、趙盾被迫讓步。說明史官和史書的歷史作用是超政治的。孔子雖無史官之名而《春秋》有史書之實。陳小姐后來又問:王安石說: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可否認為他是反傳統(tǒng)的?我說,所謂“祖宗不足法”是指宋代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所制定的規(guī)章制度已不能充分滿足現(xiàn)實的需要,應(yīng)該“變法”,即擴充、修改,建立新的法規(guī)制度。王安石作《三經(jīng)新義》、倡太學(xué)三舍法,改革以詩賦取士為重經(jīng)義,這些都是對傳統(tǒng)的補充而非反對,故后來以上措施得以延續(xù)。至于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的改革,在現(xiàn)實執(zhí)行中有偏差,失敗了,與反傳統(tǒng)與否關(guān)系不大。
謝老先生夫婦回上海后,湖南的陳老先生到了紐約。多次接觸中得知,陳小姐的祖父在解放前是長沙著名中學(xué)校長,后來是長沙市民主黨派負責(zé)人之一,長沙政協(xié)副主席。陳小姐父親是中學(xué)歷史教師,喜歡藏書,有一間私人圖書館,《長沙晚報》有介紹文章和該圖書館的照片。陳先生出版過一本書《輕輕松松上北大》,介紹如何培養(yǎng)女兒從小學(xué)、中學(xué)到大學(xué)一路領(lǐng)先的經(jīng)驗。我回國后在國家圖書館見到此書。
若干年內(nèi),陳小姐分別寄來兩篇文章:一篇是《春風(fēng)玉門》,仿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筆調(diào),用散文詩一般的語言,描述漢唐幾位公主出關(guān)和番,為促進胡漢團結(jié)和睦而忍辱含垢,作出巨大犧牲;張騫、班超等外交家,為加強中原與西域的聯(lián)系不懈地努力奮斗;衛(wèi)青、霍去病等軍事家,在沙漠中征戰(zhàn),為今天中國的疆域打下基礎(chǔ)。作者熱情贊頌,著力刻畫他們經(jīng)歷的艱辛,特別是內(nèi)心的煎熬。我推薦給中國內(nèi)地一家文學(xué)刊物發(fā)表了。另一篇題為《臺灣故宮所藏宋元明帝王畫像與其隱喻的王朝正統(tǒng)性》,從歷代帝王服飾顏色變化發(fā)掘其中所謂火德、土德、水德的更替過程,直到最后被清乾隆帝所取消。文章涉及五德始終觀念、古代服飾、歷代禮制等復(fù)雜問題,很見歷史哲學(xué)功力。
她寄給我的兩篇文章皆署名“博士研究生”。她已經(jīng)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兼讀高級學(xué)位,很不容易啊。
否去泰來的楊教授
楊教授從武漢某大學(xué)建筑系退休后到美國探親,一個兒子在紐約,另一個在華盛頓,孫輩已經(jīng)上中學(xué),老夫婦兩處輪流居住,所以很輕閑。他和我每天沿河岸散步,來回走一個多小時,談話較多。
他問我:你是文學(xué)研究所的,知道三十年代有個作家楊某某嗎?我說知道,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稱之為“第三種人”。楊教授說,那是先父,于是便談起往事。作家楊老先生是廣東人,年輕時思想激進,寫文章揭露社會黑暗,評論文化界各種現(xiàn)象,曾加入共產(chǎn)黨。三十年代中期到紅二方面軍所在湘鄂西,正趕上清算托派,抓AB團,不少朋友被關(guān)押甚至處死,他嚇壞了,不辭而別跑回老家,宣布脫離共產(chǎn)黨,但繼續(xù)從事文學(xué)批評。右翼不喜歡他,左翼也討厭他,故被稱為“第三種人”。建國后擔(dān)任中學(xué)和大學(xué)教師,反胡風(fēng)和肅反運動,算老賬,挨整,自殺。
我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查找有關(guān)資料,看到近幾年有文章為之呼吁。認為其早期文學(xué)活動對革命有積極作用。二三十年代脫黨而解放后受重用者不乏其 人,建議出版楊某某文集。楊教授說,父親的是非功過怎么評論,做兒子的沒有發(fā)言資格,故鄉(xiāng)的父老鄉(xiāng)親們?nèi)绾蔚卮瑑鹤硬粎⒓佑懻摚蓺v史來作結(jié)論吧。
楊教授談及自己,感慨良多。1956年十七歲上大學(xué),1957年十八歲劃右派。從寬處理,繼續(xù)在校學(xué)習(xí),1961年摘帽,分配到粵北韶關(guān)地區(qū)工作,修橋、筑路、蓋房子,都在深山區(qū)。遇上全國大饑荒,吃不飽,勞動強度大,十分艱苦,靠著年青力壯,挺過來了。七十年代末平反,調(diào)回母校工作,先到學(xué)報編輯部任編輯,做到編輯部副主任,后又擔(dān)任系副主任,從講師、副教授到教授。參加民主黨派,成為武漢市政協(xié)委員,湖北省建筑學(xué)會副會長,退休后任學(xué)會顧問。
他問我:你是兩個全國性學(xué)會的會長,有“好處”嗎?我說:純粹義務(wù)。他說:我這個省級學(xué)會副會長有“好處”,來源是建筑工程驗收,幾乎每次都給紅包。我說,出了豆腐渣工程,追究你們責(zé)任嗎?他哈哈大笑,你聽說過哪幾項建筑事故追究驗收委員會責(zé)任的?得過且過嘛。這些年不參加驗收了,還頂著系一級督學(xué)的頭銜,每年要回校一段時間,對建筑系的教學(xué)作考察、評估,提出整改意見。我問:意見管用嗎?他說,不疼不癢的意見有時能管點用,傷筋動骨不行。比如,評職稱、安排職務(wù)不公正,老師們不滿意,你能變動得了嗎?發(fā)放獎金、津貼不透明,你能改變各種莫名其妙的“照顧”和潛規(guī)則嗎?
盡管如此,楊教授對他的現(xiàn)狀還頗為知足,不像有些人那樣發(fā)牢騷,罵這個那個。他每月有正高級教師退休金,武漢有一套教授級的福利房,在職時編過幾本教材,現(xiàn)在不編不寫了,何必忙忙碌碌跟自己過不去呢?兒子在美國買房子,住了不久發(fā)現(xiàn)有質(zhì)量問題,楊教授可以用英語跟房產(chǎn)公司的工程技術(shù)人員爭論,可以看懂美國的民居建筑工程手冊。“他們糊弄不了咱”,我開玩笑說,你開辦個住宅建筑維權(quán)事務(wù)所吧,中國和美國這類官司多著哩。他輕輕一笑:只為自家維權(quán),管不了別人的事。
不斷跨越的顧小姐
在練習(xí)太極拳時認識杭州來的顧先生,五短身材,頭腦精明,喜歡聊天,以他的寶貝女兒為榮。
顧先生出身于民族資產(chǎn)階級家庭,受過良好的中小學(xué)教育。高考前夕,“文革”開始了,阻斷了大學(xué)之路,進工廠當(dāng)繪圖員。他熱愛文藝創(chuàng)作,常為廠報撰稿,作畫。“文革”后期結(jié)婚,不久得千金,小學(xué)、中學(xué)都是優(yōu)等生。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新加坡到中國招收大學(xué)生,那一年從浙江、江西各招50名。新加坡派人從九月入大學(xué)的新生中挑選,十月送到新加坡學(xué)習(xí)一年英語,然后讀四年大學(xué),接著為新加坡工作五年。前五年的學(xué)費、生活費由新加坡公司提供。顧小姐被選中,家人高興,所在中學(xué)也高興,機會難得啊!
我告訴顧先生,新加坡實施上述人才培養(yǎng)計劃,是九十年代初開始的,我正好在新加坡國立大學(xué)任客座教授。第一批從中國招來的大學(xué)新生,與我兒子是同一年入學(xué)。(小兒是從新加坡中學(xué)畢業(yè)考取的),其中有幾個同學(xué)曾到我家來玩過。顧小姐就讀時,我兒子已經(jīng)畢業(yè)在新加坡工作,并不認識。后來我在馬來西亞大學(xué)任客座教授,經(jīng)常到新加坡。據(jù)朋友們和報紙反應(yīng),中國來的大學(xué)生成績普遍好,畢業(yè)后各公司爭相聘用。
顧先生接著講女兒如何到美國的經(jīng)過。顧小姐在新加坡國立大學(xué)畢業(yè)前夕,考取美國某大學(xué)的碩士研究生,打算去美國深造,新加坡政府不允許。按照合同,工作五年才能離開新加坡,否則要償還五年學(xué)費和生活費,數(shù)額巨大。顧先生多方籌措,向親戚朋友借錢,所得甚微。這時,顧小姐的新加坡男朋友也要到美國深造,其家境殷實,愿意以無息借款方式資助。于是雙雙到了美國。他們倆是戀愛關(guān)系,尚無婚約。然而那位男友把她視同未婚妻,不許接近其他男青年,甚至進行跟蹤。顧小姐很生氣,我不是你老婆,你有什么權(quán)利限制我的正常交際?男友認為,你是用我家的錢到美國的,就是我家的人。顧小姐無法忍受,決定分手。對方提出,必須還錢。經(jīng)過律師協(xié)調(diào),同意畢業(yè)后三年還清。于是,顧小姐在學(xué)習(xí)后期就做兼職,畢業(yè)后拼命工作,表現(xiàn)出色,薪酬不斷提高,而又省吃儉用,果然三年還清債務(wù),不久把父母接到美國同住。
顧先生到美國后,看女兒工作很辛苦,很心疼。二老身體欠佳,無法照顧女兒生活,勸她早成家。經(jīng)過多方尋覓,一位來自中國西北農(nóng)村的男朋友進入他們家庭。為人憨厚誠實,家境貧寒,每年要寄錢回去。我見到顧小姐時,他們正準備結(jié)婚。
顧小姐得知我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xué)任教,我兒子曾在該校讀書,視我為老師,稱我兒子為校友,幾次請我們?nèi)プ骺汀n櫺〗阏勍绿拐\,她說,在新加坡情況您都知道,不必講了。在美國這些年,可以說是多次闖關(guān)。放棄新加坡可以期待的良好工作前景,背著巨大金錢債務(wù)和人情債,硬要到美國讀書,這是第一次闖關(guān)。拼命掙扎,擺脫前男友金錢和情感糾纏,這是第二關(guān)。為了按時還債,一年換一家公司,換一次工資提升一大節(jié),都不是輕易來的,也是一關(guān)又一關(guān)。邁不過去就會摔下來的。目前,顧小姐是一家著名投資銀行交易員,成功一筆交易,收入可能是驚人數(shù)字;如果遭受重大損失,后果難以設(shè)想。風(fēng)險和收益并存,只能一步一步繼續(xù)前進,沒有想過后退。
我兒子說,她所言屬實。美國金融業(yè)是中國留學(xué)生趨之若鶩的目標,職場競爭激烈,淘汰率很高。金融業(yè)充滿冒險性,投機性,一般人是不敢貿(mào)然進場的,只能作些為金融服務(wù)的技術(shù)性、咨詢性工作。
探秘美國基層政治的趙博士
趙博士一家與我兒子同住一所公寓,我們在南樓,他們在北樓,門前庭院里經(jīng)常見面。他很健談,送我一本新著《美國草根政治日記》,副題是“第一本中國人親身參與寫出的原生態(tài)實錄”,中國某著名出版社2005年出版,26萬多字,附有許多照片。我隨便翻閱,很快被那獨特的視角,真實的記述和風(fēng)趣的文筆所吸引。一邊看書一邊就其中一些問題不時向他請教,下面是他的講解與我的讀書體會。
趙說,他在中國是學(xué)法律的,到美國取得博士學(xué)位,工作幾年后,想親身體驗美國基層社會政治和法制實施情況,便加入一個小黨派:美國自由黨,以義工身份參與2004年美國大選助選活動。這本書是2003年10月至2004年11月所見所聞所感知的政治經(jīng)歷。
他首先解釋美國政黨與中國政黨的本質(zhì)不同。中國國民黨(包括同盟會)和中國共產(chǎn)黨都是革命黨,都以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權(quán)為目的,以武裝起義、軍事斗爭為手段。早期的黨員都要有不怕犧牲的精神。
美國的政黨不是革命黨,而是選舉黨。一些政見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目的不是以革命手段推翻政府奪取政權(quán),而是以其政治主張宣傳群眾,爭取選票,得到勝選就成為總統(tǒng)、州長、市長或各級議員,從而推行其主張。敗選者成為在野黨,或為議會中的少數(shù)派,繼續(xù)鼓吹其政見,以爭取下次的勝利。主政黨的黨員不一定能當(dāng)官,因為州長、市長乃至鎮(zhèn)長都是層層競選產(chǎn)生的,不是總統(tǒng)或政黨任命的。各個黨派的黨員身份不固定,政見相合則留,不合則去,入黨退黨自由,平時沒有黨的組織生活,到了選舉年才顯現(xiàn)出來。
趙博士所在的自由黨,人數(shù)很少,根本沒有當(dāng)總統(tǒng)的可能,選上國會議員、州議員都很難。明知如此也要競選,借機表達自己的政見,揭露社會弊端,提出下層民眾訴求。趙參加自由黨之后,主要活動議題就是反對種族歧視,堅持“反毒戰(zhàn)爭”,停止伊拉克戰(zhàn)爭,改善草根生存狀況等等。趙是華人,所宣傳的對象主要是亞裔,包括華裔、韓裔、越南裔等等,活動場地主要是公園、體育場、郊區(qū),租不起大會場。活動經(jīng)費靠黨員捐獻,20元、50元、100元都可以。我看到書中這一部份,覺得像小孩玩游戲。趙認為,他們的同志都是認認真真辦實事,有這班人出來呼吁訴求,總比沉默忍受強。你有話不講出來,別人怎么會理睬你呢。至于成敗,在所不計。
趙的著作大部份篇幅是記述2004年助選見聞。自由黨競選總統(tǒng)、國會議員無望,乃同時支持政見接近的民主黨候選人克里,阻止共和黨人現(xiàn)總統(tǒng)布什連任。趙所在地區(qū)助選團成員都是義工,自己貼錢、花時間、耗費精力,而無任何報酬。第一步工作是培訓(xùn)助選團成員,集合起來講解如何開展工作,并分配任務(wù)。而后一干人馬分別拿著名單到各街區(qū)挨家挨戶動員他們參加選舉,摸清選舉意向,叫做“戶訪”。趙是華人,分配到華人較多的街區(qū),按圖索驥,有的住址寫錯了,竟是監(jiān)獄。有的住家無人,就從門縫里塞傳單。有的有人,卻不開門,“請勿打擾”。好不容易開門了,只說一兩句話:“我支持克里,”“我支持布什”,“我還沒想好”,于是就說服動員,努力爭取支持克里。有時這批人走了,下一批人又來了,是布什助選團“戶訪”了。或先或后,互不相犯,也不爭論,君子風(fēng)度。還有一些助選團員在大型超市出口或體育場館、娛樂場所散發(fā)傳單。這活兒比較輕松,不用多說話,發(fā)完就完事。
接著要參與各種見面會。從自由黨州議員見面會,到共和、民主兩黨候選人與選民見面會、講演會,還有大大小小的各派支持者的造勢集會,以及多黨派的辨論會。趙作為義工有時去維持秩序,有時是聽眾,力求一睹克里或布什風(fēng)采。有時是沖著助選的名人去的,如前總統(tǒng)克林頓來了,某歌星來了,一定會唱她最拿手的歌曲,以吸引好事者。趙著的這一部份,描寫生動具體,各色人等,形態(tài)互異,妙趣橫生,語言幽默,每每使人忍俊不禁。
到了投票日,助選團員開著自己的車,到各處去接選民,主要是那些年老體弱,出無車、食無魚的窮人。到了投票站,還要幫他們填選票,如何簽名,如何按電鈕確定等等。我看到這一部份不免心里嫌煩,真佩服趙博士們白干活的耐心。
選舉結(jié)果終于出來了,布什勝出,克里敗選。自由黨的總統(tǒng)候選人得票百分之零點三。兩名州議員得票僅百分之十幾,黨員們并不在意,重在參與嘛。
我問趙博士,辛苦了一年,收獲了什么?他說:我沉到底層,親身探秘,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書本里是得不到的。中國的朋友看到我的書,有人約我去國內(nèi)開會,講演,或約稿,寫文章。能夠?qū)χ袊x者了解美國基層政治有所幫助,我已經(jīng)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