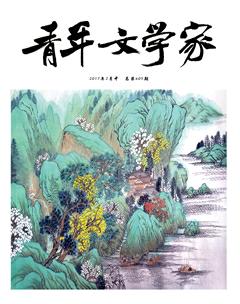社會(huì)邊緣人的思考
王超
[中圖分類號(hào)]: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7)-05-0-01
緒論:
村上春樹和王小波可以說是兩位不同于中日文壇主流的兩朵“奇葩”,兩位“另類”,他們的思想與風(fēng)格均不同于各自國(guó)家的文壇的主流和大多數(shù),曾經(jīng)都被視為社會(huì)邊緣人,而現(xiàn)如今他們的作品與思想?yún)s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與推崇,雖然這兩位作家素未謀面,但是他們二位卻被評(píng)論家稱為“具有相同質(zhì)地的靈魂”[1]的人,而且經(jīng)常被相提并論,可見他們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所以厘清他們相互作品之間的關(guān)系,理解他們作品風(fēng)格、精神之間的相同與不同變得越來越重要。本文將從人物形象出發(fā)對(duì)這兩位“時(shí)代邊緣人”來進(jìn)行深入分析比較,希望從中能夠找尋他們之間“相同質(zhì)地的靈魂”。
(一)人物精神——孤獨(dú)個(gè)體的形象
在他們的作品中無論是村上春樹還是王小波的人物精神都是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首先作為社會(huì)邊緣人的主人公,他們的思想孤獨(dú)且迷茫,失望且彷徨,面對(duì)社會(huì),他們掙扎在反抗與不得志的邊緣,面對(duì)生活,他們迷失在孤獨(dú)與不理解的迷宮里,社會(huì)中人際關(guān)系在他們的眼中是可有可無的,或者他們更在意的是自我的感受,與自我的自由,而選擇回避這些讓他們感到麻煩的關(guān)系。在《海邊的卡夫卡》田村卡夫卡選擇離家出走,選擇一個(gè)人孤獨(dú)的尋找自我;在《挪威的森林》木月之所以自行結(jié)束生命,無非就是因?yàn)橥找孀兓纳鐣?huì)無法溝通無法相適應(yīng),綠子和永澤也是不止一次的說“孤獨(dú)的要命啊”,王小波《黃金時(shí)代》的王二也在知青的歲月感到孤獨(dú),想要尋求解脫。
(二)村上春樹與王小波人物精神的區(qū)別
1、村上春樹:渺小的微光、個(gè)體的矛盾
村上春樹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xué)獎(jiǎng)時(shí)發(fā)表了他著名的演講詞:“以卵擊石,在高大堅(jiān)硬的墻和雞蛋之間,我永遠(yuǎn)站在雞蛋那方,我寫小說只有一個(gè)原因,就是給予每個(gè)靈魂尊嚴(yán),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yáng)光之下。”[2]我想這段話可以看做村上作品的一個(gè)高度凝結(jié)與概括,為每一個(gè)脆弱而渺小的個(gè)體抒寫他們的時(shí)代,為他們尋找自我的意義,為每一個(gè)人孤獨(dú)的個(gè)體譜寫他們的內(nèi)心之曲。無論是《且聽風(fēng)吟》中的“我”和“老鼠”,還是《舞舞舞》里的五反田,還是《海邊的卡夫卡》里的中田聰還是田村卡夫卡,還是《挪威的森林》中的直子,村上筆下的主人公往往是作為一個(gè)社會(huì)中脆弱而孤立的個(gè)體出現(xiàn)的,這個(gè)獨(dú)立的個(gè)體的外殼下往往是寂寞、空虛、孤獨(dú),而其內(nèi)核是對(duì)世界或者是對(duì)社會(huì)的反叛,對(duì)信念的堅(jiān)持,對(duì)希望的追求。他們處于社會(huì)的邊緣或者下層,沒有服從這個(gè)荒誕社會(huì)的秩序,他們時(shí)刻孕育著反叛,內(nèi)心深處的反叛卻經(jīng)常以孤獨(dú)、惆悵、麻木、無助來展現(xiàn),對(duì)命運(yùn)時(shí)刻想要反抗,卻時(shí)刻無法反抗。兩種相互抵觸的思想在村上筆下的主人公身上共存——頹廢與積極、彷徨與向上、絕望與希望,村上筆下的主人公就是這樣矛盾的結(jié)合體。就像《挪威的森林》里面的渡邊,他就有一種深深的孤獨(dú)與寂寞時(shí)刻縈繞在心中,書中的永澤就曾經(jīng)這樣評(píng)價(jià)他:“他和我一樣,在本質(zhì)上都只對(duì)自己感興趣的人,只不過在傲慢上有所差別,自己想什么,自己感受什么,自己如何行動(dòng),除此之外對(duì)別人沒有任何興趣,所以才把自己和別人分開考慮。”[3]我們看出村上春樹小說中的主人公惆悵與頹廢,始終想要找到自我的意義。
2、王小波,一個(gè)人從容的自由
誠(chéng)如王小波的妻子李銀河形容小波一樣,自由、詩(shī)性、精神騎士,他就像一頭駱駝一樣[4],他沙漠中孤傲的走著。王小波努力在他的作品中為我們構(gòu)建屬于個(gè)體的獨(dú)立精神王國(guó),為個(gè)體而吶喊,為有趣而奮起。他卻不太像村上的筆觸總是顯得那么寂寞、淡然,我明顯能感覺到在王小波筆下為人物跳動(dòng)著的心律,他總是以第一人稱敘事來寫小說,在當(dāng)中我們能夠感覺小波對(duì)于主人公所注入的熱情與力量,我們亦能感受到小波的才思與幽默,所以小波筆下的主人公總是充滿了一種向上的氣氛,不管周遭的環(huán)境有多艱難與困苦,但時(shí)時(shí)刻刻總會(huì)有像一個(gè)樂天派似的充滿樂觀,用自己樂天派的想法去戰(zhàn)勝、反諷那個(gè)時(shí)代的荒誕與不正常。例如在《黃金時(shí)代》中,主人公王二因?yàn)榕c陳清揚(yáng)所謂不正當(dāng)關(guān)系被發(fā)現(xiàn)后,黨組織讓他們寫交代材料,王二繪聲繪色且不失幽默的將他與陳清揚(yáng)的關(guān)系描寫出來,本來應(yīng)是他們的交代“罪行”的材料,卻成為審查者津津樂道的話題,在開批斗會(huì)的時(shí)候,臺(tái)下的看客忘我的高喊:“打倒王二,打倒陳清揚(yáng)。”臺(tái)上的王二也振臂高呼:“打倒王二,打倒陳清揚(yáng)。”對(duì)于荒唐時(shí)期的荒唐,小波從來不會(huì)有悲情的控訴,而是在微笑中從容中捍衛(wèi)了個(gè)體的自由,讓個(gè)體在時(shí)代中的價(jià)值閃爍別樣尊嚴(yán)的光芒,他的“時(shí)代三部曲”,再到他的其他小說,我們能清晰的感覺到小波筆下的這個(gè)“我”是一個(gè)正常的普通人,同每一個(gè)人一樣都會(huì)有一點(diǎn)點(diǎn)幻想,一點(diǎn)點(diǎn)個(gè)性,一點(diǎn)點(diǎn)對(duì)兩性的渴望,但是在一個(gè)異化的時(shí)代,一個(gè)異化的世界下,個(gè)人的獨(dú)立與追求變得不正常與不正確,所以小波筆下的主人公在不斷想要排除這個(gè)荒唐社會(huì)的影響,追求一個(gè)正常人的自由。
結(jié)語(yǔ):
村上春樹與王小波筆下共同的社會(huì)邊緣人的人物形象,讓我們看到了兩位作家彼此相同的思想內(nèi)涵與人生追求,讓我們更加深入的了解了他們?cè)谌宋镄蜗笊系南嗤c不同,我想在今天這個(gè)追求多元、個(gè)體尊嚴(yán)與價(jià)值的今天,更多了一份現(xiàn)實(shí)意義和借鑒意義,或許二人的思想能夠?qū)ξ覀兊奈磥碛兴砸妗?/p>
參考文獻(xiàn):
[1]林少華. 村上春樹與王小波之間[N]. 中華讀書報(bào)2007-12-21.
[2]村上春樹. 耶路撒冷文學(xué)獎(jiǎng)獲獎(jiǎng)演講[M]. 東京:文藝春秋 四月號(hào)2009 p20.
[3]村上春樹. 林少華譯 且聽風(fēng)吟[M].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1.8 p71.
[4]李銀河.追憶生命的愛人王小波[J]. 河北:燕趙都市報(bào),2003.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