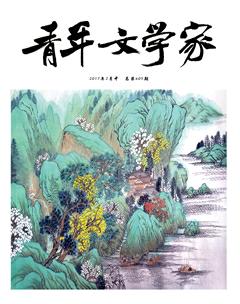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談宋代理學背景下的“思無邪”
楊怡
摘 要:本文主要以兩宋理學為學術背景,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討論傳統儒家詩教思想中的“思無邪”。結合兩宋“政治文化”的背景,闡述兩宋理學家有關“思無邪”的代表性對論述,借以說明兩宋理學家對“思無邪”這一概念的理學闡釋上承漢唐,下啟明清,有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是兩宋“政治文化”的產物。
關鍵詞:宋代理學;思無邪;政治文化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02
自兩漢經學起,《論語·為政》中的“思無邪”三字已成為評價中國古代詩歌、文章的重要理論標準。相應的,漢代之后的學者也不斷對這一標準進行新的闡釋,可謂眾說紛紜。綜觀歷來學者對“思無邪”的闡釋,多以“思想純正”為“溫柔敦厚”詩教理想的佐證,當代學者也認為“思無邪”意味著“中正平和”的中庸思想。兩宋時期,文人地位極高,理學肇始,對“思無邪”的闡釋進行斷代討論,宋代無疑是較好的選擇。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認為宋代理學生長的土壤乃是兩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作為重要的社會轉型期,自宋太祖起,宋代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上體現了較強的重文輕武色彩,愈趨完善的科舉制令寒門學子真正實現了布衣取士,士大夫階層因此得以興起。北宋時期,高舉儒學復興的旗幟的宋代理學的興起,成為多數士大夫寄托自身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負的一門學問。根據這種學術背景,我們可以從宋代“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理解宋代理學家眼中的“思無邪”。
東漢鄭玄稱“思無邪”:“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1]魏何晏《論語集解》援引東漢包咸語: “蔽,猶當也。思無邪,歸于正也。”[2]二者都強調了“思無邪”中的“無邪”, 也就是說《詩經》中的詩歌思想純正,能夠做到“歸于正”。清代劉寶楠則在《論語正義》中對“思無邪”作出了總結性的闡釋:“言心有所念,能容之也……詩者,思也……系于作詩之人,不系于讀詩之人……原夫作者之初,則發于感發懲創之苦心,故曰思無邪也。”[3]這一闡釋綜合了前人“歸于正”的看法,且著意于作詩之人的思想“純正無邪”。北宋經學家邢昺向為后代理學家推崇,他稱“思無邪”一章:“言為政之道在于去邪歸正,故舉詩要當一句言之……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都歸于正。”[4]總結以上言論,宋人對“思無邪”的闡釋有著明顯承上啟下的特征,漢代學者解經多就基本的文意出發較少牽涉“為政”,而宋代學者注經則更多的涉及政治層面的問題,推之于以政治文化為生長土壤的宋代理學家,他們闡釋經典也往往從“為政之道”的角度考慮。
既然以宋代理學為限進行討論首先應該明確宋代理學的界分。理學流派很多,這里要說的是廣義的理學,包括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道學和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
一、北宋理學家程頤認為:“‘思無邪者,誠也。”[5]與鄭玄的解釋相當,這里的“思”也解作“思想”,“誠”則可以理解為“正心誠意”,也就是說,程頤認為《詩經》中的作品能夠做到正心誠意,表達善而非“邪”。從理學觀點上看,程頤主張“性即理”,聲稱人的本性與天地萬物客觀的“理”相和,事關基本道德準則的“理”乃是人生存的根本,因而詩歌、文章需要如《詩經》般“修辭以立誠”,表達良好的、符合“理”的思想。當代學者陳來稱理學“以儒家的圣人為理想人格,以實現圣人的精神境界為人生的終極目的。”[6]程頤承繼中唐韓愈復興儒道的理想,師承宋初標舉“文以載道”的周敦頤,他對思無邪的解釋流露出重振儒學道統的使命感。那么,結合程頤的具體主張,不難看出他的目的在于使理學思想能夠從文化層面有效過渡到上層建筑,構建“合理”的社會秩序,因而學術思想之外,程頤的解釋也顯露了他的政治理想。
二、朱熹是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在《論語集注》中說:“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7]朱熹顯然比程頤表達的更為明顯,指明《詩經》中表達“善”的作品能夠使人得“情性之正”,而這段評述明顯的特征是他強調了詩感發讀者的作用,并且這種感發是有善惡之別的。關于這點,朱熹又說:“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也。”他認為《詩經》中大有“淫詩”在,讀者應該學會分辨善惡,從而使得“善為可法,惡為可戒”。[8]朱熹基本繼承了二程的理學思想,但是更加系統深入,他認為每個人都與普遍的“理”存在著必然的關系。他闡發“性即理”比程頤更進一步,他把“性”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天命之性”都是善的,與天地之理相統一,“氣質之性”則因人稟氣有清濁之分而產生善惡之別,既然對每個人來說“天命之性”是沒有差別的,那么就可以用以儒家道德準則為基準的“理”來啟發人的“天命之性”,從而使復興儒學道統、構建符合理學要求的社會秩序成為可能。這就從另一個層面解釋了朱熹為何從讀者角度對思無邪進行闡釋,也使他的闡釋相較程頤具有更為明顯的政治意義。關于這一點,身處清末同樣處于社會變革時期的康有為對“思無邪”的看法可以與朱熹互為佐證。康有為《論語注》稱“……詩意無窮,然執要守約,以一言以貫之,則思無邪盡之。”[9]這同樣是說“思無邪”即是要求詩歌做到思想純正、中和不偏,但康氏繼而總結道“(詩)乃人情之至,風俗之原。惟使之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淘汰其逸邪,而揚詡其神思,則繼三百而作可也。”[10]這里的“淘汰”、“揚詡”說的都是讀者的主觀行為,康有為身處社會大變革時代,極力變法以革舊制,但他仍然特崇《論語》,其所重即是《論語》使讀者“歸于正”的社會功用。
三、心學是理學中的重要派別,對“思無邪”有著自己獨到的闡釋。陸九淵的學生楊簡認為孔子刪詩“取其無邪,無邪即道心。”[11]這段評述直接把“無邪”對等于“道心”,拋棄程朱理學中宇宙根本的“理”,因而“道心”雖然是朱熹著重闡釋的概念,但是楊簡的闡釋更具有心學特色。楊簡的老師陸九淵雖然也認為存在著一種代表普遍道德準則的“理”,但是理在人心、“心即是理”,因而“六經注我”而非“我注六經”,這就解釋了楊簡為何直接把“思無邪”與道心對等起來,“道心”在楊簡那里就是陸九淵所謂的“本心”。陸九淵曾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12],因此不同于朱熹的“格物窮理”,他的格物格的是“本心”,言明要以人們自有的、內在的道德素養為基礎來做功夫。盡管這種學說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但是不同于主張出世的佛、道二教,心學是積極入世的。余英時認為兩宋是士大夫主體意識崛起的時代,陸九淵的學說正體現了這種強烈的主體意識,他一生中與朱熹多有辯論,卻有著共同之處:企圖用自己的學說來宣揚儒家道統,進而參與政治生活。
四、為更好的理解兩宋理學家對“思無邪”的闡釋,可以對比并非理學家的蘇軾對“思無邪”的闡釋。對“思無邪”三字,蘇軾可謂情有獨鐘,被貶惠州時他就將居所取名為“思無邪”。在《論語說》中,蘇軾曾引《周易·系辭》佐證自己的觀點:“《易》稱:‘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有思者,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13]他認為有“思”則“邪”,無“思”則“無邪”,也就是說為文應該任憑性情,這有著明顯的老莊思想特征。在理學家那里,無論針對作者還是讀者,“思”所代表的思想都應是理性的,因而蘇軾的解釋與其時理學家的觀點大相徑庭,也因此受到一些理學家的批評。觀點雖相齟齬,蘇軾生存的環境與理學發生的時代背景畢竟相同,他與其時的理學家們都處于兩宋士大夫階層,而同是一心報國的蘇軾相較其時的理學家們仕途更加多舛。從這個層面出發,重新理解蘇軾對“思無邪”的看法,在老莊之外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與宋代心學的相通之處。楊時的“不起意”雖然意旨在不起私意,但配合其“神明妙悟”注重內心體驗的觀念,他實際也描述了一種無思無為的精神境界。蘇軾對“思無邪”的鐘情也是一種對個人精神境界的追求,而理學家們關注“理、氣、性”、講求格物致知,追求“天人合一”、“內圣外王”,首先就要在自身修養上下功夫,他們與蘇軾區別在于用世與出世,而且他們思想闡發的方式也更加傾向于現代意義上的哲學。
綜合兩宋理學家對“思無邪”的注解,比照蘇軾的獨特闡釋,可以看出理學家對“思無邪”的理解都以自身的理學觀點為基礎,在宋代士大夫階層地位空前提高的形勢下表達著自己的政治訴求。陳來先生在《宋明理學》中的一段話可以作為這一點的佐證:
新儒家的努力構建社會所需要的價值系統,并將其抽象為天理,同時將其規定為人性的內涵,體現為強烈的價值理性的形態。另一方面,努力在排斥佛道二教出世主義的同時,充分吸收二教發展精神生活的經驗……建立基于人文主義的并具有宗教性的精神性。[14]
余英時認為兩宋“政治文化”的發展分為建立期、定型期及轉型期三個階段,其“延續大于斷裂”,[15]都處于兩宋政治文化的發展的整體之中。處于“政治文化”定型期的程頤承繼建立期范仲淹提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提出“天下治亂系宰相”, 處于轉型期的朱熹、陸九淵和楊簡則在王安石變法失敗的背景下,發揚兩宋士大夫精神,追求“內圣外王”的精神境界,同時積極出仕從政、開辦學校以踐履他們的理學思想,成為兩宋“政治文化”的核心構成。由此觀照“思無邪”,在新儒學復興道統的旗幟下,在帶有較強價值理性色彩的兩宋理學的闡釋下,《論語》“思無邪”一語出現了“思想純正”、“中正平和”等多種闡釋并逐步發展為“溫柔敦厚”詩教學說的重要注腳。
注釋:
[1]唐·孔穎達《毛詩正義》,《武英殿十三·注疏》本。
[2]魏·何晏《論語集解》(元盱覆宋本),第23頁。
[3]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40頁。
[4]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 。
[5]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6]陳來《宋明理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6頁。
[7]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8]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9]清·康有為《論語注》,中華書局,1984年,第17頁。
[10]同上
[11]宋·楊簡《慈湖詩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轉引自陳來《宋明理學》,第146頁。
[13]宋·蘇軾《論語說》
[14]陳來《宋明理學》,序言第10頁。
[15]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聯書店,2004年,序言第10頁。
參考文獻:
[1]陳來《宋明理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
[2]程剛《“易無思”與“思無邪”—蘇軾對于“思無邪”的獨特闡釋》,暨南學報,2012年第3期
[3]清·康有為《論語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4]柳詒徵 《中國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錢穆《論語新解》,成都:巴蜀書社,1985年。
[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8]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