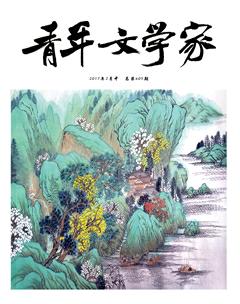談《史通》之人物記載史觀
摘 要:歷史上賢明大德之人被遺忘沒有記載,這是誰的過錯呢?當然是史官的過錯了。那么,選定人物載入史冊的標準原則是什么呢,就是“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后”,載入史冊的人物必須要其惡行可以警戒世人,其善行足以示范后人這樣的人物才能夠而且必須記載到史書里,這是史官的責任。
關鍵詞:人物;載入史冊;標準;警戒世人
作者簡介:夏玉嬌(1991-),女,漢,吉林省吉林市人,碩士學歷,研究方向為中國語言文學古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01
唐代著名史學家、編輯學家劉知幾的《史通》歷來被推崇為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與中國第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文心雕龍》享有同等地位。宋代學者黃山谷說:“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書不可不觀,實有益于后學”。劉知幾在《史通》中分別對史書中的敘事、評點、紀傳等方面進行了評說,其中,對史書中對歷史人物的記載更是有獨到的見解。
劉知幾在《人物第三十》開篇便寫道“夫人之生也,有賢有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1]歷史上賢明大德之人卻被遺忘沒有記載,這是誰的過錯呢?當然就是史官的過錯了。那么,選定人物載入史冊的標準原則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句話“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后”,載入史冊的人物必須要其惡行可以警戒世人,其善行足以示范后人這樣的人物才能夠而且必須記載到史書里,這是史官的責任。劉知幾在人物篇中主要說明了以下幾點觀點。
一、闕如
作者舉例《尚書》說明其中虞舜的八元八凱,夏朝的寒浞,殷商的飛廉、惡來等人,這些人有的是行善積德聲明蓋世之人,有的卻是罪惡滔天的人,但是這些人《尚書》中卻沒有記載,這是很大的損失。作者也認為《三傳》的編纂也遺漏了很多功成名就,可以激勵世人的人物。在作者看來,只要是此人的善行能夠給后人做出榜樣,此人的惡行能讓后人引以為戒就應該記載在史書中,讓后人能夠以史為鑒。也就是說被載入史冊之人要么是大善人,要么是大惡人,這樣的人不能給遺漏掉。還有一類人也不能夠不記載,那就是與當時重大政治事件相關的人也需要記載。
作者總結出三種人,大善人、大惡人和與政治相關的人物需要史官記載,如果這些人都不記載那就是史官的過錯了。史書的人物記載不能“網漏吞舟,過為迂闊”。
二、濫如
對有關時政的正反面人物不可缺書,但對那些才不拔萃、行不逸群的“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丑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對于這樣的小人物, 缺之不足為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清責其譜狀,征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2]。
劉知幾認為史書的編纂最次等的就是簡單的事件羅列,沒有標準的記載。史學著作對歷史事件的記述只是一種手段,更重要的是其中要滲透作者的價值評判,要使史學作品成為社會的價值尺度。劉知幾心目中最高的史學典范是《春秋》,最低檔次的史學著作便是“整齊故事”,即只能把事情排比起來罷了,言外之意《史記》就屬于這個檔次。而記載人物也是如此,像“《漢傳》之有傅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這些人有的才能并不突出,有的行為并不超群,僅僅以一點小善行而為別人知曉的人物就無需記載了。
作者認為史學的最高典范應該達到這樣一種境界,既以好善為主,又能以嫉惡為次,并且又有文飾。符合這一要求的,只有《左傳》,而《史記》僅僅達到其中的一個方面。“‘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何則?史者固當以好善為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以降,吾未之見也”。人物的記載不能將有一點點的小善行就為記載的標準,就為其著書立言,這樣就失去了史書的勸誡教化的作用。
三、不當
作者認為有一些史書中對人物的記載是不當的。劉知幾提到《史記》中把伯夷、叔齊作為開頭,認為這樣的編排是狹隘的,在作者看來,應該將人物分類并且按照年代順序編排。他對《史記》中各篇目的編排次序提出批評:“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并編。此所以為短也。”[3](《史通·二體》 )顯然,劉知幾認為史書中同類人物的編排只能是按出生時間的先后順序,至于為什么,他沒有作出解釋。這是《人物第三十》提出的人物記載不當處之一。
劉知幾對于選取所記載人物的觀點可謂也體現他整個的文史觀。簡單看僅僅是三點“闕如、濫如、不當”的要求,然而再細細探究,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內心對于歷史上的人物記載的責任感。編輯工作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沒有編輯,就不會有篇籍;沒有篇籍,就不會有文化的繼承;沒有文化的繼承,“則善惡不分,妍媛永滅者矣”。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他們的光輝事跡,何固而無?何時不存?但“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歷史上一切篇籍的存毀,也同一個人的命運一樣,假如“時無識寶,世缺知音”,也“將煙盡火滅,泥沉而絕,安有段而不朽,揚名于后世者乎!”由于歷代編輯的辛勤勞動,才有浩如煙海的古代圖書保存下來,“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筐,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人們學習文化知識,學會如何做人的道理,都離不開由編輯們編撰和不斷整理的篇籍。“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參考文獻:
[1][2][3]劉知幾.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