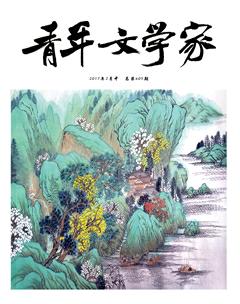試論島崎藤村《家》的社會性
摘 要:島崎藤村的名作《家》通過典型描寫小泉、橋本兩大舊家走向衰敗過程,對明治時代封建舊家走向衰敗的過程進行了真實再現。同時,作者通過冷靜、細致的筆觸,真實地描寫了封建家族制度所強制的個人犧牲,真實表現了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合理性。作者借三吉之口,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家族制度,對其進行了猛烈批判。雖然其批判還不夠徹底,但小說所具有的社會性值得高度評價。
關鍵詞:《家》;封建家族制度;社會性
作者簡介:陳知清(1988-),男,河南南陽人,湖北民族學院外國語學院日語系教師,研究方向為日本近現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5
引言:
島崎藤村(1872-1943年)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1897年發表《若菜集》,開創了日本近代詩歌的新時代,隨后發表《一葉舟》(1898年)《夏草》(1898年)《落梅集》(1901年),君臨日本近代詩壇。之后他轉入小說創作,1906年發表《破戒》,開創了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新時代,《春》(1908年)《家》(1910-1911年)《新生》(1918-1919年)《黎明前》(1929-1935年)均是其代表作。《家》是藤村的自傳性作品,描寫了小泉家(以島崎家為原型)和橋本家(以藤村長姐園子的婆家高瀨家為原型)兩大地方上的舊家族從1898年夏到1910年夏十二年的歷史。日本近代文學研究界對于藤村《家》的研究,以平野謙、吉田精一、三好行雄、関良一、十川信介等為代表主要從《家》的主題、構造、描寫方法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國內對于藤村《家》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與巴金《家》的對比研究上。《家》雖然是一部自傳性很強的作品,有時甚至會被劃入“私小說”的行列,但是這部自傳性作品卻具有明顯的社會性,筆者試從作品的社會性這一角度分析這部小說,以下將具體分析。
一、走向衰敗的兩大舊家
小說從小泉三吉訪問長姐種的婆家木曾福島的橋本家開始。作者首先給我們描寫了這一地方封建舊家的繁榮景象。在那里三吉看到的是“光潔的地板”、“漆得發亮的碗櫥”、“高大宏偉”的房子,以及奮發圖強的家長橋本達雄。橋本家以達雄為家長,其妻種,長子正太,長女小仙,另有男傭六人。三吉為小泉家末男,其上有長兄實,次兄森彥(三歲時過繼給三吉舅舅家做養子),三兄宗藏。三吉的長姐種將小泉家和橋本家聯系在一起。
小說上卷第一章、第二章描寫的這一富足、繁榮的橋本家后來卻逐漸走向衰敗。家長達雄亂搞女人,且不加悔改。此外在他擔任地方銀行要職期間,受小泉實請求,將銀行資金投資給實的投機事業,結果實投機失敗,達雄受此牽連,舍棄妻子、家庭,偷偷地攜帶平時相好的藝妓私奔,輾轉名古屋、神戶,最后逃亡滿洲。達雄出走之后,留下了爛攤子,值錢的東西都被搬走,橋本家在形式上雖然勉強維持了下來,但已失去昔日繁榮。料理完父親達雄留下的爛攤子之后,正太將橋本家的制藥生意交給年輕的男傭們,自己前往東京打拼,以振興舊家。來到東京的正太在兜町從事股票交易工作,將在股票投機中掙的錢也用在了亂搞女人上。后來兜町的股票投機事業失敗,前往名古屋準備東山再起,再一次以失敗告終。正太終因身心交瘁,患病早死。結果,橋本家唯一的兒子正太早死,只留下主婦種和大腦發育不良的女兒小仙,橋本家的血統由此中斷。
橋本家逐漸走向衰敗,小泉家也未能幸免。小泉家的家長實“有一個被尊為‘一村之長的大地主父親”。《家》是一部自傳性很強的作品,小泉實以藤村的長兄秀雄為原型,實的父親小泉忠寬則以藤村的父親島崎正樹為原型。島崎家在信州馬籠是世代擔任本陣(江戶時代,中山道上專為過往大名等提供住宿的旅館)、莊屋(類似于村長)和問屋(批發商)的地方豪門。忠寬“終生過著憂悶的生活,在彷徨之余曾經遠離故鄉,為國家大事而奔走”,終因理想與現實的不一致而導致發瘋,最后被關進家里的禁閉室,發瘋而死。藤村晚年以其父為原型創作了《黎明前》,對其父及維新歷史進行了詳細描寫。實十七歲繼承家業,“父親在世的時候,他在地方上已經被選為郡議會議員和縣議會議員,是個深孚眾望的人物。以后他來到城市,從事過種種事業,一樁樁都失敗了。從經營制冰開始,后來在經濟上一個虧空接著一個虧空”。實后來經營自來水鐵管,因涉嫌違法,被逮捕入獄。出獄后,他又輕信他人,投資人動快進車事業,結果又以失敗而告終。隨后實又進行第四次投資(小說中沒有具體交代投資什么事業),再次失敗,并二次入獄。其妻子、女兒由三吉和森彥來養活。第二次出獄后的實已年逾五十,森彥、三吉為避免其重蹈失敗覆轍,敦促其前往滿洲。
小泉、橋本兩大舊家隨著明治維新的開展、近代化的推進,逐漸走向沒落,這并不是特例,而是典型代表。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在各個領域進行了改革,士族的特權被分階段剝奪。經濟上失去特權的士族們,為了生計,只好開始從事工商業或農業。一些歸農士族通過“土地低價払下”(払下:政府向民眾出售、轉讓)購買土地,成為地方中小地主。而那些從事工商業的士族,因為“士族的商法”不斷失敗,其家亦逐漸衰敗。小說中,無論是橋本家的正太,還是小泉家的實,均一次次嘗試各種投機性事業經營,并一次次失敗,最終破產。作者藤村通過典型描寫小泉、橋本兩大封建舊家走向衰敗的過程,對明治時代封建舊家逐漸走向衰敗的過程進行了真實再現。
那么關于兩大舊家走向衰敗的原因,作者藤村又是如何思考的呢?關于這一問題,三好行雄分析指出:
“《家》的主題,與其說是主題,不如說是這部小說中‘家的含義包含兩個側面。一個是從外部限制人的作為機構的家,另一個是與其微妙地聯系在一起的、從內部讓人破滅的作為生理的家。前者可以說是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封建大家族制度的本質,藤村在這一共同體內部發現了編織封閉的傳承關系的家系,即放縱之血的詛咒,及由此造成的人格頹廢的危機。這部小說中的登場人物都未能擺脫這種陰濕的宿命。達雄、正太、宗藏,甚至三吉都因這血的詛咒而瀕臨破滅。”[1](著重點為原文所有)
三好的分析有其一定道理,但是把造成小說中人頹廢的原因僅僅歸結于內部“生理”(遺傳因素),筆者感覺說服力不夠充分。在小說中,三吉對次兄森彥說過這樣的話:
“只要沒有亂搞女人的毛病,對橋本父子就沒有什么好說的。這就是她們的根本思想。所以,她們盡為丈夫跟女人的關系而苦惱,難道除此之外就沒有什么值得擔心的嗎?她們總是認定達雄是敗于女色而棄家不顧的。所以這就成了問題。”(《家》下卷第五章)[2]
橋本家的種和其兒媳豐世將一切歸結于血統遺傳,認為丈夫的亂搞女人是破壞“家”的原因。而三吉卻將原因歸結于他們身上的“老爺氣質”,并對種和豐世的觀點持批判態度。瀨沼茂樹認為:“(作者)把舊家沒落的原因沒有歸結于資本主義原則的貫徹這一經濟原因,而認為是因為‘老爺們及其后代的人格頹廢。而造成人格頹廢的原因,舊家血的渾濁所導致的淫蕩性是一方面,而更應該引起注意的是家制社會本身對‘老爺們的人格頹廢所造成的影響。”[3]上述三吉對種和豐世的批判中所說的“老爺氣質”可以理解為舊家人物的“人格頹廢”,筆者認為瀨沼的分析較為符合作者的意圖。
但是作者藤村僅僅認為,封建家族社會及遺傳因素造成舊家老爺們及其后代的人格頹廢是導致舊家的沒落的原因嗎?小說下卷第九章中,三吉時隔十二年再訪木曾福島橋本家,這次他看到的不再是上卷第一章中描寫的一派富足繁榮景象,而是橋本家衰敗的景象。而且他看到了日本近代化對舊家的破壞。
“當順著那條原先通往倉庫的石階路爬上去之后,三吉看到了那邊有被挖低了的斷崖。/削成了斜面的斷崖,顏色鮮艷的紅土,剛剛鋪設的鐵軌和貫穿庭院中央的鐵路工地等,都盡收在三吉的眼底。從前,他在姐姐陪伴下看過的醬油坊、貯藏室的白墻和那棟他曾在窗邊讀過達雄寫的日記的小樓房,如今都無影無蹤了。梨園、葡萄架、還有阿春常去打水的那口大石井,也都看不見了。”(《家》下卷第九章)
不僅如此,之前以家長達雄為中心的主從關系現在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為領取每月的薪水才到這里來干的”。以鐵路為代表的近代化破壞著“家”的外形,薪金雇傭制生產關系改變著“家”的人際關系。作者藤村用這些描寫暗示我們“近代化”是如何破壞舊家的。
那么作者藤村對“近代”又是如何認識的呢?小說下卷第九章中,三吉在橋本家發現了一幅“黑船”畫。對于這幅畫,“‘這條船簡直象個幽靈!'三吉好像一下子記起了什么似的,看著荷蘭船的圖片說,‘我們老爺子成了瘋子就是因為這條船啊!'”。藤村在其感想集『後の新片町より』中,關于“黑船”畫有如下感想:
“今年秋天我去木曾旅行,在姐姐家發現一張船畫。雖是半紙(筆者注:和紙的一種)一頁左右大小、很粗糙的木板畫,但是看著它還是能夠想象當時的景象。因為它(黑船),又有多少人發狂而死呢?變了形狀的黑船也有很多來到了日本。/但是這還不夠。無論是托爾斯泰,還是易卜生,在一般人的眼里他們還只是幽靈。我們應該進一步確認黑船的真面目。然后打破沉夢。雖說我們一直在接觸西洋的事事物物,但是那都仍很間接。”[4]
從上述引用很明顯可以看出,“黑船”畫是“撼動封建日本的象征,是讓《家》中各人物的原點——小泉忠寬發瘋而死的原因”[5]。但是此時的黑船”畫對于三吉來說還是“幽靈”般的存在,還不知道它的真面目。這可以說是因為作者寫作當時對于破壞舊家的“近代化”認識還不夠充分。而藤村對其真面目的探究還要等到晚年大作《黎明前》。
二、對封建家族制度的批評
小泉家雖然已經沒落,封建家族制度的現實基礎已經解體,但是封建家族感情(意識)仍然殘留于從小泉家四兄弟的意識里。小泉實雖然事業接連失敗,可是“一直沒有改變他作為家長的威嚴。他在外面為人處世顯得極為圓滑,可對待家里人實在太嚴酷了”,而且妻子“從未聽到他對自己推心置腹地說過話”。實的心里有著各種打算,“故鄉寬闊的住宅和大片的山林土地,所有交給別人的財產,無論如何都要重新拿回來。這是為了祖先,也是為了自己的名譽”。可以看出,封建家族制度下培養起來的封建家族感情(習俗、道德觀念)仍然濃厚地殘留在他的意識里。
三吉新婚之后組成自己的新家,從小泉家分離出去,并遠赴山村當小學教師。雖然三吉的新家已經從舊家中分離了出去,但是在當時的封建家族制度下,這新家被看作是本家的分家,仍然要尊重本家的權威。封建家族制度以義理人情的形式,從倫理上限制個人的行為。三吉組成新家,遠赴山村教書,在地理上雖然擺脫了舊家的束縛,但是經濟上未能逃脫舊家的束縛。三吉本身靠微薄的收入養育妻子兒女,即使在這種狀況下,三吉收到了實發來的電報,電報中說要馬上給他寄錢去。而且所要的書目對于鄉村教師三吉來說“真不算小”。“事先沒有打過任何招呼,突然接到這么一封電報,很使三吉吃驚”,“雖說是兄弟,可這封電報的口氣簡直就像是命令似得,一點不客氣地張口就是跟他要錢,三吉想著想著便回到了家里”。從三吉的這種感想中我們明顯可以讀出他的不滿。那么是什么讓在沒有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僅僅一個電報就要所要索要金錢的行為成為可能的呢?毫無疑問,那只能是封建家長權威使其成為可能。
三吉很難拒絕大哥的要求,只好把妻子帶來的以備不時之需的錢寄了過去。當年的十一月,三吉又收到了實的寄錢電報,三吉也知道“很難滿足哥哥的要求,可是自己作為一個弟弟,還得盡量給他想辦法。即使不能如數寄去,多少也得寄上一點才行。為此,三吉只好把花了三個月左右才寫完的稿件賣了出去”。其后實再次入獄,他的妻子、女兒以及宗藏只能有三吉和森彥共同幫扶。
第二次出獄后的實第一次去搬到東京的三吉的新家拜訪,面對三吉,實的話“就象在繁華街上走道,左拐右抹努力避開行人一樣,盡量不涉及弟弟。他既沒心思拉著弟弟的手,暢敘昔日的辛酸,也不想對自己不在家期間給弟弟增添了不少麻煩,說上幾句深表歉意的話,而是儼然以一付舊小泉家長者對待晚輩一樣的姿態”。三藏本來是“實應當照顧的家庭成員之一,但這事也得讓三吉出錢”。實已經讓三吉“承擔了不少額外的款項,現在又來命他籌一筆款”。面對“面帶難色的弟弟”,“‘托給你啦!'哥哥讓三吉勉強答應下來,就匆匆離開了弟弟的家”。對于擺家長權威的哥哥,三吉惟有嘆息“不在家期間讓你受累了之類的話,那怕是一句也好,總該說吧”。從作者冷靜的敘述和三吉的嘆息,我們明顯讀出三吉對于擺家長權威的實所抱有的強烈不滿。作者藤村通過這些細致的描寫,向我們真實表現了封建家族制度所具有的不合理性。
出獄后的實遠赴滿洲,撫養其妻子、女兒的負擔再次落在了三吉和森彥身上。連其女兒小俊的婚事,都是“由森彥提議,決定由他們兩個人湊出錢來,為小俊作好結婚的一切準備”。三吉終于不能忍受這種長年對于親人的經濟援助,他感到“自己滿腦子想著創作、創作,只不過是在為親人們操勞而已”。面對森彥,他對于這種對親人的長年經濟援助抱怨道:
“‘難道要我們一輩子這樣做下去!象這樣扶助我們的親人,到底是好事呢,還是壞事呢?我越來越弄不清楚了。你們覺得怎么樣?'/森彥靜靜地聽著弟弟說的這些話。/‘我們當初為兄弟們想好的事,現在都事與愿違了。讓小俊進學校,當時是想指給她一條獨立生活的道路,也好養活她母親。可是誰料想到,她竟成了一個不適合做學校老師的姑娘。大姐不也是那樣嗎?由于她軟弱,我們體貼她、照顧她,可現在,她成了實足的窩囊人。這不是等于花這么長的時間在教弟兄們依靠別人過日子嗎?用名倉老爺子的話說,我們幫助弟兄們是錯誤的。他說,哪里有借錢去幫人的。'”(《家》下卷第五章)
三吉(藤村)對于這種長年幫扶親人的行為產生疑問,并從名倉老爺子(三吉的岳父)的話“我們幫助弟兄們是錯誤的”、“哪里有借錢去幫人的”給自己的觀點找依據。他還懷疑道,“這不是等于花這么長的時間在教弟兄們依靠別人過日子嗎?”,深刻地指出了家的道德所培養的厚顏無恥的依附行為。后來,連森彥也開始向三吉借錢,對于封建家族制度,三吉傾吐了比之前更加猛烈的批評。小說中有如下敘述:
“不知為什么,我總有這樣一種感覺,總覺得死去的老爺子老師纏著我們。無論走到哪里,或是做點什么,總覺得老爺子在跟著我們。森彥哥,你沒有這種感覺嗎?……(中略)橋本家的大姐過著那種生活,你住在這么一家旅館里,而我又總是在那樓上的斗室里冥思苦想。我們這些人和關在禁閉室里的小泉忠寬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們無論走到哪里,不都在背負著一個老朽衰敗的家嗎?……(中略)我想砸爛這個家。我一直在想,等有機會的時候,也給你講一講……。”(《家》下卷第八章,著重點為筆者標注)
三吉的批判很明顯把矛頭指向了封建家族制度。在此之前,作者通過客觀冷靜的描寫,真實表現了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合理性,到了此處,三吉對這種不合理性開始抱有強烈的反抗心理,并表示“想砸爛這個家”。三吉的這種認識也可以看做是作者藤村的態度。針對藤村(三吉)的這種強烈的批判,平野謙評價道:“三吉雖然被拉入充滿膿血的舊家框架內,但是他并沒有被同化,而是吐露了上述沉痛的批評之言。這可以說是針對封建習俗的市民批判”[6]。
雖然三吉對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合理性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但是對于對于森彥的借錢要求,他的回復卻是:“想想辦法看吧。早晚會給你一個答復”。此外,在小說中三吉對其岳父名倉老爺子做過如下評論:
“名倉家的老爺子認為我們兄弟,眼看就要破落了,他卻默默地看著我們,他絕不會幫助我們,真是個鐵石心腸的人呀![7]可是,我也不示弱。雖說在工作上,取得這個老爺子的幫助。可是在生活上,我卻從不開口要老爺子幫忙。他也就那個樣,深怕幫倒忙,在一旁看著。老爺子的有趣之處,也就在這里。”(《家》下卷第八章)
在小說中三吉的岳父名倉老爺子被作為“一生蓋了好幾棟房子,進行了大規模的建筑”的新興商人階級的代表而出現。瀨沼茂樹評價這位老爺子說,“他在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是,不像小泉兄弟那樣依附于他人、凡事有自己獨立的見解、擁有做事堅持到底的強烈意志力和旺盛的精力”[8]。三吉(藤村)一方面評價名倉老爺子“堅強的人”“有趣之處”,但是卻沒有把其道德準則作為自己的行為規范。三吉一直到最后都沒能停止“兄弟孝行”。藤村的市民批判還不夠徹底,有其局限性。
三吉為什么一直到最后都沒能停止“兄弟孝行”呢?其原因可能有兩個。首先,雖然三吉因為難以忍受長年對周圍親人經濟上的援助,對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合理性進行了猛烈的批評,但是三吉本身卻未能擺脫在封建家族制度下培養起來的封建家族感情(習俗、道德觀念)。作品中,實雖然是個進過監獄的人,但是三吉“每當聽到講起他過去的這些故事,對他仍然抱有特別的敬重之情”。雖然三吉對于次兄森彥的借錢請求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但是對著侄子正太,卻評價他說,“他既有極像平民的一面,可又有像貴族的一面啊!不管怎么說,他畢竟是一個出生在大戶人家的人呀!誰要是有了難處,他總是說別擔心,我給你想想辦法。我們的祖先過去就是這樣說的,他的口吻多像我們的祖先”。從這種肯定性評價中我們不難讀出三吉對于作為森彥的弟弟所流露出的自豪感。三吉所持有的這種對舊家長的尊敬之心、對舊家的愛惜之心、作為舊家一員的自豪感,也可以看做是作者藤村本人的態度。藤村雖然較早接觸西方近代思想,一直在尋求個人解放、自我的確立,具有近代個人主義倫理觀念,對封建家族制度也進行了猛烈批判,但是,作為舊家曾經的一員,在封建家族制度下所養成的封建家族感情(習俗、道德觀念)卻一直殘存在他的意識中,左右著他的行動。
其次是因為藤村本人畏懼破壞封建家族道德之后所招致的道德制裁。明治時代,日本一方面學習西方在各方面實行改革、推進日本的近代化,另一方面卻將在江戶時代完善起來的、以舊武士階級的封建家族道德為基礎的家族制度寫進民法(1898年)。這一取得法律地位的封建家族制度對近代日本(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一般民眾的家倫理意識所產生的影響可想而知。1910—1911年間寫作《家》的藤村肯定明白,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如果破壞了舊家的道德,接踵而至的肯定是來自周圍的道德制裁。藤村本人性格謹慎,這已被很多藤村研究者提及。謹慎的藤村對于破壞舊家的道德所帶來的道德制裁抱有顧慮,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這些原因,藤村對現實采取了忍受、觀望的態度。
三、社會性的缺失?
小說描寫小泉、橋本兩大舊家1898年到1910年間的歷史,但是小說對于在這期間發生的日俄戰爭(1904—1905年)、當時的激烈的歷史變動幾乎沒有涉及。而且作品中小泉實所從事的事業及其交往、小泉森彥所致力解決的“山林事件”這些本身是社會性很強的素材,但是這在作品中也基本沒有涉及。二戰后很長時間,日本的很多研究者據此批評《家》社會視野及社會性的缺失。但是筆者認為,藤村之所以在作品中沒有將上述社會性素材納入作品,這與《家》的創作方法有很大關系。藤村在1937年發行的收錄《家》的《定本版藤村文庫 第五卷》中寫有「『家』奧書」,在這篇文章中他談道:
“我寫《家》的時候,像建造房子一樣,用文字建筑起這部長篇小說來。對屋外發生的事情一概不寫,一切都只限于屋內的光景。我嘗試著從廚房開始寫,從玄關開始寫,從庭院開始寫。只有到了能夠聽見流水響聲的屋子里才寫到河。”[9](著重點為筆者標注)
由于作者“對屋外發生的事情一概不寫,一切都只限于屋內的光景”,所以才會將上述社會性素材沒有寫進小說中吧。而如果將那些素材寫進小說中,勢必淡化主題,影響小說主題的突出。那樣的話,我們讀到的就不再是這樣一部將那些被封建家族制度下的‘家壓得喘不過氣的人物真實地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家》了。對于《家》的這一創作手法,平野謙評論道:
“在《家》中,作者努力將‘一切都只限于屋內的光景。對于這種技巧的固執對于作品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眾所周知,日本的家族制度是以其家長絕對權為中心、作為一個從社會中被完全隔離的、閉鎖的組織被確立起來。令人意外的是,藤村所采取的偏狹態度,對于深刻描寫封建的日本的‘家是再適合不過了。家庭成員對于家長所采取的犧牲自我的忍從與《家》的忍耐克制技巧非常相稱。”[10]
雖然平野謙對藤村在《家》中對社會性視點的舍棄持批判態度,但是上述對藤村創作手法與作品主題表達之間關系的分析筆者非常贊同。
作者藤村通過典型描寫小泉、橋本兩大封建舊家走向衰敗的過程,對明治時代封建舊家逐漸走向衰敗的過程進行了真實再現。同時,作者通過冷靜、細致的筆觸,真實地描寫了封建家族制度所強制的個人犧牲,真實表現了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合理性。作者借三吉之口,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封建家族制度,對其進行了猛烈批判。但是作者所持有的封建家族感情(習俗,道德觀念),以及對破壞舊家道德后隨之而來的道德制裁所抱有的顧慮,讓他對現實采取了忍受、觀望的態度。這也可以認為是藤村對于封建家族制度批判的局限性。雖然《家》帶有這些不徹底性,但是其社會性值得高度評價。這也是《家》之所以被譽為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杰作的重要原因。
注釋:
[1]三好行雄「『家』のためのノート」(三好行雄著『島崎藤村論』筑摩書房、1984年1月),206—207頁。 <除《家》的譯文外,論文中所有日語資料原文的翻譯均由筆者完成,責任自負,以下不一一贅述。>
[2]《家》的譯文均參考枕流譯《家》,以下不一一贅述。
[3]瀬沼茂樹『評伝島崎藤村』(実業之日本社、1967年12月),203頁。
[4]島崎藤村「黒船」(『後の新片町より』所収 『藤村全集』第六巻、筑摩書房、1967年4月),136頁。
[5]十川信介「『屋內』と『屋外』―『家』の構造―」(十川信介著『島崎藤村』、筑摩書房、1980年11月),127頁。
[6]平野謙「『日本文學全集7 島崎藤村(二)』の解説」(『日本文學全集7 島崎藤村(二)』、新潮社、1962年3月),601頁。
[7]原文為「実に、強い人だネ」,根據原文,譯為“真是個堅強的人呀”應更為恰當。
[8]瀬沼茂樹『評伝島崎藤村』(実業之日本社、1967年12月),204頁。
[9]島崎藤村「『家』奧書」(『藤村全集』第四巻解題、筑摩書房、1967年2月),622頁。
[10]平野謙『島崎藤村』(巖波書店、2001年11月),62頁。
參考文獻:
[1]瀬沼茂樹『評伝島崎藤村』(実業之日本社、1967年12月)。
[2]島崎藤村『藤村全集 第四巻』(筑摩書房、1967年2月)。
[3]十川信介編『鑑賞 日本現代文學第4巻 島崎藤村』(角川書店、1982年10月)。
[4]黒古一夫『思想の最前線で―文學は予兆する―』(社會評論社、1990年5月)。
[5]平野謙『島崎藤村』(巖波書店、2001年11月)。
[6]片岡良一「近代日本文學と家の問題」(『自然主義研究』、筑摩書房、1957年12月)。
[7]平野謙「『日本文學全集7 島崎藤村(二)』の解説」(『日本文學全集7 島崎藤村(二)』、新潮社、1962年3月)。
[8]小栗朝子「島崎藤村作『家』の研究」(『日本文學』第18巻、1962年3月)。
[9]平野謙「『家』の方法」(『藤村全集』第四巻月報、筑摩書房、1967年2月)。
[10]杉浦明平「『家』について」(『藤村全集』第四巻月報、筑摩書房、1967年2月)。
[11]島崎藤村「『家』奧書」(『藤村全集』第四巻解題、筑摩書房、1967年2月)。
[12]島崎藤村「黒船」(『後の新片町より』所収 『藤村全集』第六巻、筑摩書房、1967年4月)。
[13]関良一「家―まぼろしの三部作―」(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刊行會編『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島崎藤村)』、有精堂、1971年2月)。
[14]広津和郎「藤村覚え書」(『藤村全集』別巻上、筑摩書房、1971年5月)。
[15]山室靜「作家と作品―島崎藤村(一)」(『日本文學全集9 島崎藤村集(一)』解説、集英社、1974年4月)。
[16]佐々木浩「『家』」(伊東一夫編『島崎藤村―課題と展望』、明治書院、1979年11月)。
[17]十川信介「『屋內』と『屋外』―『家』の構造―」(『島崎藤村』、筑摩書房、1980年11月)
[18]吉田精一「『家』とその前後」(『吉田精一著作集第6巻 島崎藤村』、桜楓社、1981年7月)。
[19]平岡敏夫「『家』―花袋『生』『妻』にふれつつ―」(『一冊の講座編集部編『一冊の講座 島崎藤村』、有精堂、1983年1月。
[20]三好行雄「『家』のためのノート」(『島崎藤村論』、筑摩書房、1984年1月)。
[21]高橋昌子「リアリズムの極北―『家』の敘述―」(『島崎藤村―遠いまなざし―』、和泉書院、1994年5月)。
[22]水本精一郎「藤村における近代―『家』の構造と方法―」(『島崎藤村研究―小説の世界―』、近代文蕓社、2010年12月)。
[23]島崎藤村著,枕流譯《家》(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
[24]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
[25]劉曉芳《島崎藤村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