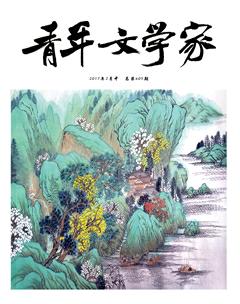同一性準則中個體的生存寓言:對加繆《局外人》開篇的分析
摘 要:《局外人》的第一節寫了主人公“我”接到母親的死訊,前往養老院參加母親的葬禮。這一節對整部小說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生動地介紹了“我”的人物背景與性格特點,也以大量細節和線索為后面的敘事埋下諸多伏筆,奠定了整本書的荒誕基調。
關鍵詞:局外人;荒誕;存在;個體
作者簡介:畢聰正(1990-),男,漢族,研究方向:文藝學、文藝美學基本理論。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2
(一)母親的葬禮:情感羈絆與道德準則
全書第一句寫道:“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主人公并不知道母親去世的確切時間,對母親去世這件事了解不多,顯然也并沒有多加詢問和深究。語氣顯得異常平淡,仿佛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沒多少關系的事情發生了一樣,這更加令讀者感到,喪母一事對“我”而言其實并不多么重要。而且在對這一非常重大的事件的敘述中,以自己對此事的不甚了解作為講述的起點,仿佛母親去世這件事再沒有什么更加重要的事情值得多去注意一般。“我”對母親之死的漠不關心,意味著“我”對母親本人的不關心、對母子親情的淡漠。正是這種淡漠的性格,最終造成了“我”的悲劇。此外,喪母之事本身重大,而“我”的反映卻顯得十分淡然,這一不合常理的反差呼應著貫穿整部小說的荒誕基調。
在寫到“我”向老板請假時,“我”甚至對他說:“這并不是我的過錯。” “我”仿佛把母親的去世當做了一種不可避免、不可抗拒之事。“我”請假去參加葬禮,不是因為“我”愛母親,因而“我”必須去送她最后一程,而是因為母親去世,兒子出于社會給定的倫理、道德法則的外在要求,必須去扮演一次送葬者這一角色。因此,“我”甚至如此向老板辯解,“這并不是我的過錯”,這仿佛是在說:我也并不想為此事而請假,但是作為兒子給母親送葬,這是社會道德的要求,你也不能不給我這幾天的假,就像我不得不去一樣。在“我”看來,母親的死似乎早已經注定,就像四季交替、日出日落一樣必然發生,“我”作為兒子去參加母親的葬禮,也就像夏天要避暑、冬天要御寒一樣,是一件生物性的、必須做出的事情,而在這件事中,除了必然性之外也不再具有任何情感意義上的、特殊性的理由。由此,“我”不是作為一個情感充沛的、飽受喪母之痛的兒子去置入這件事情,而是以一種局外人的姿態涉入此事。“局外人”這一題目在這里第一次顯露出它的意義。作為整部小說的主人公,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局外人,“我”不僅是社會公共領域、主流意識形態的局外人,同時也是血緣、親情、私人領域、家庭小共同體的一個局外人。從小說開篇至此,一頁的內容里,絲毫看不到任何對母親的留戀與不舍。這種母子之情的淡薄,恐怕并非是主人公一人造成的。事實上,從小說后面的敘述可見,主人公和母親之間的關系并不融洽,兩個人很少說話。換言之,這種情感的淡薄是雙方共同促成的。在一個富有同情心、尊重個體尊嚴的社會中,這樣的特殊境況,無疑是應該被尊重的。而這種往昔生活造成的母子之間的疏離,也顯然不應成為一種道德評判、意識形態強制的目標。
(二)“院長”形象:權威與社會等級
小說寫到“我”到達養老院之后,被告知必須首先會見院長。如果那種“失去母親必然要悲傷形于色”的道德輿論要求是社會意識形態、道德倫理強加于人的,那么“得先會見院長”則是代表政治權威、等級制度的現代科層與體制對個體的強制。這種來自于政治權威的外在壓力無疑比普通的道德倫理更加具有強制性,不管主人公是否真正出于道德倫理所強加的“真情”而去急于見到母親的遺體,在政治等級的面前都不得不做出讓步。而事實上,從小說后面,作為政治暴力機器的法庭,以社會意識形態、道德倫理對主角進行道德層面的審判時,已經顯示出政治權威不僅對個體進行強制與脅迫,同時也對整個社會意識形態進行利用,使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成為服從于政治權威的工具。
隨后,“我”走進了院長辦公室,作家借院長之口,道出了“我”因為工作和生計而不得不將母親送進養老院的難言之隱。這種將老年人送進養老院的原因,幾乎堪稱現代生活中的一種范本式的原因。然而,院長對“我”理解究竟是正確的理解還是出于臆測的隨意之語?
根據院長的所言,“我”之所以對母親感情淡漠,絕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原因。母親在家時跟“我”無話可講,母子間交流的空白不可避免地使二人間的關系越來越逼仄。母親“一天到晚總是瞧著我”,這種母親對兒子的冷淡、失語,甚至給人一種陰森、可怕的不正常印象。接下來寫母親初到養老院總是哭,但“那是因為不習慣”,因為“過了幾個月,如果要把她接出養老院,她又會哭的,同樣也是因為不習慣。”母親離開家、離開朝夕相處的兒子,并沒有任何親情意義上的不舍,而僅僅是對生存環境的不習慣,這再一次從母親的角度印證了“我”與母親之間雙向的漠視與冷淡,同時也展示出了一個性格同樣怪異的母親形象。由此,一種復雜的、往往追根溯源一番后仍然無法簡單地判定孰是孰非的家庭問題,終究不可能被用來決定一個人的道德品行高低,更不可能用來決定是否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小說在這一部分著力渲染的復雜、特殊的母子關系,在引起讀者對這對母子之間歷史狀況的猜測的同時,間接地暗示了小說后半部分法庭上以道德審判取代法律審判這一狀況的荒謬與不合理。
當然,“我”歸根結蒂也不是一個無可指摘的兒子。正如前文所說,“我”與母親的關系走到現在的地步,責任幾乎可以肯定是雙方的。“我”作為一個安于現狀、少于追求、封閉在自我世界的小職員,一種自私自利、對外界大多數人事都漠不關心的態度,應該說是“我”身上最主要的缺點。然而,這種自私也只是相對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私自利。由后面“我”身陷囹圄之時對情人瑪麗的牽掛,可以看出“我”也絕非是一個無情無義心中只有自己的人。“我”的這種自私不是非人性的自私,而是一種內在于人性、內在于角色性格的必然的自私。因為“我”的生活就局限于一個小城市中一個職位上,“我”的生存世界相比于大多數人可能小得多。在這樣一個人的身上,自私很可能只是一種狹小、內向的生存境況的衍生物,是一種被視野、見識等因素所決定的必然性格。更進一步地說,“我”的身上即便有著一定程度的自私自利、漠不關心,但作為個體的“我”,在整個社會與體制的巨大道德化強制性權威面前,仍然是一個受害者,是一個被踐踏、被玩弄者。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我”這個人物,在他身犯命案卻遭到“錯位”的道德審判之時,也就成為了一個堅持個體價值、個體取向和個體尊嚴而拒不向外界整體合作的“荒誕的英雄”。
現在,如果我們再回到“我”與院長的對話,我們便可以印證院長對“我”的安慰和理解并非憑空臆斷。院長在這段文字中,展現出的乃是一種善解人意、賦予同情的長者形象。然而,如果我們參考小說后半部分的庭審情節,我們就會看到,當院長走上證人席指證“我”為人不孝、漠視尊長時,展現出的完全是另一套說辭、另一副嘴臉。此時的理解和安慰變成了彼時的惡意和控訴,這種仿佛是蓄意的急轉,給“我”和讀者都造成了一種震驚效果。
(三)“門房”形象:在“局外”與“局內”之間
與此類似的還有養老院的門房。小說中,當“我”結束跟院長的談話,進入大廳進行守夜時,“我”喝了門房提供的咖啡加牛奶,感到味道很好而且很提神,之后,在守夜過程中又多次喝了咖啡加牛奶進行提神。但這一看似正常的行為,在小說后半部分的庭審中卻成為了另一個指向“我”的不利證據。在庭審中,門房親自上前指證,控訴“我”在為母親守靈期間,三心二意,多次索要咖啡、飲用咖啡,表現出嚴重的隨意感。然而,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或者至少可以猜測到,“我”所喝的咖啡加牛奶,原本是“我”路途勞頓來到養老院后,門房出于地主之誼而招待“我”喝的,是門房主動為“我”提供的。此時,“我”對咖啡加牛奶的接受,不僅是一種無傷大雅的需求,更是一種出于禮貌的舉動。然而,讀者卻不能說,門房此時此刻就已經心懷不軌,故意給“我”布下了一個險惡的陷阱。因為,在整個從見面、開始守靈,到送葬、葬禮結束,門房一直對“我”表現出了一種朋友般的尊敬和親熟感。沒有任何文本中的線索或邏輯上的推斷,可以證明門房在一邊跟“我”交談,一邊心懷叵測地搜集著“我”不孝的種種證據。
事實上,門房作為一個跟“我”相對的“局內人”,一方面深諳世俗的禮貌,同時又深受世俗的、主流的意識形態的浸染和塑造。他可以一方面在內心之中對“我”所表現出的厭倦、隨意和漠不關心進行評判,但同時又囿于世俗的禮儀規范而將自己的評判藏在心底。而當“我”成為一個法庭上受審的罪犯時,這種深藏再心底的記憶與評判,便被激發出來了。而正是這種世俗的、想當然的、狹隘而愚昧的道德評判方式,不斷地傳遞和強化著同一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對特殊個體的壓迫。在這場對“我”所進行的道德的、意識形態的暴力壓迫之中,無論是宏觀的社會整體,還是微觀的具體個人,無論是代表統治權威的法官、代表具有一定實權的基層官僚養老院院長、代表普通民眾的門房,還是審判之時法庭內外的看客,社會每一個階層都有人參與其中,沒有任何一個“局內之人”能夠置身事外、坦然地袖手旁觀、保持中立。
然而,到“我”在犯下謀殺罪之前,也是一個默默遵守同一性社會準則的普通人,“我”的遭遇與其說是“我”性格的必然,倒不如說是命運的偶然。從“我”長期保持一種孤立的、隨遇而安的局外化生存狀態,到小說后半部分中作為千夫所指的“局外人”而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我”的遭遇盡顯命運的荒謬和隨機性。由此觀之,每一個融入同一性社會意識形態中的個體,又都有可能因某一件突發之事而成為下一個被送上法庭的有罪者。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每個人都站在自己被灌輸、被培養出來的社會道德準則上評判、排斥并間接地毀滅那些特殊的他者;而每個人又隨時可能成為那個被眾人評判、排斥和毀滅的特殊個體。這也正是同一性社會準則下,對每個特殊個體都可能遭遇的生存之悲劇的荒誕寓言。
參考文獻:
[1]加繆:《局外人》[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3-17.
[2]《加繆全集(小說卷)》[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3]加繆:《西西弗斯的神話》[M].杭州: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