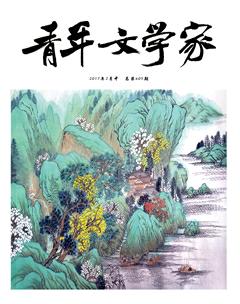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最藍的眼睛》中的黑人身份探究
摘 要:《最藍的眼睛》是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處女作。白人強勢文化中對人的價值判斷深刻影響了黑人的自我定位。本文以托尼·莫里森的《最藍的眼睛》為研究底本,以黑人女孩佩科拉的人物命運為線索,試圖對黑人身份進行探究。
關鍵詞:托妮·莫里森;文化;身份
作者簡介:薛丹(1988.10-),女,藏族,四川西昌人,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2015級碩士。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2
一、黑人身份的形成
1970年出版的《最藍的眼睛》是莫里森的第一部作品,奠定了她在文學界的重要地位。莫麗森自幼在黑人文化的耳濡目染中成長,在家學習黑人歌曲,了解有關南方黑人的許多傳說。她生長在主流文化是白人文化的美國,但她一直都尊重和稱贊黑人文化,并自豪的稱自己為“黑人”女作家,并于1993年,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黑人女作家,獲獎的理由:“其作品想象力豐富,富有詩意,顯示了美國現(xiàn)實生活的重要方面。”
亦如頒獎詞中講到的,這是美國現(xiàn)實生活的重要方面。這一面在作品中,以小說的形式展現(xiàn)出來,就形成了種族歧視這一主題。種族歧視主要是白人文化與黑人文化的博弈中,主流文化(白人文化)與邊緣文化(黑人文化)的對抗。在莫麗森的作品中對于種族歧視和沖突的表現(xiàn),并不是兩種文化的正面對抗,而是站在邊緣文化(黑人文化)的角度,從黑人的立場來看待這種沖突和對抗。作品中的黑人是一個自卑、自怨自艾的群體,他們不被主流文化接受,并在文化浪潮中迷失自己,找不到歸宿,并且也沒有強勢地保護自己的黑人身份,沒有自主的肯定和接受自己所屬的黑人文化精神的價值和意義,在浩大的文化浪潮中,他們總是處于被動的、弱勢的地位之中。廣大的黑人努力實現(xiàn)種族平等,在與白人文化對抗的過程中,他們是飽受壓迫的,但卻不是以一個獨立堅強的形象來堅守自己的文化立場,更不是以一個自信的態(tài)度來保護自己獨特的身份。20世紀美國黑人文學的創(chuàng)作中,黑人男性作家是主要的創(chuàng)作群體。他們關注的問題是種族歧視的問題,主要是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宏觀層面上黑人受到的不公正的對待為出發(fā)點,對白人社會中黑人受到的歧視和壓迫表示明確的聲討和抗議。例如在圖默、賴特、艾里森、鮑德溫等人的作品中,十分明顯的展現(xiàn)了黑人對于白人文化的一種對抗態(tài)度,在白人文化的強勢作用之下,黑人依然堅守著自己的特色,不被人文化輕易同化。這種描寫是粗糙的,也是生硬的,看到的更多的是黑人文化與白人文化之間的對抗和差異,書寫范圍也比較的有限,這中書寫對于黑人的內心世界的透視顯然是不夠的。
新一代的黑人文學主要以黑人女性作為主要的創(chuàng)作群體。她們的作品不再是單一的反應黑人文化與白人文化的對抗,而是筆觸細膩的深入到黑人女性的內心,通過對黑人女性的內心透視,來看待生存在白人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男人對女人的性別歧視這兩重壓迫之下的黑人女性的命運抉擇和身份認同。黑人與白人的對抗不僅僅是統(tǒng)治階級與被統(tǒng)治階級的矛盾對抗,更是在白人文化洪流中黑人對于自身黑人身份的堅守。這個過程是艱難的,也是漫長的,更是微妙的,因為黑人不僅僅是要尋求白人對于黑人身份的認同,也要尋求黑人自身對于黑人身份的確認。黑人身份不僅僅是膚色賦予的身份,也是在白人文化為主流文化賦予的黑人身份,更是黑人被動接受的黑人身份。對于每一個黑人來說,黑人身份已經成為了她們的自我身份。可是在白人文化為主流文化的社會中,黑人身份是一個被侮辱、被嘲笑備受白人歧視的身份。特別對于黑人女性來說,在種族歧視與男性對黑人女性的性別歧視雙重重壓之下,黑人身份已經不能詮釋自我身份了,而且變成對于自我身份的貶低和壓迫。黑人女性就將視角放在了黑人女性對于自身身份的探究和追尋中,將黑人對于身份的探究放到更大的視野中,來細致的觀察黑人對于個人命運和身份的抉擇。
二、佩科拉自我身份的尋找
在黑人女作家的眾多作品中,筆者以為《最藍的眼睛》最能展現(xiàn)黑人對于自身身份的探究。故事講述的是在俄亥俄州洛林市某個黑人社區(qū),一個11歲的黑人小姑娘佩科拉 (Pecola Breedlove)努力尋找“最藍的眼睛”的故事。佩科拉生長在備受白人歧視的環(huán)境中,作為一個天真可愛的黑人女孩,在黑人社區(qū)也沒有得到黑人朋友、親人的關愛而總是被忽視,她成長中得到的是無盡的白人對她的歧視、譏笑、不尊重、不友好。她渴望從家庭得到溫暖和關懷,渴望從同學那里得到尊重和愛。她努力的尋找,“她久久地坐在鏡子面前,想發(fā)現(xiàn)丑陋的秘密。”鏡子能照見的是人最直觀的外貌,在鏡中發(fā)現(xiàn)自己不被人喜愛的原因是她的黑皮膚黑眼睛。佩科拉眼中那些受人喜歡的人都是,白皮膚、藍眼睛的,那些人是如此的美麗。從佩拉的視角來看待自己與白人的差異,她看到的是自己的眼睛和皮膚的顏色是不被人們喜愛。白色、藍色原本普通的色彩現(xiàn)在變成了一種擁有眾星捧月般的愛戴,而黑色成為了骯臟、丑陋、遭人白眼與厭惡的象征,這種帶有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改變了佩拉的生命色彩,原本鮮活、跳動的生命在自我身份的追尋的過程變得茫然、恐慌、懷疑、不自信。佩科拉在鏡中看到自己有一天有最藍的眼睛就會得到人們的關注和愛,她渴望自己能有這樣的藍眼睛。不難發(fā)現(xiàn),這是一種幻想,不會實現(xiàn)的,但希望有一天能擁有一雙最藍的眼睛就成為了佩科拉在“黑”社區(qū)生存下去的唯一光亮。
佩科拉這個柔弱的生命光亮也沒有得到身邊人的支持和維護。在被父親強奸而懷孕后,現(xiàn)實的殘酷無情使得佩科拉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遙遠。她對那個受人尊敬、喜愛的自我身份地追尋在現(xiàn)實生活中已無實現(xiàn)的可能。無能為力是佩拉在現(xiàn)實中的寫照,面對白人文化,她是被歧視與被嘲笑的對象;面對黑人文化,她是受黑人朋友、親戚討厭的女性;面對家庭成員,她是可有可無的存在;面對自己她沒有現(xiàn)實的能力來保護自己追尋自我身份。現(xiàn)實生活對于她和她的身份都是拒絕的,但值得稱贊和令人心生敬畏和憐憫的是佩拉始終不放棄對于自我身份的追尋,現(xiàn)實生活將她拒之門外,她在精神錯亂的幻想中也在進行著自己的追尋,進行著對自己身份的確認。
三、黑人文化身份的丟失及其原因
佩拉對于“最藍的眼睛”的追尋就是對于那個受人尊敬的身份的追尋,也是在白人文化中眾多黑人對于自身身份的追尋的代表。佩拉的愿望在幻覺世界中實現(xiàn)了,擁有了最藍的眼睛。可是,現(xiàn)實畢竟是殘酷的,佩拉的這點童話般的愿望,即便在神志不清的狀態(tài),這種愿望的實現(xiàn)也是不被允許的,“這種愿望著實可怕,但是欲望得以實現(xiàn)更為罪惡。”因為讓這個黑人小女孩在“實現(xiàn)愿望”后,就變成了和白人一樣擁有了藍色的眼睛,然而這雙藍眼睛是看不見黑人社區(qū);同時,這雙幻覺世界中“眼睛”看不見真實的世界復雜與斗爭,看不見她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并且在幻想中依然覺得自己的“藍眼睛”沒有他人的藍,在無盡的比較和嫌棄之中,不會給自己生命帶來光亮,只會削弱一個人生存的活力與勇氣。
佩拉幻想中得到的藍眼睛,就像眾多黑人脫離現(xiàn)實在幻想中擁有的黑人身份一樣,連他們自身都不認同自己所擁有的“最藍的眼睛”,因為她們的這雙“眼睛”看不到現(xiàn)實的紛爭,更加看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是眾多黑人缺少文化自信的集中體現(xiàn)。在強大的白人文化浪潮中,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是渺小的,而社會是具有強大魔力的染缸,單個社會成員在這個染缸中容易“著色”。社會環(huán)境的方方面面對佩科拉的教育都是“黑色皮膚和黑色眼睛”是丑陋的,就像白人文化對黑人社區(qū)的定義也是“黑色”是丑陋的,而這種定義就連身處在這個社區(qū)的人都是這樣認為的。正如莫麗森所認為的那樣:丑陋來自于一種確信,他們自己的確信。白人文化把黑人社區(qū)的“黑”定義為丑陋,黑人社區(qū)的人們在不自覺的狀態(tài)中自主的接受了白人文化對黑人文化的定義,并且深信不疑。所以,“黑”是丑陋的這一觀念成為了黑人、白人的共同認知,黑人不可否認的接受了這種說法,也在這種說法的氛圍中創(chuàng)造種種讓他們信服的事實。他們也不會意識到,長在臉上的顏色、身上穿的“丑陋的外衣”都不是一個人身份的標簽,更不是一個人身份的唯一體現(xiàn)。他們盲目的接受著白人文化的信息,在每一張廣告牌和每一部電影中都滲透著白人文化的價值判斷,黑人找不到屬于自己文化的價值判斷,看不到自己文化的廣告牌亦或是電影,所到之處都是白人文化的符號,他們在這些證據(jù)面前只能說“是的”,“您說的對”,簡短的回答是在現(xiàn)實面前對白人文化的肯定,也是不知不覺得選擇對黑人文化的否定,逐漸變成對自己身份的不確定。在強勢的主流文化與弱勢的黑人文化的對抗中,他們堅守自己的最后的底線黑人身份;在白人文化符號包圍的環(huán)境中,他們認可白人文化,并且逐步認為這種“丑陋”就是屬于自己,并且是自己身份的象征。就像溫水煮青蛙一般,白人文化在他們周圍持續(xù)升溫,從最綿密的地方開始,逐漸讓他們接受這種意識,當白人文化與黑人文化在對抗時,他們這只溫水中的青蛙不斷向反抗、想跳出去,可是已經喪失了抗爭的力量和可能。
這一切正是在白人文化為主流文化的美國,黑人身份的認同在文學文化中一直都是一個特殊、而復雜的現(xiàn)象,反應出了黑人對屬于他們的文化身份的不確信,這種不確信不僅存在于生理層面,也存在于社會文化層面,具有深刻的社會內涵。亦如莫里森在一個政論文里提到的:人類生活由于世界上最表面的東西——身體美——而遭到徹底毀滅。美國黑人對自身的身份的迷茫,以致在“白人”文化中一味的自卑、退讓,亦如佩科拉的父親、母親都沒有意識到“金盞花不開原來是這片土地的原因”而一味的會想責難。
僅有的一個在順從中依然在用自己的綿薄之力來尋找自我認同的佩科拉,她的探索道路也仍然是“變成”藍眼睛。這條道路沒有依然沒有跳出白人社會對黑人文化設定的怪圈,也注定是只是小小的抗爭,并不是實質性的反抗,所以,注定也是失敗的。她在努力尋找自我身份的時候不斷受到白人社會的蔑視還受到黑人的阻礙,甚至她的父親還在她尋找身份和關愛的時候給她致命一擊,讓她原本脆弱的自我在現(xiàn)實世界中“死亡”。可見在這種“反抗”之中,力量是如此的渺小。上一代是麻木的,而下一代的“反抗”卻遭到社會與周圍人的不理解和無情的摧毀。與此相似的是莫里森的另一部小說《秀拉》,秀拉是反抗白人文化束縛的典型。《秀拉》一發(fā)表,就引起了軒然大波,其原因,是秀拉令人瞠目地要把這個世界“撕成兩半”的決心。“他們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沒有她們的份,她們應該創(chuàng)造一些別的東西”,因為她們身份的不允許、社會的不允許,并且在這種“反抗”中,她們也逐漸丟失了作為黑人最為寶貴的品質:純樸、自然。正向小說開篇提到的這樣一句話:“我們的天真也死去了”那么,作者所指的“天真”是什么呢?那就是“天然和真實”——黑人民族樸實、純真的傳統(tǒng)本色。
結語:
莫里森小說通過《最藍的眼睛》揭示了黑人在白人文化中身份的迷茫,并對黑人對于自我的否定感到惋惜,希望黑人能夠像佩科拉一樣勇敢的尋找自己的身份,但也對“最藍的眼睛”給予一種希望,希望這種比白人的藍眼睛更藍的眼睛,能讓黑人認識到黑人文化的魅力。同時,在主流文化之中,弱勢群體文化被邊緣化的危機,也警示人們要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邊緣文化,尊重邊緣文化的價值和存在。
參考文獻:
[1][美]托尼.莫瑞森著.最藍的眼睛[M].陳蘇東,胡允恒譯.南海出版公司,2005.
[2]閻嘉.文學理論基礎[M].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
[3]王守仁,吳新云.性別種族文化,托尼莫里森與二十世紀美國黑人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4]王守仁.走出過去的陰影[J].外國文學評論,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