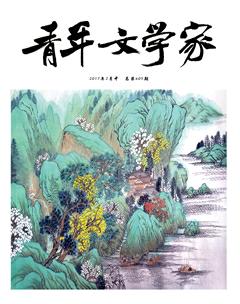論現代人的情緒管理
摘 要:動畫電影《頭腦特工隊》一經上映,好評如潮,在觀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顯見是皮克斯動畫工作室的又一成功力作。本文從皮爾斯符號三分法理論和解釋項原理入手,解讀了該影片最典型的五個動畫形象的符號學意義,籍由揭示影片成功之原因,五個情緒小人的建構與博弈符合大眾的情緒共性,故而能在大眾中引起共鳴。
關鍵詞:情緒管理;符號學;解釋項原理;《頭腦特工隊》
作者簡介:楊亞美(1989-),女,漢,西南財經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2
1、引言
《禮記·中庸》首章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則,達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萬物便生長繁育了。這可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給予現代人情緒管理的啟示。在這一啟示中,強調了情緒抒發的兩個階段。一是未發階段,強調人人都有喜怒哀樂之情緒;二是在產生情緒后,強調抒發時的自我節制及因時制宜。現代社會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緒,是現代人不可逃避的問題。
3D動畫電影《頭腦特工隊》由華特·迪士尼電影工作室、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聯合出品的。影片一經上映,好評如潮,尤其在北美市場引起了強烈反響,影片講述了小女孩萊利因為爸爸的工作變動而舉家搬到舊金山,適應新生活的過程,主要展現了萊利頭腦中五種情緒的繽紛世界。
影片中選取的五種情緒是我們最基本的情緒,因而最具代表性,充滿想象力的設定和空間構造,打動人心的共鳴點是這部影片成功的關鍵。影片的靈感來自于導演彼特·道格特的女兒成長中的變化。本文從符號學角度對影片中的這五個小人加以解讀,以符號學家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和解釋項原理作為理論支撐,挖掘符號背后的深層含義,揭示影片對現代人情緒管理的啟示。
2、文獻綜述
本部分主要概述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和符號學解釋項原理,這是本文的理論基礎,此外,筆者總結了電影符號學的研究現狀。
2.1皮爾斯符號三分法
作為現代符號學奠基人,皮爾斯是第一個全面研究符號的學者,他將非語言符號學也納入到符號學研究的范疇(Gorlée, 1994: 175)。皮爾斯從邏輯角度研究符號,主張符號三分法,他認為一個有效符號的基本成分應該包括符號代表項、對象和解釋項。所謂代表項,是相對于某人,在某個方面或在某個程度上,代表它物的某種東西。皮爾斯在定義時還特別指出:它(符號)是針對某個人的,也就是說,它在那個人的頭腦里形成一個對等符號,或者說是一個更加發達的符號。皮爾斯將那個在頭腦里形成的符號叫第一個符號的“解釋項”,符號代表某樣東西,即它的對象(Peirce, 1931-1958: 2.228)。
對于解釋項,即對符號進行感知、解釋和批判的過程,皮爾斯也進行了三分,即直接解釋項、動態解釋項和終極解釋項(Peirce, 1931-1958: 8.184)。
2.2皮爾斯符號學解釋項原理
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理論突破了索緒爾語言符號學二元研究的限制,具有更強的分析和解釋各種符號現象的功能,其符號學為我們理解符號的意義提供了理論支持(王銘玉,2006)。皮爾斯的符號原理與索緒爾抽象的能指和所指關系相比,更需要解釋項的參與,以體現替代關系。符號的橫組合和聚組合構成的是語言的結構,決定的是語言的功能,與符號的意義無關(趙彥春,2005)。故而皮爾斯提出符號系統的第三個元素----解釋項,強調了解釋項在整個符號系統中的重要意義。作為解釋項的認知元素在皮爾斯符號學中占重要地位,皮爾斯認為,只有解釋項的參與才可以使符號終究成為符號,“除非它(符號)被解釋和針對某人而言,否則它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符號”(Peirce, 1931-1958: 7.356)。如果說索緒爾對符號的界定是靜態的,那么皮爾斯對符號的定義則是動態和意指的過程(丁爾蘇,1994)。
2.3關于電影的符號學研究
通過大量閱讀文獻,筆者發現國內研究電影的符號學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符號二元研究,一類是符號三元研究。從語言符號學的鼻祖索緒爾到美學符號學的集大成者羅蘭·巴特,無不是站在符號二元論的基礎上來探討符號學。一般而言,電影符號學以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為基礎,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電影藝術,認為符號是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系,但是同屬于符號學奠基人的皮爾斯,其符號學理論,特別是符號三分法原理和解釋項原理對電影符號的闡釋更具有影響力。
解釋項的存在豐富了電影符號的意義和內涵,同時也造成了電影符號的復雜性。一方面,電影符號具有普遍性和模擬性,另一方面,解釋項使得電影符號具有不確定性。認知水平的差異使人們對同一個電影符號的直接意義、動態意義和終極意義的觀點不盡相同,人們在闡釋時也就會產生不同的答案,從而使影視作品的豐富內涵得以展現。
3、電影《頭腦特工隊》符號學解讀
電影符號勾勒的符號王國既是一個人們熟悉的世界,但又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它改變了符號交換的時空參數,并創建了新的言語情境。費斯克(John Fiske)和哈特利(John Hartley)在《解讀電視》(1978)中認為,應當分三個階段解讀傳媒如電視文本的復雜信息,先是解讀社會符碼,即現實的符碼,如行為符碼,服飾符碼和語言符碼等,再是解讀技術符碼,如拍攝距離,鏡頭運動等,最后是解讀意識形態符碼,如種族主義,男權主義和個人主義符碼等。與之對應的是,在解讀電影符號中,可以從相似符、標引符和象征符三類符號和直接解釋項、動態解釋項和終極解釋項考察。由于電影符號的解讀最終是通過人的解釋來實現的,因此形成最終解釋項的主體也是個人,同時,電影解讀的意義最終也要回歸到人。
3.1從符號學角度解讀五個情緒小人
《頭腦特工隊》的主角可以說是五個情緒小人。黃藍搭配的“樂樂”像星星,藍色的“憂憂”是一滴眼淚,火紅的“怒怒”似一團火焰,紫色的“怕怕”是神經元,綠色的“厭厭”則如同西蘭花。五種情緒小人齊聚,妙趣橫生地在主人公萊利頭腦深處操縱著她的喜怒哀樂。
對這部影片而言,符號的代表項是這五個小人,對象是人類的五種不同的情緒,解釋項則是觀眾對著五個情緒小人的感知、解釋和批判的過程。這五個符號在人們頭腦中產生模糊的第一印象,形成直接解釋項,金黃的閃閃發光的樂樂歡快充滿活力,藍色的胖胖的憂憂總是一臉憂郁,紅色的暴躁的怒怒動不動頭發就噴火,綠色的高傲的厭厭一臉不屑,紫色的膽小的怕怕神經敏感。隨著影片情節的推進,觀眾對這五個符號的解讀會產生不同的感受,這一過程是動態的,隨著時間和場景發生變化,形成動態解釋項,比如憂憂這一形象,影片最初給人的感受是憂郁的悲觀的消極的,中間我們又會發現藍色的憂憂還有知識廣博的一面,到了影片最后還表現出了勇敢的一面、理智的一面。終極解釋項是這五個小人貫穿影片始終給觀眾留下的完整印象,是觀眾看完整部影片后對情緒的認知,對情緒小人博弈的感觸,對情緒管理的思考。情緒的指揮部里,沒有“人”應該被拋棄。要讓萊利健康幸福地成長,這五個小人缺一不可。
3.2符號學折射下的影片內涵
皮爾斯認為“符號或符號媒介是某種對某人來說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種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東西” (Peirce, 1991: 227)。皮爾斯的符號學關注的不是符號,而是符號的動態過程,即意指過程。符號在意指過程中構成了一個“客觀世界—符號—闡釋者”的三分結構。符號的意義成為符號與客觀世界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站在皮爾斯符號學的基點上,來解讀電影這部影片中的符號無疑更具說服力和解釋力。
作為一部動畫電影,美好和悲傷并存是這一影片的基調,深刻的影片內涵使它完全超出了童話的范疇,而成為一個關于人生的寓言。通過解讀影片塑造的故事,解讀其中的符號意義,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自己,認識我們的情緒,我們如何被情緒挾持,我們為何會遺忘,甚至包括為什么憶起一件小事就會觸發我們情緒島的坍塌。這個關于萊利成長過程的故事不再限于萊利克服了種種不適、面對新生活,這個故事更是幫助我們全新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情緒,進而學會管理情緒。朝氣蓬勃、帶有甜甜味道的喜劇動畫背后蘊含深刻的哲思,這也是這部影片在觀眾中引起共鳴、獲得成功的原因。
4、結論
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和解釋項原理為符號意義的解讀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基礎,符號具有相對獨立性,同時又必須與客觀世界發生聯系,被主體闡釋才能獲得意義。意義生產是一種符號解釋活動,這一解釋過程離不開符號本身即代表項、對象和解釋項之間的互動。本文分析了影片中符號意義的產生過程,從直接解釋項、動態解釋項和終極解釋項三個層面考察了電影符號----最具代表性的五個情緒小人,揭示了影片的深刻內涵。
《頭腦特工隊》是一部邏輯縝密的具有教育意義的好的電影作品,對于各個年齡段的人的情緒管理應頗有助益。這部影片對我們的情緒管理啟示有二。其一,接納每一種情緒。每種情緒都塑造著我們,接納它們,才能真正地接納自己。其二,控制情緒是一種博弈。每一種情緒在不同場合通過不同的博弈達到一種平衡。對于現代人來說,在處理各類事務時,不可避免地要在心理上產生反映,發生各種各樣的情緒變化,并且在表情、行動、語言等方面表現出來。如何使表現出來的情緒恰到好處,既不過分,也無不足,而且還符合當事人的身份、不違背情理、適時適度、切合場合是很重要的。只有更好地了解情緒,接納情緒,控制情緒,才能達到“和”的境界,做自己情緒的真正主人。
參考文獻:
[1]Charles Harthorne &Paul Weis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2 (volume). 228 (paragraph), 8. 184, 7. 356.
[2]Charles Sanders Peirce, Peirce on Signs: Writings on Semiotic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227.
[3]Gorlée, Linda,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Pierce [M].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 1994: 57-58, 175.
[4]John Fiske, & John Hartley,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Methuen, 1978.
[5]丁爾蘇,論皮爾士的符號三分法[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1994,(3).
[6]王微萍,從皮爾士的符號學看符號學的意義[J].《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7,(7):11-13.
[7]王銘玉,對皮爾士符號思想的語言學闡釋[J].《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8,(6).
[8]趙彥春,《語言學的哲學批判》[M].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5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