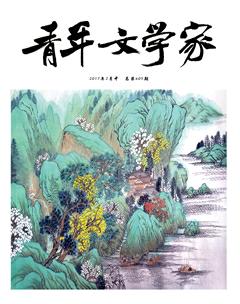在想象域和象征域中漂零的《海上鋼琴師》
摘 要:目前國內外評論往往關注影片所呈現的人生視角,而未能上升到理論高度分析男主角1900對弗吉尼亞號豪華郵輪不可思議的眷念和對陸地的頑固抗拒。本文用拉康的“三域”理論來解讀《海上鋼琴師》,指出1900因為深深迷戀海洋、音樂與游輪所呈現出來的完美想象域而失去了踏入現實社會的勇氣。
關鍵詞:想象域;象征域;鏡像階段;音樂;海洋
作者簡介:王蕾(1977-),女,山東臨沂人,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博士后研究員,上海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博士。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2
《海上鋼琴師》是意大利導演托納托雷著名的“尋找/時空三部曲”之一,是一部探討“何處安放我們的心靈”這個主題的傳記式影片。影片呈現出浪漫主義風格,精致的配樂和細膩舒緩的鏡頭語言讓這部影片成為心理影片中的經典之作。它用回憶和現實交叉的敘述方式講述了一位終生拒絕進入陸上世界的天才海上鋼琴家1900獨特而短暫的一生。
1900是弗吉尼亞號郵輪上的棄嬰,被黑人煤炭工丹尼收養,識字不多的丹尼索性叫他1900,以紀念新世紀的第一年。丹尼在工作中意外身亡,海葬儀式上,一身黑衣包裹著的1900顯得特別羸弱無助。此時悲戚空靈的音樂響起,與凄厲的海嘯聲融為一體,將災變中恍惚而創痛的1900引入了另一個世界。1900天生對音樂有著極強的領悟力,經過多年的錘煉,成為郵輪爵士樂隊中的鋼琴手。樂隊中的密友、小號手麥克斯多次勸他到外面的世界闖蕩一番,然而1900始終無法為了那個未知的物欲世界舍棄自己的精神家園,因而三次放棄了下船的機會,甚至為此錯失了唯一的一段愛情。
目前國內外評論往往關注影片的文化內涵,以及音樂如何推動故事情節發展,而未能上升到理論高度分析1900對弗吉尼亞號不可思議的眷戀和對陸地的頑固抗拒。本文援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提出弗吉尼亞號上海天一色、夜夜笙歌的慢生活還原了拉康所提出的凸顯了母性存在的想象域,成為備受母性缺位創傷的1900的靈魂棲居地和最終歸宿。
一、拉康的“三域”理論與母性缺位創傷
本片的主人公被丹尼收養后生活在一個純粹的男性世界里,然而電影畫面始終充溢著一種柔曼、包容的母性之美——波瀾壯闊的大海、搖曳前行的弗吉尼亞號和貫穿整個影片的音樂。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精神世界源于俄狄浦斯階段父親震懾頑童,阻礙幼兒完全占有母體而派生出來的精神存在。[1]弗氏的觀點無疑暗示人類進入創傷性的社會是以心理上壓抑對母體的欲望為代價的。它會促使兒童畢生不屈不撓地找尋自己失落的東西。托納托雷用憐惜的女性主義視角描述了母親缺位帶給1900的心理創傷。襁褓中的1900最開始被丹尼放在煤爐邊的金屬架上,稍大一點就睡在一個懸空的搖籃中,搖籃隨著船體的晃動而蕩來蕩去,睡在里面的小1900卻沒有任何畏懼與不適,因為這有節奏的搖晃就像母親的安撫,給他帶來了歸屬感和安全感。
根據法國精神分析家拉康的“三域”理論,母體對于幼兒在充滿創傷和分裂因素的現實世界中的自我構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將人類精神世界劃分為三個相互焦灼的階段:實在域(the real),想象域 (the imaginary)和象征域(the symbolic)。新生兒從出生到六個月,充分享受著與母體合一的幸福,置身于海洋般充盈的實在域。六到十八個月為想象域或鏡像階段,嬰兒偶然從鏡子中看到自己,而同時母親的移情凝視和動作反饋也能幫助其進一步強化這種懵懵懂懂的自我意識。想象域看似完滿,卻充斥著錯覺、幻想和欺騙,因為自我是建構在對外部虛幻形象(鏡像)的認同之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理上日漸成熟的嬰兒最終將擺脫母體的狀態,逐漸進入象征域,成長為社會學意義上的“人。”[2]
象征域是包含語言-文化在內的社會形式。象征域一方面代表著話語權和社會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強的“閹割性”,因為主體進入這個階段是以失去自身的一部分(與母體合一的狀態)為代價的。本片中,陸上的文明世界代表了充滿未知和兇險的象征域,養父丹尼也警告1900,“弗吉尼亞號以外的事物都是壞的。”因為兒時的母性缺位和養父對陸上世界的成見,1900沒有完成由想象域向象征域的轉型。因為習慣了郵輪上閑適散淡的樂隊生活,他不愿踏足光怪陸離的陸上世界,成了一名游離于象征域之外,沉浸在想象域之中的人。
1900在船上邂逅了一位來自陸上世界的女子,他一遍遍對著大理石鏡面,用支離破碎的語言演練表白,卻因為缺少內化的母性凝視的指引,始終走不出自我的羈絆而心力憔悴。這一幕也讓我們想起希臘神話中愛上自己水中倒影,最后憔悴而死的美貌少年那喀索斯。每當喀索斯試著接近水中的情人,那影子便化作一片漪漣。1900屬意的對象雖是一位姑娘而非自己的倒影,但也是因為深深迷戀海洋和音樂所呈現出來的完美鏡像世界而失去了踏入現實社會的勇氣。盡管他在女孩走下船的最后一刻追了上去,女孩邀請他有朝一日去拜訪她家,然而1900卻并沒有用心記下女孩報出的地址,因為對他來說,那個地址只是一串相互連接,喻指象征域空無性的語言符碼。
二、弗吉尼亞號郵輪:永恒的母體
本片非常巧妙地利用音樂節奏來表達人物的內心情感、推動情節的發展,鋼琴曲、小號和舒緩的爵士樂貫穿其中,渾然天成。每當琴聲響起,船上的觀眾隨著音樂翩翩起舞,1900就任由自己在想象的世界(想象域)中馳騁,借音樂排遣內心深處無以名狀的孤獨感。沉迷于1900的琴聲中的觀眾仿佛是一面鏡子,具有母性凝視特有的接納性與包容性,為他提供了一種充盈無缺的幻象。曲終人散之時,船上的游客蜂擁踏上陸地,坐在琴凳上的1900又復歸落寞。
在郵輪上長大的1900有著孩子般的天真童趣。麥克斯剛上船完全無法適應劇烈的顛簸,翻來滾去,嘔吐不止。為了安撫麥克斯的情緒,1900解開了固定鋼琴的輪索,任由沉重的鋼琴隨著風浪在大廳里滑翔,這個場景和美妙的音樂消除了初次登船的麥克斯的陌生感,鋼琴的出現不經意間就拆除了象征域中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和樊籬:剛才還互不相識的兩個年輕人趴在橫沖直撞的鋼琴上,儼然已成了風浪中同舟共濟的戰友。導演用絕妙的創意構建了一個在音樂浪尖的想象域,而咫尺之間無話不談的兩人就是彼此眼中完美的鏡像。最后,他們的音樂“沖鋒舟”沖破玻璃墻,一頭扎進船長室,完全穿越了父權象征域的時空邊界,直指深邃無底的欲望想象空間。
海洋、游輪是1900音樂創作的靈感源泉,更是因母親缺位而深受創傷的他的心靈寄托。當早已離開了弗吉尼亞號的麥克斯得知年久失修的郵輪即將被爆破拆毀的消息時,出于對音訊全無的老友的擔憂,他來到施工現場,抱著唱機讓當年與1900無數次演繹的曲子一遍遍緩緩流淌,終于,1900出現在陰影里。面對苦勸他上岸的麥克斯,1900說道:“陸地是一艘太大的船……是我創造不出的旋律。” 陸上世界看似一派繁華景象,是美國夢的具體表現,同時卻也存在著太多變數,代表兒童脫離母體后被迫面對的充滿未知風險的名利場。沒有任何親人的1900拒絕踏上陸上世界,卻對弗吉尼亞號郵輪不離不棄、致死不渝,因為那是他的家,他的母親,他的一切。
三、結語
1900的多次重要人生抉擇是整部影片討論的焦點。在現實社會中沒有身份,亦沒有親人可以依傍的1900把游離于“世界”之外的游輪視為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園,隱藏在他的人生選擇背后的,卻是生命中母性角色缺失帶來的創傷,是獨自在海浪聲中雕刻歲月的憂傷記憶。導演意在通過天才的鋼琴家的最終歸宿暗射想象域的虛幻性,而沉浸其中終將走向死亡。最終,1900在世界面前轉過身去,帶著無限的希望和眷戀,湮滅在他破碎的精神家園——弗吉尼亞號郵輪之中,留給我們無盡的沉思。
參考文獻:
[1]Freud Sigmund. The Uncanny. Trans. David Mclintoc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2]Lacan, Jacques. ?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