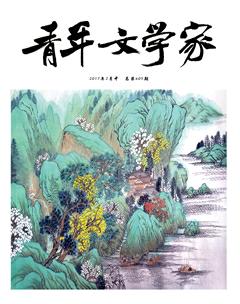《七音略》之來源探究
李怡
摘 要:七音略是至今所能見到的最早韻圖之一,在漢語語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學術界中專門對《七音略》進行研究的作品比較少。《七音略》與《韻鏡》同為早期韻圖,相似之處甚多,將這兩者互相比較,可以得出《七音略》的內容、作者來源。
關鍵詞:七音略;來源;七音;宮商角徵羽
[中圖分類號]:J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05--01
一、《七音略》研究概況
《七音略》是《通志·二十略》的第三略,北宋鄭樵所著,是至今能見的最早韻圖之一,成書于晚唐至宋,是研究中古語音系統不可或缺的文獻。
《七音略》分為七音序、諧聲制字六圖和內外轉圖三部分。詳言之,序言即七音序部分,總結字字、字音間關系的即諧聲制字六圖部分,這兩部分為作者原創。主體部分即內外轉圖部分,是在《七音韻鏡》基礎上修改增補而成的。學術界在研究《七音略》時往往只研究內外轉圖部分。本文只探討七音序與內外轉圖的內容。
就現有研究狀況來看,與《韻鏡》一類的韻圖進行的“比較研究”是最常見的,一般是對早期韻圖和等韻學的研究,用《七音略》與個別韻圖如《韻鏡》進行比較,這類論文往往涉及《七音略》與《韻鏡》的對比研究。相關研究的論作有:于建松《早期韻圖研究》、遆亞榮《宋元韻圖五種用字研究》等。
而專門、針對性的研究目前還較少見:羅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具體闡述了宋元韻圖的派別、《七音略》的來源、版本,重點比較了《七音略》與《韻鏡》的異同,是專門研究《七音略》的最早著作。高明《鄭樵與七音略》也闡述了自己對《七音略》的一些重要觀點。楊軍《七音略校注》是最近的研究著作。這些研究,都集中于韻圖與韻部和韻部中各類字音的處理等內容上。
二、“七音”來源探究
鄭樵在《七音序》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認為《七音略》的原型《七音韻鑒》為胡僧所著,“七音”之說來源于西域,但后代許多學者對此種說法都抱有懷疑態度。筆者認為,《七音韻鑒》的作者,很可能是中國佛教僧人或是對音韻造詣極深的中國學者,而非傳說中的胡僧;“七音”之說也是中國自古已有的理論,有著一定的發展脈絡,此說源頭絕不在西域。
(一)周初時已有“七音”。
《管子·地員篇》,約成書于前四世紀,是迄今為止最早記載五聲階名的文獻。我國音樂最基本的音階結構之一就有五聲,我國的傳統音樂音調以五聲為主,記錄為“宮、商、角、微、羽”五字。宮商角微羽也稱“五正聲”,加之“二變”,是傳統音樂中廣泛應用的七聲音階。
沈知白在《中國樂制與調的演變》中有:“五聲之命名:宮、商、角、微、羽。周初增二變……五聲最初演進而成六律,遂初建立旋宮的觀念……由六律演進而成七律,于是五聲音階遂增二變音,更進而用三分損益法推演而成十二律”。可知“五音”早在西周時期就已出現,周初已增變為“七聲”,可見中國樂律學“七音”之說早已產生。
《七音序》中有:“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以通百譯之義也。”序言還引用《隋書·音樂志》論樂之語:“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先是周武帝之時,有龜茲人曰蘇抵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作者認為七音之說源自西域龜茲國的“七調”。如果此說成立,唐代僧人依據西域七音之說“以三十六為之母”,那為何唐人守溫創制三十字母時用的是“五音”的理論呢?而且,“龜茲七調”屬于音樂上的概念,由西域樂律“七調”發展為中國音韻之學的“七音”,似乎有些勉強。這里的“七音”根本不是來自西域的理論,而是來自中國傳統的“五音”理論。
(二)“七音”理論系統發展。
從古人對字母認識來看,由最初的三十字母發展到三十六字母,“來母”從牙音發展到舌齒音,“日母”由舌上音發展到齒舌音,別立二音,體現出了音韻體系進一步的完善。同理,再看音韻學上由五音到七音,增加半商、半徵二音,同樣是我國傳統音韻理論的自我進步與完善,西域之說并不能解釋這些演變。
綜上可知,“七音”在我國西周時期已經出現,大大早于西域的“七調”。并且“七音”的理論有自己系統的發展進程,七音源于西域一說并不成立。
(三)《七音韻鑒》作者探究
鄭樵在《七音略》的序言中說“臣初得《七音韻鑒》,一唱而三嘆,胡僧有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表明了作者認為撰寫《七音韻鑒》的是“胡僧”——即外國的僧人,很可能是來自印度的佛教僧人。筆者認為《七音略》的作者應該為中國佛教僧人或是音韻知識淵博的中國學者。
據羅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一文,對比《七音略》與《韻鏡》,在韻目排列次序與等列等內容上有一定,這說明鄭樵和張麟之在寫書之說所依據的原理與書籍上確有不同參考。但大體上,《七音略》與《韻鏡》相似之處甚多:都有四十三轉圖,都有內轉、外轉的術語,五音與七音相互對應,開合與重輕名異而實同,說明二者在體系和韻圖結構上是一樣的。歸字或術語、轉次上的出入,只能說明二者有不同參考,結構與體系上的相似可證明二者實際同出一源,同為一系,來自同一個祖本。
綜上,《七音略》的作者并不是鄭樵所認為的“胡僧”,“七音源自西域”一說也并不可靠。《七音略》是中國傳統音韻學積淀的成果。
參考文獻:
[1]羅常培.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高明.高明小學論叢[M].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80.
[3]于建松.早期韻圖研究[J].蘇州大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