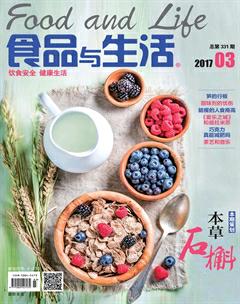追憶上海小吃
程爾曼
經常常有外地親友們問我:“上海有啥小吃?”聽到的無非是生煎、小籠、餛飩,常使我扼腕嘆息:上海原有的那些小吃哪里去了?所謂的小吃應該是量少價廉、口味純正、體現本味的食物,而且食材出自當地。
以往上海馬路上有不少固定的攤檔,也有街頭巷尾常見的“提籃小賣”、“挑擔串貨郎”,邊走邊叫,邊燒邊賣,一年四季絡繹不絕。賣的是用時令食材燒制的點心小吃,體現江南風味、民風民俗。哪怕在寒風凜冽的冬季,品種也很多。
我記憶中有白糖蓮心粥、桂花赤豆湯、“香是香來糯是糯”的現炒熱白果、烤熟藕以及雖有薄棉被捂著但還是透出特有香味的熱老菱,還有腌金花菜芥辣菜、刮拉松脆白糖梅子、五香豆腐干、桂花甜酒釀、酒釀餅、面衣餅,煎蔥花薄餅、排骨年糕等。
老城隍廟里基本上都是固定攤販,現做現賣,如梅花糕、海棠糕,那些攤位前總是人頭濟濟。我小時候只要進老廟,就必定會站在攤頭前贊賞一會兒,不吃也算過了癮。那糕實在精巧,模具講究,材料是紫銅,模樣兒十分可愛。梅花糕外皮烘得呈淡金黃色,皮上有四個凹槽,糕面蓬起微凸,還撒滿了紅綠瓜絲,迫不及待咬上一口,頓時溢出香甜軟糯如厚糊似的豆沙,燙得你張口想吐出卻又舍不得,趕緊嘶啦、噓噓、嘶啦、噓噓地呼氣。那海棠糕呢,薄薄扁圓形一塊,直徑約6厘米,高僅2~3厘米,糕面有金黃色的糖漿,欲流欲淌,誘得你趕緊吃起來。那點滴欲淌的糖漿是怎么會“留”在糕面上的呢?原來在海棠糕被烘熟成型時,攤主立即打開鍋蓋,隨手抓一把略黃的砂糖撒于糕面,又迅即拿鉤子鉤起出售,說時遲那時快,糕面砂糖粒已被燙融成亮晶晶的漿狀了。
回想起的小吃都是上海時令食品,合節氣,味獨特。那時候除了定點攤位,還有挑著擔子邊吆喝邊游穿于街頭巷尾的流動攤。有的邊走邊吆喝,有的用金屬殘片敲出特殊的聲調。
叫賣吆喝聲雖無樂器伴奏,倒也有腔有調,例如一頭鍋灶一頭碗筷、邊燒邊賣的糖粥擔,有的叫賣:“桂花——赤豆湯”,有的高喊:“白糖——蓮心粥”。賣赤豆粥時,往往是盛上一碗滾燙的白米粥,然后用湯勺舀起濃厚噴香、酥爛如泥的赤豆羹蓋在粥面,當你端起來時香味會饞得你忍不住用匙子邊拌邊塞進嘴里。
更妙的是賣熱白果的攤檔,他挑的擔子也與眾不同,稱為“廚頭擔”,一頭放鐵鍋、小柴爿(劈開后的木柴),另一頭放白果,鍋鏟用的是大河蚌的殼,邊炒邊唱:“買熱白果喲唉——白果要吃熱白果,香是香來糯是糯,一粒開花兩粒大,我的白果鵝蛋大——一個銅鈿買三顆,要吃白果我來數……勿買白果我挑過喲,挑過仔勿要牽記(惦記)我的熱白果喲——”吆喝聲配上切擦、切擦的蚌殼翻炒鐵鍋的撞擊聲,實在合拍、動聽。吆喝聲極富藝術感染力,它像抒情歌曲唱出了人們對熱白果的喜愛和思戀,印象之深如刻心底。
隨著社會的發展,城市規劃必然會考慮以環境衛生、食品安全為首要原則,不知不覺間許多討人喜歡的小吃消失、泯滅了,但好吃當令是硬道理,我這個上海本地人就是忘不了那些簡俗的小吃。我認為,合作化道路使提籃挑擔、走街串巷的小販生活有了保障,但無形中使得某些小吃消失了。
記得多年前,延安東路“大世界”隔壁的“盛福齋”食品店有供應冰凍酸梅湯。這是店家用烏梅為主料自制而成,甜酸適口,沁入心肺,大熱天一杯下肚,全身暢爽。
滅絕的還有“冬至團”,這是冬至歲時上海人的風俗習食之一,可祭祖亦是闔家點心,早年曾是上海“五芳齋”糕團店的熱門產品,冬至前半個月就有出售,一直賣到冬至這天。冬至團有甜、咸兩種,咸的是圓形,白糯米粉作皮,炒熟的蘿卜絲蝦米為餡,下襯箬葉爿,上屜蒸熟;甜的面皮是將老而粉的南瓜肉煮爛,搗成泥,與糯米粉揉勻而成,取豬油豆沙作餡,包成似圓團,蒸籠內蒸熟后,底部變得平坦,成扁圓形,需立即開蓋透風,以防皮面變色而不鮮麗。咸團白色,甜團深黃,十分誘人。此外,還有現蒸現捶打,可包裹各種餡的年糕團,以及基本上與生煎相似,面皮略發酵的緊酵饅頭(上海人不分包子、饅頭,一律以“饅頭”相稱)等,緊酵饅頭可蒸吃,也可再炸煎。
我最想念的是酒釀餅、面衣餅,都由甜酒釀發酵,面皮分別為小麥粉、大米粉,前者揉成面團,烘制而成后者調制成面糊,采用蒸烘法制熟。所謂的蒸烘是蒸與烘于一鍋內同時進行的煮法。大鐵鍋中間有個凹塘,內放清水,四邊高凸處平而燙,倒上一勺酒釀發酵過的面糊,排溜成餅,圍成一圈,炭火一燒,凹塘內水沸而水汽四面涌出,將面糊餅表面蒸熟,而底部與鐵板吻接,無水無油,于是被熱量烘烤成了表面潔白、底部淺黃、表皮脆香的面衣餅。甜酒釀發酵后的面粉不僅甜度較高,且含有淡淡的酒香,不少人愛之。